二戰后美國三個大氣模式中心的美日組合
Th 聞新宇 朱清照
二戰后美國三個大氣模式中心的美日組合
Th 聞新宇 朱清照
著名計算機科學家高德納(Donald E. Knuth)曾經這樣定義科學與藝術的邊界:“科學是那些我們理解得足夠清楚,以至于可以描述成計算機語言的知識;而藝術則是其他還未達到這種程度的認知。(Science is what we understand well enough to explain to a computer; Art is everything else we do.)”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氣象學的發端似乎不是20世紀初以V. Bjerknes為首的挪威學派,而應是二戰后的1950年。
從1950年Charney首次在ENIAC上成功試驗了正壓渦度方程開始,發展數值模式就成為了那個時代大氣科學領域最激動人心的主旋律。Rossby于1947年從美國回到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領導發展了全世界第一個業務化的正壓預報模式,在瑞典BESK計算機上一周三次地預報北大西洋地區的天氣狀況。然而由于諸多原因,歐洲在模式研發的道路上雖然贏在了起跑線上,卻輸在了途中。美國最終以蓬勃向上的絕對優勢,領導了二戰后數值模式的研發方向。特別地,美國在1950—1970年代,先后誕生了三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模式研發中心:位于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市的美國國家大氣科學研究中心(NCAR)、位于加州洛城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和位于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市的地球流體力學實驗室(GFDL)。其中最耐人尋味的是,這三個模式中心中最早領導模式研發工作的,都是一個美國學者和一個日本學者的組合:NCAR的Warren Washington和栗原秋良(Akira Kasahara)(圖1)、UCLA的Yale Mintz和荒川昭夫(Akio Arakawa),以及GFDL的Joseph Smagorinsky和真鍋淑郎(Syukuro Manabe)。這種固定的“美日組合”究竟有哪些優勢?這種優勢如何推動了大氣環流模式的早期發展?這樣的組合在特殊的歷史年代又有怎樣的必然性?當我們回望這段歷史,仔細考察這三個模式中心早期的發展經歷時,就會更深入地理解這些看似巧合的故事其實都孕育在某種必然中。(圖2)。
一、國家大氣科學研究中心(NCAR)
NCAR作為美國高校大氣科學聯盟(UCAR)下屬的研究中心始建于1960年,其紅色建筑由華裔著名建筑師貝聿明設計,坐落在美麗的博爾德市西南郊Mesa路盡頭的小山上。在NCAR發展早期,領導其模式研發工作的是美國黑人氣象學家Warren Washington和日本學者笠原秋良(Akira Kasahara)。

圖1 1975年Warren Washington和笠原秋良的合影(見于NCAR檔案)
笠原秋良于1926年生于日本東京,1944年考入東京大學修習氣象學專業,1948年畢業后師從日本著名氣象學家正野重方(Shigekata Shyono)攻讀研究生。當時的日本處于戰后恢復期,美國盟軍在東京建立圖書館大肆傳播西方文化和價值觀,也向東大提供了許多美國最新的氣象學雜志,這些專業雜志使得包括笠原在內的很多日本學者,了解到美國正在積極發展一種稱為“數值模式”的計算機與程序相結合的設備。正野重方敏銳地意識到這一革命性的新方向對于彌合動力學與經驗天氣預報之間的鴻溝具有重要意義,并開始思考如何發展日本自己的數值模式。正野教授當時與自己的研究助理、學生和日本氣象廳(JMA)的相關研究人員一起成立了一個數值天氣預報小組,定
期討論相關問題。笠原曾生動地回憶道:那是1949年的一天,正野教授興奮地舉著Charney的論文沖進教室,激動地說:“看!氣象學將因這篇文章而真正實現現代化!”1952年,正野重方的研究助理岸保勘三郎(Kanzaburo Gambo)因在長波頻散和數值預報理論方面的工作受邀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所與Charney合作兩年,期間他經常寫信給笠原,告訴他Charney那邊在模式發展方面的工作進展。1954年,岸保堪博士回到東京和正野教授共同組建了更大規模的數值預報小組,共包括25名研究生和日本氣象廳雇員,他們每月都要集中討論和匯報進展。這個活躍而充滿激情的小組,在整個1950年代一直活躍在日本數值預報領域的最前沿。后人也稱之為“東京NWP小組”。
正是由于出身于正野教授的NWP小組,笠原接受了廣泛的學術熏陶和良好的專業訓練。1956年,笠原受Platzman的邀請到芝加哥大學參與熱帶氣旋的研究,并在那里工作了6年。當時芝加哥大學的計算設備并不好,笠原經常要跑到位于首都華盛頓的美國氣象局去完成計算任務。1961年,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NSF)和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達成協議,共同促進美日在尖端科學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兩年后,笠原秋良受此計劃資助前往NCAR工作,NCAR則承諾將提供最好的研究環境和計算設備。在笠原到達NCAR工作后的第三個月,他遇到了同樣新加入NCAR的黑人青年:沃倫?華盛頓(Warren Washington)。
沃倫?華盛頓于1936年生于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1960年畢業于俄勒岡州立大學獲氣象學碩士學位,1964年畢業于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獲氣象學博士學位,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二位獲得大氣科學博士學位的非洲裔美國人。據華盛頓自己回憶,1963年8月28日,他正在驅車前往NCAR報到的路上,在汽車旅館的電視里看到了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著名演講“I Have a Dream”,這段演說極大地激發了他作為一位非裔美國人在科學研究領域中爭取平等的熱情,這對他后半生的事業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華盛頓加入NCAR不久后的一天,他主動向笠原提出共同建立一個大氣環流模式(GCM)的想法,這讓笠原感到非常震驚,因為那時華盛頓還只是一個剛剛畢業的青年學生。盡管笠原一直關注著GCM的發展,但此時NCAR在模式方面已經落在了后面。GFDL、UCLA和LLNL 氣象學家Chuck Leith都已經發展了自己的數值模式。笠原認為1917年理查森的手算試驗不能算是完全的失敗,他所使用的控制方程在本質上應該可以用計算機計算并得到更精確的解。于是笠原提出,NCAR的模式研發要采用理查森的原始方程組,全球覆蓋,這可以使NCAR的大氣環流模式研發趨向科學意義上的真正完善和成熟。

圖2 1950—1990年GFDL、NCAR和UCLA有關模式發展和模式傳播的示意圖(修改自Randall D(2000)第二章Fig 1)
1964年5月,華盛頓和笠原秋良共同向NCAR主
任湯普森(Thompson)提出建立一個氣候模式的想法,并得到了支持。他們最終決定購買一臺先進的CDC3600計算機用于數值計算。在模式發展初期,他們兩人主要專注于科學方面的研究,由大量程序員負責編寫和完善代碼。整個團隊幾乎每天都要開會討論模式的輸出結果并確定第二天的改進方向,模式在這種不斷地修改中也變得越來越穩定。最終在科學家和程序員的共同努力下,笠原和華盛頓共同署名于1967年發表了基于原始方程、覆蓋全球的GCM論文,在這篇文章里他們系統介紹了NCAR比較復雜的氣候模式的動力框架、物理過程和初步的模擬結果。作為NCAR第一代大氣環流模式,這個5?分辨率的兩層模式也被稱為Kasahara-Washington Model或NCAR 1。之后的1970年,他們進一步大幅改進了模式的靈活性,發布了第二代的NCAR 2,這一代模式默認分辨率仍為水平5?,但垂直增加到6層。1973年他們又發布了NCAR 3,重點改進了差分算法。縱觀Kasahara-Washington大氣環流模式的發展歷程,他們始終在計算方法穩定性、極點處理,以及如何控制計算機舍入誤差方面給予了更多的關注。
1970年代后期,NCAR逐漸放棄了Kasahara-Washington模式系列,轉而開發給美國所有大學使用的新一代氣候模式CCM(Community Climate Model),這一方面是出于更好地服務UCAR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澳大利亞數值預報研究中心(ANMRC)發展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譜模式。CCM系列一直發展至今,經歷了CCM0B,CCM0A,CCM1,CCM2,CCM3,CSM1,CCSM2,CCSM3,CCSM4,是今天CESM1一脈的源頭。
從1964年至今,NCAR一直努力延續著模式研發的傳統,使得今日NCAR的全系列數值模式,包括氣候模式CESM、化學模式MOZART、天氣模式WRF等,被世界范圍內的眾多科學家所廣泛使用。今天NCAR的諸多數值模式都已成為美國模式領域最重要的風向標。
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大氣科學系是由挪威學派的J. Bjerknes(Jacob Bjerknes)于二戰期間建立的。1940年4月,挪威剛剛被德軍占領,J. Bjerknes便接受美國的邀請,著手在UCLA建立氣象系為美國空軍培養氣象預報員。這里成為當時美國5個基于大學的緊急軍事氣象訓練基地之一。從那時起,UCLA氣象系逐漸成為美國最重要的大氣科學研究中心之一,在動力氣象、大氣環流模式、海氣相互作用、邊界層氣象、平流層物理化學等很多領域都保持了領先的研究水平。
荒川昭夫(Akio Arakawa)生于1927年,中學時他就對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很感興趣。二戰結束后的1947年,近20歲的荒川考取了東京大學物理系,一直接受純粹的物理學訓練。1950年荒川本科畢業,也曾考慮過繼續讀研究生,但由于當時剛剛訂婚,迫于生計需要他還是選擇了工作。與他同班畢業的有30名同學,但當時日本經濟慘淡,根本沒有招收物理系畢業生的工作崗位,全班只有3個工作機會,其中之一便是去日本氣象廳。荒川惡補了氣象學知識,沒想到面試時主要被問了很多物理和數學問題,他被順利錄取了。對于自己的教育背景,荒川曾這樣回憶道:我從來沒讀過研究生,也沒有獲得過碩士、博士學位(實際上1961年他被授予東京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我本科也沒接受過氣象學訓練。在步入JMA工作之前,我對氣象學一無所知,也毫無興趣。
荒川自己也沒想到,他畢業后進入JMA后的第一份工作,卻是隨船出海。在經過半年的培訓后,荒川和另外幾名入職新人被送上了JMA氣象監測船。在之后一年的時間里,他隨船往返于日本東北部X-Ray測站(152?E,39?N,測美日之間的天氣狀況)和西南部的Tango測站(135?E,29?N,測臺風)。船上的生活并不緊張,由于他們幾個新人是被作為未來JMA中層領導人員進行培養的,因此荒川有很多時間觀察中緯度海面風暴路徑上的鋒面氣旋云系和低緯度的強對流云團,而且還能經常見習其他15名真正的氣象員每天開展日常觀測、手繪天氣圖、并進行相關天氣討論等活動。正是這一年內6~7次的隨船出海,使荒川真正愛上了氣象學。
一年期的出海結束后,荒川面臨兩個選擇,或者去JMA做統計員,或者繼續隨船做海洋觀測。此時JMA下屬的氣象研究所(MRI)主任荒川秀俊(Hidetoshi Arakawa)教授突然主動邀請荒川昭夫加入MRI從事天氣預報、分析工作。當時MRI沒有計算機,所有預報工作都依賴在500hPa天氣圖上應用挪威人Fjortoft(1952)的勻速平流公式。而1950年代中期,國際氣象學界最前沿的領域是對大氣環流的研究,比如Fultz的轉盤試驗,這深深吸引了荒川的關注。1958年荒川將國際上對大氣環流的研究進行了總結,用日語出版了單行本《大氣環流的現代理論》,向日本氣象學界介紹國際上有關大氣環流的最新進展,這本書直到今天仍被很多看過的人大加稱贊。
到了1959年,MRI幾經權衡從美國購買了IBM
704計算機,這比MRI原來的富士通電腦能力強很多。荒川也從業務預報部門轉到了新成立的數值預報(NWP)部門。新部門沒有程序員,荒川就從零學起,對這臺計算機的硬件和剛剛誕生的Fortran語言(1957年,Fortran語言誕生在IBM 704機器上)逐漸有了全面的了解,并開始用計算機解決工作中的具體問題。要知道,當時即使IBM駐日本分公司里也沒幾個人懂Fortran語言。同時,開始接觸數值計算的荒川也開始規律地參加“東京NWP小組”的每月討論,并受到了正野重方教授的賞識。1960年,國際數值預報大會(NWP Symposium)在日本東京召開(亦稱東京NWP大會)。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會,當時國際上著名的有關NWP和大氣環流方面的權威專家幾乎悉數到場,包括:Bolin,Charney,Doos,Eliassen,Fjortoft,Gates,郭曉嵐,Lorenz,Mintz,Namias,Pfeffer,Phillips,Platzman,Shuman,Smagorinsky,Wurtele等。在這次大會上,東大的正野教授與Mintz有過深入的交流,Mintz表明他想發展能模擬季節變化、可長期穩定積分的大氣環流模式的宏大愿望,正野便向他推薦了荒川昭夫。Mintz在拜讀了一些荒川的日語論文的英譯本后,決定邀請荒川去UCLA進行為期2年的訪問研究,其核心目的就是幫助他發展大氣環流模式。
Yale Mintz(1916—1991年)于1937年畢業于達特茅斯學院的人類學系,1942年于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地質學的碩士學位,然后到紐約大學氣象系工作了2年,又考到美國西岸的UCLA師從創建氣象系的J. Bjerknes。Mintz是個熱情奔放、興趣廣泛、智力過剩的年輕人,J. Bjerknes曾生動地回憶道:他來報到的時候,除了人之外,就是滿滿一大車的書。1949年,Mintz獲得氣象學博士學位,這是該校歷史上第二個獲此學位的人(第一個是Charney)。之后,Mintz留校工作,并作為J. Bjerknes的得力助手參與很多UCLA氣象系的建設和管理工作。
1950年代,天氣預報多是局地、大陸尺度的預報,剛剛興起的NWP預報通常也只能報2天。而受到逐漸興起的有關大氣環流的研究的啟發,Mintz想發展能長期穩定積分的GCM,并把預報推廣到全球。1961年荒川受邀來到UCLA,他們兩人便開始了一段長達20年的合作。他們兩人的工作風格其實天差地別,Mintz由于教育背景的限制并不是一個徹底的氣象學家,但他眼界寬廣,因此他只關心宏大圖景,專注于不斷拓展GCM的功能。他總覺得荒川工作進度很慢,而荒川總是不得不說服Mintz慢下來,并告訴他目前工作的難點在哪里。荒川曾回憶道:“我們每天都要討論1個小時,或者是在電腦前,或者是在電話旁,他每天都有很多新想法,我通常要否定一多半,而剩下的都是非常好的點子。”由于當時UCLA比那些國家實驗室(如NCAR,GFDL,LLNL等)小很多,甚至連程序員都沒有,而Mintz又有野心要與他們競爭,所以荒川幾乎承擔了全部的代碼開發工作,而且每個周末都要加班趕工。當時UCLA剛剛購買了一臺很先進的IBM 709,荒川憑借自己在日本積累的編程經驗,很小心地編寫Fortran程序卡片,實際的工作進展并不算慢。
1961—1963年,荒川和Mintz主要解決了平流方程中常見的雅可比算子(Arakawa’s Jacobian operators)難題,并順利發展出了第一代UCLA兩層模式,也稱Mintz-Arakawa Model。到了1963年,荒川由于學者(J)簽證到期不得不返回日本,并且2年之內不得再入境,荒川便回到了JMA工作。離開荒川的Mintz失落不已,專門請了程序員Dennis Subsay才能繼續開展工作,同時急切地每個月給荒川寫一封信,希望他能盡快返美。1965年,荒川再次赴美,并獲得了UCLA的永久教席。他們兩人的再次合作爆發了前所未有的能量,如向模式里加入水汽、完善格點設計、改進守恒性更好的差分算法等。
UCLA的大氣環流模式在1965年之后發展很快,但兩人都沒有時間停下來撰寫論文,以至于有關UCLA模式的論文是三個模式中心發表最晚的;不僅如此,荒川和Mintz湊巧一生都沒有共同署名的文章發表。但是,這沒有妨礙UCLA的模式成為世界上傳播最廣泛的模式。這一方面是由于UCLA作為大學相比于那些國家實驗室更自由、更友好的開放態度所致。事實上,1965年之后,全世界各地的學生和訪問學者紛紛去UCLA交流訪問,他們畢業或回國后又把模式代碼帶到了世界各地。另一方面是由于IBM公司對UCLA提供了巨大的技術支持,IBM大規模科學計算部的工作人員每周從加州圣何塞(San Jose)到UCLA來聽課、調程序,并最終幫助他們撰寫了高質量的文檔,這些文檔里甚至包含了完整的源代碼,這使得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可以輕易地復制UCLA的模式。
第一代UCLA的大氣環流模式是原型模式,大體于1965年成型,沒有水汽過程,水平分辨率7?×9?,垂直兩層,物理過程方面也很不完善,荒川稱之為UCLA I。第二代模式UCLA II于1960年代后期完成,這是第一個可以稱得上是“產品級”的代碼,水平分辨率4 ?×5 ?,使用B格點,同樣只有兩層。UCLA II流
傳很廣,是因為1970年Mintz的研究生Lawrence Gates畢業后將模式帶到了蘭德公司(RAND Corp.,美國智庫),并將其應用在很多美國國防部的項目中,這個蘭德公司的版本后來又被進一步帶到了俄勒岡州立大學。第二代模式的垂直擴展版UCLA II-3L在第二代模式的基礎上,主要把垂直分層增加到3層,這一版本后來又增加垂直分層后擴散到了三個NASA中心:1972年,一個9層版本傳播到NASA/GISS;幾年后又傳播到NASA/GLAS和NASA/GLA。第三代模式UCLA III重新設計了混網格,采用C格點,這也是后來UCLA模式一直沿用的格點設計,垂直方向增加到6或12層。1970年代中期,UCLA III被傳播到美國海軍和日本氣象廳MRI。第四代模式UCLA IV從1980年代早期開始研發,重新設計了σ垂直坐標,這一版標志著UCLA模式基本走向成熟。這一版代碼被傳播到美國海軍、NASA/GLA、DOE/LLNL,甚至中國氣象局,其中荒川的學生David Randall將這一版的模式代碼帶到科羅拉多州立大學(CSU),CSU成為后來最重要的模式發展分支之一。
Mintz于1977年退休。他在1980年代一直在NASA/GSFC擔任科學顧問,但轉而關注陸面過程和水循環。他于1990年獲得Rossby獎,于1991年4月27日在以色列死于癌癥。荒川早在1977年就獲得了Rossby獎,于1998年從UCLA退休,但他一直留在UCLA繼續工作至今。他的學生David Randall將荒川退休紀念會上的很多科學家的發言結集出版(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Develop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這是一份全面回顧UCLA模式發展的文獻。
三、地球流體力學實驗室(GFDL)
GFDL的前身是美國氣象局于1955年在von Neumann倡議下建立的大氣環流研究部(General Circulation Research Section,GCRS),位于馬里蘭州的Suitland市,距離氣象局的聯合天氣預報小組(Joint NWP Unit)非常近,Joseph Smagorinsky受邀擔任主任。當時這個部門的成立主要是為了與von Neumann繼續合作開發濾波模式。1959年該部門改名為大氣環流研究實驗室(General Circulation Research Laboratory,GCRL)并遷至首都華盛頓,從這時起,Smagorinsky開始獨立研發9層原始方程模式。1963年,GCRL更名為現在的名字GFDL,并于1968年再次遷至現在的普林斯頓。今天的GFDL已經成為美國最重要的大氣科學研究中心之一,其在氣候動力和模式模擬方面都具有領先地位。
真鍋淑郎(Syukuro Manabe)于1931年生于日本愛媛縣,并分別于1953,1955和1958年獲得東京大學的本科、碩士和博士學位。同他的學長笠原秋良一樣,他研究生階段的導師也是著名的正野重方教授。在研究生階段,真鍋就在正野教授和岸保堪教授的指導下,在日本氣象學報上發表了幾篇論文,其聰穎、活躍的性格深得正野教授喜愛。特別地,他在“東京NWP小組”里也異常活躍,這都為他今后從事數值模式研發方面的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受導師正野教授的推薦,真鍋在博士畢業的1958年就收到了來自美國Smagorinsky的邀請,畢業后直接飛赴美國加入Smagorinsky領導的GCRS。
Joseph Smagorinsky于1924年生于美國一個油畫商之家。二戰時他正在紐約大學讀大二,他毅然選擇參加空軍,并先后被派到布朗大學學習數學和物理,以及MIT跟隨Lorenz學習動力氣象。在這期間,他能親身感受到戰爭對氣象信息的巨大渴求,也積累了很多實際的氣象觀測經驗。于是二戰結束后,他決定繼續深造氣象學。在一次由Charney主講的天氣預報課程上,Smagorinsky在提問環節問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問題,Charney認可他的才華,便邀請他到普林斯頓的高級研究所去用計算機來驗證他的一系列想法。1950年4月,年輕的Smagorinsky參加了Charney領導的著名的ENIAC試驗,這使得Smagorinsky成為最早一批親身參與1950年ENIAC數值試驗的學者之一。之后他便正式加入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與Charney和von Neumann合作,共同推進數值試驗方面的工作。1953年,時年29歲的Smagorinsky得到了一個美國氣象局下屬的聯合數值天氣預報中心的工作機會。兩年后,美國氣象局又在von Neumann的建議下新成立了一個大氣環流研究部(GCRS),由Smagorinsky直接領導。如上文所述,之后,他領導的這個機構幾度搬家,并最終以GFDL的名字遷至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
Smagorinsky在1955—1956年,通過與von Neumann、Charney和Phillips合作,已經發展出兩層半球模式;從1959年開始,他又與真鍋合作著手發展9層半球原始方程模式。盡管當時他們的模式使用了過多的黏性耗散,使得模擬的結果看起來更平滑漂亮,但計算不穩定一直是GFDL模式頭疼的問題。在GFDL,由于有大量的程序員的支持,真鍋得以全身心投入科學方面的思考中,特別是對很多物理過程如何在模式中表達,他做了海量的調查研究工作。比如真鍋最早發展的對流調整方案,就是對輻射傳輸和積云對流過程簡潔的高度抽象。除了模式研發本身,真鍋還最早提出了使用模式進行CO2加倍試驗,這成為
今天利用模式進行全球變暖研究的起點。Smagorinsky并不具體負責模式代碼的發展,他更多地關注方向性的問題。比如他最早意識到氣候模式不能只有大氣分量,海洋在長期氣候模擬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為此他于1961年邀請海洋模式方面的專家Kirk Bryan加入GFDL(當時叫GCRL),這使得GFDL的模式最早于1970年代就成為了耦合的海氣模式。
1960年代中期以后,Smagorinsky的精力更多地轉移到WMO下屬的全球大氣研究計劃(GARP)的規劃中,使得真鍋成為GFDL模式研發方面實際意義上的領軍人物。從這時起直到1998年真鍋從GFDL退休,他成為世界上領導模式發展時間最長、最富有進取精神的領袖。在漫長的30多年的歲月中,一大批圍繞在真鍋身邊的合作者也逐漸成為模式研發領域的翹楚,包括:Kurihara,Strickler、Wetherald、Holloway、Stouffer和Bryan等。
GFDL模式的命名不像其他單位那么自成一體,主要包括如下系列:MARKFORT系列,由Smagorinsky最早領導開發的9層半球原始方程模式,1960年代很多有影響力的論文都是基于這個系列;Zodiac系列,這是GFDL第二代模式,主要引入了Kurihara設計的新一代全球減網格,這一代模式一直使用到1970年代;Sector系列,這是一個東西方向只有60個經度的非全球GCM,且海陸分布也高度理想化;SKYHI系列,是從1975年之后開始發展的垂直高分辨率GCM,包含對流層、平流層和中層;GFDL譜模式系列,這是GFDL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從澳大利亞數值氣象研究中心(ANMRC)引入的,當時ANMRC的Bourke等人在1970年代早期發展的譜模式大有席卷全球之勢;Supersource系列,1970年代后期,Holloway等人重寫GFDL的譜模式代碼,大大增加模塊化和用戶可選項,使其成為GFDL模式延續至今的一個譜模式系列,直到2000年之后,才被林山建等發展的有限體積動力框架所取代。
Smagorinsky于2005年9月去世,享年81歲。Smagorinsky一生著作等身、獲獎無數,并于1972年獲得Rossby獎。真鍋于1998年退休,之后曾回到日本擔任全球變化尖端研究院的科學顧問,但由于深感不適應日本僵化的學術氛圍,他于2002年又返回GFDL繼續從事研究工作至今。
四、對美日組合的反思
1950—1970年這20余年間,美國在模式研發領域,除了以上所述的三大中心外,還曾誕生過三個富有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開拓者,比如1950年領導ENIAC試驗的Charney;1956年全世界第一個真正意義使用原始方程開展GCM試驗的Phillips;在LLNL發展出LAM模式、并用電影膠片展示其漂亮結果的Cecil Leith(外號“Chuck”Leith)。他們都曾經對模式發展起到過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最終遺憾地沒能留下代碼遺產。
本文所記述的三大模式中心NCAR、UCLA和GFDL,為什么能站在那個年代模式發展的最前沿,為什么又恰巧都是一個美國人和一個日本人的“美日組合”,卻是很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除卻一些泛泛的原因外,我們想提出至少四個最重要的理解角度。
第一,二戰后特殊的日本經濟狀況與美日戰略同盟。二戰后日本作為戰敗國經濟十分困窘,據“東京NWP小組”的回憶,當時東京大學的老師們薪水很低(除了岸保堪三郎工資較高之外),他們不得不利用課余時間去中學代課。當時為了維持NWP小組每月一次的活動,他們還到外面去拉贊助,比如當時的《朝日新聞》出版社就曾經資助他們2800美元(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么會從《朝日新聞》得到這筆慷慨的資助)。困窘的經濟使得優秀的日本青年不得不直面生活的挑戰,荒川就是因此接受JMA的工作走上氣象監測船的。當時更多的日本優秀青年學者都愿意赴美工作,他們大都承認有相當一部分原因是迫于生計。而恰巧當時受冷戰影響,美日結成了特殊的同盟關系,美國不僅可以賣給JMA當時最先進的IBM計算機,還把國際性的NWP會議放到日本東京去開,兩國甚至達成協議促進尖端領域的科技合作……這都反映出當時的美日關系是親密無間的。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很多優秀的日本年輕學生紛紛踏上去往美利堅的航船,在遙遠的大洋彼岸繼續尋找他們的科學之路。
第二,計算機成為戰后尖端科學發展的有力武器。美國在戰后最先發展出世界領先的計算機工業,誕生了像IBM、Cray等先進的計算機制造商,這為大氣環流模式的研發提供了必備的硬件平臺。當時的瑞典、日本都有自己的計算機品牌,但由于速度不夠快,都只能做NWP的短期預報。比如當時日本的NWP就可以完成2天的計算,卻無法更長。只有美國生產的高速計算機,才能真正支撐起大規模的GCM計算。這種硬件上的領先,為美國在GCM研發領域領先世界打出了足夠的提前量。使得只有美國才最終成為了GCM研發最好的土壤。
第三,美日在人才培養方面的天然差別與互補。日本在戰后把教育放在了最重要的基礎地位,并于1947年重新頒布《教育基本法》,強調教育對完善人
格、提升個人價值和培養自立精神的巨大作用,在學制、教材、教學方法上也努力與世界全面接軌。這使得日本即使在最貧窮的戰后恢復時期,也保證了學生能學到全世界最先進的知識,并以日本人特有的嚴謹、扎實的學習習慣內化到年輕人的頭腦中。這一切,使得當時的日本年輕人,在個人知識層面似乎并沒有因戰爭而經歷任何“斷層”。諸如荒川昭夫等人在來到美國后,可以直接上手最先進的計算機,并用最新的Fortran語言進行編程,再加上日本人特有的嚴謹、求實、腳踏實地,使得他們可以很好地完成與編程相關的工作。而美國的教育體制則更注重對人宏觀判斷力和領導力的培養,這導致三個模式中心無一例外都是美國人擔任宏觀領導角色,負責設計模式發展的大方向,因為他們對總體的把控力和對未來的想象力都大大領先于日本人。如此一來,美日組合脫胎于各自的教育體系,盡管有著與生俱來的差別和短長,但卻具有天然的互補性。
第四,一個人,一個小組,一次國際會議,成為歷史的關鍵節點和契機。這個人就是東京大學的正野重方教授;這個小組就是由正野重方與岸保堪三郎共同領導的“東京NWP小組”;這次會議就是1960年在日本東京召開的國際NWP大會。正是由于正野教授經常鼓勵自己的學生關注模式發展前沿、鼓勵他們大膽實踐、推薦他們到美國最頂尖的實驗室去合作,正是由于有東京NWP小組這樣的研討氛圍,才孕育出訓練良好的笠原秋良、荒川昭夫和真鍋淑郎這一批模式專家。不僅這三人,還有很多同時代的日本氣象學家皆出自這一血脈,比如Kurihara和Matsuno等。正是由于有1960年“巨星”云集的東京NWP大會這樣的平臺,使得東京NWP小組得以向世界展示其研究水平和人才儲備,并因此走出了像荒川昭夫等許多優秀的年輕人。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三大模式中心的美日組合現象,應當歸功于東京大學正野重方教授的遠見和推動,應當歸功于一個人、一個小組、一次國際會議這樣的關鍵性樞紐。
20世紀中期,模式發展的浪潮將日漸成熟的動力學應用在傳統的天氣學分析之上,徹底改變了天氣預報和氣候預測的面貌,使得大氣科學最終站上了現代科學的舞臺。一個時代漸漸遠去,但那些五彩斑斕,甚至有些激動人心的故事并沒有因此被人們忘記。細細品味他們背后的種種偶然,感慨之余不免發現其實一切又在必然中。
致謝:感謝中科院戰略先導專項(XDA05080801)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41005035, 41130962,41130105)對本文的支持。并特別感謝日本早稻田大學水上弘子女士對本文日文資料的翻譯和整理。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物理學院大氣與海洋科學系)
深入閱讀
Anon. “Suki” Manabe, Pioneer of Climate modeling. IPRC Climate, 2005, 5(2): 11-15. http://iprc.soest.hawaii.edu/ newsletters/iprc_climate_vol5_no2.pdf
Johnson D R. 1996. On the scientif i c contributions and insight of Professor Yale Mintz. J Climate, 9: 3211-3224.
Lewis J M. 1993. Meteorologist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Their exodus to the United States following World War II. Bull Amer Meteor Soc, 74(7): 1351-1360.
Randall D. 2000.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Develop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Utah: Academic Press.
Smagorinsky J. 1983. The beginnings of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and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ing: Early recollections. Advances in Geophysics, 25: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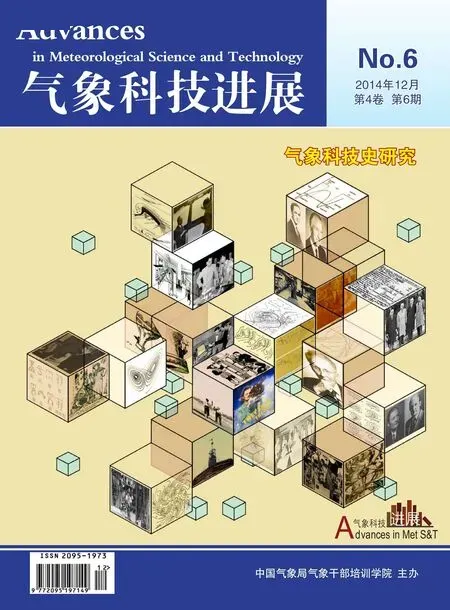 Advances in Meteor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4年6期
Advances in Meteor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4年6期
- Advances in Meteor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其它文章
- 編輯選編
- 1949年以前我國氣象臺站創建歷史概述
- 氣象科學的發展與時間觀變革的初步探索
- 大氣科學歷史進程中多學科的交叉影響
- 淺談氣象史料積累的意義
——《全國基層氣象臺站簡史》叢書編輯手記 - 新中國氣象事業發展的壯美畫卷
—— 簡評《全國基層氣象臺站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