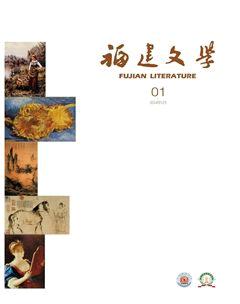萬斤苕
劉益善
從一個人的本名看不出這個人的為人,從一個人的綽號卻可以看出這個人的特征。《水滸傳》里的一百單八將,個個有綽號,個個綽號都符合它主人的性格。
萬斤苕是他的綽號。
他并不姓萬,他姓張,叫張發子。如今,村里沒有一個人喊他張發子,都喊他萬斤苕。弄得年青人真以為他叫這個名字,還說,什么名字不好叫,偏叫萬斤苕,多難聽!
要知道紅薯有好幾種叫法,有叫番薯的,有叫山芋的,有叫地瓜的,在張發子家鄉一帶,偏偏叫苕。鄉里人還把傻子,心里不通竅的人也叫苕。苕變成了形容詞,像“這個人苕里苕氣”,“這人是個大苕”,意思就是這個人傻里傻氣,這個人是個大傻瓜。他叫萬斤苕,一萬斤,多大的一個苕。
那是在火熱的、沸騰的、共產主義前腳跨進了中國的一九五八年。在金水河畔的金水大隊,一群從武漢來農村鍛煉的大學生,在吃了半個月的不要錢的三菜一湯,雪白的大米飯后,給金水大隊房屋的山墻上留下了形形色色、花花綠綠的壁畫:稻堆子堆到了天上,堆稻的老頭正就著太陽點煙;一個娃娃抱著西瓜大的芝麻嘻嘻笑著;十輪大卡車拉著一只大包谷棒子,輪胎都快要壓癟了;一個社員正用一把鋸子鋸一棵稻子,那個拉鋸的社員真像張發子。嗯,不能叫張發子,否則就是不尊重他,應該叫張連長,他是金水大隊的民兵連長哩!前天有人喊他張發子,他裝著沒聽見,不理人家;人家趕快改口喊張連長,他才滿臉笑容地答應,還敬了那人一支喇叭筒煙。
大躍進的年代,戶戶無閑人,煉鋼的煉鋼,生產的生產。唯有張連長穿著從部隊復員時帶回的那件黃不黃、白不白的破棉大衣,領子油膩膩的發黑,倒背著一支套筒槍在村里溜達著,他在維護治安。雖然是共產主義時代,共產主義聽說還有警察呢!他感到不滿足的是,當一個連級干部,卻背著這種老套筒槍。當年,他在部隊時,他們連長掛的是閃光的盒子炮,可威風了。現在,他統領的這個民兵連,攏共才五支破槍,他還是挑的一支好一點的。
他在村里溜達著,碰到有人,上前喝問兩句:干什么的?為什么不勞動去!沒人時,他就靠墻坐一會。今天,他的心緒很不好。他是村里唯一從部隊回來的,他還到過朝鮮呢!可惜革命了好幾年,連個黨也沒入上。回到村里,大伙熱情地歡迎他,在大隊當書記的是他本房族的一個弟弟,叫張富子。他從小就看不起這個張富子,穿個破襠褲鼻涕吊了半寸長,哼,還當書記哩!我張發子論水平比你高,憑資格比你老,這個大隊書記應該我來當。可惜他還不是黨員。他一回村就申了請,準備一入黨就代替富子當書記。他的這個思想,富子似乎看出來了,偏偏不發展他入黨,老是說支部通不過。還好,他多少弄了個民兵連長當當,連級干部啊,不容易哩,部隊里的連長帶百把號人啦!當連長也當的憋氣,富子一點權力都不給他,只讓他維持一下治安,好多會也不讓他參加。昨天,當他打聽到富子又要在大隊部召開干部會后,就耐心地等著,直到晚上也沒見到有人通知他,這下他生氣了。
“媽的個×,開什么玩意會,把老子撇了,老子偏要去看看。”
他背著他的套筒槍,氣沖沖地推開大隊部的門時,幾個大隊干部正油光滿面地喝著雞湯,這香味使他暗暗咽了一口涎水。他憤怒了,狗日的們,躲在這里享口福,也不叫老子一聲,太小看我這個連長了,老子叫你們也吃不成。他揮起他的套筒槍,把桌上的碗嘩啦啦掃了個精光。
張富子霍地站起來:“張發子,你要干什么?”
“我是民兵連長,為什么開大隊干部會不通知我?我當兵去朝鮮打仗時,你們都躲在屋里偎老婆哩,到今天,你們排斥欺侮我這老革命,老子就是不答應!老子不干什么,要你們吃不成!”
張富子見他充起老子來,臉上發青,氣得眼睛直冒火。
“你個混蛋,你給我滾出去!你不夠格參加這個會,我們是開支部會!”
張發子一聽,心里慌了,怎么不搞清楚呢?說不定他們今晚正準備研究我入黨的問題哩!這下可完了,他們要同意也不同意了!他抬頭看看在座的人,果然都是黨員,大家把眼睛都瞪著他。他想糟了,趕忙背著老套筒,用破大衣裹著身子,溜了。
只聽見身后響起哈哈的笑聲與罵聲:“神經病!”
他靠墻根坐著,想到昨天晚上自己的粗野行為,懊悔地用拳頭擂著自己的腦袋:張發子喲張發子,你真是個混蛋,這次把支部的人都得罪光了,你還入得了黨嗎?想到張富子,自己能斗過他嗎?想代替他當書記,自己連黨員都不是哩。嘿,聽說張富子的叔岳父是公社的書記哩,他有后臺呀!
他嘆了口氣,朝對面望了一眼。對面墻上正好畫著那幅社員用鋸子鋸稻子的壁畫,那社員正鋸得汗流滿面,汗珠子畫得有他家小寶玩的皮球那么大。嗯,都說這個人像我,他回憶了一下在部隊照的一張照片上的他,還真有點像哩。不過,連級干部能夠去鋸稻子么?他還從來沒流過這么大一粒的汗哩!哪有一棵稻子這么大?畫畫的學生娃娃真是扯他媽的蛋。
他從破大衣口袋里掏出了煙荷包,從另一支口袋里掏出一張小報,撕下一小塊,很熟練地卷起一支喇叭筒,伸出舌頭舔了舔,把喇叭筒粘住,劃著火柴,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股濃煙。看看報上有些什么玩意吧,民兵連訂了一分縣報,這張縣報就成了他的卷煙紙。他被一幅照片吸引住了,嗬,稻田里密密麻麻的稻子,畝產五千斤哪!高產!高產!這里的稻子過去最高產量也只能打個六百斤。嗬,全縣勞動模范哩,一個中年漢子,在報上望他笑著;試驗田里畝產五千斤,他成了全縣勞動模范,縣委書記和他握手,他上了報紙,全縣有名。我也來這么一下,怎么樣?畝產一萬斤,那時不怕你張富子不叫我入黨,我當這個金水大隊的書記怕是穩當當的!嗯,我去種塊試驗田試試,說不定能成功。好主意!他高興得一下從墻邊站起來,懊悔的心情早被一陣風吹走了。他背起他的老套筒,一只手插在破大衣口袋里,哼起了兩句漢腔:
“本帥打馬下山林,要到唐營走一程。”
吃飯的時候,他又犯難了。別看這米飯好吃,可種起來難哪,他畢竟是農村人,知道一些種莊稼的事。要畝產一萬斤,別說難達到,就是讓他去耕田栽秧的,他也有點怕,那才是累人呢,他的勇氣消失了一半。
回到屋里,愛人帶著兒子小寶剛從河對岸的娘家回來。小寶的外婆在河那邊的山里住,與這金水大隊不是一個公社,愛人每隔個把月都要回去看看娘。
小寶穿著新衣褂,拿著一個苕在啃。
“爸爸,這苕好吃哩,外婆屋里蠻多!”
他在兒子拿著的苕上啃了一口,嗯,是還蠻甜。愛人說:
“我娘她們那里今年苕多哩,一個都有斤把重,一畝地能挖幾千斤,就是沒人挖,都去煉鋼了。我娘看著可惜,自己去挖了幾籃子回來,其余的都在地里怕要爛掉了。”
什么?一畝地能挖幾千斤!種苕,這東西肯定能高產。岳母她們那里都是山地黃土,我們這里土地黑烏烏的肥得流油,種苕一定比她們那里挖的多,搞個畝產萬斤不成問題。搞一塊好地,多施些肥,一定能行。他高興得身子直搖晃,消失了的勇氣又鼓起來。他決定種苕,一嗚驚人。
“小寶他媽,你再抽個空到你娘那里去一趟,叫她們給我留點苕種,我要種苕!”
“咳,你瘋了!食堂的白米飯吃厭了,要吃苕么!你種苕?哼,我怕要苕來種你。”
“就我自己種,我要搞一塊試驗地,創一個高產紀錄。哼,別小看我啦,我要叫你們看看我這個連長是怎么當的!”他這話不知是說給小寶媽聽的,還是說給大隊書記張富子們聽的。
愛人好不容易才答應過幾天再過河去說說。他這才背著套筒槍,晃蕩著出門去執行他的任務去了。
經過幾天的轉游、偵察,他把認為比較好的幾塊地進行了選擇比較,最后選定了大隊學校門前的一塊菜園地。這塊地在金水河邊,離水近;又在學校前邊,離肥近,他可以把學校廁所的肥全部施到田里;同時還可以解決勞力問題,叫那幾個老師和些小學生娃挖地、送肥也方便,學校門口不是寫著“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么!
說干就干,第二天一早,他就披著他的破大衣,背起套筒槍,到學校找到了校長。
“劉校長,今天你們全體老師和學生都拿上工具,把那塊地翻一遍,要深翻,挖三尺深。”他把下巴朝那塊菜園地揚了揚。
小學校的劉校長領導著兩個老師、三個年級的百把名學生。劉校長聽到這位連長的命令,忙忙點頭答應:
“好!好!張連長,你這是要種什么東西啦?”劉校長明白這連長的權力,半個不字都沒說,反正學校這年頭上課不上課都無所謂。
“嗯,我種苕,這里種試驗地。”他眼睛望著河那邊答應。
好熱鬧的場面,一百多個學生娃娃吵吵嚷嚷,哭哭叫叫,一年級的學生只有七歲,三年級最大也才十歲,張發子家的小寶也上一年級。劉校長帶著兩個老師挖地挖得汗流滿面,學生娃子們的積極性也高得很,好像這挖地比坐在教室里聽老師教那些頭痛的粉筆字要好得多,雖然個子還沒鍬把高,他們也拖著鼻涕格嗤格嗤地挖著。兩個小娃子打架了,一個娃子哭了,老師吼了半天,才止住。張發子閑悠地背著槍在地邊踱來踱去,這里指點一下,那里指點一下,有時也從小娃子手中接過鐵鍬挖一陣,然后再蹲在地頭卷起喇叭筒抽幾口。他感到很快活,他的理想,他的希望,就要實現了啊!
這時,大隊書記張富子從那邊走了過來,大概是從野地里檢查煉鐵爐回來的。張發子老遠就看見了,哎,書記還是不能得罪的,他只好迎上去,好像沒發生過前幾天晚上的事一樣,打著招呼。
“富子,你這是從哪里回來?”
常言說,伸手不打笑臉人,書記的肚量也還大,見他主動打招呼,也笑著說:
“發哥,你這是搞么事呀?和娃子們玩得這大勁?!”
“嘿,書記,我準備把這塊地翻出來做試驗地,培育高產作物。”
富子書記驚奇了,這條懶龍大概閑得無聊了,今天出來汲水哩。管他的,隨他搞去吧!
“種什么東西?”
“種苕!我要培育大苕,高產苕。”
什么?種苕。這可是金水大隊的稀奇事了,這里過去從來不種苕。這家伙搞么新鮮板眼?嗯,隨他吧!隨他吧!
“那好,好!你弄吧,我走了。”書記匆匆離開了。
張發子望著書記的背影,心里罵道:看你小子神氣的!
在他的親自督促下,學生娃子和三個老師挖了幾天,才按他的要求把一畝地深翻了三尺,倒把一些生土都翻出來了。隨后,他又親自督促老師和學生把學校廁所的糞肥全都弄到地里,潑了一層,剛好起南風,弄得個小學校上課臭了三天。
愛人到娘家要苕種也很順利,那邊生產隊說,你們要多少就挖多少去吧!他和愛人一起,揀那個兒大的,背了兩筐子回來。他小心翼翼地侍弄了一塊地埋下去,只等苕藤長起來,他就可以把藤子剪成一截一截的。往試驗地里插了。這些事,他沒有要人幫忙,都是親自動手,也難為了他。他后來又到他岳母那個隊里,向有經驗的人請教過苕的栽法、管理等技術,他感到胸有成竹。
往地里插苕藤了,他又去找校長下了一道命令,小學校又全體出動。這次只讓學生娃從河里用臉盆端水,由他和三個老師往地里插苕藤,苕藤插下去后,只留那片芽葉在地面,再澆上水。他的要求是那樣嚴格,棵距、行距都按尺寸來,稍微歪了一點,他都要重新來插,整整忙了一天。
真是老天也開恩助他,苕藤插下去后,下了兩場小雨,那在野地里筑的煉鐵小土爐都被雨澆滅了,而他的苕秧子長出來,綠油油的,愛人得很。他背著套筒槍,有事沒事都到地頭轉幾次。要松土啦,施肥啦,他就到學校給校長打個招呼,老師和學生就出動。他覺得他這個連長調動小學校的老師學生,比調動他統領的民兵要容易多了。媽的,那些民兵可不大聽他的調遣,富子那小子說去煉鋼,呼啦一聲就把他的兵帶走了,他都成了個光桿司令。不過,能調動老師和學生娃也可以,總比沒人調動強。等著吧,等他的奇跡創造出來后,他的威信就會比富子高得多,那時看他們聽不聽我的吧。
他叫大隊的木工師傅給他做了個大木牌子,牌子刨得光光的,他找來了紅油漆,用他剛掃過盲學的幾個字,在牌子上歪歪斜斜地寫著:
牌子寫好了,他欣賞了半天,覺得自己寫的這幾個字還蠻不錯的,油漆紅艷艷的,字兒歪歪斜斜的,這是一種體哩。欣賞了半天,就扛到試驗地插起來。木牌樁子插進地里一尺多深,他用手搖了搖,絲紋不動,看來是不會叫人拔走的。
插好木牌,他又圍著地邊轉了轉,綠油油的苕藤已經快把黑色的土地蓋住了,他似乎聽見黑色土地里的苕正長得咔咔直響。快長吧,長吧,最好長得一個有南瓜大、磨盤盤大、石磙大。明天再叫劉校長帶學生娃們施一次肥,舍不得施肥,苕長得大嗎?
試驗地正處路口,來往行人很多。人們看到這個牌子,覺得蠻稀奇的,都要停下來看看。
“畝產萬斤,牛皮吹破天吧!”
也有人看到那綠油油的、翠綠欲滴的苕藤,也夸兩句:
“這苕還長得不錯哩!”
內行人卻說:“這苕不能再施肥了,要瘋長哩!”
一天,公社的王書記,大概是張富子的叔岳父吧,從試驗地路過,看了牌子和試驗地,找到了張發子,把他大大地表揚了一番:
“嗯,老張哪,你的試驗地不錯哇,這樣搞很好嘛,你創造一條經驗來,大面積推廣嘛!畝產萬斤,如果全公社都達到這個產量,那要增產多少哇?你放了個大衛星哩!”
這下可把張發子喜得屁股都要顛成兩半了,見人就說:
“我那試驗地可是大衛星哩!公社的王書記都表揚了我哪,我可要成為了不起的人了!伙計,將來得了好處,我決不會忘了你。”
被大躍進躍得有些頭腦發昏的人們,誰也不能斷定他的試驗地就達不到一萬斤的產量,說不定還要超過呢!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人們恭維他:
“張連長,這下可出名了,你怕要升官了吧!”
他嘿嘿地笑著,裝得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連忙熟練地卷起一支喇叭筒煙,遞給為他戴高帽子的人,然后又背起老套筒,樂顛顛地轉到地頭,嘴里又哼起漢腔:
“本帥打馬下山林,要到唐營走一程。”
小學生們下課就跑到地邊玩玩、看看,可誰都不敢動一動苕藤。有一次,一年級的一個學生娃子摘了一片苕藤葉子,被張發子看見,耳朵都擰得發腫了。小娃子們圍在地邊,不敢動苕藤,就念木牌上的字。大隊書記張富子的兒子張小軍讀二年級,如今的學生讀書認字都是橫著一行行地念。張小軍按木牌上橫的字讀著:
“干部試驗地,試驗人畝產品種,張發子萬斤苕。”小軍有些奇怪,又把第三行讀了一遍:
“張發子萬斤苕!”
娃子們轟地笑起來。“哈哈,萬斤苕!萬斤苕,張發子!張發子,萬斤苕!”他們一遍遍地叫著、跳著。
“小寶,你爸爸是萬斤苕,你爸爸是萬斤苕,哈哈!”
小寶哭著背起書包,找到了正在村子里轉游的張發子。
“爸爸,他們罵你是萬斤苕!嗯嗯。”小寶邊哭邊說。
“什么?罵我萬斤苕,哪個狗日的敢罵我?”
“是張小軍罵的。”
小軍,張富子的兒子,這不是他老子教的么?哼,老子今天要收拾你。他丟下哭著的小寶,從口袋里掏出根繩子,背起套筒槍跑到學校,教室里正在上課,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闖進二年級教室,把小軍一把擰了出來,把娃子捆在了門前的電線桿上。小軍扯起喉嚨哭,教室里一下亂了套,劉校長忙跑過來。
“張連長,這是怎么了?”他結結巴巴地問。
“這小狗日的仗他爹的勢,辱罵革命干部,說我是萬斤苕,老子今天要教訓一下這小狗日的!”
劉校長嚇得不得了,早有另一個老師跑去喊來張富子。
書記趕到學校,看見自己的兒子被捆在電線桿上,火光直冒,上前對著張發子就是一掌,把他推了丈把遠,把小軍身上的繩子解了。張發子從來沒受到這么大的侮辱,爬起來抓住老套筒,把槍栓拉得嘩嘩響,大吼一聲:
“舉起手來,狗日的東西,竟敢打老子,老子斃了你!”
這下可把劉校長和兩個老師嚇得臉都白了。劉校長哆哆嗦嗦地撲到張發子跟前:
“張連長,嗯,嗯,嗯,做不得!有話好說,好說。”
張富子冷笑了一聲:“打吧,朝老子胸口打!”他把胸口拍得啪啪響。“你那破槍嚇別人還行,嚇老子可不行!狗日的神經病,小心點。”說完牽著兒子憤憤地走了。張發子懊喪地拍拍槍,槍里沒有子彈。
書記和民兵連長的意見越鬧越大了,兩人結下了仇。張發子想,等老子的試驗地打響了,看老子整你。張富子想,這狗日的神經病,等有機會,非把他的民兵連長撤了不可。他還想入黨,白日做夢去吧!
書記和民兵連長鬧崩了不說,萬斤苕三個字不脛而走。萬斤苕,哈哈,這名兒不錯,加在他身上剛剛合適。看他酸樣兒,芝麻大個官,露水大個銜,偏擺出個天大架子。哼,畝產萬斤苕?真是個萬斤苕。
人們只敢在背后議論,誰也不敢當面喊他這雅號,不知是人們怕他那支套筒槍,還是怕他是個連級干部。
這一年的雨水特別好,大片的田地里莊稼因沒人管,荒草比禾苗長得還高。人們早出晚歸去煉鋼,誰還顧得種莊稼。張發子試驗地的苕長得特別好,他三天兩頭命令劉校長帶領學生施肥,翻藤,綠汪汪的苕藤長得有半人高,把黑油油的土地遮蓋得連縫都沒有,像一床綠綠的厚毯子。人們對這塊地也來了興趣,見了張發子的面,都要豎起姆指夸上兩句:
“張連長,你這試驗地畝產萬斤沒問題,只會多,不會少!”
“張連長,你這回創奇跡,放大衛星,要上報,出名哩!”
這些不知是奉承還是真心贊揚的話,把張發子抬到了半天云里,他像喝了一瓶漢汾酒一般,渾身飄起來了。天氣熱了,那件黃破大衣脫去后,身上剩一件白布對襟衫,腰里扣根從部隊帶回的武裝帶,老套筒仍然倒背著。他不斷地給說好話的人卷喇叭筒煙,一天三遍地在地邊轉游,看著那一片綠色,撫摸著軟乎乎的苕藤,肚子里像裝了幾斤糖水,都流出嘴角了。有時,他抱著槍打坐在地頭,望著苕藤出起神來。啊,理想馬上就要實現了,報上登著他背槍的照片,他在嘻嘻地笑著,一個像石磙一樣的大苕放在展覽館里,苕上系著紅綢帶子,縣委書記親切地握著他的手。他入黨了,他當了金水大隊的書記。張富子因打擊革命干部,打擊模范被撤職了。張富子來了,朝他諂媚地笑著,“發子哥,發子哥”叫得那樣親熱,他決定頭也不回,從鼻子里哼一聲。
“你哼什么?”張富子叫子起來,把他從夢中驚醒了。他懶洋洋地站起來,張富子果然站在面前,臉上并沒有諂媚的笑,而是對他冷冷地說:
“你這民兵連長蠻負責哩,成天保衛著你這一畝試驗地,不可出岔子哩。我說,發子哥,公社王書記來電話,要在你的試驗地挖苕時開現場會哩,你是不是明天上午把苕挖了,下午通知開現場會的人來。”不等他回答,張富子就走了。
嗬,開現場會!啊,露臉的時候到了。張發子喜孜孜地背起老套筒,去學校安排明天上午挖苕的事。可是關鍵時刻啊,他一遍遍叮囑自己,要穩重,萬萬不能昏了頭,產量肯定能達到的,人家都這樣說。他一身輕快,走著走著,連跑帶跳起來。
第二天一早,張發子像迎接盛大節日一般,全副武裝起來,穿起單軍裝,扎起武裝帶,帶起老套筒,威風凜凜。百多名學生吵吵嚷嚷地挖著苕。學生娃子的口水都快流出來了,可誰也不敢啃一口那甜甜的苕,張連長在地邊監視著哩,小寶扯住他的衣角:
“爸爸,我要吃苕!”被他給了一巴掌:
“小狗日的,這苕不能吃,下午要展覽用。”
挖著,挖著,張發子心里有點慌了。那石磙一樣大的苕呢?沒有!連磨盤大的也沒有。最大的只有他只從部隊帶回的搪瓷杯那么大。哎呀,怕要出問題了,哪來一萬斤苕?這怎么交差呀!一時,他心里發火了,媽的×,這地也跟老子作對。嗯,說不定大的都長到地底下去了。
“哎,龜兒子們,再挖深些,下面有大的!”
小學生們拿出了吃奶的力氣,把地挖了三尺深,還是沒有挖出石磙大的苕來。他急了,他慌了,他罵人了。
“媽的×,媽的×,這是怎么搞的?這是怎么搞的?”
學生姓們黑汗水流地挖了一上午,好不容易把一畝地的苕都挖出來了。堆成兩大堆。他在堆子旁來回地估量著。嗯,好大兩堆,苕是壓秤,苕鐵苕鐵嘛,看樣子有一萬斤。他喊住了帶著學生正要離去的劉校長。
“哎,校長,你說這有一萬斤吧!”
劉校長把堆子估了一番。“有!有!肯定有一萬斤,張連長你放心吧!”說完堆著笑臉,趕忙溜了。
他等大家都走光,又圍著苕堆轉起來。有一萬斤嗎?好像差不多。不,好像差得遠,那怎么辦?下午要開現場會,得想個么法子呀!他就這樣在苕堆邊轉來轉去,轉了一個中午,連午飯都忘了回去吃。
下午,開現場會的人都來了,公社的王書記,各大隊的書記們都和張發子打著招呼。
“伙計,來向你學習呀!”
張發子心里像揣了只兔子,腿肚子有些發軟,他越來越覺得這兩堆苕沒有一萬斤,肯定要砸鍋了。他一邊和開會的人應酬著。一邊用兩只眼盯著苕堆,希望苕堆突然變大,達到一萬斤。
擔心的事終于發生了,張富子幾個人很快用磅秤把兩堆苕稱了一遍,天啦,兩千多一點,還差七千多斤啦!
公社的王書記說:“老張,還有苕呢?”
張富子說:“就這兩堆,還哪里有啊!”
各大隊的書記一陣轟笑。王書記氣沖沖地拔木牌子,拔不動,張富子連忙上去幫忙,木牌子拔出來了,王書記把木牌子朝路上一摔:
“哼,萬斤苕,你欺騙領導,吹牛撒謊,富子!”
張富子忙跑到叔岳父跟前:“在!嘿嘿,您有什么指示?”
“你們支部開個會,嚴肅處理這件事,處理結果上報公社。”張富子正中下懷,連連答應:“好!好!”
張發子腦子響成一片:完了!全完了!
王書記帶著開現場會的人走了。
張富子狠狠地瞪了張發子一眼,意思是說,怎么樣?你的期限到了。
張發子坐在地上,腦殼深深地埋在大腿下,嘴里是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他干么事要找這個麻煩呢?民兵連長當得好好的,偏偏種他媽的么事試驗地!現在后悔也來不及了。
試驗地的路邊上,木牌被王書記摔成了兩半,下半塊上赫然地寫著“張發子萬斤苕”,顯得格外醒目。
金水大隊黨支部在書記張富子的領導下,對張發子的處理一點情面都沒留。張發子不是黨員,無黨籍可開除,把他的民兵連長撤了,由連級干部降到社員。張發子沒什么話說,他想,算我倒霉,我又沒有后臺。連級干部撤了,套筒槍上繳了,連那縣報也成了新連長的卷煙紙。嘿。提起那縣報,張發子就一肚子火,要不是它,他的連級干部怎么會撤呢?他怎么會想著去種什么試驗地呢?
張發子正式變成了萬斤苕。沒有往日的威風,沒有老套筒,人們當面喊他萬斤苕了。書記的兒子張小軍見了他,邊跑邊喊:
“萬斤苕!萬斤苕!”
小寶從學校哭著回來:“爸爸,小軍罵你是萬斤苕,嗯,嗯!”
“哭你媽的鬼,老子還沒死!”小寶倒挨了一巴掌。
共產主義的前腳跨進了中國的大門,后腳又從后門里跨出去了。什么原因?大約是沒有好東西招待它。沒日沒夜的大煉鋼鐵,糧食沒有收上來,人們一天三兩米的定量,樹葉、草根都吃光了,共產主義餓跑了。
萬斤苕老了許多,他的腰弓了,人瘦得像只大蝦子,那件棉大衣更破了,腰上緊緊纏著一根草繩,一來防寒,二來把肚子捆住,免得咕咕直叫。他仍然愛在村里轉游,代替套筒槍的,是一只撿糞用的小糞扒。他走到那些學生畫的壁畫前,望望那些畫,心里罵道:
“扯他媽的蛋,芝麻哪能長得西瓜樣大呢!”
有人喊他“老萬”,這是對他的尊稱,代替了萬斤苕。
“你吃過了嗎?”
“吃什么,一碗稀湯屙泡尿,早沒有了!”那人嘆了一口氣說:“要是真能一畝地挖一萬斤苕,我們也不會餓了。”
他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找個墻根坐下來,掏出煙荷包,煙葉早沒有了,煙荷包里裝的是枯荷葉。他用枯荷葉卷了一支喇叭筒,卷煙紙是小寶的舊課本。他吐了一口濃煙,望見了對面那堵墻,墻上正畫著一個社員拿鋸鋸稻子,那社員真像他。
多少年過去了,萬斤苕的雅號再也離不開他了。
別人喊他萬斤苕,他也習慣了,也能笑著答應了。張發子這個本名被人忘記了。
關于萬斤苕的故事,當年的金水大隊如今的金水村的老人都知道。張發子的孫子后來讀了大學中文系,做了作家,他在家鄉作鄉村調查時,知道爺爺綽號的來歷,寫進了他的非虛構作品中去了。
責任編輯 石華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