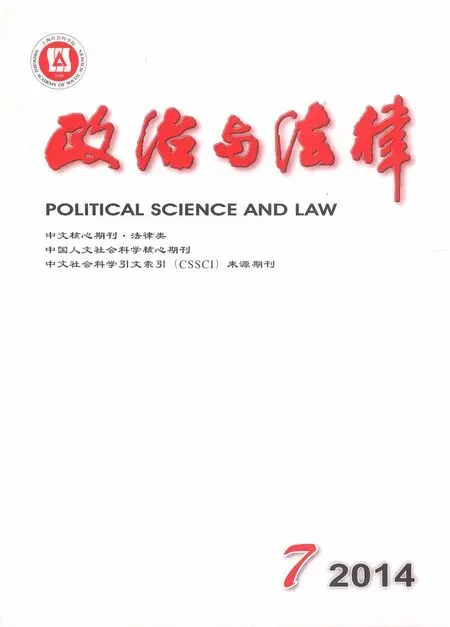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實行行為的重新界定:非法獲取*
李本燦
(南京大學法學院,江蘇南京210093)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實行行為的重新界定:非法獲取*
李本燦
(南京大學法學院,江蘇南京210093)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實行行為并非“不能說明”,也不是“持有”巨額不能說明來源的財產。以“不作為”作為本罪的處罰依據具有明顯的不周延性,難以涵蓋因客觀原因造成的不能說明或者概括性說明。持有犯罪的本質在于持有行為本身抽象的或現實的客觀危險性,危險性源自于持有對象本身的重大利益相關性,財產僅僅是交換媒介,不能成為持有犯罪的對象。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處罰的是獲取巨額財產的非法行為本身,這種非法由法律推定完成,“以非法所得論”表征了這一點。“不能說明”只是“可以說明”的同義表達,為推定非法提供了出罪路徑。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實行行為;不作為;持有;非法獲取
一、研究的起點:理論紛爭及其指導下的實踐混亂
(一)關于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行為性質的爭論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在我國理論及實務部門的爭論一直都在持續。縱觀對該罪名的眾多紛爭,大都可以歸結為一點,即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實行行為如何界定。對于該罪實行行為的性質,國內學界存在不作為論、持有行為論以及復合行為論三種觀點。基于對我國《刑法》第395條第1款中“責令說明而不能說明”的法條解讀,有論者認為該罪屬于刑法理論中的純正不作為犯罪。①參見李文燕主編:《貪污賄賂犯罪證據調查與運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05頁。同樣持不作為論的學者還有高銘暄、馬克昌、陳興良、侯國云等。這是基于我國刑法中不作為犯罪理論的傳統解讀,也是目前處于正統地位的學說。為了論證這種解釋的正
當性,學者們提出了作為義務來源的不同主張。認為作為義務來源于《刑法》第395條第1款自身的規定者有之,②參見周光權:《刑法各論講義》,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頁。認為作為義務來源于司法人員的責令者亦有之。③參見侯國云:《有關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幾個問題》,《政法論壇》2003年第1期。另外根據學者介紹,我國甚至有人認為該義務來源于國家工作人員財產申報制度。④參見孫國祥、魏昌東:《反腐敗國際公約與貪污賄賂犯罪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20頁。對于不作為論,有學者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該罪的本質特征是擁有巨額難以說明合法來源的財產本身,而不是“不能說明”,因此,該罪屬于持有型犯罪。⑤參見儲槐植:《三論第三犯罪行為形式“持有”》,《中外法學》1994年第5期;持同樣觀點的學者還有薛進展、梁根林等。結合了不作為論和持有論的內容,有學者提出,該罪是非法獲取巨額財產的作為與拒絕說明巨額財產來源的不作為的復合;⑥參見孟慶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客觀方面問題探討》,《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也有學者提出,該罪是持有巨額財產與拒絕說明巨額財產來源的不作為的復合。⑦參見孫國祥:《貪污賄賂疑難問題學理與判解》,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頁。
(二)司法認定的混亂
對于該罪行為性質的不同認識,會產生不同的犯罪行為時的認定問題,而如果這個時間跨越了《刑法修正案(七)》,那么,將會導致刑罰在橫向維度上的不均衡。具體來講,如果以不作為犯論或者以復合行為犯論,那么其不作為的時間發生在后,將適用修正后的刑罰;如果以持有犯論,那么,持有的事實可能形成于修正案之前,只能適用修正之前較輕的刑罰。對此,有論者早已敏銳地察覺,并列舉了不同的案例加以說明。⑧參見薛進展:《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行為本質的實踐檢示——從刑法修正案(七)修改后的法律適用展開》,《法學》2011年第12期。同樣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卻因對該罪本質的認識不同而適用差異較大的刑罰,這就提醒理論工作者,應該對于“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實行行為究竟是什么”作出一個清晰的界定,而不是在爭論中誤導實踐。恰恰是理論上的紛爭以及在該理論指導下的混亂的司法現狀,才構成了本研究的起點。
二、研究的中點:對傳統理論的反思⑨
(一)對不作為論的質疑
傳統上對不作為論的質疑多從義務來源上著手,認為,我國不存在財產申報制度,因此也不存在作為義務來源的問題。“我國目前尚無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申報制度,只是在1995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中有所涉及。財產申報制度因涉及公職人員的隱私權問題,應以法律形式頒行,而不能停留在政策層面。我國財產申報制度的現狀,不可能成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前置法,無法提供特定義務。”⑩同前注④,孫國祥、魏昌東書,第520頁。問題是,我國刑法對不作為犯采取的是形式說,刑法明文將不作為規定為犯罪構成要件要素的犯罪才是真正的不作為犯。?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頁。如果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學者認為的純正不作為犯,那么就不應該從刑法規范之外,而應該從刑法
規范本身進行檢視,因為從刑法之外進行義務來源討論,針對的是不純正不作為犯。可以說,在這一點上,傳統觀點是對不作為義務來源基本理論的一種誤讀。基于這樣的考慮,對《刑法》第395條第1款本身的檢視構成了本部分的立論基點。
基于這樣的考慮,即“復合行為論是在結合持有論和不作為論兩種學說觀點基礎上的合成,總起來說,它與不作為論都是以不能說明財產來源的合法性為其行為的標志或者行為終點,脫離不了不作為的范疇,可以說是不作為論的進一步發展,因此理論的爭議實際上就是持有論和不作為論兩者的分歧”。在該部分,筆者僅僅對不作為論和持有論展開評述。
1.“不能說明”的重新檢視
第一,“不能”不等于“不”、“拒絕”。純正不作為犯中,“將不作為規定為構成要件要素”主要是指,規定了不作為犯的保證人和對行為使用了“沒有”、“不”、“拒絕”之類的表述。?同前注?,張明楷書,第150頁。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進行檢視不難發現,《刑法》第311條“拒絕提供間諜犯罪證據罪”以及第261條“遺棄罪”是典型的純正不作為犯罪。“拒絕提供間諜犯罪證據罪”中,行為人“明知”他人有間諜犯罪活動,當受到國家安全機關調查時而“拒絕”提供;“遺棄罪”中,行為人有撫養義務而“拒絕”撫養。兩個犯罪中法律評價的重點都在于“拒絕”,但前提條件是行為人具有作為的能力,前者具有提供間諜犯罪證明的能力,這一點由法條中的“明知”可以看出,而后者則可以通過法律解釋得出,因為“具有撫養能力”就蘊含于“拒絕撫養”本身,如果確實沒有撫養能力,法律也不會強人所難,將“沒有撫養能力而不養”的行為解釋為“拒絕撫養”。歸結起來,純正不作為犯表現為“具有作為的能力而不作為或者拒絕作為”,它表明的是一種行為,而非不能作為的狀態,由此體現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以及可罰性。反觀《刑法》第395條第1款中的“責令說明而不能說明”,“不能”表明的是一種狀態,這種狀態的發生,可能是由于主觀的不愿意說明而造成,也可能是因為客觀的原因而不能說明,例如因為貪腐次數太多、時間過于久遠而難以明確說明財產來源。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對于《刑法》第395條第1款規定的“不能說明”也作出了具體解釋,主要包括:行為人拒不說明財產來源;行為人無法說明財產的具體來源;行為人所說的財產來源經司法機關查證并不屬實;行為人所說的財產來源因線索不具體等原因,司法機關無法查實,但能排除存在來源合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這一司法解釋也表明“不能”體現的是一種結果和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講,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中的“不能說明”并不是純正不作為犯中的不作為的行為表征,因此也不能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誤讀成不作為犯。
第二,對“不能說明”的刑事苛責有違責任主義原則。如果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當作純正不作為犯,那么它仍然要接受責任主義的檢閱,即行為不僅僅要“有體”,同樣應該“有意”。如果以這個原則去衡量上述《紀要》中關于“不能說明”的解釋,那么,“拒不說明”和“行為人所說經查證并不屬實”都具有處罰的正當性基礎,因為它們同樣表征了行為人主觀的惡。但是,“無法說明”和“所說財產來源線索不具體而無法查實”則有結果責任的嫌疑。因為這兩種情況表示的僅僅是一種狀態,而導致“不能說明”這種狀態發生的原因并非是主觀的,而是客觀的,例如上文提到的時間久遠、貪腐次數太多等因素。實際上,作出這樣的論斷絕非憑空而論。現實中,行為人在跨度較大的時間段內貪污受賄上百次,甚至上千次的案件比比皆是,無論是從人體生理的角度還是從當事人的現實情況考慮,行為人對于那些對他們僅具有符號意義的金錢難以說清來源十分正常。例如,封丘縣原縣委書記受賄案中,經法院審理查明,行為人在2002年至2009年期間,先后1575次收受他人巨額賄賂,創歷史之最。?《1575次封丘縣委書記受賄創紀錄》,http://news.163.com/10/1111/01/6L61B8J500014AED.html,2014年3月26日訪問。拋開如何查實這個數字暫且不論,從嫌疑人的角度看,能夠記清楚1575次的受賄行為應該不是一種常態。可以說,因客觀原因而導致難以記清財產來源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如果不分緣由,均以“不作為”為由加以刑事處罰,顯然有違背責任主義原則的嫌疑。當然,這里需要說明的是,
這里并不是說對這種情況不加處罰,而是變換形式加以處罰,后文對此詳細論述。
2.對“不能說明”行為差異化處理的思考
如果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視為不作為犯,那么刑罰的基準是不說明財產來源的行為本身,而不是其他。行為本身決定刑罰量的配給,從理論上講,對價值1萬元來源不明財產的不予說明與對價值100萬元來源不明財產不予說明的情況并無本質的差異,客觀上都是對訴訟活動的一種干擾,影響刑罰量的因素只能是情節嚴重與否,而這個情況不應當是財產數額,或者不應當僅僅是財產數額。這一點,在《刑法》第311條“拒絕提供間諜犯罪證據罪”中就有體現,該條并沒有將證據的多寡視為升格刑罰的條件,更多考慮的是行為的情節。而反觀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法條表述:“……不能說明來源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差額特別巨大的,處……”其僅僅將數額作為升格法定刑的標準,這也從側面說明,刑法關注的重點是“巨額財產”本身,而不是“來源不明”或者“不能說明”。按照財產犯罪認定的一般方法和邏輯,數額僅僅是一個虛假的關注焦點,更重要的是獲得巨額財產的行為本身。對于什么行為應當是刑法關注焦點的問題下文將有論述,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不能說明”并不是刑法關注的焦點。
3.不作為論造成的刑罰過量問題
按照不作為論,刑法處罰的僅僅是“不能說明財產來源”的行為,“當司法機關在事后查明巨額財產真實來源的情況下,行為人通過其貪污、受賄等違法行為獲取非法巨額財產的行為,因與拒不說明的行為并非同一行為,對其科以貪污罪、受賄罪等罪的刑罰,并不會導致刑法對同一行為的重復評價,這恰恰符合‘一事一罰’的刑罰原則”。?同前注④,孫國祥、魏昌東書,第521頁。問題是,在數罪并罰的情況下,可能會產生刑罰過量的問題,尤其是在學界提出的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加大處罰力度的情形下。以修正后的刑罰為例,如果嫌疑人有50萬元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則首先要面臨5年至10年的自由刑,當查清楚以后,還要面臨貪污受賄的10年以上的刑罰,這顯然有刑罰過量的嫌疑。
(二)對持有論的質疑
1.持有犯罪的立法目的考察
對于持有型犯罪的立法目的,國內研究多數認為,其側重于堵截犯罪、保護法益的功能訴求,而非輕縱犯罪、保障人權的功能訴求。?梁根林:《持有型犯罪的刑事政策分析》,《現代法學》2004年第1期。它是風險社會語境下,刑法的應對策略之一。?郝艷兵:《風險社會下的刑法價值觀念及其立法實踐》,《中國刑事法雜志》2009年第7期。嚴密法網、堵截犯罪的立法目的在毒品持有犯罪立法背景說明中更是明顯,“對于被查獲的非法持有毒品者,首先應當盡力調查犯罪事實,如果查證是以走私、販賣毒品為目的而非法持有毒品的,應當以走私、販賣毒品罪定罪量刑。只有在確實難以查證犯罪分子走私、販賣毒品的證據下,才能適用本條的規定”。?李淳、王尚新:《中國刑法修訂的背景與適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465頁。但是,這種將持有型犯罪當作其他同類犯罪“備胎”的立法目的與持有型犯罪規范本身并不相符合。因為按照一般學者的理解,只有在難以查明具體犯罪行為或者犯罪企圖的情況下才能適用持有型犯罪,因此也出現了所謂的證明標準有所降低的論調。也是因為如此,學者才提出了持有型犯罪是一種推定型犯罪,并對這種推定可能出現的錯誤表示擔憂。?張建軍:《謙抑理念下持有型犯罪的立法選擇》,《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言下之意,如果行為人不是出于違法手段獲得的特定物品或者并非企圖使用該特定物品進行其他違法犯罪活動,那么這種違法推定就是對人權的一種侵害。問題是,從持有型犯罪法規范本身并不能推斷出這一點。以“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
為例,具有持有資格的公務人員或者機構的持有自不在討論范圍之內,如果是沒有經過許可的一般民眾持有槍支,那么,理論上講,不管獲得槍支的方式是不是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抑或是繼承所得、受贈所得、拾得,都應當構成非法持有槍支罪。司法實踐中這樣的案件也不少見。理論上的這種解釋使我們認識到一點,即法律對持有犯罪的規定并不是堵截犯罪,或者不僅僅是為了堵截犯罪,堵截犯罪僅僅是持有型犯罪的客觀效果。我們更應該強調持有犯罪本身的獨立性,不依附于任何其他犯罪。有論證考察了各國刑法中的持有型犯罪,論稱其主要限于兩種情形:“一是作為實質預備犯規定的持有特定犯罪工具或兇器的獨立犯罪構成;二是具有重大法益侵害直接危險的持有特定物品的行為、可能掩飾、隱瞞重大犯罪行為的持有特定物品行為或者僅針對具有特殊法律義務的行為主體即國家公務員設定少量持有型犯罪構成,如非法持有國家秘密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等。”?同前注?,梁根林文。對于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暫且保留意見,其他的總結可謂中肯。由此可以看出,對持有犯罪的規定,一方面是由于持有特定物品本身的直接危險性,想必也是論者認為持有犯罪屬于抽象危險犯的原因;?參見勞東燕:《公共政策與風險社會的刑法》,《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另一方面是出于犯罪預防的目的而設定持有犯罪。對于持有犯罪的立法理由,邊沁總結出兩點:首先是剝奪行為人實施其他犯罪的能力,其次是預防“主要犯罪”,這個目標主要是通過禁止持有特定物品而實現的。?轉引自張忠國:《持有型犯罪立法理念偏差及價值沖突檢討》,《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這兩點歸結起來也就是預防未然之罪,這一點與我們通常強調的懲罰“可能存在的已然之罪”的觀念顯然不同,顯然前者更具合理性。以預防為持有犯罪的立法目的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合法形式取得非法物品后的持有仍構成非法持有犯罪。但是,以預防為目的而處罰持有行為難以解釋為什么非法持有槍支構成犯罪,而非法持有刀具或者其他工具不構成犯罪。對這個問題的解答還要回到持有犯罪的持有對象本身,出于限縮持有犯罪立法圈的考慮,只能將持有特定物品的行為規定為犯罪,而這些特定物一定是具有顯著抽象危險性之物品,例如,槍支、彈藥;或者是具有重大的利益相關性的物品,例如國家機密文件、毒品,這也是持有行為入罪化的實質根據,同時也是持有犯罪的顯著特征。
2.對典型持有犯罪立法的考察
國內部分學者將“非法攜帶槍支、彈藥、管制刀具、危險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也歸類為持有型犯罪,?朱世洪:《持有犯罪研究》,《法治研究》2007年第12期。但是筆者不以為然。所謂“攜帶”同義于“持”,表明的是一種行為、動作,而“持有”表現的是行為人對特定物的事實地支配、管控關系,并不以“攜帶”為必要。基于這樣的考慮,筆者認為我國《刑法》中的持有犯罪主要有:第128條第1款的“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第172條的“持有假幣罪”,第210條之一的“持有偽造的發票罪”、第282條第2款的“非法持有國家絕密、機密文件、資料、物品罪”、第348條的“非法持有毒品罪”以及第352條的“非法持有毒品原植物種子、幼苗罪”。從我國關于持有型犯罪的規定來看,其對象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非法的物品,而這種物品對于市場經濟秩序的危害是巨大的,例如假幣和偽造的發票。恰恰是因為這些物品本身對于經濟秩序的危害,所以國家禁止持有這些物品。從罪名表述看,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能持有,持有就是犯罪,因此在罪名設計上并沒有像另一類持有型犯罪一樣使用“非法”這樣的字眼。另外一類持有型犯罪對象是那些本身具有重大的利益相關性,或者可能涉及公共安全以及公眾健康的物品,例如槍支彈藥,毒品,毒品原植物種子、幼苗以及國家絕密、機密文件、資料、物品等。因為這些物品本身的危險性或者特殊性,所以只能經由相關機構許可才能持有,這種持有是合法的,例如公安機關對武器彈藥的持有、國家機關對機
密文件的持有、相關醫藥機構對于毒品的持有等。未經許可持有該類物品就是非法,即“非法持有”。有論者經過對中國刑事立法的梳理也認為:“持有型犯罪對象范圍一般比較狹窄,其主要包括一些對國家或社會公共利益具有潛在危害或者危險性的物品,具體包括以下幾類:第一類是管制物品,包括槍支、彈藥、管制刀具、爆炸物、易燃物、放射物、毒害物等;第二類是毒品;第三類是特定物品,這里主要指國家工作人員的不法財產;第四類是其他特殊物品,如假幣、國家絕密、機密文件等。”??張麗霞、劉建民:《試論持有的性質與持有型犯罪的特征》,《河北法學》2005年第2期。拋開本文正在討論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不論,其他特定物品均屬于該論者所說的“對國家或社會公共利益具有潛在危害或者危險性的物品”。這就不難理解這樣的論斷,即“持有型犯罪之所以進入刑法的視野,受到刑罰的否定評價,成為刑法罰及之對象,就在于有一定的抽象的或現實的客觀危險性,給社會秩序和安全造成了潛在的威脅”。??樊崇義、周士敏、劉根菊主編:《刑事訴訟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頁。
3.財產不宜成為持有對象
在對持有型犯罪對象進行抽象總結之時,國內學者基本都論及了特定管制物品以及巨額財產。這里有必要對兩者進行比較分析,財產究竟能否成為持有犯罪的對象。以槍支、彈藥為例,針對該特種物,刑法中往往規定了一個犯罪群,包括買賣、運輸、非法制造等,即使是合法取得該特種物而持有,例如拾得槍支后持有的,同樣也受到法律的否定評價。反觀“巨額財產”,其屬于我國《刑法》第八章“貪污賄賂犯罪”中的一種,從類罪的法益看,主要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本身,而不是財產,國家工作人員通過合法方式取得的財產,例如遺贈、拾得巨額財產,本身就被該罪排除在外,這一點與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顯然不同。另外,從持有特定物所具有的抽象或現實的客觀危險性方面考慮,持有巨額財產何來抽象危險?持有型犯罪的立法價值并不在于通常所說的堵截犯罪,而在于預防未然之罪,從這個角度考慮,通過對持有巨額財產的行為進行處罰,預防的價值何在?如果認為持有巨額財產就具有了犯罪的經濟條件的話,那么普通民眾持有巨額來源不明財產就具有同樣的危險,應當進行同等預防,但是刑法僅僅關注了國家工作人員這個特定主體,這也恰恰說明了該罪名與腐敗犯罪之間天然的聯系。實際上,財產本身是中性的,僅僅是一種公共交換媒介,本身并不具有非法性或者與公共安全、健康的相關性,任何人都可以持有,并且私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刑法評價的并非財產本身,而是獲得財產的方式。
三、研究的終點: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實行行為的重新界定
(一)推定的非法斂財行為標準的確立
1.“以非法所得論”的解讀
前文已經提及,不作為論并不能涵蓋所有不能說明來源的具體情形,具有明顯的不周延性,如果以不作為論進行刑事苛責,有違背責任主義的嫌疑;基于對典型持有型犯罪的研究可以看出,持有巨額財產本身并沒有任何的抽象或具體危險性,并不能構成刑罰處罰的正當性依據。國內學界之所以在不作為論與持有論之間持續爭鋒,相持不下,筆者認為,主要原因在于對《刑法》第395條第1款中“不能說明來源”與“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過于專注,而忽視了該罪狀表述中最關鍵的字眼,即“以非法所得論”。現行刑法典中大量使用了“違法所得”的表述,它同義于這里的“非法所得”。而“違法所得”表明的僅僅是一種后果和狀態,至多起到刑罰加重或減輕的作用,刑
法評價的重點在于取得財物的行為本身,所以刑法在表述“違法所得”之時,多與特定的行為方式并行出現。例如,《刑法》第175條“高利轉貸罪”表述如下:“以……為目的,實施了……行為,違法所得數額較大的,處……”第217條“侵犯著作權罪”表述如下:“以……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權情形之一,違法所得數額較大的,處……”由此可以推論,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中的“非法所得”也與特定的行為方式相對應,這里的特定行為方式,主要是指貪污受賄等腐敗方式。這樣的論斷從兩點可以得知。首先,從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罪名分布位置來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刑法》第八章“貪污賄賂罪”的罪名之一,其侵犯的法益自然是公職人員的職務行為廉潔性。這種造成法益侵犯的行為應當與貪污、受賄行為具有同質性。其次,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與貪污受賄犯罪發生具有同時性。國內學者對此也有認知和論斷,據學者統計,“1998年至2000年,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起訴和審判的案件只有51件52人,這些案件有一個比較突出的特點,就是通常與貪污罪、受賄罪相伴,很少有單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定案的情況”。?筆者對近年12位廳級官員的統計數字也顯示,只要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存在的案件,就同時出現貪腐犯罪,而且來源不明的財產數額甚至遠高于貪污受賄的數額。例如,原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王有杰受賄案中,不能說明來源的數額(890萬元)高于受賄數額(643萬元);原海南萬寧市副市長林禮深受賄數額5.4萬,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數額高達160萬。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與貪污、受賄犯罪近乎100%的聯系使得我們有理由推斷,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就是由于貪腐所致。“以……論”的法律表述也正是這種法律推定精神的表達。實際上,1987年1月21日王漢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的講話也表明了立法的初衷:“近幾年,國家工作人員中出現了個別財產來源不明的暴發戶,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不是幾千元,而是幾萬元、十幾萬元,甚至更多,本人又不能說明財產的合法來源,顯然是來自非法途徑。”?
歸納起來講,占有巨額來源不明財產僅僅是一種結果狀態,刑法關注的重點應當是如何取得巨額財產,而不是傳統上所認為的“不能說明來源”或者“持有巨額來源不明財產”。只不過對于如何取得巨額財產的方式由于特殊原因難以直接確定,因此而作出了推定,即“推定的非法斂財行為”構成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處罰的基準。以推定的非法行為作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處罰依據,也可以避免理論上的很多問題,例如,有論者提到的“先有偵查,再有犯罪的悖論;司法機關的偵查活動催生犯罪行為產生的悖論;偵查、審查起訴、審判三階段都產生犯罪行為的悖論;法律適用的依據不在于犯罪行為發生時間的早晚,而在于案發時間早晚的悖論等”。??錢舫:《論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政法論壇》2001年第6期。
2.“不能說明”要件的重新定位
確立以“推定的非法斂財行為”為處罰基準,似乎有“有罪推定”的嫌疑,但是法律也為這種推定設置了出口,即行為人可以提出意見,推翻這種推定,這就涉及到“不能說明”的重新理解的問題。不作為論者將“不能說明”理解為“拒不說明”,從而違背了“責令說明”的義務,構成不作為的犯罪,筆者認為這是對“不能說明”的誤讀。“不能說明”包含多種情形,“拒不說明”只是原因之一,將“不能說明”理解為“拒不說明”難逃以偏概全的嫌疑,這一點不再多論。這樣解釋不通的情況下可以嘗試其他解釋,實際上,“不能說明”是“可以說明”的同義語,是一個問題的另一面表達。不能說明巨額財產來源構成犯罪,那么,“可以說明財產來源”自然成為了出罪路徑。如果說“以非法所得論”是立法對基本訴訟法原理的一種背離,那么“不能說明”就是立法者的自我矯正。如果說“以非法所得論”是立法者面對嚴峻的腐敗形勢的一種無奈策略,那么“不能說明”則是立法者智慧的一種彰顯,因為僅通
過法律推定技術的使用就達到了懲治犯罪與權利保障之間的平衡。
(二)域外經驗與該標準的暗合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20條規定了“資產非法增加罪”,國內學界一般認為,該罪名與我國刑法中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大致對應。但是這樣的認識是在傳統不作為論、持有論以及復合行為論的基礎上作出的,在這一點上有探討的余地。筆者認為,“資產非法增加罪”與我國刑法中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確實具有對應關系,但并不是傳統的不作為犯或者持有犯,亦或不是復合行為犯,其處罰的依據都是獲取巨額財產的非法行為。按照筆者的理解,“資產非法增加罪”的核心在于“非法增加”。“增加”表達的是一種獲取資產的行為,而不是資產增加的狀態本身,因為這里的“非法”明顯是一個副詞構造,其修飾的對象“增加”只可能是一種行為。兩個詞組合起來應理解為,行為人通過非法手段實施了資產增加的行為,這恰恰是該罪的實行行為,也是處罰依據。筆者這樣的理解也得到其他論者的印證,例如,有論者對“資產非法增加罪”作出這樣的界定:“它是指公職人員故意實施的,促使其資產非法顯著地增加,而本人無法以其合法收入作出合理解釋的行為。”??夏明飛:《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現實境遇與對策》,中國法院網,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0/04/id/402738.shtml,2014年3月28日訪問。由此可以看出,這種解釋與上文筆者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界定是一致的,即兩者都表明的是,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而實施的非法獲取巨額資產的行為。可以說,在精神實質上,兩者是一致的,只不過,“資產非法增加罪”更準確、科學地表述出了這種精神,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在罪名擬定的科學性上尚顯不足。
無論是我國刑法中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還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中的“資產非法增加罪”,都是為了堵截腐敗犯罪而設置的具有兜底性質的罪名,其所兜之非法行為無非就是貪污、賄賂等腐敗犯罪,只不過我國法律是通過推定的方式實現腐敗犯罪懲治目的的。而諸如資產非法增加這樣的行為在部分國家立法中則直接被法律擬制為賄賂犯罪。例如,“新加坡以《沒收貪污賄賂利益法》和《防止貪污法》兩部法律作為刑法、刑事訴訟法之補充,突出了國家重點打擊貪污賄賂的刑事政策,將政府官員們的財產來源不明直接擬定為貪污罪:一個人所擁有的財產在本法公布實施之后已經占有而該人又不能向法院作出合理滿意之解釋時,其財產應視為貪污。文萊《防止賄賂法》、印度《防止腐敗法》對官員財產來源不明的情形稱為‘擁有無法作出合理解釋之財產’,以賄賂罪處罰”。??鄧君韜:《順應的“苛嚴”:“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修正案草案解讀》,《政治與法律》2009年第1期。無論是法律推定還是法律擬制,無論是以貪污、賄賂犯罪的罪名還是諸如“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這樣的獨立罪名處理“擁有無法作出合理解釋之財產”的行為,其精神都有融通之處,處罰的實質根據都是獲取巨額財產的非法行為。
(三)推定的正當性依據
對于這種推定型犯罪,學界質疑其公正性,從程序法上講顯示的是有罪推定的理念,實體法上的后果是,寬縱犯罪或者冤枉無辜。??同前注?,錢舫文。但是,“‘以非法所得論’的過程中,采取的是‘事實推定’方法。事實推定,是指根據已知的事實推斷出與之具有某種聯系的另一事實是否存在或是否真實。事實推定與有罪推定不是一回事。有罪推定是封建專制國家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要求被告人自證其罪的一種定罪方法,而我們的事實推定是與重證據重調查研究的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兩者性質完全不同,不能混為一談”。??徐國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證明方法》,《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92年第1期。從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案發事由講,多是由于貪污、受賄等腐敗犯罪所引發,在現有證據難以證明巨額財產是貪污、受賄所得的情況下,以非法所得論。因此,巨額
財產來源不明罪往往發生在細致入微的前期證據調查之后,進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評價視野之后,對于行為人所說的財產來源因線索不具體等原因,司法機關即使無法查實,也應當排除存在來源合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這是《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要求。由此可以看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同樣需要大量的證據調查,最后運用事實推定的方法得出結論,客觀上就降低了冤枉無辜的概率。同時,刑法也為該推定設置了出口,即行為人可以通過說明財產來源的方式推翻推定,這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出錯概率。另外,從經驗和常識的角度去考察,“不能說明”首先是因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與腐敗犯罪刑罰的顯著差異,導致行為人拒不說明,將該罪當成避風港、免死牌。??查慶久:《這條刑律何以尷尬——析反腐敗斗爭中“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處境》,《法制日報》2001年6月3日,第2版。而這里的拒不說明包括兩種情形,一是知道財產明確的來源途徑而不說明,二是概括知道財產的來源途徑而不說明,不管哪種情形,拒絕說明總是基于利弊分析而作出的選擇,基本不會存在冤枉無辜的情形,因為無辜者自然會抓住法律給予的出罪機會。除了上述行為人出于規避重罪而不予說明財產來源的情形外,還可能存在其他僅僅是道德層面上的行為,例如女公職人員受包養而取得的巨額財產。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基于道德層面或者維護家庭完整性的考慮而不予說明,最終被冠之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確無辜。對于這一點,有論者認為,出于功利主義的考慮,也應該設置這樣的罪名,否則將會導致更大的惡。??蘇明月:《制度不足與兜底條款——論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法理沖突、現實選擇與司法應用》,《中國刑事法雜志》2009年第9期。這樣的論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筆者考慮是否可以通過刑法中的“被害人”承諾理論去解釋。這種情況下僅僅是倫理沖突,行為人可以通過澄清事實實現出罪,但是其基于自己內心的標準,選擇了承擔自我概念中較輕的損害,維護了“更大”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行為人并無利益受損,即使我們從客觀的角度認為這是一種法律給予的傷害,那么,這種傷害也因為行為人的承諾而具有了正當性色彩。
對于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在刑法中的確立,再多的溢美之詞也難以抵擋學界洪水般的批評。即使承認,從功利角度考量,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具有必要性,但仍難以逃脫學者出于對傳統刑事法理論的堅持而提出的質疑。實事求是地講,這樣的質疑并非全是求全責備,但是,“風險社會的到來,使得刑法體系面臨著從罪責刑法到安全刑法的轉變。刑法領域現有的研究狀況是內在視角的研究范式的結果,該范式過于注重規范體系中危害與罪過等內在變量的探討,忽視社會性的外在參數對刑事立法與刑法理論的構造性影響”。??同前注?,勞東燕文。面對這樣的轉變,刑事立法應當何去何從,刑事法理論是否要堅守自己的傳統,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四、余論:本罪實行行為厘清后刑罰體系的重構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實行行為應當被界定為非法獲取財物的行為,而不是對作為義務的違反或者持有巨額財產本身,只不過,這種非法獲取財物的行為由法律推定完成。就具體行為方式而言,應當與貪污、受賄罪中的行為方式具有同質性。雖然我國刑法對這些行為以單獨設立犯罪的形式進行處理,但是基于相同行為相同處罰的考慮,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應當與貪污罪、受賄罪的刑罰保持一致,最起碼不應當過分地偏離。之所以出現巨額財產來源不明這樣的現象,并且與貪污、受賄罪如影隨形,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該罪輕微的刑罰制造了自我的繁榮,但是這種繁榮的代價是貪污腐敗犯
罪懲治效果的折損,也是對罪名設立初衷的背離。因此,如何調整其刑罰體系是實行行為厘清后急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對此,學界存在不同的聲音,部分學者主張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加重刑罰,“鑒于這類犯罪社會影響惡劣,為適應反腐敗斗爭的需要,對其加重刑罰是必要的,建議將本罪的最高法定刑由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有期徒刑”。??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全文及說明。這樣的建議在《刑法修正案(七)》中也已經得以體現,但是也有學者提出,加重刑罰并無意義,因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屬于舉證責任倒置的犯罪,不宜設置過高的刑罰。上述兩種聲音都大量存在,至于刑罰體系究竟如何構建,是一個有待專門深入討論的問題,但是筆者基本的思考是,為了做好與貪污、賄賂犯罪的銜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應當提高法定刑,這不僅是對立法初衷的遵守,更是對嚴峻的“選擇性領罪”的司法現狀的合理應對。但是,在死刑問題上應當慎重,因為它畢竟是一種推定型犯罪,即使可以用“被害人承諾”的理論去解釋部分因為倫理沖突而選擇承受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刑罰之痛的個案,但是生命權畢竟不在可以承諾放棄的范圍之內。歸結起來講,從腐敗犯罪懲治體系協調性的角度考慮,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不應該偏離基本犯罪,但也應當適度地張揚個性,因為它終究是一個個性化的存在。
(責任編輯:杜小麗)
D F636
A
1005-9512(2014)07-0032-10
李本燦,南京大學與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外國與國際刑法研究所聯合培養博士生。
*本文系孫國祥教授主持的司法部課題“預防和懲治腐敗的刑事法律研究”(項目編號:12SFB2026)的階段性成果;同時受到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