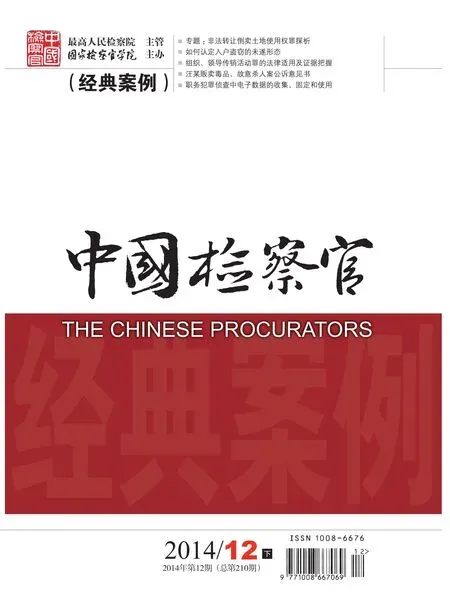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的司法適用
文◎金懿何維
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的司法適用
文◎金懿*何維**
一、基本案情
2014年2月2日晚,犯罪嫌疑人陸某酒后來到其母親程某位于本區周浦鎮安康新村59號501室家中,因向程某討要2萬元錢款未果,而用扳手將廚房灶臺內連接燃氣表的進表管道卸下,導致天然氣泄漏,并同時將門窗關閉,揚言要同歸于盡。后陸某的妹妹陸某華趕來,將程某及陸某之子接出房屋,并電話報警。民警及消防員趕至現場,將整棟樓的燃氣總閥關閉后進入房屋采取通風、檢查等防險措施。此時陸某在空氣中含有高濃度燃氣的情況下點燃香煙,所幸未引起爆炸后果。根據消防單位搶險測爆數據,當時屋內的天然氣濃度含量已遠高于燃氣引爆范圍,足以引起火災、爆炸等嚴重后果。陸某交代,拆卸燃氣管道致使燃氣泄露是為發泄不滿;在現場點燃香煙是煙癮發作為了抽煙,當時并未考慮過可能發生嚴重后果。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犯罪嫌疑人陸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具體理由又有兩種:一種理由認為,《關于辦理盜竊油氣、破壞油氣設備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只適用于以盜竊為目的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的情況,本案行為人并非出于盜竊目的,故無法適用。同時,陸某的行為也不構成其他犯罪。另一種理由是,本案可以適用上述司法解釋,但由于司法解釋并未明確給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量化標準,故無法判斷陸某的行為是否達到犯罪的嚴重程度。
第二種意見認為,犯罪嫌疑人陸某的行為已構成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應對陸某以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追究刑事責任。
第三種意見認為,犯罪嫌疑人陸某的行為已構成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及爆炸罪,應數罪并罰追究刑事責任。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上述第二種處理意見,對該案中的具體問題評析如下:
(一)本案可以適用《關于辦理盜竊油氣、破壞油氣設備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司法解釋可以分為“限定式”和“非限定式”。如,關于賭博犯罪有許多司法解釋,這當中,兩高2010年頒布的《關于辦理網絡賭博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就屬于限定式的司法解釋文件,其中的許多條文內容(如對賭資數額的特殊計算方式)只能適用于網絡賭博犯罪這一特殊場合,不能類推適用于其他類型的賭博犯罪。而兩高2005年頒布的《關于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則屬于非限定式的司法解釋文件,其條文內容可以廣泛適用于各種類型的賭博犯罪。
我們認為,從“立法原意”來看,《解釋》并不屬于限定式司法解釋。該解釋出臺的背景是,實踐中采用破壞性手段盜竊油氣的案件常發常見,而在處理這些案件時,由于既涉及盜竊,又關乎破壞易燃易爆設備,就產生了應該定性為盜竊罪還是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的爭議。從法理上看,這種情況屬于想象競合犯。想象競合犯應根據“一行為一罪”的基本原則應該從一重論處。兩高的司法解釋主要明確了對采用破壞性手段盜竊油氣的案件,在何種情況下按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從一重罪處罰(一般情況下,此類案件按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論處比按盜竊罪論處要重),在何種情況下按照盜竊罪處罰。簡言之,《解釋》只是以現實中的常發情況(即以盜竊為目的實施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的行為)為例對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犯罪進行了解釋,但我們不能據此認為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犯罪僅限于“以盜竊為目的”的情形,因此,該解釋并不屬于限定式的司法解釋。
按照立法權限,兩高的司法解釋只能進一步明確刑法條文的具體含義,而不能進行法律擬制。上述司法解釋中規定可以按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從一重論處的情況,前提是該行為符合破壞易燃易爆罪的構成要件,同時也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解釋》第3條規定:“盜竊油氣或者正在使用的油氣設備,構成犯罪,但未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264條的規定,以盜竊罪定罪處罰。”這也說明了采用破壞性手段盜竊油氣案件按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從一重處罰的前提是這一行為本身已符合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的構成要件,在破壞易燃易爆設備行為尚不構成犯罪的情況下,則不存在依照想象競合犯從一重處罰的問題,只能根據該解釋第3條的規定判斷是否構成盜竊罪。同樣道理,如果行為人不以盜竊為目的破壞易燃易爆設備,但符合《解釋》有關對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構成要件的具體規定的,也可以按《解釋》認定為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而不是不構成犯罪。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陸某雖非出于盜竊目的破壞易燃易爆設備,但其行為仍可適用《解釋》。
(二)本案應按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屬于危險犯。危險犯是指“行為人實施的行為足以造成某種實害結果的發生,但實害結果尚未發生,即構成既遂的犯罪,或者說,是以行為人實施的危害行為造成的危險結果作為犯罪構成條件的犯罪。”[1]因此,本案認定構成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需符合“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構成要件。然而《解釋》并未規定“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具體量化標準。對此有意見認為,因司法解釋未規定具體量化標準,所以不能確定本案的情況是否屬于“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不能對行為人追究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的刑事責任。
司法人員理應嚴格按照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辦理案件,貫徹“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的罪刑法定精神。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司法人員可以“法無具體規定”為由,拒絕適用刑法、司法解釋已有明文規定但尚無具體規定的法律條文。對待法律、司法解釋尚無具體規定的法律條文,司法人員應抱著審慎的態度,綜合全案各種具體情況,謹慎地適用既有法律條文。
本案中,消防單位在現場測得屋內空氣中天然氣濃度數值已遠高于燃氣引爆極限數值范圍,足以引起火災、爆炸等嚴重后果,并出具了正式的書面說明。犯罪嫌疑人陸某拆卸的燃氣管道為燃氣公司統一安裝的進戶管道燃氣裝置的一部分,而非瓶裝液化氣的管道,如果消防員不將居民樓總閥關閉,天然氣將源源不斷地泄漏。案發時,正值農歷正月初三晚上,按照中國百姓的傳統習俗,將在當晚燃放爆竹,燃氣在這一特定時間段泄漏,極易產生嚴重的實害結果。犯罪嫌疑人陸某不僅將燃氣管道拆卸,致使天然氣泄漏,還在消防員、民警采取防險措施時點燃香煙,這一高度危險的行為使得爆炸的危險性大大提高。綜合本案各種具體情況,應當認定犯罪嫌疑人陸某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的行為已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構成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
(三)本案不應以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爆炸罪數罪并罰的方式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刑法》第114條、第115條分別對爆炸罪的危險犯與實害犯作了規定。行為人如故意實施危險行為,足以引發爆炸后果,對公共安全造成危險的,亦可按《刑法》第114條的規定追究行為人爆炸罪的刑事責任。有意見認為,陸某當晚在破壞燃氣管道致使燃氣泄漏的危險產生后,已構成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既遂。其在消防員、民警趕到現場防險時,在高燃氣濃度情況下點燃香煙這一行為,足以引發爆炸后果并危害公共安全,此行為又觸犯了《刑法》第114條之規定構成爆炸罪(危險犯)。因此應對犯罪嫌疑人陸某以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爆炸罪(危險犯)兩罪并罰。
筆者不同意上述意見。一方面,從證據角度來看,認定陸某涉嫌爆炸罪的主觀故意方面的證據不充分,而只能認定其點煙出于過失。過失實施爆炸行為沒有造成實害后果的,不構成犯罪。綜合文中所述,陸某點煙引發危險的主觀方面應認定為過失,雖然我國刑法規定,醉酒后實施犯罪的應負刑事責任,但這并不表示行為人醉酒后實施的所有行為均可推定其對行為所造成的實害結果或引發的危險狀態在主觀上表現為故意,行為人醉酒后實施某些危害行為主觀上也不排除可能出于過失的情況。如,醉酒駕駛造成危害后果被定性為交通肇事罪的,就表明行為人主觀上屬于過失。另一方面,從法理角度來看,即使推定陸某點煙的行為出于故意,那么其意圖實施爆炸的行為與破壞易燃易爆設備致使燃氣泄漏的行為也符合目的行為與手段行為牽連的罪數形態,應認定為牽連犯從一重罪論處,而不應數罪并罰。
注釋:
[1]鮮鐵可:《新刑法與危險犯理論研究》,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5期,轉引自楊興培:《危險犯質疑》,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3期。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檢察院[200135]
**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檢察院[36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