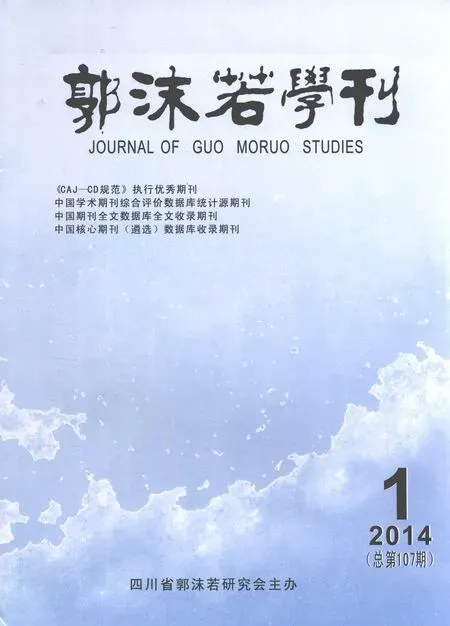答中央電視臺主持人問
2014-01-31 02:53:46白巖松
郭沫若學刊
2014年1期
關鍵詞:小說
白巖松 王 火 金 弓
(根據中央電視臺《東方之子》節目整理而成)
地點:四川成都王火家中
時間:1998年2月5日
白巖松:茅盾文學獎是我國長篇小說創作的最高獎項。1997年底,第四屆茅盾文學獎揭曉,四川作家王火以他的《戰爭和人》三部曲獲此殊榮。這位50年代就以《赤膽忠心——紅色游擊隊長節振國的故事》一書成名的作家,傾其半生精力從事《戰爭和人》的創作。十年動亂期間,他的近百萬字的書稿被焚燒盡凈。直到80年代,他才有機會重新開始寫作。憑著對原書稿的記憶,在左眼意外受傷失明后,他硬是靠著右眼和頑強的毅力完成了小說的第一部到第三部,最終寫出了這部被評論家稱為“譜寫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史詩”的優秀作品。

白巖松:六十年前的這場戰爭,在您個人生命中留下的是什么樣的記憶?
王火:這是很奇怪的事,近一二十年的事情,印象很快淡薄了,抗戰八年印象卻仍非常深刻。這可能跟年齡有關系,因那時正是我生長發育的時期。
白巖松:初一到大學三年級的階段?
王火:是的,聽到許多事,親身經歷了那個時代,我就感到不能不寫了,因為抗日戰爭對我來說是一段永遠也無法磨滅的經歷。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受到列強的侵略,老是打敗仗。只有抗日戰爭中國取勝了,而且是全民動員起來了。那個時候解放區動員得好,國統區動員得差,而淪陷區的抗日情緒愛國精神十分高漲……這都令我十分難忘。
白巖松:我想,您這本書雖涉及戰爭,但筆的著墨處還是在寫人。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英語文摘(2021年2期)2021-07-22 07:57:06
文苑(2020年11期)2020-11-19 11:45:11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作品(2017年4期)2017-05-17 01:14:32
中學語文(2015年18期)2015-03-01 03:51:29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
小說月刊(2014年8期)2014-04-19 02: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