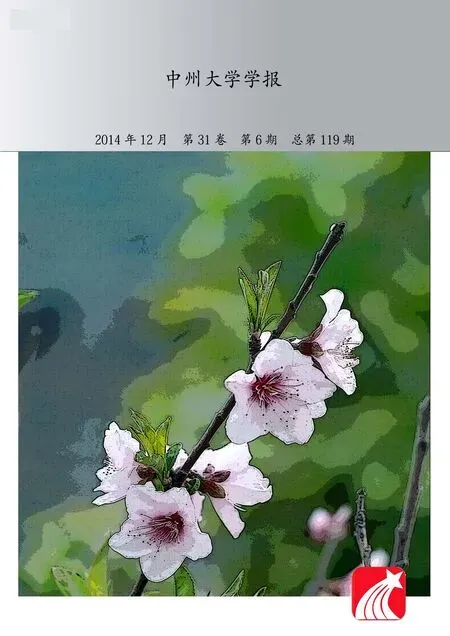我國古代刑法中的自首制度初探
付傳軍
(河南警察學院 學報編輯部,鄭州 450046)
一、引言
刑法中的自首制度,一向被認為是中華法系所特有的刑法制度。[1]323其理論基礎是“過則勿憚改”。正如《唐律疏議》中對自首律條的疏文所說:“過而不改,斯成過矣。今能改過,來首其罪,皆合得原。”
根據現存刑法史料,自首規定最早出現在《尚書·洪范》中:“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守即“首”,自首之意。整句話的意思是:凡是處罰庶民的犯罪,對預謀犯罪的,實施犯罪行為的,犯罪后自首的,要區別這些情節,分別給予不同的處罰。
秦時稱自首為“自出”。《秦簡·法律答問》載:“把其段(假)以亡,得及自出,當為盜不當?自出,以亡論。其得,坐贓為盜……”即攜帶借用的官有物品逃亡的,如果是自首的,以逃亡罪論處;被抓捕的,則計贓按盜竊論罪。[2]277由此可知,自首者可以減輕處罰。
漢時稱自首為“先自告”,漢代首先在法律上規定“先自告,除其罪”的原則。據《漢書·衡山王傳》記載,漢武帝元狩元年衡山王太子劉孝就因向官府自首自己以及其父諸人的謀反活動而得以免除其參與謀反的罪責。
自首制度經歷代相因,至唐朝時已規定相當完備,在明清兩朝又有發展。以下以《唐律》規定為基礎,兼顧明清兩代的發展,從幾個不同的方面簡要探討一下我國古代刑法中自首制度的具體規定。
二、自首的主體
自首的主體即依法律規定應由誰去自首才是法律所認可的自首。唐律將罪犯親自首告稱為“身自首”。除此之外,唐律又規定了“遣人代首”和有關容隱關系的親屬自行代為自首兩種形式,“即遣人代首若于法得相容隱者為首及相告言者,亦同身自首法”。法律同時又規定,罪犯遣人代首,或知道親屬出首及告發,在官府追傳時本人不歸案的,不得適用自首原罪之法。第37條的疏文解釋說:“犯罪之人,聞有代首,為首,及得相容隱告言,于法雖復合原,追身不赴,不得免罪。”在這種情況下,代為出首及告發的親屬仍以自首免罪處理,“首告之人及余應緣坐者,仍以首法”[3]150。
《唐律》對“遣人代首”情形的規定比較簡單,對所遣之人也無特別規定。但《唐律》“于法得相容隱及相告言”的規定則較為復雜,下面進行較為詳細的分析。
根據儒家“父子相隱”的思想,唐律規定了“同居相隱不為罪”的原則。根據《唐律·名例》總第46條:“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凡同居大功親之間及部曲奴婢對主人適用容隱制度,在這個范圍內的人員出首或者相告發的,罪犯以自首免罪,“亦同身自首法”。但其中依具體情況又有所不同,若是有相隱關系的親屬出首告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出首告發主人,倘若首告之罪不是謀反、大逆、謀叛以上之罪,出首告發之子女、孫子女或部曲奴婢要處以“絞”刑,而被出首告發之人以自首論處。如《唐律·斗訟》總第345條規定:“告祖父母、父母者,處絞;謀反、大逆、謀叛以上之罪,雖父祖聽捕告;告余罪者,父祖得同首例。”據此條可知即使是卑幼首告尊長,若首告之罪為謀反、大逆、謀叛之罪,則首告者無罪,被首告者要“聽捕告”。本條疏文又進一步解釋說:“謂謀反、大逆、謀叛以上,皆為不臣,故子孫告亦無罪,緣坐同首法,故雖父祖聽捕告。”如果主人犯謀反、大逆、謀叛之罪,奴婢也可控告而無罪。因反、逆、叛及其他罪緣坐的親屬及犯反、逆、叛等罪中不緣坐的期親,起來捕捉、告發罪犯,出首告發人皆以自首論處,不再受緣坐。《唐律·名例》總第37條注文:“緣坐之罪及謀叛以上本服親,雖捕告,俱同自首例。”
關于自首主體的規定,明律并無特別變動,清律沿用明律規定,但在實際應用中以條例的形式做了進一步的發展。乾隆五年纂定的條例:“小功、緦麻親首告得減三等;無服之親減一等。其謀反、逆未行,如親屬首告或捕送到官者,正犯俱同自首律,免罪,若已行者,正犯不免,其余緣坐人亦同自首律免罪。”在清律“犯罪自首”條中“得相容隱者”作為自首主體是不包括小功、緦麻及無服親在內的,條例的這個補充擴大了自首主體的范圍,有利于充分發揮自首制度的作用;同時根據本條例的補充,對于謀反、逆等嚴重的犯罪,于律得相容隱的親屬首告正犯,對正犯以謀反、逆“行與未行”來確定自首的成立與否,而對應緣坐的出首人來說,不管反、逆是否已行,俱按自首免罪,這有利于促使緣坐的人首告反、逆等嚴重的犯罪,維護封建專制統治。
對“于法得相容隱”的人,如同居之父、兄、伯、叔與弟,明知為匿或分受贓者,自身亦構成犯罪,若據實出首,如何處理?雍正七年定例規定:“強盜同居之父、兄、伯、叔明知為匿或分受贓物者,其據實出首,均準免罪,本犯亦得照律減免發落。”出首不僅對自身有效,而且效力還及于本犯。此例補充了律條及律注之不足,有利于鼓勵自身亦構成犯罪的人據實出首其同居親屬強盜罪行。
三、自首的時間與對象
自首的時間即法律對自首在時間上的要求。《唐律·名例》總第37條規定:“諸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本條的疏文解釋說:“犯罪已發,雖首不原。”可見唐律對自首的時間要求是“犯罪未發”。而所謂案件“未發”唐代司法實踐中有兩種基本情況:其一,是指官方未發現犯罪并進行追究。如果官方自行發現犯罪并進行追究,唐律中稱為“案問欲舉”,屬于已發的情況。其二,是指未有人去官府指控告發犯罪。有人指控告發也屬于“已發”,疏文解釋說:“若有文牒言告,官司判令三審,牒雖未入曹局,即是其事已彰,雖欲自新,不得成首。”所以其界線是官府受理告發,即使狀子文書未正式送達有關部門,也屬“已發”。[3]147應注意的是,這里犯罪未發的核心是指犯罪事實是由誰實施而言的,若是僅知受害事實而不知犯罪人是誰,并不能認為是犯罪已發。[1]324
自首是在犯罪未被發覺的情況下而先自首告所犯罪行,那么知人欲告而自首、亡叛而自首以及亡叛后歸還本所應如何處置?這里的“亡叛”疏文上說是“逃亡之人”或“叛已上道者”即叛者已經出走上路的情況。依《唐律·名例》總第37條規定:“其知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減罪二等處之。即亡叛者雖不自首,能歸還本所者亦同。”這對防止犯罪人知人欲告而逃亡及分化瓦解亡叛的犯罪人具有積極意義。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逃亡有兩種情況:一是單純的逃亡罪;二是犯罪之后因事發而逃亡。第二種情況下就同時存在本罪與逃亡罪,自首對本犯之罪不起作用,僅逃亡之罪可因自首而減二等處罰。
在自首的時間規定上,明清律沿襲唐律的規定,而清律又以條例的形式增加了“聞拿投首”的情形。乾隆三十八年所定條例規定:“凡聞拿投首之盜犯除律不準首及強盜自首有正文外,其余一切罪犯俱于本罪上減一等科斷。”聞拿投首是指犯罪已被官府發覺,并派人捕捉緝拿。因聞拿投首比之聞拿不投首是有差別的,故條例增此一條,規定減輕處罰,以體現區別情節追究刑事責任的原則。
自首的對象是指依法律規定自首應向誰進行。唐律規定接受自首的官府是所在地非軍事的官府。《唐律·斗訟》總第353條規定:“諸犯罪欲陳首者,皆經所在官司申牒,軍府之官不得輒受。其謀叛以上及盜者,聽受,隨送隨近官司。”疏文解釋說:“但非官府,此外曹局,并是所在官司。”
此外,作為變通規定,《唐律·名例》總第39條規定:“諸盜詐取人財物而于財主首露者,與經官司自首同。”即犯盜罪及詐騙罪的罪犯到財物主人那里去歸還財物自首,同到官府自首一樣有效,體現出一定的靈活性。對于官吏因事接受他人財物“悔過還主”,唐律則有不同規定:“其于余贓應坐之屬,悔過還主者,聽減本罪三等坐之。即財主應坐者,減罪亦準此。”即對本人只能減輕處罰,財主亦不能免罪,但自首效力及于財主,同樣可以減罪,這較之于后來明律在這一問題的規定“受人枉法不枉法贓,悔過回付還主者與經官司同”更科學一些。明律律注指出:“枉法不枉法贓,征入官……”既屬應征入官,就不應還于主,而且依照律例,出錢求人枉法,與受同科,財主亦有罪名,故于事主處首服不應與經官司同,“悔過回付還主”,更不應按自首免罪,此應屬立法技術上的失誤。
四、自首的內容
犯人自首后根據自首的內容不同,法律規定給予不同的對待。《唐律·名例》總第37條規定:“其輕罪雖發,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即因問所劾之事而別言余罪者亦如之。”根據此規定,在犯有數罪的情況下,如輕罪已發而重罪未發而自首重罪的,則重罪可被認為是自首而免罪。疏文舉例解釋說,假如一人輕罪盜牛被發現,又自首了未被發現的私鑄錢幣的重罪,那么私鑄錢幣免罪,而盜牛照規定處罰。同樣在犯有數罪的情況下,在推問已發覺的罪行時,又自首了其他未發現的犯罪的,則未發現的罪,按照自首免罪。
《唐律·名例》總第37條規定:“自首不實及不盡者,以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者,聽減一等。”律注稱“自首贓數不盡者,止計不盡之數科之”。所謂不實,是指所犯之罪為重罪,而以輕罪自首;所謂不盡,是指犯贓十匹,自首犯贓五匹。“以不實不盡之罪罪之”,即原犯重罪而以輕罪自首者,以重罪應處的刑罰減輕罪應處的刑罰,以所得的余刑處罪之。若以不實不盡之罪罪之仍要處死刑的,可寬大減死一等處理。疏文解釋其理由說:“為其自有悔心,罪狀因首而發,故至死聽減一等。”
明律中對“因問所劾之事而別言余事”的規定進一步設律注解釋說:“謂因犯私鹽事發,被問,不加考證,又自別言曾盜牛,又曾詐欺人財物,止種私鹽之罪,余罪俱得免之類。”即別言余罪必須是在未加考證,即拷訊的情況下自動陳述余罪,所陳述的余罪才能按自首免罪。如果是在對其所劾之罪進行拷訊的情況下別言余罪,則不能免其陳述之罪。這使對“別言余事”的規定在立法技術上更加完善。
五、自首的特別情況
無論是唐律、明律,還是清律及條例都有關于自首的特別情況的規定,從而使法律關于自首的規定更加細致,自首制度適用的范圍進一步擴大。
《唐律·名例》總第38條規定:“諸犯罪共亡,輕罪能捕重罪首,及輕重等獲半數以上首者,皆除其罪。即因罪人以致罪,而罪人自死者,聽減本罪二等;若罪人自首及遇恩原減者,亦準罪人原減法;其應加杖及贖者,各以杖贖例。”罪人共逃亡,是指罪人在犯罪后結伴逃亡,對社會威脅很大,故本條規定只要輕罪能夠捕獲重罪,輕重罪相等的能獲半數以上而去自首的,皆可“除其罪”,借以對犯罪人實行分化瓦解。對“輕罪能捕重罪者”的律注指出:“重而應死,殺而首者,亦同。”重罪人犯應處死重罪的,輕罪人殺之而自首的,也免除其刑。對以上兩種情形,律注又指出“常赦所不原者,依常法”,即如果所犯為常赦所不原的犯罪,則依常法處理,不適用本條規定。對因被株連而入罪的人,若本罪人死亡,則被株連人將減本罪二等;若本罪人自首及遇恩赦減刑的,被株連人適用本罪人原減法。
明律對于“犯罪共逃亡”的規定除沿用唐律規定外,又在“其輕罪囚能捕重罪囚,輕重罪相等但獲一半以上首告者,皆免其罪”條加律注規定:“謂同犯罪事發,或各犯罪事發而共逃者,若流罪囚能捕死罪囚,徒罪囚能捕流罪囚首告。又如五人共犯罪在逃,內一人能捕三人首告之類,皆得免罪。若損傷人及奸者,仍依常法。”規定傷人及奸罪不適用本條自首免罪規定,而唐律僅規定“常赦所不原者,依常法”,由此可見,明律對適用“犯罪共逃亡”自首規定的條件要求更嚴。
明律在“犯罪自首”條規定:“強、竊盜若能捕獲同伴經官司首者,亦各免其罪,又依常人一體給賞。”本條規定的情況同上述“犯罪共逃亡”條規定的情況差別在于,在本條中罪人是在所犯強、竊盜罪未被發前即捕同伴經官司首,這同“共逃亡”后再行投首性質是不同的,所以規定在“犯罪自首”條,不僅免其罪,而且與常人一體給賞。這是自首又有立功表現受賞政策的體現。強、竊盜罪是封建社會常見而又被視為極為嚴重的犯罪,在“犯罪自首”條增此規定正是加強對強、竊盜犯罪作斗爭的表現。
《唐律·名例》還規定了過失犯罪自首的條文。在總第41條規定:“諸公事失錯,自覺舉者,原其罪;應連坐者,一人自覺舉,余人亦原之。其斷罪失錯,已行決者,不用此律。其官文出稽程,應連坐者,一人自覺舉,余人亦原之,主典不免;若主典自舉,并減二等。”公事失錯大致相當于現代的瀆職犯罪,屬于過失犯罪。這類犯罪“自覺舉”成立自首。覺察舉發后,能有效地阻止危害結果的發生,因此,一人自覺舉,效力及于連坐之人。“公事失錯”在沒有發生危害結果時,自覺舉可原其罪,但若危害結果已經發生則不能適用本條,即官員斷罪出現失錯后,按判決執行刑罪,若笞杖已決,徒流已配,自覺舉后不能糾正,則“官司雖自覺舉,不在免例”,仍以過失入人罪論處。延誤官文書傳送的官文書稽程罪也是由過失構成,自覺舉能夠防止或減少危害的結果,故應負連坐責任的有一人自覺舉的,皆原其罪。專司官文書收發責任的官員“主典”則不能免除處罪。主典自覺舉的,主典減二等處刑。主典自覺舉的效力及于連坐的人,所以律條規定余人亦減二等。
明清律多沿用唐律規定,但清律在“犯罪自首”條增加“叛而自首者減二等坐之”,意思是“叛去本國”而能自首其罪行,減謀叛罪二等處刑。這是針對清初尖銳的民族矛盾而實行的以民族軟化為目的的刑事政策。清順治十八年條例規定:“被擄從賊,不忘故主,乘間歸來者俱著免罪。”但在后來清統治者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并未貫徹這一刑事政策。
關于監斬、絞重罪囚犯及遣軍、徒、流罪人因變逸出而后投首的情況,清嘉慶五年改定的條例規定:“在監斬、絞重囚及遣軍、流、徒人犯,如有因變逸出自行投與首者,除謀反、叛、逆者之犯,照原擬定罪,不準自首外,余照原犯罪名減一等發落。”“事發在逃”不在自首之律,但“因變逸出”并非有意脫逃,與“事發在逃”是不同的,故除了謀反、逆、叛之犯不準自首外,余犯自首減一等發落,以示區別對待。
如果人犯在配及中途脫逃的,后又自首或者其父、兄稟首拿獲的,如何處理呢?清嘉慶六年改定的條例規定:“由死罪減為發遣的盜犯并以藥迷人的竊盜在配及中途脫逃被獲應即行正法者,如有畏罪投回并該犯父兄赴官稟首拿獲,均準其從寬免死,仍發原配地方。若準免死一次之后復敢脫逃,雖自行投回及父兄再為首告,均不寬免。”
誘拐婦人子女脫離家庭的犯罪是封建社會常見而又多發的犯罪,對于此類犯罪的自首,根據清嘉慶三十五年刑部奏所定的條例規定,要根據犯罪的結果來確定是否成立自首。若被拐婦人子女被罪犯自為妻妾,或者典賣于人已被奸污的,則不準自首;若尚未被奸污或典賣于人,悔過自首后使之同家人團聚的,則減二等發落;如果被拐之人已經典賣于人,罪人自首之時尚無下落,則按律擬罪,監禁從到官司自首之日起三年限內仍無下落的,或者在限內拿獲而已被奸污的,即按原擬罪名發落。原處絞監候的,入于秋審辦理,擬流罪的,即確定向發配地發配。如果在限內拿獲未被奸污的,則在原罪名上減一等發落。[1]338
此外,針對鴉片犯罪,清道光十九年所定條例規定:“凡鴉片案內人犯,如有事未發而自首及聞拿自首的,各按律例分別減罪、免罪。首后復犯加一等治罪,不準再首。”但隨著鴉片戰爭的失敗,這一規定成為一紙空文。
六、不適用自首的情況
《唐律·名例》總第37條規定:“其于人損傷,于物不可備償,即事發逃之,若越度關及奸,并私習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例。”此規定亦為后世刑律所沿用并加以發展。歸納起來,我國古代刑律中規定不適用自首的犯罪情況有:
(1)“于人損傷”即傷害罪不適用自首免罪。傷害罪自己出首不減不免,因盜而傷人自首,盜罪可免,傷害罪仍不免。注文說:“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疏文說:“假有因盜故殺傷人,或過失殺傷財主而自首,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若過失殺傷,仍從過失本法。”
(2)“于物不可備償”即標的物為“不可償”之物不適用自首。侵犯別人不可償還而事后又無法追回和復原的物的犯罪,不適用自首免罪的規定。但法律同時還規定,罪犯能帶原物自投官府的,是自首,可免罪。注文說:“本物見在首者,聽從免法。”疏文說,所謂不可償之物是指寶印、符節、制書、官文書、甲弩、旌旗、禁兵器之類私家既不合有之物。
(3)非法度關罪中“私度”“越度”罪不適用自首免罪。
(4)侵犯良人的奸罪不適用自首免罪。唐律律注規定:“奸,謂良人。”疏文說:“若奸良人者,自首不原。”未言奸賤奴,可知屬于侵犯賤民的犯罪可自首。
(5)私習天文罪不適用自首免罪。私習天文之所以作為自首不原的犯罪,是因為古人認為天文星相之事涉于社稷禍福及帝王氣數,習學此等技藝,必須嚴加控制,私自學習,即為大罪。但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和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清律中即已刪去此規定。
另外,在清朝乾隆年間,為杜絕強、竊盜犯與捕役勾結,串通舞弊,欺罔官司的弊端,乾隆五年改定的條例規定:“不論強、竊盜犯有捕役帶同自首者,除本犯不準寬減外,仍將捕役嚴行審究,倘有教令及賄求故捏情弊,照捕役照受財故縱律治罪。”但這種不區分情況,捕役帶同自首,概不寬減,是不符合律設“犯罪自首條”的本意的。[3]151
參考文獻:
[1]寧漢林,魏克家.中國刑法簡史[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
[2]陳鵬生.中國古代刑法三百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錢大群.唐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