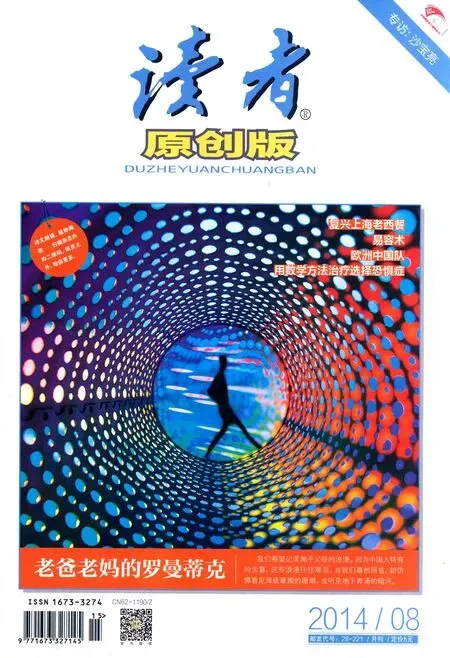我的朋友那可
文 _ 淡 豹
我的朋友那可
文 _ 淡 豹

那可是我的朋友,一名在紐約工作、年近30歲的單身男青年。我在芝加哥讀文科博士,那可在紐約上班寫程序,我們之間毫無交集。能相識,緣于他在網上貼出的一系列介于日記和小說之間的文章,我讀到后,覺得他寫得很好,有一次去紐約就找到了他。
那可文章的特點是:動不動就悲痛欲絕。他擅長淋漓盡致地描寫自己的各種負面情緒,讓讀者感到:“哦,原來有人比我心情更不好!”讀完就開心了。那可的文章雖然情節各異,故事發生地不同,但全是以第一人稱敘事。
文章里呈現出的那可是這樣一個人:喜歡跑步,有時會參加馬拉松;喜歡旅游,經常去世界各地晃蕩,還是一副懷揣萬金卻很低調的架勢——興許他去哪兒都吃三明治,可至少買得起環游世界的機票。但無論他寫紐約、東京,還是伊斯坦布爾,是寫找工作、長跑、養狗,還是參加朋友聚會,都明里暗里地透出一種“找不到女朋友好苦惱”的憂郁。
那可長期找不到女朋友這事,客觀上讓人有點納悶。目前紐約市年齡在20歲到34歲的居民中,53%是女性。若把巨大的紐約市分解成一個個小的單位來看的話,數字就驚人了:在曼哈頓區及年輕人聚居的布魯克林區,明顯女多男少,而在曼哈頓中央公園旁的上東區,年輕單身的女性數量則比男性多出幾乎整整一倍。
要是單說年輕華人男女,那紐約簡直是中國男生的福地。坊間流傳的說法是,美國西海岸的中國男生最難找女朋友,因為這里未婚男青年的比例奇高。有個從清華畢業、在硅谷上班的男生說:“硅谷比國內理工科大學還殘酷。”而紐約的情況恰恰相反:讀書的、做藝術品經營的、在銀行和律師事務所上班的、拍獨立電影的……處處是有吸引力的單身中國女孩。總之,身在紐約應該特別容易找到女朋友才對。
但那可就是找不到女朋友。我分析出的原因是:太丑。
第一次與那可見面是在10月,這個時節紐約天氣很好,葉子不急于入秋,仍綠得飽滿,愜意地與金色的陽光調情,中央公園湖面清幽,有把人吸進去的魅力。
那可身高1.9米有余,我頭回見到他時,覺得他確實很高,在小樹、旋轉門、街上行人這些客觀參照物的映襯下,那可明顯高出一大截,但單看他卻又并不顯得高。
按說初次見面應該多聊天,但我心中念著“為什么實際很高的人看起來不高”這個《十萬個為什么》未能收錄的問題,既無心聊天,也顧不上欣賞紐約的秋色。跟在那可身后走了一會兒,我細致觀察,光速思考,終于得出了結論:此人頭太大。
于是,剛認識他7分鐘的我直言道:“那可,你頭太大了。”
他一怔,旋即聊起了其他話題。我既已解決了心中的大疑問,便開始心滿意足地聽他談公園歷史、坂本龍一、金融業前景等有格調的問題。直到后來我們坐下,我再次觀察分析,又忍不住說:“那可,我發現你肩膀窄,可能是這個原因讓你的頭顯得格外大。”這次他充耳不聞。
通過這件事我發現,那可這人寬容、脾氣好。這個優點一方面讓人更為其找不到女朋友而悲傷,另一方面也助長了我在關心他的個人問題時不斷揭其短的惡習。和那可熟了以后,我和他談了我對他找不到女朋友這一困境的想法。
我說:“那可,我覺得是因為你太丑。”那可說:“但我也不是最丑的。你看某某和某某,比我還丑。”我說:“真有自信,幸虧你個子高。”那可說:“對吧,我也覺得女孩應該喜歡個兒高的,這是個優勢。”我說:“不,是一般人看不清楚你有多丑。”
我還告訴那可,他應該設定一個難以滿足的選女朋友的標準,這樣朋友們就不會覺得他是因為丑而找不到女朋友,而會認為問題在于他定的標準太苛刻。
說實話,我一直在自我反省,覺得自己欺負那可有點過分。反省帶來的罪惡感讓我決定以后再也不打擊那可了,我要認真幫他物色女友。
今年5月,那可從莫斯科旅行回來告訴我,在紅場的長凳上,有一個叫尤莉婭的俄羅斯女生搭訕他,他感到“很長自信”。我心頭一喜,問他有沒有約人家喝酒——我不了解俄羅斯,但在美國,約女孩子去酒吧喝一杯,是表達好感的方法和約會的必要步驟。
那可說:“尤莉婭主動說我們一起喝一杯吧。”我追問:“太好了!后來你們去了什么地方?有沒有帶她回酒店?尤莉婭漂亮嗎?”那可娓娓道來:“她說喝一杯,我說好,然后尤莉婭帶著我走到紅場旁,她買了一瓶雪碧,給我買了一瓶可樂。原來‘一起喝一杯’就是喝這個!”
后來,尤莉婭喝完雪碧就回家了。我失望地問那可為什么不約尤莉婭去酒吧,他告訴我兩個原因:第一,他隱瞞了旁邊還有一個新加坡男人,一直是他們仨一起聊天的事實。第二,“關鍵是我太困了,所以要回酒店睡覺了。”
我從哀其不幸,變成了怒其不爭。“困了就告別主動搭訕的女孩子,你這樣還能找到女朋友嗎?”我責備那可。但他仍舊沾沾自喜:“主要是尤莉婭太差勁了,光喝雪碧,也沒有主動找我去酒吧。但是她夸我英語講得好,我覺得自己像內布拉斯加州土生土長的!”
在有關英語的得意中獨自回到酒店,旋即睡倒在床上的人,找不到女朋友,恐怕是老天安排的命運吧。那可的樂觀主義像伏爾泰的小說《老實人》中的主人公“老實人”一樣——“老實人”堅信自己身處“有萬千可能的世界中最美好的地方”,也相信“結局永遠會是美好的”。他浪游歐洲,看到無數人陷于窮途末路,戰爭鼠疫、饑餓災荒席卷大地,可他仍然一味向往著遍街黃金、地上鋪滿鉆石的“黃金國”。最終,“老實人”在現實的不斷打擊下,放棄了樂觀主義,意識到并無注定的幸福,人還是要靠每日的勞動,通過“種自己的田”獲得微小的和諧與幸福。也不知道我長期處于求偶狀態但懶于行動的朋友那可,什么時候才能像“老實人”一樣頓悟,真正開始求偶呢?
圖/元熙
淡豹,人類學博士生,以琢磨人為本行,現居美國廣闊的中西部大草原中心的“風城”。她惦念家鄉的親人和食物,為美式脫口秀哈哈大笑,在學院中做知識的信徒,貼近歷史,觀察世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