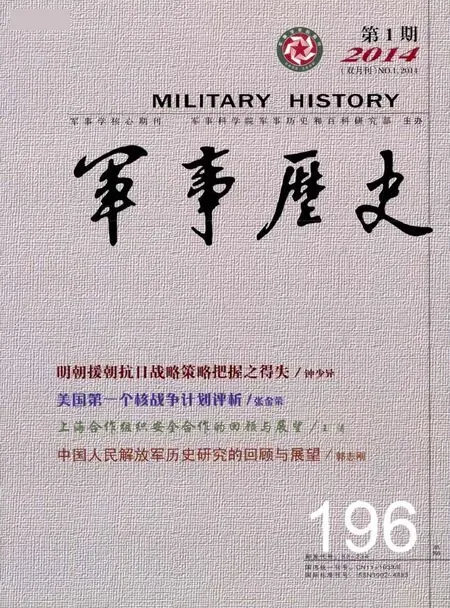試析吳起“勵士”思想
□ 楊 斐 李 瑩
吳起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他戎馬一生,“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其軍事著作《吳子》在北宋時被收入官修武學教材《武經七書》,影響深遠。所謂“勵士”就是激勵士氣,培育戰斗精神。勵士思想是吳起軍事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綜合《吳子》全書和作者的軍事實踐來看,其勵士思想包含勵之以義、勵之以譽、勵之以利及勵之以和等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勵之以義
“勵之以義”的思想遠古先民早有踐行,并非吳起首創。《尚書…湯誓》載,商湯伐桀時,在亳都誓師,揭露夏桀的暴虐罪惡;《尚書…泰誓》載,武王伐紂時,亦曾在孟津誓師,揭露商紂無道,申明討伐的正義性。此二例被后世視為以“義”勝“不義”的典范。吳起“勵之以義”的主要內涵就是以戰爭的正義性鼓舞軍心,激勵士氣,培育軍隊戰斗精神。
在吳起看來,正義戰爭就是禁除暴政、挽救危亡的戰爭,所謂“禁暴救亂曰義”。中國先人很早就注重區分戰爭性質,如《周易…師》認為:“師貞,丈人,吉,無咎”,明確提出堅持戰爭的正義性。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墨家等也都重視區分戰爭性質。儒家則從人性與戰爭沖突的角度,闡述他們的“非戰”立場,認為戰爭是天下無道的表現,同時又肯定救民于水火,為實施仁政開辟道路的“義戰”,并主張在現實中推行“義戰”。吳起曾師事儒家學者曾子,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吳起認為“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這兩戰都是“舉順天人”的正義之戰。
吳起所處的時代,是以封建兼并戰爭為主題的時代,“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真正“舉順天人”的正義戰爭幾不可見。在這種情況下,吳起并沒有被理想主義色彩和倫理道德意義濃厚的“義”所束縛,過分糾纏于“義”與“不義”之間,指出“義”是用來建立功業的,所謂“義者,所以行事立功”。從吳起豐富的軍事實踐來看,無論是率魏軍與秦國爭奪河西的一系列戰爭,還是率楚軍“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都難與“禁暴救亂”掛上鉤,而維護和拓展魏國、楚國的國家利益才是這些軍事行動的根本目的。可見,在吳起思想中,正義戰爭的內涵并非僅限于“禁暴救亂”,為國家利益而戰也屬正義之舉。這與《孫子…地形篇》中所主張的將帥指揮作戰不能求名避罪,而應將“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作為決策依據,是有暗合之處的。
當然,“勵之以義”僅靠宣傳戰爭的正義性是不夠的,還要有其他手段。吳起認為,首先要使“民安其田宅”。百姓平時能夠安居樂業,一旦有事,應征入伍之后,才能為保衛家園而奮勇作戰。其次要“內修文德,外治武備”。國家強盛,政治清明,武備強大,軍民戰時才能與國君將帥同心同德,才能軍心穩固,士氣高漲。在做好這兩點的基礎上,宣傳己方的正義才真實可信,才能為百姓所接受。
二、勵之以譽
榮譽,是支撐軍人直面各種困難和危險,直面鮮血和死亡的重要精神力量。軍人個體的榮譽,始終與國家的興衰、人民的安危、軍隊的榮辱緊密聯系,是國家、人民和軍隊對軍人個體價值的充分肯定。通過精神獎勵,以榮譽激勵三軍將士,是培育軍人戰斗精神的科學方法。
吳起指出,在治軍上僅僅做到“嚴明刑賞”,是不足以克敵制勝的,還必須能夠做到“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而要做到這三點,就要“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吳起還向魏武侯提出了“舉有功而進饗之”的具體操作辦法,即在宮廷設宴,分前、中、后三排席位款待將士。從前至后,參與宴會的將士所享受的酒食器皿等待遇依次降低標準。并對功臣家屬進行賞賜,其標準也依戰功大小而有所差別。每年還要派人對陣亡將士家屬進行慰問和賞賜,表明國君沒有忘記他們。顯然,這些措施給予功臣們的,不僅僅是物質上的獎勵,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榮譽。在莊嚴隆重的筵席之上,將士們的功績得到了國君的肯定。這會使他們有成就感和認同感,在精神上獲得滿足。功績不同,待遇不同,進一步強化了他們對榮譽的不懈追求,使之獲得了繼續為國家、為君王、為人民奮勇作戰的不竭動力。無功人員,自然也會從中獲得精神促動。吳起進諫三年之后,“秦人興師,臨于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奮擊之者以萬數”,顯現了“勵之以譽”的效用。吳起認為,通過上述措施的激勵,加上對禮、義、廉、恥等社會倫理道德的教育灌輸,就能在將士中培育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為核心內容的社會榮辱觀。這種榮辱觀一經形成,就能轉化為戰場上奮勇殺敵的行動自覺,戰斗力自然會得到提升。
三、勵之以利
正義感和榮譽感一經形成,便會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和強烈的滲透性,影響軍人個體的一舉一動,并會與之相伴一生。因此,勵之以義、勵之以譽都能長久地發揮作用。但獻身正義、崇尚榮譽這樣的價值觀卻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必須經過長期、有效的教育引導才行。而在階級對立嚴重的古代社會,統治階級在維持和不斷加大對被統治階級的壓迫剝削的同時,卻又要通過培育這樣的價值觀,使被統治階級心甘情愿地為其戰斗,就更加困難了。在此情況下,如何鼓舞軍心士氣呢?就要“勵之以利”,通過利益驅動來培育軍人戰斗精神。勵之以義、勵之以譽穩定、持久、可靠,但收效慢;勵之以利,見效快,作用大,但效用不持久,三者可以相互補充。
需要說明的是,“利”和“譽”在某些情況下是互為表里,不易截然分開的。比如,古代對有功將士常常授以爵位官職,這既是一種精神獎勵,也是一種物質獎勵。因為爵位官職的背后是俸祿和權力,而在中國古代社會權力又往往意味著經濟利益。不能否認歷史上有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不計個人名利得失的兵家戰將,對他們也是敬仰滿懷。但歷代王朝對他們不惜筆墨的大力宣傳,恰恰說明了這種賢能之士的匱乏,更多人效命疆場還是為了搏個一官半職、封妻蔭子。因此,相對于前兩種勵士之法,勵之以利更有其發揮效用的現實基礎。吳起勵之以利思想也證明了這一點。
雖然吳起在其兵法中專設《勵士》一篇,重點探討勵之以譽的問題,但從《吳子》全書及其軍事實踐來看,他更為重視、運用更為嫻熟的卻是勵之以利。如,吳起主張對于精銳的“虎賁之士”,“必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吳起初到西河之時,“南門置表”,以長大夫的官職賞賜搬動桿表的百姓,從而取得了百姓的信任。在 “取秦小亭”的過程中,吳起則用“上田上宅”和“國大夫”的官職為“誘餌”,激勵民眾的參戰熱情。吳起在魏國編練精銳常備軍“武卒”的過程中,也使用了勵之以利的辦法。魏國規定,在應募者當中,“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即免除符合條件的入選者的賦稅,并給予條件便利的良田美宅,以優厚的報酬激勵百姓應募。勵之以利發揮效果,關鍵在于賞罰。賞罰分明正是吳起治軍所依奉的重要原則。吳起指出“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四、勵之以和
《吳子…圖國》篇指出,賢明的君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必須搞好國內、軍內的團結,才能成就大事。“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不和于陳,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從而深刻揭示了內部團結對于取勝戰爭的重要性。“兵貴其和,和則一心”,內部團結必然戰斗精神旺盛,戰斗力自然強大。反之,軍隊內部不團結,必然導致內耗嚴重,離心離德,渙散軟弱,喪失戰斗精神和戰斗力,不僅難以克敵制勝,甚至會不戰自潰。
團結與否是一支軍隊是否具有戰斗精神的重要標志。增進團結,是培育軍隊戰斗精神的重要途徑。對于如何增進團結,吳起要求舉國上下應保持政治思想上的高度一致。吳起不論是在魯國,還是在魏國、楚國,都是盡心盡力地為新興的封建統治者服務,堅持與沒落的奴隸主貴族斗爭。他主張用符合封建統治者利益的“禮”、“義”來教化民眾,也是為了使民眾能夠與封建統治者同心同德、上下一心。“上下一心,乃克有濟”。
古人講軍隊內部的團結,主要指將領與士卒之間的團結。作為軍隊的管理者和指揮者,在促進“和”的過程中,將領有著不可替代的主導作用。對于將領如何團結部屬士卒,吳起的答案是愛兵。一要體恤士卒疾苦。吳起要求將帥必須具備“仁”的道德品質,要能體恤他人疾苦,要有關愛他人之心。吳起為士卒吮疽,既為明證。正如孫子所言:“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二要與士卒同甘苦。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吳起為將,能夠與最下級的士卒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食物,睡覺時不鋪席子,行軍時不騎馬,親自攜帶行裝軍糧,能與士卒分擔勞苦。吳起的例行,反映了樸素的封建社會的官兵平等思想。三要與士卒安危與共。將帥在戰場上與士兵安危與共,甚至身先士卒,就能極大地鼓舞士氣,激勵部下舍生忘死,勇往直前。吳起指出,將帥“與之安,與之危”,則“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他在《論將》篇提出將帥需要具備“五慎”的基本素養,即“理、備、果、戒、約”,其中“果者,臨敵不懷生”,同時還主張將帥應該自“師出之日”起,就下定決心,“有死之榮,無生之辱”。這些都包含著要求將帥與士卒共安危的思想。四要愛與罰相結合。吳起既是愛兵模范,能為士卒吮疽,同時又鐵面無私,立斬不聽號令的士卒于陣前。這說明吳起能正確看待“愛”與“罰”的關系,并能在實踐中運用自如。古人主張的愛兵對加強軍隊內部團結,融洽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培育軍隊戰斗精神,增強軍隊的戰斗力還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