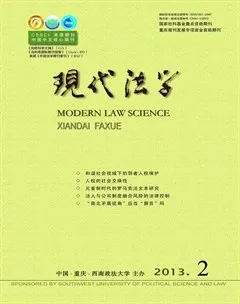元首制時代的羅馬憲法文本研究
摘要:《韋斯巴薌諭令權法》是西方世界保留下來的最古的較完整憲法文本,其發現證明了“羅馬公法不存在或雖存在但無價值論”的錯誤。該法被銘刻在兩塊銅表上,第一塊銅表佚失,得到保留的第二塊銅表包括8個條文外加一個制裁,它授予韋斯巴薌皇帝外交權、元老院會議主持權、召開元老院會議通過法律權、官吏推薦權、城界外推權、自由裁量權、免受一定法律約束權等權力,還包括溯及力條款和免責規定。該法確定了元首制時代皇帝與元老院的權力分配關系,是長期存在的王權法的一個例證。盡管該法表現了皇權擴張的趨勢,但仍維持了皇帝在法律之下的西方憲政傳統。
關鍵詞:《韋斯巴薌諭令權法》;王權法;憲政;元老院
中圖分類號:DF04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3.02.06
一、該法的發現過程及其對于羅馬公法研究的意義
1347年,愛好收藏古董的公證人科拉·迪·李恩佐(Cola di Rienzo,1313—1354年)在羅馬的圣喬萬尼拉特蘭諾大教堂一個祭壇上發現了被龕在墻上的刻有《韋斯巴薌諭令權法》(Lex de ImperioVespasiani)的銅表,它長164厘米,寬113厘米,厚4.5厘米。同年5月,他發起了一場革命,短暫地建立了羅馬共和國,自任為保民官,力圖恢復古羅馬共和國的榮光并統一當時破碎的意大利。李恩佐用他收藏的記載了一部羅馬憲法的銅表作為向其同胞做演講的道具,以喚起他們對光榮的過去的驕傲。李恩佐領導的羅馬共和國于1350年終結,他自己于1354年被羅馬的暴民殺害,但他留下了《韋斯巴薌諭令權法》的發現作為其遺產。我們知道,自1070年代起,波倫那大學開始教授羅馬法,形成了羅馬法的復興,但那里教授的主要是羅馬私法。被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優士丁尼《學說匯纂》、《法典》和《法學階梯》的內容也以私法為主。但這并非當時的人們有意排斥羅馬公法研究,而是因為流傳下來的羅馬公法文本很少,人們無研究對象。《韋斯巴薌諭令權法》的發現無疑為羅馬公法研究提供了素材,為刺激未來的羅馬公法研究提供了可能。
李恩佐死后,刻有《韋斯巴薌諭令權法》的銅表又被保存在圣喬萬尼拉特蘭諾大教堂。1576年,根據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的命令,它被移往卡皮托爾山展出,以此把它還給羅馬人民,該銅表如今保存在卡皮托爾山博物館的Fauno廳。由于它是羅馬憲法史上最重要的碑銘證據,引起了學者廣泛的興趣。撇開較古的研究成果不談,這里只說20世紀至今的研究成果。它們有如下列:1902年,美國學者Fred Burton Ranney Hellems發表了《(韋斯巴薌諭令權法):對元首制時期羅馬憲法的一些方面的思考》;1915年,意大利學者L.Cantarelli完成了《(韋斯巴薌諭令權法)》;1936年,英國學者H.Last也寫作了《(韋斯巴薌諭令權法)》;2006年,西班牙學者Xesús Peréz López出版了《羅馬元首之權力:韋斯巴薌諭令權法》一書(El Poder del Princi—pe en Roma.La Lex de Imperio Vespasiano,Tirant loBlanch,Valencia),作者研究了韋斯巴薌的個人經歷作為理解他制定的《韋斯巴薌諭令權法》的背景,然后逐條評注了該法的8個條文和制裁部分;2008年11月20—22日,顯然是為了紀念韋斯巴薌誕生2000周年,意大利學者舉行了《(韋斯巴薌諭令權法)與弗拉維王朝時期的羅馬》國際研討會,會議成果結集為同名的論文集于次年出版,該書包含19篇論文,分別涉及《韋斯巴薌諭令權法》的經歷及其主要內容,尤其聚焦于元首的權力問題,并有論文對佚失的《韋斯巴薌諭令權法》的內容進行了推測。這些成果對于推進元首制時期的羅馬憲法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其他這方面的成果還有不少,這里不再列舉,它們都會出現在本文的注釋中。
但在我國,尚無一篇中文文獻專門研究這一如此重要的羅馬憲法文本。韋斯巴薌是我國學界對Vespasianus的通譯,2012年10月7日,我以“韋斯巴薌”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進行題名檢索,所得結果為零,故得出這一結論。本文力圖填補這一空白。在方法論上,我打算采用文本評注的方法,以此力圖減少主觀性,為讀者提供一個真實的元首制時期的羅馬的憲法文本以及我對它的解釋。當然,為了實現上述目的,首先要把待評注的文本翻譯為中文。所以,本文是翻譯與寫作的混合。
二、該法的文本及其譯文
該法可能頒布于從69年12月22日到70年1月初之間,共8個條文,外加一個制裁,依據李可波諾(Salvatore Riccobono)整理的拉丁文本并參考Johnson.Coleman—Norton&Bourne的英譯本翻譯如下:
第1條:……他可合法地與他希望的當事方訂立條約,如同神君奧古斯都、提貝流斯·優流斯·愷撒·奧古斯都、提貝流斯·克勞丟斯·愷撒·奧古斯都·日耳曼尼庫斯合法做過的。(foedusuecum quibus uolet facere liceat ita,uti licuit diuo Aug(usto),丨 Ti.Iulio Caesari Aug(usto),TiberioqueClaudio Caesari Aug(usto)Germanico)
第2條:他可合法地召集元老院會議并在其中發表或取消演說,通過上述演說或退席作成元老院決議,正如神君奧古斯都、提貝流斯·優流斯·愷撒·奧古斯都、提貝流斯·克勞丟斯·愷撒·奧古斯都·日耳曼尼庫斯合法做過的。(utique ei sena-tum habere,relationem facere,remittere,丨 senatusconsulta per relationem discessionemque facere liceat丨 ita,uti licuit diuo Aug(usto),Ti.Iulio CaesariAug(usto),Ti.Claudio Caesari 丨 Augusto Germani—co)
第3條:在根據他的意志和權威委托、命令在他出席的情況下召開元老院會議時,所有的程序將被維持并遵守,完全如同此等元老院會議是依法召集并舉行的。(utique cum ex uoluntate auctoritateueiussu mandatuue eius 丨 praesenteue eo senatus habe-bitur,omnium rerun ius perinde 丨 habeatur seruetur,ac si e lege senatus edietus esset habereturque)
第4條:尋求長官權力、諭令權或對公物的掌管的人,他推薦于元老院和羅馬人民的,他所推薦的人選以及他已給予支持的人選,應在民會中受到特別考慮。(utique quos magistratum potestatem im-perium curationemue 丨 cuius rei petentes senatui pop—uloque Romano eommendauerit 丨 quibusque suffraga—tionem suam dederit promiserit,eorum 丨 comitis qui—busque extra ordinem ratio habeatur)
第5條:只要他認為是為了國家,他可合法地前推并擴展城界的范圍,如同提貝流斯·克勞丟斯·愷撒·奧古斯都·日耳曼尼庫斯合法做過的。(utique ei fines pomerii proferre promouere,cam exre publica 丨 eensebit esse,liceat ita,uti licuit Ti.Claudio Caesari Aug(usto)丨 Germanico)
第6條:無論何事,只要他認為符合國家的需要,神的和人的威權、公私事務,他都有權利和權力去做并實施之,如同神君奧古斯都、提貝流斯·優流斯,-愷撒·奧古斯都、提貝流斯·克勞丟斯·愷撒·奧古斯都·日耳曼尼庫斯合法做過的。(utique quaecunque ex usa rei publicae maiestatequediuinarum 丨 humanarum publicarum priuatarumquererun esse I censebit.ei agere facere ius potestasquesit,ita uti diuo Aug(usto),Tiberioque Iulio CaesariAug(usto),丨 Tiberioque Claudio Caesari 丨 Aug(us—to)Germanieo fuit)
第7條:無論什么法律或平民會決議,只要有記載神君奧古斯都或提貝流斯·優流斯·愷撒·奧古斯都、提貝流斯·克勞丟斯·愷撒·奧古斯都·日耳曼尼庫斯免受其約束,愷撒·韋斯巴薌皇帝也免受其約束。無論何事,如果神君奧古斯都或提貝流斯·優流斯·愷撒·奧古斯都、提貝流斯·克勞丟斯·愷撒·奧古斯都·日耳曼尼庫斯依據民會制定的法律可以做,則愷撒·韋斯巴薌·奧古斯都皇帝也可合法地做所有這些事情。(utique qui—bus legibus plebeiue seitis senptum fuit,ne diuusAug(ustus),丨 Tiberiusue Iulius Caesar Aug(ustus),Tiberiusque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丨 Germani—cus tenerentur,iis legibus plebisque seitis imp(era—tor)Caesar 丨 Vespasianus solutus sit;quaeque exquaque lege rogatione 丨 diuum Aug(ustum),Tiberi—umue Iulium Caesarem Aug(ustum),Tiberiumue 丨Claudium Caesarem Aug(ustum)Germanicum facereoportuit,丨 ea omnia imp(eratori)Caesari VespasianoAug(usto)facere lieeat)
第8條:在本民決法通過前,愷撒·韋斯巴薌·奧古斯都皇帝做過、簽署過、命令過的任何事情,或任何人依據他的命令或委任做過的任何事情,它們都應合法和有效,如同是根據人民或平民的命令所做的。(utique quae ante hanc legem rogatam actagesta 丨 decreta imperata ab imperatore Caesare Vespa—siano Aug(usto)丨 iussu mandatuue eius a quoquesunt,ea perinde iusta rataq(ue)丨 sint,ac si populiplebisue iussu aeta essent)
制裁:如果任何人由于本法做了任何違反法律、平民會決議、元老院決議的事情,或如果他沒有做依據法律、平民會決議、元老院決議他應該做的事情,他不構成對法的詐欺,也不承擔向人民繳納罰款的責任,任何人不得因這些行為被起訴或受判處,也不允許任何人就此等行為起訴。(Si quis hui-usce legis ergo aduersus leges rogationes plebisue seita丨 senatusue eonsulta feeit fecerit.siue quod eum exlege rogatione 丨 plebisue seito s(enatus)ue c(onsul-to)facere oportebit,non fecerit huius legis 丨 ergo,idei ne fraudi esto.neue quit ob ealn rem populo daredebeto,丨 neue cui de ea re actio neue iudicatio esto,neue quis de ea re apud 丨[s]e agi sinito)
三、李恩佐留給我們的銅表包含的《韋斯巴薌諭令權法》是否完整問題
對如題問題的回答當然是否定的,因為顯然,第1條肯定殘缺。而且按羅馬人頒布法律的慣例,作為公法文件的《韋斯巴薌諭令權法》應有一個序言,而李恩佐發現的銅表中無此等序言。這些缺項都是部分性的,要命的是有些學者認為該法留給我們的文本存在整體性的缺項,意大利學者MartaSordi就認為還有至少一塊銅表佚失掉了,持有這種看法的還有意大利學者Gianfraneo Purpura和加拿大學者Christer Braun。Marta Sordi認為佚失的銅表應與找到的這塊并列放置而非重疊放置,因為在后者的左緣有一凹處并有放螺栓的空間。肯定殘缺一整塊銅表的理由有如下列:1.無名羅馬人在其《編年史》中記載的李恩佐的一個演說;2.注釋法學家Odofredo Denari的所見;3.既有規范的殘缺性;4.從其他羅馬憲法文件出發得出的邏輯推論。容分述之。
其一,李恩佐于1347年在一個羅馬人的會議上發表演說,提到羅馬人民授予韋斯巴薌如下權力:1.同意與他愿望的人民訂立的盟約;2.擴大或縮小羅馬和意大利的花園;3.如其所愿增加或減少給農民的土地;4.把一個人推到統帥的位置也可把他拉下來;5.毀滅城市也可恢復之;6.廢掉河床并將河流移往別處;7.依其決定征稅或免稅。然而,上述7項權力除了第一項和第二項(“有權擴大或縮小羅馬和意大利的花園”被理解為第5條的中世紀式表達)外,都不曾出現于找到的銅表中,由此可自然得出其他項權力被規定于另一銅表的結論。所以,李恩佐除了保有流傳給我們的銅表,還應保有另一銅表,可惜它并未流傳給我們。
其二,意大利著名注釋法學家Odofredo Denari(?-1265年)于1236年在圣喬萬尼拉特蘭諾大教堂看到兩塊刻有《韋斯巴薌諭令權法》的銅表并誤認它們是《十二表法》的最后兩表。當然,也有學者對這一論據提出反對,例如,Gianfranco Purpura就指出,作為法學家的Odofredo看不出他遇到的兩塊銅表的內容,是不可思議的。
其三,按共和時期的術語,諭令權包括軍事權,而在《韋斯巴薌諭令權法》中,無論是在找到的銅表上還是在下文要講到的現代學者對佚失的銅表所載內容的還原上,都找不到關于軍事權的規定,這就可以假定佚失的銅表上包含關于這一權力的規定。
Marta Sordi推測的殘缺銅表包含的規定有:1.土地分配權(ius agris dandis adsignandis);2.統帥設立與罷黜權(ius regibus creandis vel deponendis);3.設立殖民地、建立城市及毀滅城市權;4.臺伯河河岸和河床的定界權;此后的內容就是找到的那塊銅表上的了。所以,佚失的是第一表,留存下來的是最后一表。它包含“制裁”也是它為最后一表的證據,因為這是民會立法最后一部分的內容。
上列四種權力大多可望文生義,只有第四項權力除外,Christer Braun對之進行了研究,認為它關涉的并不是臺伯河河床和河岸管理官(Curatoresalvei et riparum Tiberis)的劃界權,或據此可以確定臺伯河沿岸的土地哪些屬于國家,哪些屬于私人,而是關涉授予皇帝興建包括改變河道的大型工程的權力。在韋斯巴薌之前,已有一些皇帝享有并行使此等權力,例如愷撒讓臺伯河改道的計劃、提貝流斯改變Clanis河的水道、Nar河和臺伯河的流向的做法、克勞丟斯在臺伯河口建立運河的做法、圖密善改變Volmmus河的水流的做法,韋斯巴薌不過是依循先例行事而已。
但意大利學者Dario Mantovani認為,佚失的那塊銅表里可能包含的是保民官特權,也就是人身不可侵犯權和對所有長官之行為的否決權。當然,這種說法以被找到的銅表中未包含保民官特權為前提,而日本學者鹽野七生認為,其第2條和第7條規定的就是保民官特權。
正因為包含本法的第一塊銅表佚失,本法的《韋斯巴薌諭令權法》的名稱出自后人之手,這一冠名割斷了本法與蓋尤斯《法學階梯》和優士丁尼《法學階梯》以及諸多其他文獻中提到的授予羅馬最高領導人權力的王權法(Lex regia)的關聯,為一些學者不滿。讀者可看到,本文援引的Dario Man—tovani的論文就把本法的名稱改為《關于韋斯巴薌諭令權的王權法》,本文援引的Gianfranco Purpura的論文把本法的名稱改為《韋斯巴薌權威法》,李可波諾把它譯成《被說成關于韋斯巴薌諭令權的法律》(Lex quae dicitur de imperio Yespasiani)。做了這樣的解釋性重命名后,本法就不再是羅馬憲法史上的一個個例,而成了每個皇帝都要經受的一個授權程序的見證。
四、韋斯巴薌其人其治
要想理解《韋斯巴薌諭令權法》的規定,不了解韋斯巴薌的人生經歷是不成的。
韋斯巴薌(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于9年出生于羅馬以北的小城列提(Rieti,古名Reate),也就是說未出生在羅馬,這構成他的皇帝之路的第一道障礙。第二道障礙是他屬于騎士階級。眾所周知,這是羅馬的第二等階級,不甚高貴。成年后,他加入軍隊,36年在色雷斯擔任軍團司令官,后來擔任昔蘭尼加和克里特行省的財務官。38年當上營造官。在卡里古拉為帝時期擔任過裁判官。在克勞丟斯為帝時擔任日耳曼軍團的副將。43年,參加不列顛戰役并立有戰功。51年,擔任備位執政官。63年,擔任阿非利加行省的總督。67年,被尼祿啟用鎮壓猶太人起義。68年,率軍攻陷耶路撒冷。韋斯巴薌至此的歷史都是作為軍人出現的。
就在耶路撒冷陷落的這一年,尼祿的暴政引發了民變。是年6月9日,尼祿自殺,愷撒開創的優流斯一克勞丟斯王朝覆滅,引發了一年四帝的混亂局面。先是伽爾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被西班牙軍團推舉為皇帝,但萊茵軍團的士兵不服,于69年1月2日推舉下日耳曼軍團司令維特流斯(AulusGermanicus Vitelius Augustus)為帝。69年1月15日,伽爾巴在羅馬被殺,禁衛軍推舉奧托(M.SalviusOtho)為帝,形成一國兩帝局面,內戰再度降臨羅馬。支持奧托的多瑙河軍團與支持維特流斯的萊茵河軍團相斗,于69年4月16日會戰于貝德里亞克,奧托軍敗,在當皇帝三個月后自殺。維特流斯被元老院確認為唯一的皇帝,但他治國無方,引來群雄逐鹿。其中有韋斯巴薌及其黨人當時的敘利亞總督穆恰努斯(Gaius Licinius Mucianus)和埃及總督亞歷山大(Tiberius Iulius Alexandrus)。三人于69年6月底在現今的貝魯特商定,穆恰努斯率兵往意大利奪取政權;韋斯巴薌前往埃及待機而動,避免在當上皇帝前手染同胞的鮮血。他于69年7月1日被埃及的羅馬軍隊擁立為帝;韋斯巴薌的兒子提圖斯(Titus)則繼續完成猶太戰役的余下部分,亞歷山大協助之。穆恰努斯的軍隊與維特流斯的軍隊舉行了第二次貝德里亞克會戰,后者戰敗,殘部于69年12月15日投降。但12月22日,仍在羅馬爆發了巷戰,維特流斯被殺。數日后,穆恰努斯進入羅馬。所以,《韋斯巴薌諭令權法》是在韋斯巴薌不在羅馬的情況下由其盟友穆恰努斯籌劃制定的。70年11月中旬,韋斯巴薌從埃及回到羅馬,才真正統治其國家。從其軍隊占領羅馬到他回到羅馬,整整10個月的期間都是穆恰努斯代理他當皇帝。在代理期間,穆恰努斯召開了元老院會議,讓韋斯巴薌及其兒子提圖斯擔任70年的執政官,并派兵鎮壓日耳曼裔高盧人的叛亂,對受內戰之害的個人和城鎮進行賠償,重建了在內戰中被焚毀的卡皮托爾山上的朱庇特神廟。最后說到但最重要的是,在69年12月22日羅馬的巷戰日到70年1月初之間的某天,舉行元老院會議通過了《韋斯巴薌諭令權法》,確認了韋斯巴薌地位的合法性及其權力的范圍。
韋斯巴薌在擔任皇帝10年后于79年去世。其子提圖斯即位。提圖斯后由其弟弟圖密善(Domitianus)即位。三個族名弗拉維的皇帝的統治構成弗拉維王朝,它是對優流斯一克勞丟斯王朝的取代,取代它的是五賢帝時代。韋斯巴薌在位期間,國泰民安,由此證明一個低下階級出身的人也可以當羅馬皇帝,而且可以當得很好。所以,2008年,意大利政府成立紀念韋斯巴薌誕生2000年委員會,在其家鄉列提舉行了一系列的紀念活動。但意大利政府從未為韋斯巴薌的前任尼祿舉行過這樣的紀念活動。
韋斯巴薌有兩件遺跡讓我們經常想到他。第一是羅馬斗獸場,這是他在位時期開建的,現在是羅馬的象征;第二是小便稅。他是開征此稅的皇帝之一。韋斯巴薌向收集公廁中的尿液,用來去除羊毛油分的纖維業者收取這種小便稅,稅率不詳。此舉導致一些歐洲國家的公共小便處以“韋斯巴薌”名之。
五、對《韋斯巴薌諭令權法》殘存部分的逐條評注
本節撇開佚失的那塊銅表中記載的《韋斯巴薌諭令權法》的條款不談,因為如果這樣做,有太多的不確定性,只分析流傳給我們的那塊銅表中包含的條款,以求獲得對一個元首制時期的憲法文本的較深入認識。
(一)對各條文屬性的整體描述
第二塊銅表原文并無條文的序數編號,每個意思轉折用拉丁詞Utique(意思為“如同”)表示,這是元老院決議的格式,Utique是個關系代詞,它們跟隨的主句在佚失的第一塊銅表中,是“元老院決定”(Scnatu plaeuit)。每項決定的文字以Utique開頭,故今人以每個Ufique后面的文字為一條,把它們按序數標號,一共8條。其中,第1、2、5、6、7條在確權的同時,指出優流斯一克勞丟斯王朝的數個或某個皇帝也曾享有此等權力,被后世學者稱為“有先例條款”。學者認為韋斯巴薌是在運用先例制度為自己確權。優流斯一克勞丟斯王朝曾有奧古斯都、提貝流斯、克勞丟斯、卡里古拉、尼祿五位皇帝,最后兩位未被提到,因為他們遭受了記錄抹殺刑。以“數個”方式被作為先例提到的,有奧古斯都、提貝流斯(采用全稱提貝流斯·優流斯·愷撒·奧古斯都)、克勞丟斯(采用全稱提貝流斯·克勞丟斯·愷撒·奧古斯都·日耳曼尼庫斯),分別出現于第1條、第2條、第6條、第7條中;被以“某個”方式作為先例提到的只有克勞丟斯,只出現于第5條中。第3、4、8條確定韋斯巴薌皇帝的權力卻不援引優流斯一克勞丟斯王朝皇帝們的先例,被后世學者稱為“無先例條款”。
對以上分析存在爭議。首先,第3、4、8條是否無先例是個問題,論者證明優流斯一克勞丟斯王朝的皇帝們也享有過它們規定的權力,《韋斯巴薌諭令權法》之所以不援引前朝的先例,是打算把它們打造成效果條款,也就是調整君主行為的效果的條款。換言之,這3個條文賦予皇帝的權力在所謂的有先例條款中已規定,這些所謂的無先例條款不過是規定皇帝實施有先例條款賦予的權力的法律效果而已。其次,從形式上看援引了前朝皇帝擁有有關權力的先例的第6條和第7條是否真的無先例,遭到Gianfranco Purpura的質疑,他認為它們是無先例的,因為第6條是空白委任狀,優流斯一克勞丟斯王朝的皇帝們未曾以這種方式被授予過權力,因為如果真的授予過他們這樣的絕對的權力,等于正式取消了他們力圖保持的共和的外表。所以,韋斯巴薌妄稱這兩條有先例,是為自己拋棄共和的外衣虛列論據。
(二)逐條評注
第1條評注首先要說的是,本條并不完全。從本條的殘存部分來看,它規定的是皇帝的戰爭與和平權以及相應的訂立同盟權,總體上可稱為外交權。在訂立和約的情形,皇帝要對條約條款的起草承擔完全責任,當然,他在這樣做時要受到其元首顧問委員會的支持。按蒙森的見解,奧古斯都曾被根據一個特別法授予這一權力,他的繼任者后來也被認為享有此權。在共和時期,此權屬于元老院,統帥在外締約,是否有效要最終取決于元老院批準,元老院不批準的,要把訂約的統帥捆起來交給敵人。現在皇帝直接享有此權了,但不排除皇帝在行使此權時與元老院進行協商。比較共和時期和元首制時期外交權的行使,可發現元老院的外交權在元首制時期被架空了。
第2條評注本條規定的是皇帝召集、主持元老院會議并在其中提出法案的權力,屬于保民官特權。按歷史學家Cassius Dio(150—235年)的記載,元老院曾于公元前23年通過決議授予奧古斯都終身保民官頭銜,授予他在他愿望的任何時間參加每次元老院會議的特權,即使他不擔任執政官時也不例外。在奧古斯都之后,提貝流斯勤政,熱衷于參加一切元老院會議并解決有關問題。事實上,元老院作為一個長官的咨詢機構不能自行開會,必須南長官召集之。在共和時期,能為此等召集的是執政官。共和晚期,保民官也獲得了召集元老院會議的權力。所以,Cassius Dio把奧古斯都召集元老院開會的權力與保民官特權掛鉤,并說明他不擔任執政官時也有此權,意思是說他可以不以執政官的身份,而是以終身保民官的身份召集元老院開會。由于元老院會議的消極性,它只能就長官提出的問題進行討論和表決,本身并無動議權,所以,誰擁有了元老院會議召集權,誰就擁有了“橡皮圖章”使用權。對于長官提出的動議,無疑義的,直接付諸表決,此時采用退席(per discessionem)的方式,也就是同意報告人提出的法案的元老離席站到此等報告人身邊表示支持,這是用腳投票。如果對提出的法案有爭議,則先進行討論,然后采用經逐一征詢意見(per singulorum sententia exquisitas)的方式表決。表決通過后形成元老院決議。此等決議是對民會立法的取代,因為羅馬人民的數目增長到了必須以間接民主取代直接民主的程度(I.1,2,5)。這樣的轉折實際上賦予了元老院代議機構的職能,承擔起立法權——主要是私法方面的。公法方面的立法權仍然由殘存的民會承擔。但在本條的框架內,實際的立法者是皇帝,他通過與元老院協商完成立法活動,他的演說就是元老院決議的內容。不過,從純粹的理論可能性來看,元老院對于其立法權還保有制衡的功能。所以,蒙森把元首制時期的皇帝——元老院共治體制稱為雙頭制(Diarchia),是有道理的。不過,把這種體制叫做兩頭半制,可能更確切,因為自奧古斯都以降,每個皇帝都設有自己的元首顧問委員會,他們由皇帝的友人、部分元老和法學家組成,其功能之一是為皇帝準備法案,所以,皇帝在元老院發表的演說,大都是這個班子起草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皇帝提出的法案并非個人決定,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在元首制時期,元首顧問委員會還處在隱而不顯的地位,但到了多米納特時期,皇帝直接享有立法權,通過頒布敕令行使此等權力。這個時候,倒是元老院在立法權行使問題上處在隱而不顯的地位了,元首顧問委員會成為取代它的機構,它負責為皇帝起草敕令,在其內部,七讀通過才能以皇帝的名義頒行。
本條提到奧古斯都、提貝流斯、克勞丟斯3個皇帝都行使過本條賦予的權力,確實如此,但這三個皇帝都處在民會仍存在的時期,所以,他們有時通過民會立法,有時通過元老院立法。例如,奧古斯都的《鼓勵結婚的優流斯法》和《優流斯私人審判法》就是通過民會制定的,而其他大量的“優流斯法”就可能是通過元老院制定的了。克勞丟斯皇帝也是如此,他通過民會制定了《克勞丟斯婦女監護法》,他也通過元老院制定了幾個元老院決議,其中有名者有《關于與奴隸同居的克勞丟斯元老院決議》,它禁止自由婦女與奴隸結合。按意大利學者馬里奧·塔拉曼卡的研究,羅馬統治者對于不同的法律門類通過不同的立法機關制定,民法一般走元老院決議的途徑,而公法則走民會的途徑。
那么,本條中的“取消演說”何解?按蒙森的為眾人接受的解釋,是皇帝駁回或遲延談論其他人提出的法案的權力,可以理解為皇帝對有關法案的否決權。按瓦羅(公元前116-27年)的記載,可以在元老院演說的長官還有獨裁官、執政官、裁判官、平民保民官、攝政、市長官。這是共和時期的情況,到了帝政時期,至少執政官還可以在元老院演說,例如,在尼祿時代,特雷貝流斯·馬克西姆斯就作為執政官提議制定了《特雷貝流斯元老院決議》賦予遺產信托的受益人繼承人的地位。又如,在韋斯巴薌時代,貝加蘇斯就作為執政官提議制定了《貝加蘇斯元老院決議》賦予繼承人對被信托交付的遺產的留置權。當然,如果這樣的執政官提出法案于元老院而皇帝又不贊成,后者可以駁回之。
第3條評注本條規定皇帝通過他人召開元老院會議并通過法律的權力,是對第2條規定的引申,因為該條規定了皇帝可親自召集元老院會議。本條涵蓋兩種情形,其一,皇帝本人出席元老院會議,但由別人根據他的意志主持;其二,皇帝本人不出席元老院會議,別人根據他的安排主持此等會議。本條的第一種適用讓皇帝退居二線,讓他的政治代理人在第一線活動,提出法案,如此可避免一些攻擊。在提出一些觸犯眾人利益的法案的時候,尤其容易發生這種情況。本條的第二種適用是為了維持穆恰努斯在70年1月初召開的元老院會議的效力設立的。如前所述,在該次元老院會議上通過了作為本文討論對象和韋斯巴薌統治合法性依據的《韋斯巴薌諭令權法》,其時,韋斯巴薌本人并不在羅馬,更談不上召開元老院會議。所以,《韋斯巴薌諭令權法》的程序合法性存在問題,通過制定本條就把這一問題解決了。這是面向過去對本條作出的解釋,從面向未來的角度也可將本條解釋為可以委托他人召集元老院會議并通過法律,這就可以把皇帝從事務性工作中解放出來集中精力執行重大任務。這樣的安排在皇帝作為全軍統帥出征在外的情況下,可以保證立法工作和其他工作不斷。
第4條評注此條規定了皇帝的官吏推薦權。首先把長官分為3類。第一是有權力(Potestas)的長官;第二是有諭令權的長官;第三是掌管公物的長官。日本學者鹽野七生認為前者包括裁判官、監察官、執政官等官職;中者包括皇帝行省的總督、元老院行省的總督;后者包括稅務官員。總之,第一種官吏是羅馬城內的官;第二種官吏是督理行省的官;第三種官吏是管理國家財產的官。此說可堪參考。
本條其次列舉了決定官吏人選的憲法機構:元老院和羅馬人民,皇帝有權向它們推薦自己中意的任職人選。羅馬人民以民會的方式體現其作為憲法機關的存在。民會包括百人團會議和部落會議,它們在共和時期享有立法權、長官任命權和審判權。前者制定的為民決法(Lex rogata),通常是公法,后者制定的為平民會決議,通常是私法。但到了帝政時期,由于羅馬市民的人數極度擴張,召開民會已困難,但仍然在改革的基礎上召開。改革的內容之一是去掉民會的審判功能。之二是改革百人團會議的組織。1947年發現的提貝流斯時期(19年)的《赫巴銅表》告訴我們,那個時候只有15個百人團了,它們由元老和騎士組成,其使命是選舉執政官和裁判官,這樣,相對于塞爾維尤斯·圖流斯時期有193個百人團,百人團的階級構成甚至包括無產者的情況,帝政時期的百人團會議的規模更小,更容易組織;之三是改革投票方式,對于居住在意大利的殖民地的百人隊長,允許他們通訊投票,也就是把封好的選票在民會召開日那天寄到羅馬。通過上述改革,民會維持下來,它負責選舉高級長官,偶爾也通過法律,在內爾瓦(35—98年)皇帝時期(96年和98年),民會最后一次發揮了其立法功能,頒布了皇帝提議的土地法。在那以后,民會再未召開過,它已經被民眾在公眾場合(例如競技場)的歡呼或喝倒彩取代。要指出的是,本法頒布在提貝流斯皇帝之后,內爾瓦皇帝之前,所以,本條關于民會選舉皇帝推薦的人選為長官的規定,并非虛言。
本條再次提到了皇帝向元老院薦人的兩種方式:推薦、給予支持。
推薦的做法來自公元前44年的《安東紐斯候選人法》(Lex Antonia de candidatis),該法允許當時的獨裁官愷撒推薦一半官員,其方式是愷撒寫條子給部落會議,其辭日:我向你們推薦此人和彼人,希望根據你們的投票讓他們獲得有關的職位。這樣的權力為后來的皇帝們繼承,通過本條,韋斯巴薌希望自己能繼續享有這樣的權力。
“給予支持”的做法來自共和時期,其內容是恩主公開表示對特定候選人的偏愛,此等恩主的門客因此有義務投該候選人的票。到了帝政時期,給予支持的方式包括有影響力的支持者帶著候選人訪問選民的部落等。可以認為,推薦是用言辭或文字的方式支持候選人,對承受者有約束力;給予支持是用行為的方式支持候選人,約束力比較含糊。
本條最后提到了“特別考慮”,意思是對于韋斯巴薌推薦的官員人選,民會要不拘一格地考慮。具體而言,是不受任職條件的限制。此等任職條件至少有三。其一,擔任特定官職的資歷限制,例如,必須先擔任財務官才能擔任營造官,擔任了營造官才能擔任裁判官,擔任了裁判官才能擔任執政官,擔任了執政官才能擔任行省總督,擔任了行省總督才能擔任監察官;其二,擔任特定官職的年齡限制。例如,擔任營造官的年齡資格是37歲,擔任裁判官的年齡資格是40歲,擔任執政官的年齡資格是43歲。其三,擔任不同官職的時間間隔限制,通常,這一時間間隔是2年。但對于皇帝推薦的候選人,可以打破這些陳規任命之。
本條屬于無先例條款,因為它未援引任何皇帝曾享有這方面權力的先例,但它實際上是有先例條款,因為白愷撒以來,奧古斯都、提貝流斯、克勞丟斯等皇帝都行使過本條規定的權力。
第5條評注本條規定了皇帝的城界外推權。城界是用排列的石柱表示的羅馬城的界限,也是一些長官權力的界限,例如保民官的權威以及其他長官的諭令權以城界為界限,外推城界等于擴張此等長官的管轄權范圍。而且是否出生在羅馬城界內是區隔兩種身份的事實,出生在城界內的,謂之世家;出生在城界外的,謂之寄寓者(Inquilinus),被人作為鄉巴佬瞧不起。所以,擴大城界包括的范圍等于擴大世家的范圍,非常類似于現在中國的郊區人口因為城市擴張“農轉非”的情形,被轉者喜不自勝也!更有甚者,羅馬城界還是界定某個羅馬市民能否享受以“面包和馬戲”名之的羅馬國家社會福利的尺度,只有城界內的羅馬市民能享有此等福利,形成首都人特權。所以,擴大城界包羅的范圍,等于擴大面包和馬戲的享有者的范圍,自然是惠民之舉,受人歡迎,有如此作為的皇帝將被授以金環。
本條屬于有先例條款,與其他有先例條款同時援引奧古斯都、提貝流斯和克勞丟斯作為先例不同,本條只援引克勞丟斯作為先例。事實上,克勞丟斯確實于49年行使過此等權力,他為了表征其不列顛戰役的成果而這樣做,暗示他已擴大羅馬帝國的領土,因為只有擴大過羅馬帝國在意大利的領土的元首才能外推城界。所以,城界外推權具有帝國主義或擴張主義色彩。當然,城界外推還有再造羅馬的含義,因為第一個城界是羅慕路斯劃定的,羅慕路斯是羅馬城的締造者。如果有人外推了城界,他當然是羅馬的第二個締造者了。所以,韋斯巴薌通過本條宣示自己具有城界外推權具有宣傳目的,暗示自己將獲得軍事勝利并擴大羅馬帝國的版圖。果然,韋斯巴薌最終行使了本條賦予的權力,于75年外推了羅馬的城界,以昭示他在猶太戰爭中的勝利。
第6條評注本條規定的是皇帝的自由裁量權。此等自由裁量權涉及四個對象,神的和人的威權、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它們共同構成國家的需要。那么,什么是神的威權?威權(Maiestas)一詞來自maius(較大的),故神的威權表示神對人的統治關系。與神的威權相隨的是人的威權。這里的“人”并非一般的人,而是指羅馬人民。西塞羅如此定義它:威權是市民團體的地位和尊嚴。如果說神的威權是一個涉及人與神之間關系的概念,那么,人的威權主要是一個涉及羅馬人民與其他人民關系的概念,后者冒犯前者,例如凌辱其使節,就侵犯了其威權。當然,羅馬人民內部的成員也可能損害羅馬人民的威權。
冒犯神的威權的行為例如有:不守諾言、偷移界石,因為諾言由信義女神確保遵守;界石的位置也有界神保證。冒犯羅馬人民的威嚴的行為有:沒有元首的命令殺死人質、jRTX/Hb+OdrOlxriF2g51g==武裝聚會占據要地或神廟、為叛亂聚會、殺害或教唆殺害羅馬人民的長官,給敵人通風報信、煽動兵變等。
什么是公共事務?我們知道,在拉丁語中,公共的(Publicus)是人民(Populus)一詞的形容詞,因此,公共事務就是人民的事務。西塞羅就此說:“如果人民保有其權利,便沒有什么比這更美好、更自由、更幸福的了,因為他們是法律、審判、戰爭、和平、締約、每個公民的權利和財富的主人。……只有這樣的體制才堪稱res pubhca,即人民的事務。”由此可見,“公共的事務”就是法律、審判、戰爭、和平、締約、每個公民的權利和財富等。要說明的是,Res Publica一詞在拉丁語中還有國家財產的意思,那就是國有的土地、森林等有體物了。按照上述西塞羅對Res Publica一詞的解讀,它不是指人民的有體物,而是指屬于人民的無體物。
弄清了什么是公共事務,私人事務為何就清楚了,因為在本條中,用“公私事務”一詞涵蓋所有的人事,那么,不是公共事務的,都是私人事務。當然,私人所有權、私人間的合同肯定屬此。
至此可見,本條授予皇帝的權力相當廣泛,從神事到人事,從公事到私事,只要符合國家的需要,他都可以干預,這樣,他的干預權就幾乎無所不包了。無怪乎人們說本條是自由裁量權條款,也就是少有限制的賦權條款。
本條規定的皇帝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手段有Ius和Potestas。什么是ius?眾所周知,該詞是權利、法院的意思。什么是Potestas?保羅認為該詞表示一種支配關系,官員的諭令權、父親對子女的權力、主人對奴隸的權力,都在它的涵攝下(D.50,16,215)。可否將Ius理解為權利,將Potesatas理解為權力呢?答曰不能,因為這兩個詞用“和”連在一起后有獨特的含義,指由公法授予的某種權力,被授權者由此取得一種法律地位。當然,運用這種法律地位,皇帝可以對從宗教到世俗、從公到私的一切事務進行調整。
由于本條賦予皇帝的權力過于廣泛,就它的性質,學界廣有爭論,形成以下數說。首先有緊急狀態下權力說,謂本條規定的是皇帝在緊急狀態下的權力,其他條款規定的是皇帝在正常狀況下的權力。此說為意大利學者德·馬爾丁諾所持。其次有敕令發布權說,謂本條賦予皇帝就如上廣泛事務制定法律的權力。此說為德國學者蒙森所持。還有兜底條款說,謂前面的諸條款具體授予了皇帝這個那個權力,惟恐遺漏,設立本條,進行不確定授權。等等,諸說各有其道理,各有論者的主觀性,綜合考慮它們才比較全面。正因為對本條的理解不同,對它的翻譯也是五花八門,意大利學者Mari—ano Malavoha對它們一一列舉,甚有意味,讀者可以參看。
第7條評注本條規定皇帝的兩項權力,首先規定皇帝的免受法律約束權;其次規定皇帝的前任政治權力繼承權。前者屬于消極的權力,后者屬于積極的權力,兩者頗為不同,按理應分條規定,但本法將兩者捏在一條,理由似乎只能從兩者有共同的參照系找到:前者從奧古斯都、提貝流斯、克勞丟斯免受約束的法律出發建言;后者從這三個皇帝根據民會制定的法律有權做的事情出發建言。看來,先行的三個皇帝都享有過這兩項權力是它們共同的參照系。
本條第1款規定優流斯一克勞丟斯王朝的三個皇帝不受其約束的法律,故開創弗拉維王朝的韋斯巴薌皇帝也不受其約束,完全采取蕭規曹隨的合理化方式,但并未憑空提出皇帝不受法律約束的一般命題,反言之,奧古斯都、提貝流斯、克勞丟斯要遵守的法律,韋斯巴薌也要遵守。由此,君主處在法律之下,法律有明文相反規定的除外的原則得以確立。從第1款的文義來看,似乎難以得出別的解釋,所以,英國學者P.A.Brunt主張本款規定了君主一般地不受法律約束的原則,此論讓我感到奇怪。
那么,韋斯巴薌之前的君主到底免受哪些法律約束?從羅馬人的實踐來看,君主除免受特定的民事法律的約束外,還免受一定的刑法約束。具體而言,君主不受約束的民事法律有婚姻法、收養法、繼承法、遺贈法和法律行為形式法。他們免受約束的行政和刑事法律包括墓葬法和選舉舞弊法。就婚姻法、繼承法和遺贈法而言,公元前18年奧古斯都頒布的《優流斯正式結婚法》和公元9年的《帕皮尤斯和波培烏斯婚姻法》(Lex Papia PoppaeaNuptialis)規定,獨身者和婚而不育者喪失繼承能力,他人遺給他們的遺產構成落空遺產份額(Cadu—ea ex lege Papia)歸皇庫(Fiscus)繼承。但羅馬人有指定皇帝為自己的遺產受贈人的習慣,而許多皇帝不生育,如果因此剝奪他取得這方面遺產的權利能力,皇庫將遭受損失,所以,法律為皇帝在這方面設立了一個豁免權。就收養法而言,按羅馬法的規定,自權收養人必須自己無子,但奧古斯都盡管自己有孩子,還是收養了提貝流斯。而且,他還要求已有兒子的提貝流斯自權人收養日耳曼尼庫斯。這種對收養法的踐踏出于政治考慮:收養在這種場合被作為一種選擇政治繼承人的方式看待而非作為彌補無子缺憾的手段看待。就法律行為形式法而言,皇帝還免受某些法律行為的嚴格程式的約束。就墓葬法而言,《十二表法》第10表第1條以來的羅馬法都規定不得在羅馬城內埋葬或火化尸體,這樣規定是為了公共衛生的考慮,但皇帝及其家人可以被埋葬在羅馬城內,并以這種方式受到紀念。就選舉法而言,普通人要受不當影響選舉罪(Ambitus)的約束,但皇帝根據本法第4條的規定享有官吏推薦權,自然要以某種方式影響選舉,所以他們不在不當影響選舉罪的適用對象之內。
本條第2款規定了皇帝的前任政治權力繼承權,它是一個不確定規定,等于說,凡是奧古斯都、提貝流斯、克勞丟斯依據民會制定的法律可以做的,我韋斯巴薌都可以做,至于上述三個皇帝依據民會制定的法律做了什么,本款并未指出,只能任憑讀者的歷史知識和想象去探求。由于此等不確定性,它與本法第6條有重復之嫌,因為韋斯巴薌的前任也是就宗教和世俗事務、公私事務展開行動,本款再賦予韋斯巴薌以對前任政治權力的繼承權,就等于重復規定了。但要指出的是,本款并非允許韋斯巴薌做他們做過的任何事情,只允許韋斯巴薌做他們依據民會制定的法律允許他們做的事情,這似乎暗示民會在這三個皇帝就職時分別制定了一個類似于《韋斯巴薌諭令權法》的法律完成像70年1月初的元老院對韋斯巴薌一樣的授權程序。事實上,撇開民會授權的程序情節不談,在韋斯巴薌之前,每個羅馬皇帝都會在就任時獲得授權的,以提貝流斯為例,他于14年9月17日被元老院授予全軍最高指揮權、保民官特權,以及奧古斯都享有過的為保衛羅馬所需之一切權力。確實,這個元老院決議很類似于《韋斯巴薌諭令權法》,其第三項授權為概括性的,很類似于本款的授權方式。
第8條評注本條是溯及力條款,也稱過渡條款,旨在追認韋斯巴薌稱帝到69年7月1日前韋斯巴薌及其黨人做的事情的法律效力。在這一期間前,韋斯巴薌及其黨人的行為按照規制他們當時的憲法角色的法律定性。那時,韋斯巴薌是征猶大軍的司令;穆恰努斯是敘利亞的總督;亞歷山大是埃及總督。在這一期間之后,他們就是以叛逆者的角色進行活動了,因為維特流斯是取得了元老院合法授權的皇帝。韋斯巴薌取代維特流斯后,必須在自己的元老院授權文件中增加這一條確認自己及其黨人在“叛逆期”行為的合法性。此等行為,無非是韋斯巴薌在埃及的行為,穆恰努斯在意大利的內戰行為,以及提圖斯和亞歷山大繼續猶太戰爭的行為。其中,穆恰努斯的政治行動最多,如前所述,他召開了元老院會議,讓韋斯巴薌及其兒子提圖斯擔任70年的執政官,并派兵鎮壓日耳曼裔高盧人的叛亂,并對受內戰之害的個人和城鎮進行賠償,重建了在內戰中被焚毀的卡皮托爾山上的朱庇特神廟。按照本條,這些行為視為依據人民和平民的命令實施,合法有效,反言之,盡管其中有忤逆之處和殘暴之處(例如在首都羅馬發動巷戰),后人不得以其不合法為由攻擊之。所以,也可稱本條為勝利者條款,揭示了勝利者無非的歷史真理。其設立也表明了本法的策劃者穆恰努斯的行事的滴水不漏,他不打算留下任何空子讓人鉆。非獨此也,本條還確定了韋斯巴薌的諭令權起始日(Dies imperii)。顯然,這個日子并非元老院通過《韋斯巴薌諭令權法》的日子,而是他被在埃及的羅馬軍隊推舉為皇帝的日子。
本條把本法稱為民決法,等于說本法不是一個元老院決議(盡管如前所述,本法采取了元老院決議的格式),而是民會通過的法律,這樣就提高了本法的合法性,因為元老院的立法權以私法為范圍,本法屬于公法中的憲法,應由民會通過。我在對第4條的評注中已證明民會在韋斯巴薌時期仍然存在并運作,所以,本條把本法宣稱為民決法,應符合事實。后人把本法名之為《韋斯巴薌諭令權法》而非《關于韋斯巴薌諭令權的元老院決議》,表達了他們對于本法是一個民會制定的法律而非單純的元老院決議的認識。通說認為本法最初是70年1月初由元老院通過的一個決議,但后來此等決議得到了民會的通過,成為民決法。
如果上述證明成立,則本法還要追認韋斯巴薌及其黨人在第二個過渡期中的行為的法律效力,也就是從記載本法內容的元老院決議通過日到本法被民會通過日之問的期間,這可能是一個多月的期間。
制裁評注本部分的標題以大于各條文字號約兩倍的字號鑄造,表明了立法者對本部分的重視。
與前面各條都以Utique開頭不同,本部分以“如果”(Si)開頭,表明它不受Senatu placuit的主句管轄,而是開啟了一個新的部分。
本部分首先反映了羅馬的公法文本的結構。此等法律應包括前言(Praescfiptio)、法案(Roga—tio)、制裁(Sanctio)三個部分。前言應包括提出法案的長官的名字;法案包括法律的全部內容;制裁通常包括如下5項內容。其一,規定長官或元老的適用所涉法律并不得阻礙之的誓言;其二,規定對故意不適用所涉法律的長官、元老、法官的罰金;其三,禁止廢除或破毀所涉法律或在元老院提出討論此等可能性;其四,規定為遵守新法而違反舊法的人免責;其五,規定不能形之于民決法的法或神法的規定無效。本部分只包括制裁的第四項內容。富有意味的是,本部分的內容與制裁一語的最初意思相合。馬爾西安在其《規則集》第4卷中說:“制裁(Sanctus)一詞源于馬鞭草(Sagmina),它是羅馬人的使者為使任何人都不能傷害他們而經常攜帶的那種草”。看來,有了本部分第四項內容意義上的制裁,行為人就可以不受傷害了。正因為本部分體現了羅馬公法中的制裁的這種含義,鹽野七生把這里的Sanctio翻譯成“免于罰則之認可”。此舉并非無理,但這種譯法僅適合于本部分,否則就閹割了作為羅馬公法文件最后一部分的“制裁”的豐富含義。
如前所述,本法的序言部分和法案的前半部分已佚失,但法案的第二部分和制裁部分得到保留。但為何在制裁部分省略該部分應有的第1、2、3、5項內容?我認為,這種省略可歸之于制定《韋斯巴薌諭令權法》的匆忙。當然,也可歸之于本法的性質,例如,本法是根本大法,不存在由某個長官、元老、法官適用的問題,所以也無必要規定對他們不適用本法的罰金。
本部分分為3個單元。第一個單元從積極的角度規定了遵守本法的人違反先前的法律、平民會決議、元老院決議的情形;第二個單元從消極的角度規定了遵守本法的人未履行先前的法律、平民會決議、元老院決議課加的義務的情形;第三個單元規定了上述作為或不作為的法律效果:不構成違法、不繳納罰款、任何人不得起訴或判處他、也不允許任何人對他起訴。所列事項中的“罰款”讓我想,到這些被實際上違反的法律、平民會決議的制裁部分包括了對違反者罰款的規定。
質言之,本部分規定的還是新舊法的交替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另一個過渡條款。
六、結論
《韋斯巴薌諭令權法》是一個難得的保存得比較完好的元首制時期的羅馬憲法文本,它被譯成中文并受到評注,是對羅馬公法不存在論或雖存在但無價值論的一個否證,它同時是對自努馬王以來羅馬人民以法律文件對最高行政長官進行授權、從而昭顯政治權力的民授性的憲法傳統的一個立證。就其內容而言,它是一個明確皇帝權限的法律,其基本的理路是蕭規曹隨,凡是優流斯一克勞丟斯王朝的三位未被判處記錄抹殺刑的皇帝曾享有的權力,作為弗拉維王朝的開創者的韋斯巴薌皇帝也要享有,這樣就保持了政治權力分配的連續性,在兩個王朝之間完成一個銜接,并讓卑賤的弗拉維王朝的第一個皇帝取得血統高貴的優流斯一克勞丟斯王朝的皇帝一樣的尊榮。要強調的是,授權者是元老院,被授權者是皇帝,在權力量守恒的條件下,皇帝的權力多一點,元老院的權力就少一點,所以,本法調整的是皇帝與元老院的權力分配關系。元老院并非民選產生,所以不能把它看做人民的代議機關,這樣造就了元首制時期的羅馬憲法與當代憲法的極大不同:后者首先調整國家與人民的關系,其次調整國家機關彼此間的關系,前者缺乏調整國家與人民的關系的部分,并把豐富的國家機關彼此間的關系簡化為皇帝與元老院之間的關系。由此出發評斷,前者不符合現代憲法的條件,但它在另一個方面與現代憲法相通,那就是憲法的限權性。盡管本法的有些條款賦予了皇帝無所不包的權力,但皇帝并非法本身,而是一個憲法機關,它被置于法律之下,而非凌駕于法律之上,所以,說元首制時期,羅馬的憲政體制是立憲君主制,是符合事實的。這種體制當然強于絕對君主制。這種立憲君主制是共和憲政的延續,因為本法規定的皇帝權力林林總總,但實際上可把它們類聚為保民官特權、前執政官大權、最高裁判權等共和時期的長官享有過的權力。
然而,這部憲法是對西塞羅和波里比阿極為推崇,并被譽為羅馬力量來源的三元混合憲法傳統的背離,這種傳統中的“三元”是民會、執政官和元老院,但在韋斯巴薌的時代,民會已奄奄一息,元老院盡管大限將至,仍維持運作,與皇帝形成共治,蒙森把本法的體制描述為雙頭制,是確當的。人民被虛化了,愈加成為臣民,元老院正在被虛化,它在本法第6條授予的自由裁量權的壓迫下如此,但本法畢竟是一部元首制時期的憲法,它預示著多米納特制時期徹底架空元老院、集權于皇帝的憲法。盡管如此,無論君權如何擴張,人們始終記得隱含在三頭制或雙頭制下面的一“頭”,即確認了這種或那種權力分配體制的憲法,在羅馬法史上,即使到了君權最擴張的時代,它也作為一種制衡力量與君權形成對立。在我看來,有一部憲法限制權力并被認真執行,總比沒有這樣的憲法或雖有但不適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