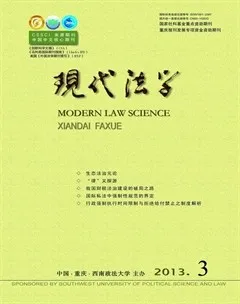想象競合的功能及其存在根據
文章編號:1001-2397(2013)03-0130-10
收稿日期:2013-03-15
基金項目:日本東北大學“GCOE項目”
作者簡介:丁慧敏(1984-),女,內蒙古呼和浩特人,清華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專業博士生,日本東北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生。
摘 要:將罪數論升級為競合論,關鍵在于要使罪數論的定罪量刑功能轉變為競合論的量刑功能。想象競合是競合論中最為重要的成員,它是一個針對自然行為犯數罪如何量刑的理論。在對想象競合行為定罪時,犯罪構成仍是定罪的惟一標準,因此想象競合為數罪,在判決書中,要將數罪一一列明。如果對想象競合數罪并罰,就否定了其存在的必要性。不能對想象競合數罪并罰的理由,就是想象競合的存在根據。想象競合的數罪中,不法量刑情節與特殊預防必要性的情節高度重合,數罪并罰會造成量刑中的重復評價。較輕的一罪在想象競合的量刑中仍具有一定的發言權,即宣告刑不能低于輕罪的最低刑,同時必須考慮輕罪的附加刑。
關鍵詞:競合論;想象競合;量刑規則;存在根據
中圖分類號:DF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3.03.12
罪數論是我國刑法學中極易折戟沉沙的湍流。傳統觀點一般將罪數分為一罪與數罪兩種類型:一罪進一步被分為實質的一罪(繼續犯、想象競合犯和結果加重犯)、法定的一罪(結合犯和慣犯)、處斷的一罪(連續犯、牽連犯和吸收犯);數罪分為實質數罪與想象數罪、異種數罪與同種數罪、并罰數罪與非并罰數罪、判決宣告以前的數罪與刑罰執行期間的數罪[1]。近幾年,為將我國紛亂如麻的罪數論做到內容上適正,體系上相輔而成,陳興良教授多次主張用德國的競合論改造我國的罪數論:將繼續犯、結合犯、結果加重犯、慣犯等放入刑法理論的其他部分討論;將連續犯、牽連犯、吸收犯從競合論中剝離,力爭將討論的范圍縮減為“法條競合-想象競合-實質競合”[2]。在這場競合論取代罪數論的運動中,重新定位想象競合的功能是最為關鍵的一環:想象競合是取舍定罪的標準,還是數罪的量刑規則?到底該如何對想象競合定罪量刑,其原理又是什么呢?
一、想象競合的功能
通說認為,想象競合為“實質的一罪”,按照行為人所犯數罪中最重的一罪定罪量刑即可[1]。司法實踐也是按照這種方式來對想象競合定罪量刑的。例如,盜竊正在使用中的電力設備的行為成立破壞電力設備罪與盜竊罪的想象競合。倘若行為人盜竊的是3000元左右的電力設備,破壞電力設備罪的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盜竊罪僅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在這種情況下,破壞電力設備罪的法定刑重于盜竊罪,故僅按照破壞電力設備罪定罪量刑。但一個行為已經觸犯了數個不具有法條競合關系的犯罪構成,為何最終僅按一罪定罪量刑?在想象競合的情況下,犯罪構成是否仍是定罪的惟一標準?想象競合是否既具定罪功能,又具量刑功能?
(一)競合論的功能
能否將我國凌亂不堪、寸步難行的罪數論轉變為競合論,關鍵在于能否將舊的罪數論思維轉變為新的競合論理念;想象競合是競合論中最為重要的內容,對想象競合功能的探討要以定位競合論功能為前提。
傳統罪數理論往往會首先探討一罪與數罪的區分標準,學說中依次出現過五種標準:行為標準說(實施一個行為是一罪,實施數個行為為數罪)、法益標準說(侵犯一個法益為一罪,侵犯數個法益為數罪)、犯意標準說(基于一個犯意的為一罪,基于數個犯意的為數罪)、構成要件標準說(符合一個構成要件為一罪,符合數個構成要件或數次符合同一構成要件的為數罪)與犯罪構成標準說(行為符合一個犯罪構成的為一罪,符合數個犯罪構成的為數罪)[1]195。傳統觀點在肯定犯罪構成說的同時,又在分析具體罪數類型時,將該標準棄如敝履。例如,通說認為牽連犯“是指以實施某一犯罪為目的,其方法行為或結果行為又觸犯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態”。我國通說認為,德日的犯罪論體系為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有責性,而“構成要件標準說”(日本通說)僅將構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斷作為區分罪數的標準,忽略了違法性、有責性,失之片面,故不可取。 但“構成要件標準說”中的“構成要件”并非僅指與違法、有責并列的“構成要件”,而是泛指犯罪論體系中的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有責性。因此,我國的“犯罪構成標準說”與日本的“構成要件標準說”并無本質不同。 顯然,牽連犯雖符合了數個犯罪構成,但通說仍將其認定為了一罪[1]211。又如,一個自然意義上的行為犯數罪的為想象競合。雖然想象競合符合了數個不同的犯罪構成,但其僅為“實質的一罪”。
現 代 法 學 丁慧敏:想象競合的功能及其存在根據毫無疑問,自貝林格-李斯特犯罪論體系建立以來,構成要件理論就是大陸法系刑法學界公認的定罪標準;犯罪構成也是我國刑法學界公認的惟一定罪標準,故將構成要件標準說或犯罪構成標準說認定為判斷罪數的標準完全符合犯罪論中的基本共識。但緣何定罪的惟一標準會在牽連犯、想象競合的定罪中失效?為何“一個犯意”、“原因與結果或手段與目的的關系”(牽連犯)、“一個自然意義上的行為”(想象競合)可以取代犯罪構成,成為取舍定罪的標準?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我國的罪數論具有消解犯罪構成定罪功能的作用,即即便行為根據犯罪構成應認定為數罪,也還是可以基于案件事實的特殊性(如“一個自然意義上的行為”、“基于一個犯意,且存在原因與結果或手段與目的的關系”等)被認定為一罪。而這一點正是我國罪數論與德國競合論功能的差異所在。
德國的競合論規定在德國刑法總則第三章“法律后果”的第三節“觸犯數法規的量刑”之下,從其所在章節就可以一目了然地推知,德國的競合論并不涉及定罪,僅關涉量刑。不同于我國罪數論中“琳瑯滿目、眼花繚亂”的各種“犯”,德國競合論基本上呈現出的是條清縷陳的面貌和嚴謹有致的結構,體系僅為“法條競合-想象競合-實質競合”。競合以行為構成數罪為前提,而法條競合屬一罪而非數罪,其徒具競合之表卻無競合之實,故法條競合又被稱為“假性競合”(scheinbare Konkurrenz)、“不真正的競合”(unechte Konkurrenz),想象競合與實質競合才是真正的競合。
“同一行為”(dieselbe Handlung)概念是走入德國競合論堡壘的惟一通道。德國《刑法》第52條規定,“同一行為觸犯數個刑法法規,或數個行為觸犯同一刑法法規的,只判處一個刑罰。觸犯數個刑法法規的,依規定刑罰最重的法規為準。所判刑罰不得輕于數法規中任何一個可適用法規的刑罰”。該“同一行為”是區分想象競合與實質競合的惟一標準:前者是指一個自然意義上的行為實現了不同的構成要件或者多次實現了同一構成要件;后者是指數個自然意義的行為實現了不同的構成要件或多次實現了同一構成要件。“同一行為”并不具有任何定罪功能。第52條中規定的“只判處一個刑罰”并不涉及想象競合的定罪。在定罪階段,仍要根據構成要件將“同一行為”所犯數罪一一定罪,只是在量刑時“判處一個刑罰”,但“所判刑罰不得輕于數法規中任何一個可適用法規的刑罰”。故想象競合與實質競合在定罪階段并無區別,二者均為數罪的量刑規范,只不過想象競合貫徹的是結合原則(Kombinationsprinzip)或者限定的吸收原則(begrenzten Absorptionsprinzip),即按照一重罪的刑罰進行裁量,且受限于“輕法的封鎖作用”(Sperrwirkung des milderenTatbestands),最終的宣告刑不得低于輕罪的最低刑罰(包括附加刑、保安處分等);實質競合貫徹的是“限制加重原則”(Asperationsprinzip),即對所犯的各罪各自定罪量刑后,在最重一罪的宣告刑之上、總和刑期以下決定最終的宣告刑[3]。
概言之,德國的競合論是對數罪的量刑規范(Strafzumessungsrecht),其并不具有定罪功能,定罪仍專屬于犯罪論體系(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有責性)。將我國罪數論升級為競合論的關鍵就在于把定罪歸還給犯罪構成,取消罪數論的定罪功能,將其限定為一種量刑理論。換言之,先根據犯罪構成對所犯數罪一一定罪,后在量刑階段決定相應的量刑規則。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用競合論的理念取代舊的罪數論思維,進而推進我國整個罪數論的成功轉型。
競合論是量刑理論,想象競合作為其中的核心成員,也應僅具量刑功能。以下將從定罪與量刑兩方面著手,對想象競合的功能予以論證。
(二)一罪與數罪之爭
想象競合是一罪還是數罪?如果認為犯罪構成(或構成要件)是認定犯罪的惟一標準,想象競合絕對是數罪。例如,行為人故意開一槍打死一個人、打傷一個人的行為,同時符合了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的犯罪構成,理應成立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如果認為犯罪構成標準僅供遴選哪些犯罪“入圍”,最終應由行為個數決定的話,想象競合只有一個行為,也就僅成立一罪。顯然,在定罪的最終環節,如果犯罪構成必須讓位于行為個數而不能成為定罪的最終標準,就必須說明為何行為個數具有定罪功能?
一個極易混淆視聽的理由是,犯罪是行為,故行為的個數決定犯罪的個數。必須澄清地是,“犯罪是行為”是從事實層面來描述犯罪,并不涉及到任何規范評價問題;一旦要判斷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就必須根據犯罪構成進行評價,“犯罪的個數”就是犯罪構成評價的結果,與事實層面的行為個數并無關系,質言之,事實的描述并不能達到規范的評價結果。行為與行為的個數等屬于案件的事實部分,并不具有規范評價的功能,它們只能成為犯罪構成的評價客體。顯然,通說對想象競合定罪時,同樣用行為個數取代了犯罪構成,這是一種放棄規范對事實的評價,轉而用事實來“評價”事實的不當做法。通說的這一致命缺陷已經被一些新銳學者看破,他們紛紛要求在想象競合的情況下,仍要將定罪功能或規范評價功能歸還給犯罪構成,故新說均主張要將想象競合認定為數罪,“在一個自然行為已經具備了數個犯罪非價內涵,符合數個犯罪構成,為了體現刑法中的充分評價原理,在定罪時理應評價為數罪,同時意味著在判決書主文中應宣告為數罪”[4]。“犯罪構成的評價,不能只拘泥于行為的自然性質, 而應力圖發掘行為中所包含的全部法律意義。換言之,從自然的角度觀察,想象競合犯只有單一的自然行為,但從刑法的角度觀察,想象競合犯的單一自然行為實質上具有多個危害行為的意義”[5]。
另一個十分流行的觀點認為,想象競合之所以為一罪,是因為不能對自然意義上的一個行為進行多重評價,否則就違反了禁止雙重評價的原則[6]。實際上,只要承認刑法的規范評價功能,就肯定可以從不同的規范目的出發,運用多個犯罪構成,對一個自然意義上的行為進行多重評價;一個自然意義上的行為構成一罪還是數罪,取決于刑法規范對該事實的評價結果。“犯罪本身是國家對行為的刑法評價,因而其本身必須遵守哲學上評價論的規律。而哲學上的評價是主體對客體的價值判斷活動,是以主體需要為目的支配下的判斷過程,并非是對客體本然狀態的全部接受。相應地,刑法對行為的評價,同樣并非是對行為客觀本然狀態的全盤接受,而是在評價目的性支配下對自然行為加以判斷的過程”[5]109。想象競合的數罪具有不同的規范保護目的,倘若適用其一而排除其他,就會造成對行為的不法不能全面評價的后果。例如,行為人在飛機上使用暴力搶劫或者使用暴力阻止前往某地的證人出行而危及飛行安全的,僅適用該自然的行為所涉及到的任何一罪而排除他罪,都不足以全面評價行為的不法,都無法完滿地實現立法者訂立上述各罪保護各自法益的目的,即對前者僅適用搶劫罪,就會造成置危害飛行安全的事實于不顧,僅適用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罪,就會造成無視被害人財產損害的后果;對后者僅適用妨害作證罪亦無法照顧到危及飛行安全的事實,僅適用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罪也無法關照到破壞司法程序公正的后果。顯然,為了避免這種捉襟見肘的尷尬,就必須肯定該自然意義上的行為已經構成了數罪,并一一宣告。又如,行為人明知他人提包中裝有槍支與現金而盜竊的,只有肯定該自然意義上的一個行為構成了盜竊罪與盜竊槍支罪兩罪,也才能將該行為同時侵犯他人財產法益與危害公共安全法益的不法性評價殆盡。可見,只有對一個自然行為從相同的規范目的出發反復評價,才違反了定罪中的禁止雙重評價;倘若可以對一個自然行為基于不同的規范目的進行多角度評價,只有將其認定為數罪,才能全面評價行為的不法。
只要承認刑法的規范評價功能,就必須將想象競合認定為數罪,這一點已經被德國想象競合數罪說取代想象競合一罪說的學說更迭所證實。當今德國《刑法》第52條對想象競合的規定可以追溯到1851年的普魯士刑法典草案。基于法律自然主義,早期德國刑法學界認為,犯罪是行為,多個犯罪必然存在多個行為,一個自然意義上的行為只能構成一罪。在該觀念的指導下,想象競合也理所當然地被認定為一罪。該一罪理論(Einheitstheorie)認為,自然意義上的一個行為構成的各罪共同組成了一個更大的罪名,如行為人一槍打傷一人并打碎名貴花瓶時,成立“傷害且損毀器物罪”。 但隨著毫無價值判斷的自然主義刑法理念的淡出,認為想象競合僅為一罪的觀點也就不攻自破。當前,強調刑法規范評價機能的刑法觀認為,應區分競合論與犯罪論中的行為概念,前者是自然意義上的一個行為,而后者與規范評價緊密相關。自然意義上的一個行為完全可能是規范評價上的數罪,這是因為“一個事物具有多個屬性,其各個屬性均可能成為法律評價的對象,這一點取決于規范的目的。”[7]故德國的判例與通說已經毫無爭議地將想象競合理解為一種對數罪的量刑規則[3]798。
即使在同樣倡導罪數論的日本,想象競合也為數罪。日本《刑法(總則)》第9章“并合罪”第54條規定了想象競合與牽連犯,“一個行為同時觸犯了兩個以上的罪名,以及作為犯罪的手段或結果的行為觸犯了其他罪名的,依照最重的刑罰處罰”。日本通說將想象競合與牽連犯稱為“科刑上的一罪”,該稱謂是對二者在量刑時不數罪并罰這一特征的概括。在區分一罪與數罪的標準上,日本通說持構成要件標準說,這一點與我國通說并無不同;但日本通說與判例將該標準一以貫之地堅守到了想象競合與牽連犯的定罪之中[8]。這與我國通說在這些問題上放棄犯罪構成標準,轉而在犯罪構成之外尋求其他定罪標準形成了較大反差。
綜上,競合論就是對數罪量刑的理論工具,其中,想象競合是對一個行為犯數罪的量刑理論。在定罪階段,犯罪構成仍是認定犯罪的惟一標準,應根據犯罪構成將想象競合觸犯的數罪一一定罪。
二、想象競合的存在根據
雖然新銳觀點均認為想象競合為數罪,但在量刑問題上卻亦莫衷一是:一派堅持傳統做法,認為想象競合雖為數罪,但在“想象競合犯的場合下,行為人實施的同一行為符合數個犯罪構成,其反規范意識形成于同一契機,與在并罰數罪場合下行為人反規范意識的分別獨立形成相比有所減弱,非難程度也有所降低,為了體現這種差別,應在肯定行為成立數罪的前提下,在刑罰的量定上與并罰數罪有所區分,而從一重處斷便是這種刑罰量定效果的體現”[4]56,故對想象競合僅能按照一重罪處刑,且并不需要考慮輕罪的最低刑與附加刑。另一派主張對想象競合數罪并罰,理由有四:一是既然想象競合為數罪,理所當然應數罪并罰;二是只有數罪并罰才能做到罪刑均衡;三是只有數罪并罰才能維持刑法規范邏輯結構的完整性,才能貫徹罪刑法定原則;四是數罪并罰是英美法系國家以及俄羅斯的通行做法[5]113。
想象競合既為數罪,為何在量刑中不能數罪并罰?況且,一些國家和地區確實會對想象競合數罪并罰。以刑法典中是否對想象競合與實質競合采取了不同的處罰方式為標準,競合論的立法體例被分為區別原則與單一原則。前者是指刑法對數個自然意義上的行為觸犯數罪與一個自然意義的行為觸犯數罪規定了不同的量刑規則,即區別想象競合與實質競合。采取該立法例的國家與地區包括德國、日本、我國臺灣地區等。后者是指刑法并沒有規定一個自然意義上的行為觸犯數罪與數個自然意義上的行為觸犯數罪適用不同的量刑規則。采取該立法模式的有1974年奧地利刑法、1937年瑞士刑法、俄羅斯刑法等。其中,俄羅斯現行刑法典與我國澳門地區刑法規范均規定對想象競合實施數罪并罰,故這些國家和地區并沒有想象競合的存在空間。即使在德日,也不乏要求對想象競合實施數罪并罰的觀點。例如,德國在1919年修訂《刑法》過程中,就曾有提案要求將想象競合與實質競合適用相同的量刑原則;又如,日本在1922年修訂《刑法》時,也有人提出應根據具體情節來靈活量刑,既可以對一個自然行為犯數罪(想象競合)情形實施數罪并罰,也可以對數個自然行為犯數罪的情形(并合罪)只按照其中一罪的刑罰處刑[9]。但這樣的提案均因未受到立法者的青睞而最終未能成文。
如上所述,想象競合是對一個自然意義上的行為所犯數罪如何量刑的理論工具。眾所周知,在數個行為犯數罪的情況下,要對數罪實施并罰;倘若對一個自然意義上的行為犯數罪也并罰的話,二者儼然成為了完全相同的量刑規則,也就從根本上喪失了區分實質競合與想象競合的必要性。質言之,主張對想象競合數罪并罰,就意味著否定想象競合理論本身。故想象競合量刑原則的爭論,實則關涉想象競合的存亡。要想保留想象競合,就必須回答:想象競合既為數罪,又緣何不應并罰?該問題的回答正是想象競合理論的存在根據。
(一)責任減少說、違法減少說、違法與責任減少說分庭抗禮
如上所述,我國有學者將想象競合不能并罰歸結為“反規范意識形成于同一契機”,故行為人的責任減輕。該論可謂我國刑法學界探討想象競合正當化根據的先驅。與我國僅有一把星星之火的理論匱乏狀態不同,德日刑法學界對該問題的討論已經進入了各方觀點分庭抗禮,理論研究碩果累累的完善期。大體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幾種學說:
一是責任減少說。早在1909年,德國學者鮑姆戈登(Baumgarten)認為,在想象競合的一個行為中,行為人僅有一次對法秩序的反抗。“具有非難可能性的內心態度存在于外在行為之前,正是在那個時間點上,存在著對法命令尊重或無視的意思的可能性。在想象競合的情況下,如開一槍打死一人、打傷一人的,如果行為人是出于想開槍打死人或者打傷人的故意而開槍時,對殺人罪規范的破壞就不能與對傷害罪規范的遵守同時存在。行為人在打算殺人時,其對他人身體傷害的意思絕不是一個獨立于殺人意思之外的責任形式。”參見:只木誠罪數論の研究[M]東京:成文堂,2009:19日本刑法學者平野龍一教授亦持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在一個意思活動的情況下,僅存在一次規范意識的突破,兩個意思活動的情形下存在兩次規范意識的突破。想象競合的情形下僅存在一個意思活動,也就僅有一次規范意識的突破,故其較有多次意思活動、多次規范意識突破的并合罪(實質競合)要減輕處罰[10]。
二是違法減少說。德國學者普珀(Puppe)教授極力倡導該種觀點。普珀以行為所實現的多個構成要件之間是否具有不法親緣性為想象競合的判斷標準。她認為,應從德國《刑法》第46條第3項“雙重評價禁止”的規定中導出想象競合的處罰原則。德國《刑法》第46條第3款規定:在定罪時評價過的法定構成要件要素,在量刑時不予考慮。 詳言之,在所實現的數罪之間具有不法親緣或者不法類似(die Unrechtsverwandtschaft)關系時,根據量刑中禁止雙重評價的原則,為了避免對同一不法要素多次評價,量刑時只能奉行限定的吸收原則,即按照最重一罪量刑,但宣告刑不得低于輕罪的最低刑。例如,通過行使偽造的文書詐騙錢財的行為構成詐騙罪與行使偽造文書罪,由于欺騙是該二罪的一個共通的構成要件要素,故成立想象競合。又如,搶劫的同時傷害被害人的,成立搶劫罪與傷害罪的想象競合,因為對被害人實施暴力是搶劫罪與傷害罪共通的不法要素。另一方面,倘若行為實現的數罪間不具有不法的親緣關系,即使僅有一個自然意義上的行為,也應認定為實質競合,應在量刑中適用數罪并罰的原則。例如,行為人扔出去一塊石頭,打碎他人貴重物品的同時,也打傷被害人的,并不成立毀損財物罪與傷害罪的想象競合。因為毀損財物罪與傷害罪之間沒有任何關系,故應為兩罪的實質競合。不法類似或者不法親緣關系的判斷并不適用于高度專屬的個人法益,即一行為同時侵犯了多個高度專屬的個人法益時,成立實質競合而非想象競合。例如,行為人扔了一個手榴彈炸死了數人,此時不能以數個殺人罪之間具備不法的類似關系就認定為想象競合。生命法益屬于高度專屬的個人法益,侵害的數個生命法益之間并不存在不法類似,故不為想象競合,應按照實質競合實行數罪并罰。
普珀反對上述責任減少說,她指出,責任主要的功能在于揭示行為主體與不法的關系,即行為主體要對其實施的不法負有罪責。“在論及想象競合與實質競合的區別時,必須與強調兩種競合形式具有不同的責任要素的觀點訣別。”[11]
提出該論伊始,普珀曾表示自己的理論以目的論解釋為歸宿。在她看來,正當的目的論解釋優先于歷史解釋與論理解釋。她指出,立法者的確有權力要求將一個觸犯了數個不具有不法類似性罪名的行為,在量刑時適用限定的吸收原則,但如果不適用該立法反而會使處罰更加均衡,能夠在與其他事例的比較中得到更為妥當的結論的話,就可以通過法律解釋的原理來規避該條的適用[11] 176。
通說對普珀的想象競合理論提出了三點批評:一是該論不符合德國《刑法》第52條的字面含義,該法條并沒有要求行為所侵害的各個構成要件之間必須具備不法的類似性。二是“不法類似”的概念十分抽象,較傳統觀點中的“同一行為”更不易把握。三是仍需要為想象競合提出進一步的前提,因為不法類似性標準是對已經發生的數個構成要件之間的判斷,但是否需要該數個構成要件同時發生,或是否為同一個行為引起等仍不夠明朗[3]820。
經過進一步的探索與反思,近年來,普珀從解釋德國《刑法》第52條中的“同一行為”著手,謀求自身的理論與該規定的統一,或者可以說,謀求一種與德國傳統觀點截然不同的對“同一行為”的解釋。由于“不法親緣”或者“不法類似”這樣的概念備受爭議,普珀用“結果單一”(die Erfolgeihheit)或者“不法單一”(die Unrechtseinheit)取而代之。但這只是用語的代換而已,“結果單一”的示例與之前“不法親緣”的示例并無不同。傳統觀點根據日常用語(Alltagssprachgebrauch)將德國《刑法》第52條中規定的“同一行為”理解為一個自然意義上的身體活動。普珀認為通說忽略了在日常用語中,人們往往會通過行為是否引起或者應該引起一個結果來理解行為的個數。即在日常用語中,對“一個行為”的理解也完全可能建立在一個結果之上:其既可能是一個輕微的身體動作,如開槍扣動扳機時手指的彎曲;也可能是相當復雜而漫長的活動,如建筑高樓大廈或者寫一部長篇小說。因此,即使根據日常用語,也完全可以將德國《刑法》第52條中的“同一行為”建立在結果單一之上[11] 258-259。同樣,日常生活經驗表明,除了馬戲團等雜技表演行為之外,很少有人能夠通過一個行為同時完成兩個內容完全不同的事情。相應地,《刑法》第52條的立法不應該建立在這樣的小概率事件上,而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通過結果單一來理解行為個數的生活經驗之上[11] 257。普珀進一步明確指出,即使不具有時間的同一性或者身體動作的部分或者完全的一致性,只要具有結果的單一性,就可以認定為《刑法》第52條規定的“同一行為”;相反,即使同一個身體動作同時導致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結果,因其不具備結果的單一性,也不能認定為《刑法》第52條的“同一行為”,此時應將其理解為《刑法》第53條(實質競合)中的多個行為;不同的身體動作導致的結果單一,也應認定為《刑法》第52條中的“同一行為”,例如,德國傳統觀點將不可罰的事前行為與不可罰的事后行為認定為法條競合中的吸收關系,但普珀認為,由于此時行為產生了結果單一,故應將其認定為想象競合。有觀點認為,Puppe提出的結果單一(不法單一)理論,混淆了想象競合與法條競合的界限,甚至會使得法條競合變得多余。實際上,普珀教授并沒有混淆想象競合與法條競合:普珀通過不法的同一性(結果單一)來區分想象競合與實質競合;同時,用不法的同一性(結果單一)程度來區分想象競合與法條競合。普珀一再強調,為了保護被告人的利益,必須嚴格界分想象競合與法條競合。
日本學者井田良教授也認為,相較并合罪而言,想象競合中數罪的違法減輕。與普珀教授的觀點不同的是,井田良教授并不是從“結果單一”等來把握不法減輕的。他提出,為了避免重復評價與違法性相關的量刑情節,故不能對想象競合數罪并罰。例如,行為人通過一發子彈打死A、B二人,此時成立兩個殺人罪的想象競合;倘若對兩罪數罪并罰,就會分別在對兩個殺人罪量刑時反復考慮一個開槍行為所涉及到的不法量刑情節,因此就存在對同一不法量刑情節進行雙重評價的風險。故之所以不對想象競合數罪并罰,就在于與行為所犯數罪的不法量刑情節高度重合[12]。
不難看出,雖然普珀教授與井田良教授均主張不法減少說,但二者的立足點并不相同,前者立足于不法構成要件要素的層面,后者立足于與不法相關的量刑情節層面;前者以不法相似性或者結果單一為要件,極大地限制了想象競合的成立范圍,而后者并不會導致這樣的結果。
三是不法或責任均減少說。作為該說的代表人,德國學者威爾勒(Werle)也認為,競合論的基礎是德國《刑法》第46條第3款規定的量刑中的“雙重評價禁止”,與普珀不同的是,威爾勒認為,為了滿足行為責任主義,不僅要避免不法的雙重評價,還要避免責任的雙重評價。威爾勒認為,自1871年萊比錫刑法以來,德國刑法明確規定想象競合的前提是“同一行為”,顯然,立法已經預見到了一個自然意義上的行為可能侵犯多個刑罰法規,卻沒有限定是否這些刑罰法規應具有不法的類似,這就表明立法者認為,想象競合與實質競合具有不同的法律效果是源于二者自然形態上的差異;這種差異會導致想象競合較實質競合的不法或責任的減少。普珀列舉的使用偽造文書詐騙的案例屬于不法減少的情形;與實質競合具有相同的不法程度,但責任減少的情形也是存在的,如行為人用他人貴重的花瓶將被害人砸成重傷,在行為當時,行為人不可能在違反此規范的同時遵守彼規范,故行為人只有一個企圖或者決意,與實質競合相比,其責任明顯減少[9]25。
(二)想象競合的存在根據:量刑情節的高度重合
量刑適當與否離不開刑罰正當化的根據。一般認為,報應的正義性與預防犯罪(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是刑罰的正當化根據。前者對應量刑中的責任刑(或量刑責任);后者對應預防刑,二者共同組成了量刑的兩個部分。其中,責任刑(或量刑責任)取決于犯罪行為的不法與有責;在德國,通說認為量刑責任(Strafzumessungsschuld)雖然建立在犯罪論的責任概念之上,但卻不能將二者完全等同。量刑責任取決于行為的不法強度及其非難可能性,即不法與有責共同為量刑責任提供依據。(參見:Gerhard Schfter. Praxis der Strafzumessung[M].2Aufl. München: C.H. Beck, 2001:123.)日本學者主張的責任刑中的“責任”僅是犯罪論中的責任,其理論根據是刑法中的責任主義。責任主義作為與罪刑法定主義并列的限制國家刑罰權的一項原則,要求處罰的必要性不得凌駕于行為人的責任之上。表面上看,日本通說主張的責任刑與行為不法毫不相干,但基于責任本身就是對不法的非難,不法的程度能夠反映責任的輕重。故不法還是能夠迂回、間接地影響責任刑的確定。 預防刑則由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的需要來決定。故量刑得減的原因應圍繞責任刑的基礎(不法與有責)與預防刑的基礎(特殊預防必要性與一般預防必要性)展開。
“責任減少說”、“不法減少說”、及“不法或責任減少說”都旨在論證想象競合的情況下責任刑有所減少。但責任減少說(亦包括“不法或責任減少說”中的責任減少部分)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責任減少,并不能說明緣何想象競合較實質競合的責任刑減少。理由如下:
首先,有否認想象競合成立數罪之虞。必須正視的一點是,既然承認想象競合為數罪,就意味著必須承認能夠對該行為實現的數個不法均進行主觀歸責,簡言之,有數罪勢必有數責。但責任減少說認為,在想象競合的情況下,僅有“一個規范違反的意識”、“僅有一次規范意識的突破”,這意味著行為人只能對行為導致的其中一罪承擔罪責,因而也就僅能成立一罪。但主張責任減少說的學者又往往認為想象競合為數罪[10]205。
其次,論證方法與結論已然脫離了規范責任論。自規范責任論取代心理責任論以來,刑法學已經不再從心理關系或者心理事實方面把握責任,而是強調對心理事實或心理關系的規范評價,即評價行為人對已經發生的不法是否具有非難可能性。詳言之,刑法規范的判斷遵循從不法到責任的順序,在已經認定行為具有符合構成要件的不法后,責任的判斷就是從非難可能性的角度出發,來規范地認定是否可以將已經實施的不法歸責于行為人。在規范責任論中,判斷責任是否減少,就需要對比責任的形式(故意與過失、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德國學者一般不將故意與過失認定為責任要素,而是將其納入不法中討論。在這樣的犯罪論體系下,責任的判斷就剩下責任能力、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期待可能性等十分抽象的要素。而這些要素又往往僅涉及到有或者無的判斷,在量上難以把握且差異有限。 、責任能力(完全責任能力、限制責任能力)、違法性認識可能性以及期待可能性等來得出責任輕重的結論。只有具體罪名中規定了構成該罪需要有具體的犯罪動機或者犯罪目的時,犯罪動機與犯罪目的才能成為影響責任刑的責任要素。當特定的動機與目的并非某罪必備要素時,目的與動機高尚與否、卑鄙與否僅影響特殊預防。(參見:張明楷.刑法學[M].4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507.) 反觀上述各類責任減輕說,“意思活動”、“決意”、“反規范意識形成于同一契機”等并不具備規范責任的特質,而是一種單純對行為人心理狀態的描述;“此規范的違反與彼規范的違反之間,并沒有兼顧的可能性”的說法也不涉及對期待可能性的拷問,因為既然已經承認行為構成數罪,毫無疑問的是,行為人對于其觸犯的數罪均具有期待可能性。從論證方法到具體結論,責任減少說都呈現出了脫離刑法規范評價的自然主義傾向,顯然,在倡導規范責任論的今天,該說已經不合時宜。
再次,將特殊預防必要性的情節當成了責任形式。如上所述,“責任減少說”提出的“意思活動”、“決意”、“反規范意識形成于同一契機”等概念不具有規范責任的意義,但在具體案件中,這些要素確實能夠反映出行為人特殊預防性的大小。換言之,上述要素并不能為想象競合的責任刑減少提供依據,但卻影響預防刑。這是因為,行為人犯罪前后以及犯罪當時的“意思活動”、“反規范意識形成的契機”、“決意”等能夠反映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或者再犯可能性。但特殊預防的大小必須聯系具體案件進行具體判斷,并不能脫離案件一概而論,詳言之,并不能說通過數個自然行為犯數罪的行為人的特殊預防必要性高于通過一個自然行為犯數罪的行為人。例如,行為人在深思熟慮后,通過一個行為犯數罪的,可以看出行為人比較膽大妄為;而通過數個行為犯數罪的行為人卻完全可能一直猶豫不決,后一行為人特殊預防的必要性并不必然高于前者。
犯罪構成是犯罪的最低標準,故定罪時僅就行為是否達到了成立某一犯罪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不法與有責進行評價。量刑時,就需要全面考慮犯罪事實中所有的不法、有責情節,以及影響特殊預防必要性程度的情節(行為人犯前、犯中、犯后決定特殊預防大小的各類情節)。顯然,量刑情節要較定罪的構成要件要素寬泛得多。由于想象競合的數罪僅由一個自然行為引起,倘若對數罪一一量刑,就會發現數罪的量刑情節必定高度重合,根本無法將各罪的量刑情節相互剝離,故難以保證準確的量刑。量刑情節的高度重合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在一些情況下,影響犯罪不法程度的量刑情節高度重合。在某些想象競合的數罪中,一些不法構成要件要素相同或者相似,倘若對各罪分別量刑,勢必造成對這些不法要素的重復評價。例如,行為人使用暴力妨害公務并造成公務人員受傷的,被認定為故意傷害罪與妨害公務罪的想象競合。倘若對二罪數罪并罰,既會在妨害公務罪的量刑時考慮“暴力”這一不法要素,又會在故意傷害罪的量刑中對此要素再做評價。這就違背了量刑時的禁止雙重評價原則。
“不法程度的量刑情節重合”與普珀教授的理論存在很大差異。無論是普珀早期提出的不法相似性,還是近期提出的結果單一,都力圖通過構成要件不法要素的部分重合限制想象競合的成立范圍。而本文并不認為只有不法要素部分重合才能成立想象競合。
另一方面,特殊預防情節的高度重合。量刑時通常會考慮的特殊預防情節包括:犯罪的起因、被害人有無過錯、行為人的動機、犯罪的手段、行為人犯罪之后的態度等。如果對想象競合的各罪數罪并罰,意味著對各罪要分別量刑,這就不可避免會重復考慮行為人在同一行為前后及行為當時的各類特殊預防的情節。再回到普珀列舉的投石案。顯然,普珀并沒有重視行為人罪前、罪中、罪后的各種影響特別預防必要性大小的情節。假如甲經常受到乙的嘲弄,某日,甲再次遭受乙的嘲弄時無法遏制心中怒火,在用石頭砸乙的同時,既重傷了乙又損壞了他人的的貴重財物。雖然甲的行為同時構成了故意傷害罪與故意毀壞財物罪,但倘若對兩罪分別量刑,就會在量刑中不可避免地重復評價甲的行為動機、乙的過錯、甲在行為后的表現等影響預防刑的情節,從而違背了量刑中的禁止重復評價的原則。
三、想象競合的量刑規則
雖不能對想象競合數罪并罰,但并不意味著較輕一罪的法定刑在量刑時沒有任何的“發言權”。
想象競合在德國的發展歷程,證實了在定罪中堅持想象競合一罪說,在量刑時就不能考慮輕法的封鎖效應;一旦將想象競合認定為數罪,在量刑時就必須適用輕法的封鎖效應:以是否承認想象競合輕法的封鎖效應為界限,德國對想象競合的處罰原則經歷了嚴格的吸收原則(strenge Absorptionsprinzip)到限定吸收原則(begrenzten Absorptionsprinzip)兩個階段[14]。前者僅依據想象競合中的一重罪量刑,并不承認輕法的封鎖效應;后者又稱為結合原則(Kombinationsprinzip),承認較輕一罪的法定刑具有封鎖效應。在適用嚴格的吸收原則階段,當時的通說與判例將想象競合認定為一罪,因此在定罪與量刑的兩個階段,均嚴格排斥輕法的適用[13]。隨著一罪說的淘汰與數罪說通說地位的確立,1939年德國帝國法院以判決的形式肯定了想象競合為數罪,并同時確立了想象競合中輕法的封鎖效應。該判例之后,通說與判例均承認想象競合中輕法的封鎖效應,該理論與實踐最終推動德國立法將想象競合的輕法封鎖效應規定于《刑法》第52條之中,成為法定量刑規則[15]。
又如,日本通說與判例均承認想象競合為數罪,雖然日本刑法并沒有規定想象競合的輕法封鎖效應,日本現行《刑法》第54條規定想象競合的處罰原則是“按照其最重的刑罰處斷”。 但日本法院在量刑時亦踐行該量刑規則。例如,2004年6月到2005年1月間,被告人在其經營的餐館內容留了3名外國婦女賣淫。其行為同時構成了《職業安定法》第63條第2款與《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第73條第2款規定的犯罪,兩罪成立想象競合,前罪的法定刑是1年以上10年以下的懲役或者20萬日元以上300萬日元以下的罰金;后罪的法定刑是3年以下懲役,單處或者并處 200萬日元以下罰金。東京地方法院一審認定,行為構成以上兩罪,并判處一年零兩個月的懲役。但檢察院認為法院量刑不當提起上訴。日本最高法院認為,雖然日本《刑法》第54條僅規定了“按照其最重的刑罰處斷”,但其含有不得低于想象競合中其他法條的最低刑罰處刑的意思,故原判的量刑并不妥當[16]。法院的做法也得到了學界的大力肯定[12]。
由此可見,只要將想象競合認定為數罪,在量刑過程中,輕罪的法定刑仍具有兜底性的發言權,即要求最終的宣告刑不得低于輕罪的法定最低刑,同時必須考慮輕罪的附加刑。再以盜竊價值3000元的使用中的電力設備行為為例,在判決中,應宣告該行為同時構成了盜竊罪與破壞電力設備罪。犯罪數額為3000元時,雖然盜竊罪的法定刑低于破壞電力設備罪,但破壞電力設備罪沒有規定罰金刑,故根據輕法的封鎖效應,在按照破壞電力設備罪的法定刑量刑時,還需要根據盜竊罪的法定刑,對行為人判處罰金。ML
參考文獻:
[1] 高銘暄,馬克昌. 刑法學[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198.
[2] 陳興良. 罪數論到競合論——一個學術史的考察[J].現代法學 ,2011, (3): 111.
[3] Claus Roxin. Strafrecht AT, Bd.II[M]. München: C.H.Beck,2003:800.
[4] 王明輝,唐煜楓. 非并罰數罪研究[J]. 法商研究, 2010, (1):55
[5] 莊勁. 想象的數罪還是實質的數罪——論想象競合犯應該數罪并罰[J]. 現代法學, 2006, (2):108.
[6] 陳興良. 禁止雙重評價研究[J]. 現代法學, 1994, (6):11.
[7] Günther Jakob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Die Grundlagen und die Zurechenungslehre[M]. 2 Aufl. Berlin:Walter de Grayter,1991:892.
[8]井田良. 刑法總論的問題構造[M]. 東京:成文堂, 2005:461.
[9]只木誠. 罪數論の研究[M]. 東京:成文堂, 2009:30.
[10]平野龍一. 犯罪論の諸問題「上」総論[M]. 東京:有斐閣, 1981:205.
[11] IngeborgPuppe.Idealkonkurrenz und Einzelverbrechen[M].Berlin: Duncker und Humblot, 1979:176.
[12]井田良. 講義刑法學·總論[M]. 東京:有斐閣, 2008:156.
[13] Hans-Heinrich Jescheck. Die Konkurrenz[J].Zeitschrift die gesamte Strafrecht Swissen Schaft,1956,(67):531.
[14]鄭超.論法律擬制思維在刑法中的重要性[J].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1,(6):21.
[15] 陳志輝. 刑法上的法條競合[M]. 臺北:作者發行,1998:25.
[16]村瀬正明. 観念的競合の関係にある二罪の一方の法定刑が懲役又は罰金,もう一方が懲役若しくは罰金又はそれらの裁量的併科である場合の「最も重い刑により処斷する」の意義について判示し,原判決を破棄した事例[J]. 研修,2005, (4):95.
The Function of Conceptual Concurrence and Its Foundation
DING Huimin
(Law Schoo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To transform the multiple crimes doctrine into concurrence doctrine, it is essential to convert the convicting and sentencing functions of multiple crimes doctrine into the sentencing function of concurrence doctrine. As the most critical component of concurrence doctrine, conceptual concurrence should be deemed as a theory on how to sentence reasonably when the same act has been convicted of multiple crimes.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are still the sole criterion for testing whether the same act is one or more than one crime(s), and thus all the crimes in conceptual concurrence should be convicted in the judgment. If the consolidated punishments have been announced in conceptual concurrence,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cept of conceptual concurrence is pointless; the foundation of conceptual concurrence is the reason why the multiple convictions should not be applied. During the sentencing for multiple crimes in conceptual concurrence, the sentencing circumstances of illegality and special deterrence overlap. Consolidated punishments would probably result in the doubleevaluation of those circumstances, which would go against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defendants. Although the final sentence should be mainly based on the aggravated crime, the minimum punishment of the mitigating crimes remains its “voice” in the final sentence. The final sentence should not be less than the minimum punishment of the mitigating crime, and its supplementary punishments should be considered too.
Key Words: concurrence doctrine; conceptual concurrence; norm of sentencing; foundation of conceptual concurrence
本文責任編輯:周玉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