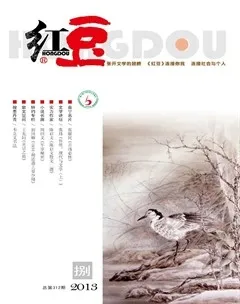夏陽小小說二題
馬不停蹄的憂傷
它們相遇,是在月亮湖,在那個仲夏之夜。
仲夏之夜,月亮湖,像天上那彎明月憂傷的影子,靜靜地泊在騰格里沙漠的懷抱里。清澈澄凈的湖面上,微風過處,銀光四溢。它站在湖邊,望著湖里自己的倒影發呆。它是一匹雄性野馬。
野馬即將掉頭離去時,聽見身后傳來一陣得得的馬蹄聲。一匹母馬在離它不遠的地方止住腳步,呼吸急促,目光異樣地望著自己。銀色的月光下,野馬驚呆了——這是一匹俊美健碩的母馬,通身雪白,鬃發飄逸。母馬的眼里,一團欲火,正在恣意地燃燒。
野馬朝母馬大膽地奔了過去。它們沒有說一句話,只有無休無止的纏綿。這時,任何話都是多余的。
天地之間頓時暗淡,月亮羞紅著臉,躲在云彩后面不肯出來。當月亮再一次露出小臉兒時,野馬和母馬已經肩并肩,在湖邊小徑上散步,彼此說著悄悄話。
母馬問,你家住哪兒?
野馬嘆了口氣,幽幽地說,我無家可歸,被父親趕出來了。你瞧我身上,傷痕累累。
母馬目光濕潤,說,去我那里吧,我家有吃有住,主人可好了。
野馬沒有吱聲,目光越過湖面,悵然地望著遠處的沙漠。遠處的沙漠,在如水的月光下,舒展綿延開來,直抵天際。
第二天清晨,巴勒圖發現失蹤一夜的母馬竟然自行回來了,還帶回一匹高大威猛的公野馬。兩匹馬一前一后,邁著小碎步,耳鬢廝磨,乖乖地進了馬廄。巴勒圖樂壞了,激動地對旁人說,它要是和我家的母馬配種,產下的馬駒子,那可是正統的汗血寶馬。到時候養大了,獻給沐王爺,我就當官發財了。
巴勒圖把野馬當寶貝一樣精心喂養,連做夢都笑出了聲。
三天后的深夜,又是一輪明月浮在大漠之上。野馬站在馬廄的柵欄邊,望著屋外漫天黃沙,飽含淚水。母馬小心地問,你在想家?
不是。我不習慣這里,不堪忍受這種養尊處優的生活。我已經下定決心,帶你走。
我不去!沙漠里太艱苦了,一年四季,一點生活的保障都沒有,無論是寒冬酷暑,一天找不到吃食就得挨餓。你看我這里多好,干凈衛生,一日三餐,主人會定時供應。
我承認你這里條件是不錯。但真正的快樂,是馬不停蹄的理想,是天馬行空的自由,是奔跑在藍天白云下,盡情地做自己的上帝。你看看現在,豢養在這小小的馬廄里,整天小心翼翼地看主人的眼色行事,行尸走肉地活著。這種生活,讓我憂傷。我的憂傷,你不懂……
兩匹馬互不相讓,爭吵不休。
最終,野馬推開母馬,掙脫韁繩,沖出馬廄,在月下急速地拉成一條黑線,消失在茫茫的大漠深處。它的身后,母馬嗚咽著,咆哮著,凄厲的嘶鳴聲,久久不散。
近百年后的一個午夜,東莞城中村的一間出租屋里,一個叫夏陽的單身男人翻閱《阿拉善左旗志》時,讀到一段這樣的文字:
民國三年仲夏,巴彥浩特鎮巴勒圖家一母馬發情難耐,深夜出逃于野。翌日晨,攜一普氏雄性野馬返家,轟動一時。三天后,野馬沖出馬廄,不告而別。數月后,母馬產下一汗血寶馬駒。然寶駒長大,終日對望月亮湖,形銷骨立,郁郁而亡。
讀到此處,夏陽已是淚流滿面。他坐在陽臺上,遙望北方幽藍的夜空,久久地,一動不動。他手里的煙頭,明明滅滅。
一地煙頭后,他掏出手機,撥通了一個電話號碼。他說,你還好嗎?我……我想回家。
電話那頭,遲疑了一會兒,響起一個凄涼的聲音,你不是說,你的憂傷,我不懂嗎?
夏陽孩子般嗚嗚地哭了。他哽咽著說,都三十年了,你居然還記得那句話啊。我老了,也累了。現在,我好想回到你的身邊……他不能想象那匹曠野深處的雄性野馬,垂暮之年是否真的還不思回頭。
電話那頭,泣不成聲。
偶然
偶然,男人把女人的肚子搞大了。非正兒八經的夫妻,攤上這等破事兒,自然是上醫院了。
和很多故事的版本一樣,女人從手術臺下來時,男人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陌生的女人。還好,這女人不是男人的老婆,而是男人花錢雇來的月嫂。
女人氣咻咻地掏出手機,一邊哭一邊質問男人,你還有沒有人性?我就問你一句,你還有沒有人性?公司再忙,也不缺你這半天啊……最后,女人徹底惱了,惡狠狠地罵道,混蛋,你去死吧!
女人仰面癱在座椅上,泣不成聲。雇來的月嫂,柔聲相勸,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女人一個勁地搖頭,虛弱地說,今年,我27歲,真的好想做媽媽,可是養不起,一個人養不起。你不知道,他一直在騙我。
平心而論,男人還沒有壞到家。男人確實是有事脫不了身。早在兩天前,女人告訴男人,和醫生約好了今天下午做人流。男人就暗自叫苦不迭,但不敢說不。為了說服女人放棄這個孩子,他可是費了姥姥勁,如果改動時間,女人一旦變卦就麻煩大了。
下午兩點,男人筆直地站在手術室門口,一臉溫柔。待女人被推進去后,他則一路小跑來到樓下,對中介推薦來的月嫂氣喘吁吁地交代了幾句,便風馳電掣,駕車狂奔到達市政府。還好,沒有遲到。待他剛剛坐定,還來不及擦去滿頭大汗,招標會準時開始了。
招標會的主要內容是答辯專家評審組的咨詢。你懂的,所謂專家咨詢,只是走個過場,男人幕后的老板,早把具有決策權的領導搞定了。但是,專家評審組對男人的表現很不滿意。男人昔日神色自若妙趣橫生的優雅風度蕩然無存。男人一身汗涔涔的,像個小學生一樣結結巴巴,甚至答非所問。更要命的是,男人中途好幾次停頓下來接聽手機,讓一幫專家非常惱怒。
男人也是迫不得已,他不敢關機。他知道女人的性格,一旦關機,女人說不定會從醫院的八樓直接跳下去。男人只能在眾目睽睽之下,面對手機用最小的聲音嘀咕道,我是公司真有事,你別生氣,回去再解釋好了。說完,掛斷手機,愣怔了幾秒鐘,一臉歉意地繼續闡述專家剛才的提問。還沒等男人說上幾句,手機又響了,盡管是靜音,但嗡嗡的震動聲在偌大的會議廳里不絕于耳。男人不得不掐斷自己的話,側過身,貓著腰,對著手機一臉猥瑣。如此,反復了好幾次,當聽到女人在手機那端破口大罵“你混蛋!你去死吧”,男人心一橫,真的關機了。男人非常懊悔,為什么不動員女人改個時間,或者不把手機帶進會場也不是不可以呀。男人心里無比酸楚,甚至痛苦地想,報應,五年積累下來的報應。
接下來的過程,手機是關機了,但男人的表現還是不盡如人意,心不在焉,疲于應付。一幫專家面面相覷,深感不可思議——一個三千萬元的市政亮化工程招標會,竟然有人會視為兒戲。
招標會結束,雖然結果還未揭曉,但男人糟糕的表現,讓幕后的老板勃然大怒。老板在電話里吼道,混蛋,快到嘴的肥肉,竟然被你搞砸了!
男人摸了摸臉上,感覺火辣辣的。男人能夠想象,如果老板站在面前,會毫不遲疑地給他兩記耳光。男人支吾了半天,一咬牙,說,對不起,我……我母親病危,正在醫院急救。
老板停頓了一下,但依然嚴厲地說,作為一個做大事的男人,一個近千人公司的老總,這個可以當借口嗎?你要知道,為這事兒,我光打點就兩百多萬。
男人見對方口氣有所緩和,便說,一切還沒結束,我們還是想辦法補救吧。顯然,男人的口氣有些輕描淡寫,把對方激怒了。對方又提高了嗓門,補救?補救個屁呀!
那怎么辦?
你去死吧!
很遺憾,一語成讖,男人真的死了。不過,男人的死有些偶然。他在回家的路上,駕車途經東部快速干線時,因車胎突然爆裂而失去控制,墜下高架橋,車毀人亡。
其實,那時男人的心情好了很多。女人小他十幾歲,在同一個被窩里滾了五年,不求任何名分,挺不容易的。女人也不是刁蠻無理,否則怎么會答應做人流呢?想想也是,女人從手術臺上下來,不見了罪魁禍首,那般孤獨無靠的滋味,豈能是一個弱女子承受的?男人想到這些,心里頓時涌起一股柔柔的疼,覺得自己虧欠女人的實在是太多了。
男人同時也想,自己今天的表現確實過于荒唐,老板發發脾氣,也是可以理解的。好在一切還沒有到覆水難收的絕境,老板的背景那么深,絕對有挽救的余地。要不明天挨個去拜訪一下專家評審組成員,私下做點工作,一切將會峰回路轉。專家是專家,不是傻子,肯定明白這只是走走過場,最終還是上頭說了算。男人發動車時,信心百倍,覺得勝券在握。他路過一家燉品店時,特意打包了一罐熱乎乎的雞湯,想給女人好好補一補。
但是,男人還是死了。男人的死,讓兩個人在內心深處長久地自責不已。一個是女人。女人回想平日里眾多細節,覺得男人是千般萬般的好,他肯定是分身無術,有難言之隱,否則真要拋棄自己,完全可以玩消失,而不會專門請拉月嫂來照顧自己。還有一個是幕后的老板。跟了自己多年的兄弟,忠心耿耿,立下過汗馬功勞,怎么可能為一點事出有因的過錯大發雷霆,傷了感情?
男人的死,也讓家人無比悲痛。尤其是其母親,痛不欲生,一急之下心臟病復發,被醫院的急救車拉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