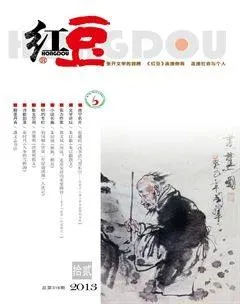記憶村莊
有人說:忘記是生活的技巧。我以為這要看是些什么事。
也有人說:忘記過去就意為著背叛。我以為這也要看是些什么事。
由此我說:
不會忘記,生活會很痛苦;
凡事都能忘記,生活會很乏味。
我基本屬于善忘之人,所以精神上的壓力和負擔就少,很少有失眠的感受。但是,有些事情我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忘記的,不但不會忘記,反而會越老越是記憶猶新,其印記深刻,可謂深入骨髓,比如對我的故鄉——生我養我成人的村莊。
故鄉處四省交界之地,有“一尿淹四省”之說。因為四省交界處有一條黃河故道,貫穿河南、山東、安徽、江蘇,每每遇大雨,雨水便會流入故道,河水漲滿后又會向河堤之外倒流,村莊就會遭到水淹,因此就有了“淹四省”之說。故鄉就處故道的北邊,南同河南的商丘接壤,東南有安徽的碭山、江蘇的豐縣為鄰,我的故鄉即山東的單(sh n)縣,同呂后是老鄉。
故鄉既無山也無水,不但不美麗而且很窮,屬窮鄉僻壤。但就是這么一個地方,它讓我魂牽夢縈了一輩子。這或許不被一些人所理解,是因為他缺少一份親身親歷。可以這么說,故鄉不但給了我一個生命,而且給了我一個健康的體魄和一個健全的品格。因為我腳踏實地氧氣充盈,頭頂藍天陽光普照,口食五谷雜糧營養齊全,在我十六歲(1966年)時,業余航校在全省選拔滑翔學員,我的身體竟達到了一個飛行員要求的條件,這讓我驚嘆不已。就是這一年,我離別故鄉只身去濟南上學,也是這一離別,讓我生命的軌跡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由此,我怎么不感激我的故鄉?怎么會忘記我的故鄉?若真的忘記了,那真的是背叛了故鄉。
十八歲(1968年)時,我應征入伍,四年后又復員到北京工作,雖有過幾次回故鄉的經歷,但也是十天半月即回,沒有發現村莊有什么變化。那時候的經濟極不發展,村上不可能有什么發展,房子還是那些房子,井還是那幾眼井,道還是那幾條道,同我記憶中的村莊毫無二致。唯一發生變化的是人口,老人走了,小孩子出生了,不少新的面孔我不認識了。從1986年起,我曾一度有二十多年不再回過故鄉。這期間常有村人來京,會到家里坐坐,是他們帶來村上的一些信息,誰誰去世了,誰誰考上大學了,誰誰有了孫子四世同堂了,誰誰家蓋了新房……我感到村上的變化太大太大,怕是讓我不曾認識了。他們一次次邀我回家看看。每每這時,我會拿筆畫一張村莊示意圖給他們看,村上有幾條道,從哪到哪,有幾眼井,幾個坑,牛屋、場院、隊部……又分別在什么位置……他們驚訝我的記憶。不過到了后來,我的村莊示意圖他們再不認識了,原因是現在村上全變了,井和坑、牛屋場院全都沒有了,老房子也沒有人住了……我就給他們講記憶中的饑餓(另文專寫)。他們告訴我,現在再不會餓肚子了,因為現在糧食已不是問題了……這反倒喚起我回家看看的念想。
2010年4月,我終于回到闊別了二十四年的村莊。二十四年啊,怕是有兩代人出生了。
像往年一樣,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情,是挨家挨戶地去看望鄉親們。真的是不看不知道,這一看讓我驚訝萬分。許多我曾經熟知的老人故去了,許多許多的同齡人和年輕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村上只剩下了老弱病殘婦女和兒童。我曾熟悉的那些標識物呢,也已蕩然無存。破舊的房屋,或已殘垣斷壁……一座好端端的村莊咋就這樣快面目全非了!我突然想到了“廢墟”二字,這讓我第一次領悟到這兩個字的深刻含義。我說不來是一種什么心情,也找不到合適的詞語加以形容。
晚上多喝了些酒,清茶上來,到家看望的人已斷斷續續來了不少,鄉里鄉親熱熱鬧鬧拉起家常。大家希望我談些外面的精彩世界,但我的思緒就是上不去,談來談去最終還是要回到我記憶中的村莊。我談的具體形象,其中還帶有些許的故事,上了年紀的人驚訝我的記憶如此之好,年輕些的人不曾見過我所談的村莊,卻也聽得出神,仿佛就身臨其境。
給了我生命之軀的村莊就叫劉樓。
其實劉姓就我們一家,也沒有什么樓房。為啥叫劉樓,我不知道,大概劉姓是建村的第一戶。如果真是這樣,說明劉樓村已有五百多年的村史了,因為我家是在明代從山西洪洞遷徙過來的。
村上的大戶人家是孫、楊兩姓,占著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他還有一些雜姓小戶。全村分為四大塊,以姓為主,依坑為鄰,近井而居。四塊以四條村道劃分而成。我家在村子東頭靠里位置,前門后院對著戚姓人家,我家西邊有陳、黃、邵和張姓人家,每姓人口都不多,在村里屬于少數派。但真正意義上的劉樓當屬這一塊。形狀南北為長,東西為寬。在南有一眼水井,井的東南向有一口圓形水坑,坑不大卻深,且四季有水;而這塊的北邊靠東一點則有一口四方形水坑,但只有在夏季時才有水。這是我初學游泳的地方之一。
我家的東邊是一塊菜地,菜地東邊是一條南北走向的村道,道的東邊住著王、李、米三姓人家。聽老人講過這里曾經叫過侯莊。為何,我不知,也沒有探究過。三姓人口幾乎相等,處三軍頂立之勢。三姓共飲一井水,水井位置在東南角,另有三口坑,一口在東北角,東西長,南北寬,水淺,一口在西南角,圓形,坑深,一口在東邊,屬小坑,南北有10米長,東西有3米寬,深也不過兩米多,但這里曾經發生過一個凄慘的故事。
其實,侯莊還有一家,姓楊,獨門獨戶,獨立單行,很少同鄰居來往。因為這家太特殊,所以要抽出來單寫一筆。這家幾世都是單傳,到了第三代,生過六個,但只有老六活了下來,爺爺送孫子一名——楊六郎。他是否有大名,我不知道,全村人都以“楊六郎”稱呼他。那個年月這家人就有經濟頭腦,所以在那個時代不發生故事才怪。這個家庭的結局很慘,屬一出悲劇。
我家隔著的陳、邵、黃姓的西邊,有一條南北走向的村道,道的北端對著一口大水坑,供全村所用,不屬于哪一姓所有,也是全村唯一好用的水塘,村人稱之為官坑。道的西邊即為楊姓一族,位置在全村的西北角,盡管有單、郭、王姓,但基本上還是楊姓的一統天下。在楊姓住地的中間有一口東西向的水坑,以此為界,一坑兩岸,分成南楊和北楊。南楊地勢高,北楊地勢低,又稱高楊和矮楊。雖屬一族,但也有三支已經出了五服。這一族內部事情時有發生,但都能迎刃而解,或能逢兇化吉,是比較團結的一族。有時也同外姓發生矛盾,但也都能在說事人的勸說中化為烏有。楊姓共享兩眼水井和一口水塘。
楊姓的南邊,有一條東西向的馬路,也是劉樓村的主干道。在它的南邊,即為孫姓居住地,中間有一條東西走向的村道,把孫姓分成南孫北孫,在孫姓的東邊還有張姓家族,也被村道分成南張北張。孫姓人口比張姓人口多很多,屬村里的多數派。但張姓人家厲害,凡事都要占個上風,而孫姓人家樸實、老實,凡事都能息事寧人,兩姓呈東強西弱之勢,長時間里,沒見過西風壓倒東風的時候,總是東風壓倒西風。兩姓人家各有一口水井,互不侵犯,大有井水不犯河水之意。張姓有一口水坑,村人稱之為張坑,是村里唯一以姓冠名的水坑,可見張姓的自強和獨立。至于孫姓人家是否有水坑,我不曾見過,也不曾探究過。孫姓人家在全村的西南位置。
以姓聚居,大概是從建村時形成并延續下來,好處在于相互之間便于幫襯,也好一致對外。
1958年成立人們公社,全村分為三個生產隊,劉姓加侯莊為一隊,楊姓為二隊,孫姓為三隊。各隊隊長自然由所在的大姓人擔任,二隊長是楊姓人,三隊長是孫姓人,一隊雖無大姓,但劉姓占了劉樓村姓的便宜,自然由劉姓人來任隊長之職,似乎舍劉無他。一隊雖為雜姓,卻無一姓占有優勢,但每姓都能做到好自為之,所以一隊很少矛盾發生,即使偶起事端,由于各姓都能做到溫良恭儉讓,便也將矛盾止于萌芽狀態,正可謂一隊無戰事。
我16歲(1966年)時離開劉樓,1958年正是我兩個8年的分界時段。前八歲雖記憶很少,但留在腦袋里的東西大都美好。而后八歲卻不然,腦子里殘留的東西大都痛苦不堪。
人民公社的重要標志是將一切生產資料全部公有化,作為莊戶人家最不愿意的是失去了土地的種植權。合作化時期我家的地在村的東邊,是一塊好地。收了地瓜花生種小麥,收了小麥種地瓜和花生。一年兩季,不但吃糧沒有問題,而且地瓜粉還可以做粉條,花生可以用來榨油,花生餅又是我們小孩子很愛吃的零食。尤其到了春節,家家戶戶都會炒上幾鍋花生來招待客人,還可以將花生疊成又甜又脆又香的花生糖。自然了,我們小孩子是它們的主要食客。可是,人民公社化以后,這一切都成了記憶,不但如此,而且連吃飯都成了大問題,尤其1960年我就差一點被餓死。因此,1966年我被驗上滑翔學員時,給我的不僅僅是驚訝,而且更多的是不相信,餓了8年的孩子怎么會有這么好的身體呢!至今我也不明白為什么。
兩個8年的落差太大太大,仿佛兩副紅黑分明的重彩畫,給我留下的印記太深太深,尤其兒時記憶最為深刻,怎么能夠讓我抹得去,涂得掉!
有人說:記憶像是倒在掌心的水,不論你攤開還是握緊,終久還是會從指縫中一滴一滴流淌干凈。
我說:這是死了以后的事情,只要我生命尚存,我對故鄉的記憶就不會消失。
現在我用筆尖留下紙的記憶,即便我到了另一個世界,還能讓人通過文字知道我的故鄉。
2013年7月寫于北京月亮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