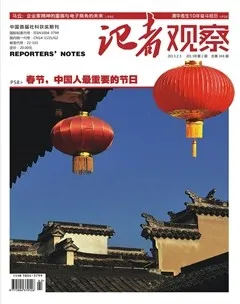孟錦云:毛澤東的最后一名守靈人

是誰,陪伴著毛澤東度過了生命的最后時刻?是誰,護理著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
是她,孟錦云,一個普普通通的姑娘。
孟錦云,對人們來說,是個陌生的名字。如果查查1976年9月13日的報紙,就可以在給毛主席守靈人的長長的名單中找到。孟錦云,最后一名守靈人。她的知名度幾乎是零。然而,就是她,卻和一個偉人朝夕相處,日夜相伴,度過了489個白天與夜晚。
她,是毛澤東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見證人。在孟錦云的敘述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毛澤東,一個由神變成人的毛澤東。毛澤東作為一個普通人,一個普通老人,也具有普通人的特性。毛澤東也要流淚,也要大笑,也要憤怒,也要固執己見……他既是偉人,也是一個具有普通人的種種情感的凡人。
“您的痣子是湖南痣子,我的痣子是湖北痣子”
孟錦云,是個湖北姑娘,12歲就考入了空政歌舞團,1959年被先進了舞蹈學員班。
1963年4月,小孟被安排去中南海“出任務”。那時候,中南海的首長們,經常性的娛樂活動就是跳舞。空政歌舞團的一些舞蹈演員,在過了政治上、作風上、生活上的嚴格審查之后,可以進中南海,去完成陪首長跳舞的任務。
來到中南海的舞廳,小孟和幾個女伴坐在軟墊靠背椅上等候。眼前的一切使小孟感到新奇。
晚上10點多鐘,舞廳里的人忽然紛紛起立,樂曲停止,舞步停止,毛主席來了。
毛主席從左側那個紅門穩步走人舞廳。他的裝束極為隨便,一身灰色中山裝,并不筆挺,袖筒又肥又長,幾乎遮手一半,特別是那條過分肥大的褲子,寬松,舒適。
主席坐在專門為他準備的沙發上。一名服務員端著盤子走過來,盤子上放著白色的打濕了的毛巾,毛主席拿起毛巾擦了擦臉和手。只見服務員小聲跟主席講了句什么,主席輕輕點點頭。不多時,小舞臺上的樂隊奏起了舞曲。在眾人目光的集中之下,一個常來跳舞的文工團員,走到主席面前,微微傾身,伸出臂掌,作出邀請姿勢,主席會意,站起來,與她跳起了舞。
全場人的目光,像舞臺的追光一樣,追隨著主席和那個文工團員。
小孟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著主席如何跳舞。主席的舞步很大,他高大的身軀不怎么靈活,像在蹭著地板走步。一邊跳,主席還一邊與那個文工團員談天。主席并不像初學跳舞的人那樣,總往腳底下看。他顯得很輕松,毫不拘泥。
一曲終了,主席和那個文工團員停在了主席的沙發那兒,女文工團員用手往沙發那邊一伸,主席便走向沙發,坐下來休息了。
小孟觀看著這里發生的一切。她的目光,一直追隨著主席,仿佛要盡量從他身上發現些秘密來,但看著看著,那種神秘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又一首舞曲開始了,是歡快的《喜相逢》。主席側臉,好像突然發現了小孟,他對她笑了。小孟也在意識到的一剎那間,向主席報之尷尬的一笑。她太沒有思想準備了,她站起身向主席走去,學著前面那個老同志的樣子做出了請主席跳舞的邀請動作。主席微笑著站起來,拉住了小孟的手,同她向舞場里走去。這時,小孟真有點手忙腳亂了,剛剛平靜了的心又猛烈地跳動起來。她慌忙上陣,不知該怎么跳舞,什么節奏、音樂、舞步,都成了模糊的一片。主席已看出了她的慌亂,輕輕松松地對她說:“小同志,別緊張,你的舞步不錯嘛。”
跳著跳著,小孟又逐漸感到輕松了。
“你是新來的?”
“我第一次來。”
“怪不得沒見過你。小同志,叫什么名字?”
“孟錦云。”
“噢,孟錦云,跟孟夫子同姓。這個名字好聽,錦上添云比錦上添花還美呢。你是什么地方人?”
“是湖北武漢。”
“噢,湖北,一湖之隔,是我的半個小同鄉呢!”
跳舞,閑聊,小孟感到主席是個很容易親近的人。主席的親切自然驅散了小孟的緊張、慌亂。
之后,小孟幾乎每周都要去中南海參加舞會,每次都要和主席跳舞,主席總是親切地稱她半個小同鄉。
小孟開始在主席面前無拘無束了。在主席面前,小孟沒有太多條條框框。她的單純、機敏、活潑,她充滿了稚氣的發問,常常引得主席開懷大笑。
“主席,您嘴巴下面有一個痣子,聽我奶奶說,這是有福氣的痣子呢。”小孟望著主席,笑瞇瞇地說。
主席聽了,看到小孟白白凈凈的臉蛋上,也有一個小小的痣子,便笑著說:“你的臉上也有一個痣子,那你也有福噢。”
“那可不是,您的痣子是湖南痣子,我的痣子是湖北痣子,長的地方不一樣。”
主席聽了小孟的回答,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也是因了這樣的初識,孟錦云在經歷了曲折的十多年后,1975年5月,終于來到了毛澤東的身邊,應毛澤東要求到他身邊工作。
“孟夫子,來,我給你講個故事”
小孟來到主席身邊工作,主席十分高興。此時,主席身邊有兩個工作人員,除了張玉鳳是他的生活機要秘書,還有個護士小李。小孟來了之后,主席與她有說有笑。飯后茶余,花園小徑的散步,臥室客廳里的談天,顯得十分和諧,主席常常把小孟逗得開懷大笑。
“孟夫子,來,我給你講個故事。”主席喜歡用這個名字來稱呼她。
小孟把沙發椅向主席的身邊搬近一些,主席操著難懂的湖南話,給小盂講起來。
“有一個人,從自己脖子上捏下一個虱子,害怕別人嫌臟,趕忙扔到地下說:‘我當是一個虱子呢,原來不是個虱子!’另一個人馬上撿起來說:‘我當不是個虱子,原來是個虱子!’”
小孟聽完了這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故事,瞪著眼睛發問:“這個故事有什么意思,一點兒也不好聽。”
“傻丫頭,你什么都不懂噢,這是告訴我們要講實話嘛,虛偽的人真是可笑。”
小孟聽了恍然大悟。
這天,主席把詩刊雜志要發表的他的兩首詞的清樣拿給小孟,對她說:“小孟,請你把這兩首詞讀給我聽聽。”
小孟拿過來,也不先看一遍,馬上就讀起來:
念奴嬌·鳥兒問答
(1965年)
鯤鵬展翅,
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
背負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間城郭。
炮火連天,
彈痕遍地,
嚇倒蓬間雀。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飛躍。
借問君去何方
雀兒答道:
有仙山瓊閣。
不見前年秋月朗,
訂了三家條約。
還有吃的,
土豆燒熟了,
再加牛肉。
不須放屁!
試看天地翻覆。
小孟高聲快速地讀了起來,當她讀到“不須放屁”這句的時候,她撲哧一下笑出聲來。
“主席,您寫不須放屁,可您今天放了二十八個屁。我都給您數著呢。”
“噢,你還給我記著黑賬。”主席也笑了。“活人哪個不放屁,屁,人之氣也,五谷雜糧之氣也。放屁者洋洋得意,聞屁者垂頭喪氣。”
小孟聽了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來。
小盂邊笑邊說:“那您為什么在詞里還寫上‘不須放屁’?”
“兩回事情嘛,孟夫子。”
毛澤東最后的生日
1975年12月26日這天,是毛澤東的最后一個生日。這一天,中南海毛澤東的家里,毛澤東的女兒李敏、李訥來了。以前的護士長吳旭君、護士俞雅菊和李玲師也來了。他那有些木然的臉上,一下子添了笑容,有了些生氣。毛澤東今天沒有長久地躺在床上,他自己提出去大廳里坐坐。小張、小孟攙著他來到大廳里,坐在沙發上。小孟說:“今天是您的生日,按我們家鄉的習慣,孩子要給老人磕頭。”主席聽了高興地說:“你的意思是要給我磕頭,我可不敢當,我承受不起噢!”小孟聽了,很隨便地說:“您都不敢當,還有誰敢當,我先給您磕。”說著就跪在主席面前,鄭重其事地磕了三個頭。主席也不時向前起身表示回敬。見小孟磕了頭,吳旭君、李玲師、張玉鳳也先后磕了頭。
這天,江青也來了。她踏著很小很輕的步子,幾乎是躡手躡腳地走進了毛澤東的臥室。此時,主席正躺在床上,眼睛微閉。江青進門便說:“主席呀,我給你祝壽來了。”江青說話的聲音雖然又輕又細,但主席還是一下子聽出來了。
毛澤東睜開惺忪的睡眼,把頭稍稍移動了一下,無神地望了望江青,臉上依舊是木然,無喜無憂,無驚無奇,什么話也沒有說,幾秒鐘的沉默后,主席很陜又把雙眼閉上了。
毛澤東對江青,不愿理睬,這已是長時間以來的做法了。毛澤東早已對江青產生了厭倦,甚至是反感。
1975年12月26日這天,毛澤東度過了他最后一個生日。這天,毛澤東又重復了他平時常說的一句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
有一次,小孟對小張透露了自己的想法:“張姐,我都快三十歲了,我真想要個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說說。”
“主席,孟夫子想要個小孟夫子啦。”小張果然把小孟的意思告訴了主席。
“再等一年吧,等我死了,她再要吧。”這是毛澤東的回答。
毛澤東也許早已感到,他已不久于人世了。“孟夫子,如果全國人民都知道了我和江青離婚的消息會怎么樣?”
1976年,毛澤東身體時好時壞。但總的趨勢,是每況愈下的。隨著身體的時好時壞,毛澤東的情緒也隨之變化。他有時變得很急躁,很容易向身邊的人發火。
經過長時間的接觸,小孟已經知道,這是主席心情煩躁的表現,這段時間里,他常常喜怒無常,一點兒事情,就使他激動。小孟知道,他過一會兒就會好的,而且發火后每次都會道歉。
這段時間毛澤東更多的是在沉思。這點,連并不敏感的小孟也察覺到了。這天,毛澤東又在那里似睡非睡地靠在沙發上發呆,右手的拇指還在不停地彈著食指。心里裝不下事的小孟,終于忍不住輕聲問道:“主席,您這段時間怎么啦?是不是身體不舒服?還是有什么事?”
毛澤東聽到這里,把微閉的眼睛睜開。從神態上看,他并不怪罪小孟的打攪,也不反感小孟的提問,而是苦笑著回答:“要說不舒服,這段時間是天天不舒服,許多事情,身不由己噢。身體是革命的本錢,看來,我的本錢已不多啰。”說到這里,毛澤東像是沉入了對往事的深深回憶之中。
“我的家鄉有句俗話,叫做甘蔗沒得兩頭甜,世上的美事難兩全。”毛澤東在十幾分鐘的沉默之后,突然對小孟說了這樣一句。
“孟夫子,你看我發愣,覺得奇怪對嗎?我自己也覺得奇怪呢。我這個人,不能說沒有值得回憶的事,可我不愿在回憶中過日子。我歷來主張,人總要向前看,這已是幾十年養成的習慣了。可最近,不知怎么的,一閉上眼,往事便不由得全來了,一幕一幕的,像過電影,連幾十年前的人和事,都很清楚。你說怪不怪?”
聽著主席這坦率真誠的話語,小孟不禁受到了感染,她不假思索地說:“主席,我聽人家說過,只有在現實生活中不痛快的人,才愛回憶往事呢。您這么大一個主席,還有什么事……”
話說到這兒,盡管在主席的臉上并沒有現出什么高興或不高興的神態,可心眼不多的小孟卻也感到似乎有什么不妥,她猛然停住了話頭。
看小孟突然不講了,主席蠻有興趣地說:“孟夫子,講得不錯嘛,知無不言,講下去嘛,我這里可還想聽下去呢。”
聽到主席的肯定,小孟得到了鼓勵:“主席,我覺得您除了身體不好之外,其他方面都挺好的。再說您的病,如果能好好治,聽醫生的話,打針、吃藥,會治好的。您這個人就是怪,不愛治病,有病哪能不治呢?我要是您,我就趕快治好病,整天都會高高興興的。”
“整天都會高高興興,那是你小孟,我的孟夫子噢。”
“您是主席呀,您這么大一個主席,想怎么辦就怎么辦,想去哪兒就去哪兒。不像我們,說話得先想想人家愛聽不愛聽,辦件事也不那么容易,您辦什么辦不到啊。您忘了,決定華國鋒當總理,您誰也不用商量,只在床上躺了兩天,就決定了。這么大的事情您都能決定,還有什么事不能決定呢?”
毛澤東被小孟的坦率感染了,竟然哈哈大笑起來,把小孟笑得有點兒摸不著頭腦。主席笑完了,小孟忙問:“我說得對不對呀?”
“你說得也對也不對。”主席很認真地回答。
又停了一會兒,主席便說:“說它對,是因為我說話確實算數,說話不算數,還叫什么主席?人稱‘最高指示’嘛,衡量一個人有權無權,就看他說話算數不算數。說話算數,當然事情就好辦。所以有些事辦起來,要比一般人容易。可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如果只看這一面,本人可真是神氣得很吶。但是問題還有另一面嘛。”
主席說到這里又停了下來,望著小孟,似乎在等待小孟回答什么。“另外一面是什么,您有什么事兒辦不到?”
“比如,你下了班,可以和家里人,和朋友到大街上轉轉,我可就沒有這個自由噢。我要是走到街上,大家都認得我,說毛主席來了,一下都圍上來,越圍越多。圍著你喊萬歲,搞不好還會影響交通呢,你說是不是?”
“那倒也是,誰讓您是大主席呢。”
“你們可以隨便聊天,但和我談話的人,大都是有顧慮的。這點,我看得出來,人都是好人,但話未必是真話,難得口吐真言吶。”
聽到這里,小孟問了一句:“主席,那您說話也有過顧慮嗎?”
“那看對誰啦,人說話總要負責嘛,不但要對內容負責,還得對后果負責嘛。你和同志探討點問題,發表點見解,甚至一句玩笑話,傳出去,就成了‘最高指示’,有人還以此大做文章,鬧得你哭笑不得。”“您說了那么多玩笑的話,我們可不敢給你傳出去。我和張姐都特別注意,每次我下班回去,總有些同志喜歡打聽您的情況,我可一句也不說。”
“噢,孟夫子不是心直口快嘛,還是蠻有心眼的啰。”
“那當然,說錯了,那可不得了。”
毛澤東忽然又沉默了一會兒,又接著說起來,帶著一種和緩,但也有一種隱隱的不滿。
“有人說,我的話一句頂一萬句,言過其實,說過了頭嘛。不用說一句頂一萬句,就算一句頂一句,有時也辦不到吶。我說要把有的人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硬是攆不動,分不開嘛!”
聽到這里,小孟知道,毛主席是在講江青了,這是小孟始料不及的。
主席主動談到江青的時候幾乎沒有。
“孟夫子,如果全國人民都知道了我和江青離婚的消息會怎么樣?”
小盂愣在那里,她停了好一會兒,才說:“您不是沒跟江青離婚嗎?”
“孟夫子,不要你回答,你是答不上來的。離婚,我到哪里去起訴喲。離婚,總要辦個手續吧。到那時,不知道是法官聽我的,還是我聽法官的,那可能要大大熱鬧一番。總有一天一了百了,統統解決。”說到這里,主席又笑起來。那笑聲里,既有一種頑強的自信與豁達,又有一種無可奈何的壓抑。
這是小孟自進中南海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聽主席主動談江青。但直到今天,有一個問題仍令小孟不解:“主席真的想過與江青離婚嗎?”
“我很難受,叫醫生來”
毛澤東的身體日漸惡化。這是醫生們、周圍的工作人員早已看到了的事實,而且已是無可挽回的趨勢。
1976年5月12日,毛澤東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那天上午,主席的理發員小周給他理了個發,又刮了臉。在接見前的一個小時,小孟從主席專用的大衣柜里拿出了那套灰色的毛式服裝。
“主席,您今天還穿這套衣服吧?”小孟說。
“就穿這個。不穿這個,穿哪個嘛!”主席點頭回答著。
小孟幫主席脫下了睡衣,換上中山裝。穿好后,又前后左右地看看,抻抻拽拽把衣服弄得平平整整。看到毛澤東現在的樣子,小孟反而感到有些新鮮了:頭發整齊,服裝筆挺。真顯得精神多了。
平日的毛澤東,多數是躺在床上,多數是穿著細布睡衣,頭發不理,很有些不修邊幅,簡直使小孟感覺不到他是個眾人矚目的一國領袖。
“您現在才像個主席了。平時,您哪兒像個主席呀。”小孟像是在開玩笑地說。
“他就是扮成個主席呢,一扮就像,別人誰也扮不像。”小張剛剛從外邊走進來,也打趣地說。
“我去接見外賓,就像出去演戲。演員登臺,哪有不化裝的?”主席也開著玩笑。
時間到了,小張、小孟一邊一個,攙扶著毛澤東,走到游泳池接見大廳。他剛剛坐下來一兩分鐘的時間,李光耀已由華國鋒陪同來到大廳。小張、小孟把主席扶起來,她倆趕緊退后。但主席剛剛站起來與李光耀握完手,撲通一下就坐下了。當時小張、小孟在屏風后面看得很清楚,她們不約而同地小聲“呀”了一聲。接見只有一兩分鐘,寒暄幾句,便匆匆結束。但是,這并不是最后一次的接見外賓。
1976年5月27日,毛澤東又會見了巴基斯坦總理布托。
這次接見,毛澤東沒有站起來,只是坐著與布托會面。但此時的毛澤東已明顯地讓人看出,他面容憔悴,表情麻木,行動不便。更嚴重的是,他的口水不斷從嘴角流出,需一次又一次地取紙塊擦拭。
封鎖極為嚴密的關于毛澤東的健康狀況信息,不得已透露出來。人們從電視中看到了無法再回避的真情。
毛澤東會見布托之后,再也沒有在外交場合露過面。
毛澤東在最后的日子里,依然是既不愿打針,也不愿意吃藥。他依舊相信,靠自己身體的抵抗力能戰勝疾病,他依舊堅守著治病也要“自力更生”,因為用藥打針,是“外援”。
但越來越虛弱的身體,使他固守的道理已處于失敗,他幾乎是水米不進。在醫生的多次勸說下,他才同意用了鼻飼插管。這種插管很細很細,是從國外進口的,可以從鼻子一直插到胃里去。用其輸送營養,維持生命。
“主席,您別老不聽醫生的意見,人家劉伯承身體不比你好,用了鼻飼管,效果特別好。您老說靠自己的抵抗力,您沒有營養,怎么有抵抗力呀。”有一天,小孟又對主席講行了一番勸說。
主席這次聽了之后,睜開他微閉的眼睛,輕輕說:“那就試試吧!”
插鼻飼管之后第二天,他果然感到身上有點力氣了。他顯出高興的樣子。“小孟呀,你比我懂得多,我得聽你的了。”
1976年9月的一天,小孟請假外出回家,晚上5點多鐘到家,7點15分,突然有人來找,要求小孟馬上返回中南海。
小孟回到主席的臥室,才知道。主席犯了病,心肌梗死,十分危險。主席的幾個醫生都來了,政治局的人也來了,氣氛相當緊張,搶救二十多分鐘之后,主席才脫離險情。
9月8日晚7時10分,毛澤東的呼吸重又急促起來。小孟過來,低頭給主席按摩胸部。主席用很低的聲音說:“我很難受,叫醫生來。”
1976年9月9日O時,毛澤東停止了呼吸,繼而心臟停止了跳動。
他的最后一句話是對小孟說的:“我很難受,叫醫生來。”
臨終前,偉人沒有感人肺腑的遺言。
小孟把主席最后換下來的衣物疊得平平整整、放在床頭的小柜子里。
小孟把主席用過的鉛筆拿起來,細細地看著,這是小周給主席削好的。這支鉛筆永遠不會再被人用了,她真想拿去做個永久的紀念,但她輕輕拿起,又輕輕放下,依舊放在小桌子上。
此時,小孟的視線變得那么模糊,她的神志變得那么飄搖,她忘記了空間,也忘記了時間,忘記了失落的自己。
小孟,毛澤東的半個小同鄉,毛澤東身邊的最后一名護士。當毛澤東離開中南海之后,她卻還留在中南海里,度過了一個多月的時光。
她不用輪流值班了,她也不用再去服用速可眠了。
一個多月里,她每天都在毛澤東的臥室書房里,整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