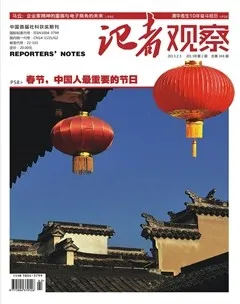公權力邊界不清難以有效解決信任危機
迅速的現代化進程令中國社會正從“熟人社會”快速轉向“陌生人社會”,而社會群體之間互不信任是轉型社會的典型特征。懷疑已成為國人的生活方式,有人將之總結為“國民不相信運動”。這樣一場運動是建基于國民的基本經驗之上的,持續愈久,愈易固化為一種內在思維模式,一種“務實的生活智慧”:吃飯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鐵路行業解決買票難的能力和誠意,上醫院不相信醫生沒有給自己多開藥,打官司不相信司法會保持公正……似乎只有不相信才是安全的。
在這樣一種普遍社會信任危機之下,如何重構信任社會,是中國能否在經濟發展成就顯著、社會財富積累形成可觀的“有形資產”的同時,遏制社會公信力“無形資產”的普遍流失,保護社會信任和社會安全,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市場經濟推動“陌生人社會”轉型
自從有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就有社會信任。信任其實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是社會共享的道德規范的產物。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信任建基于親疏有別的熟人社會之上。
為何當前中國社會普遍缺失社會信任感和社會安全感呢?
自19世紀中晚期開始,在西方工業文明不可抗拒的沖擊之下,中國遭遇“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傳統意識形態長期以來的優越感被否定,一大批精英階層開始進行反思,他們把罪責歸咎于中國既有的價值體系及其所支持的社會結構,試圖從西方尋求迅速“救國”與“強國”之路,并因此引發了一系列激進變革和革命,這對傳統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私人信任關系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和破壞。
到了1978年,改革開放的啟動,更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急劇的變化。市場經濟的引入一方面給社會增加了活力,另一方面也使社會充滿了不確定性。傳統血緣家族體系所能夠提供的社會信任感和社會安全感在城鄉地區都普遍處于衰退過程中。而中國迅猛的城市化進程,將大量農村人口和土地進行分離,促使他們進入城市工作;并且,原有中小城市人口的相當部分也在迅速向大城市集中。與此同時,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位制度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被瓦解,與城市社會個體相對應的往往是由“叢林法則”進行主導的市場,而不是曾經包辦生老病死的單位。由此,“熟人社會”在政治力量和市場力量的共同推動下,迅速轉型為“陌生人社會”。
市場經濟本身存在一個悖論:一方面,市場經濟信奉“叢林法則”,這將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并且資本的唯一本性就是攫取利潤,不會考慮社會效應;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是以社會信任為基礎的契約經濟,它必須建立在法治之上。如果缺乏法制的約束,市場的自發性必然會導致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擇手段,也會造成社會差距的拉大。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必須規范市場。市場可以有自發的市場,也應該有受規制約束的市場。自發的市場往往容易喪失道德、喪失誠信,造成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馬太效應,而受規制約束的市場可以通過一系列的法律途徑來制約這些行為或現象。
傳統的中國文化本就缺乏法治精神,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雖然急速地引進市場經濟,但相應的法治建設并未跟上。現在中國每年都有好幾起全國性的食品藥品安全事故,而且“無良奸商”似乎越壓越起,防不勝防。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商業欺詐、信用欺詐、就業陷阱和傳銷組織,使得人們對于現有的市場怯制環境產生了強烈的不信任感。
公權力對社會保護缺位
一般而言,在市場力量與社會力量進行平衡的過程中,國家公權力應當通過法律制度對社會和市場二者分別進行規制,通過提供公共服務等對社會進行保護,這是彌補市場經濟和“市場社會”本身所存在缺陷的重要路徑。但在現今中國社會,由于對于公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督制度,公權力的錯位、缺位極其嚴重。
近年來,圍繞著“國進民退”“國企壟斷”“與民爭利”等說法,引發了部分學者批評“權貴資本主義抬頭”的趨勢,進而升級為事關中國是改革還是倒退的體制之爭。目前,雖然民營企業吸納了大部分就業,但是在市場競爭中卻由于起點低,再加上復雜的體制因素,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種種利益博弈等,易處于弱勢地位;國有企業在重要的基礎性行業占據主導地位,一方面和公權力捆綁在一起,另一方面擁有大量資源甚至壟斷性資源,使其在市場競爭中占據天然的優勢。這樣兩種完全不對等的待遇,使得人們對現有市場競爭環境的公平性產生了強烈的不信任感。
同時,市場競爭與不完全競爭并存。競爭機制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動力,但是,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表象上強調個人自由,卻容易導致少數強者戰勝多數弱者,進而壟斷市場。而在中國,體制內與體制外差異、城鄉二元制結構、行業差距與地區差距等導致市場機制并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經濟活動實質上處于不完全競爭狀態,再加上收人分配不平等與財富逆向轉移共生等現象,這些都有悖于對社會公平和人人平等的基本理解,這就使得人們對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現實難以接受,對現有社會競爭機制的公正性產生不信任感。
此外,在通過公權力強力推進市場經濟的同時,國家自身也變為經濟發展的“運動員”,在片面追求“有形資產”積累的同時,卻忽視了制度建設和社會管理,甚至將毛澤東時代原本由政府或者單位提供的公共產品大部分委托給市場,由個人或者家庭進行購買。而由于財政體制和“GDP2政治錦標賽等原因,政府治理尤其是地方治理存在相當程度的權力濫用、權力尋租和非法行政的情形,使得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大為降低。讓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
在這種市場力量和非市場力量沖擊社會,國家公權力對社會保護缺位甚至聯合資本進行中國式“圈地運動”的情況下,民眾對政府產生了嚴重的社會信任危機,各種群體性事件在全國各地被激發出來。自本世紀初以來,中央政府為了維持其執政正當性,自上而下地推進社會改革。然而近些年的相關社會改革并沒有實質性地解決上述問題,致使這場“國民不相信運動”不斷摧毀我們的道德底線。
在這樣一場信任危機之中,政府的責任在哪里?我們認為要從以下幾點理清思路:
首先,要建立對法律的信任。在熟人社會中,人們彼此交往主要是靠信用取得彼此的信任,而不是靠契約。這雖然是中國傳統的美德,但道德約束主要靠的是自律,契約卻是法制性的,沒有法制進行約束,那就失去監督的機制,而沒有監督的信用并不可靠。如果說在一個熟人社會,彼此之間抬頭不見低頭見,進行小額的交易尚能維持的話,那么在市場經濟大潮中,進行跨地區、跨國的貿易,在陌生人的世界中交易,根本無以為繼。在宗族社會中,家庭是家長統治下的財產共有制,這種秩序養成個人缺失產權觀念,許多民眾至今都不知道怎樣維權。由于法制觀念薄弱,致使中國古代有高額的商業資本,卻沒有經濟法。是自律還是他律,這是禮治與法治對社會管理的根本差別。中國要從前現代的小農社會向現代化過渡,必須要有相應的法制建設,要厲行法制就必須充分認識“禮治秩序”所造成的習慣勢力,對執法可能發生的障礙,并采取應變的對策。
其次,劃定公權力的邊界。無論對市場還是對非政府組織,政府都應當依據法律規范對其進行監管,而不是直接管理。像英國這樣奉行自由資本主義的國家,在市場經濟發展上百年之后才通過政府監管來彌補市場失靈。而中國是在市場發育尚不完全、法治尚未健全的時候就啟動政府監管。市場本應當承擔的責任,例如嬰幼兒奶粉案等食品安全事件,由單純的企業制假售假行為,升級為中國乳制品行業的危機,并且波及到政府監管部門的信譽,最后會被歸咎于“政府隱瞞”和“體制問題”。從非營利部門角度而言,其存在的正當性來源于其公眾形象,對非營利部門的公眾信任是維系其組織生存和公民社會力量的基礎。紅十字會郭美美事件,本是慈善組織自身的問題,也因為中國紅十字會與政府有關部門理不清的瓜葛,被批評為“首要責任在政府”。
政府部門將所有的監管權集中于一身,其實也是將責任集中于一身。出了問題,自然是千夫所指。讓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才是最為智慧的責任邊界。
再次,建立對公權力的監督與約束機制,遏制官員尋租。中國的體制具有很大的“唯上不唯下”的特點,而“唯上不唯下”的必然結果就是“欺上瞞下”。應當建立常規的、制度化的利益表達管道,讓各種社會力量的利益訴求在法治的軌道內得以規范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