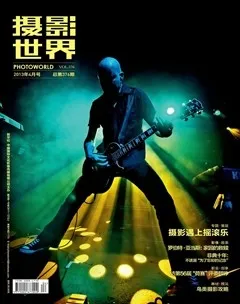48小時(shí)攝影日記





“攝影和電影在視覺上有什么顯著的區(qū)別?” 我曾經(jīng)向許多人求教過這個(gè)問題。有人認(rèn)為它們的觀看和展示方式不同,攝影是二維的而電影是四維的;也有人提到電影在內(nèi)容上比攝影要豐富;等等。大多數(shù)人認(rèn)為攝影表現(xiàn)瞬間,電影表現(xiàn)運(yùn)動(dòng)和時(shí)間。
有不少專著討論過這個(gè)大問題,總體上看,一類是側(cè)重技術(shù)本身,另一類則著重討論它們?cè)谏鐣?huì)學(xué)方面的異同。但是,那些長篇大論有沒有讓我對(duì)這個(gè)問題有更清晰的認(rèn)識(shí),我并不是很確定。自己是否可以把這個(gè)事情搞清楚,我至今也沒有把握。然而,它卻時(shí)常跳到我的面前來煩擾我。
從詞源和定義的角度來看,攝影原義為光影繪畫,電影一詞意指動(dòng)態(tài)攝影。攝影和電影是血緣親屬,都屬于攝影影像這一大家庭。然而,是什么鴻壑將它們相間為異類呢?從拍攝過程上講,似乎是時(shí)間介入的長短決定了二者的顯著區(qū)別,作為一件獨(dú)立的作品,電影容納的物理時(shí)間比相片所容納的時(shí)間要長很多;電影在視覺上表現(xiàn)運(yùn)動(dòng)、暗示時(shí)間的流動(dòng),攝影則將瞬間凝固;電影似水,攝影如冰。
其實(shí),我們都知道電影中時(shí)間的流動(dòng)是一種視覺錯(cuò)覺,是由我們觀看的生理方式導(dǎo)致的。科學(xué)研究表明,人眼在觀看時(shí),會(huì)有視覺暫留的現(xiàn)象,視覺暫留的時(shí)間大約是0.05~0.2秒,同時(shí)我們的眼睛還在觀看時(shí)進(jìn)行飛快的掃視活動(dòng),每次掃視約需0.05秒。這個(gè)生理活動(dòng)的特點(diǎn),使得膠片能夠以每秒24幀的放映速度將時(shí)間連接起來,而使肉眼看到的電影鏡頭呈現(xiàn)為連貫的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