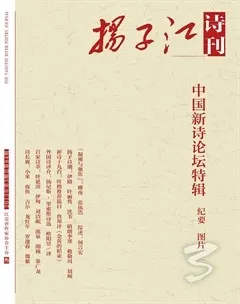評(píng)《金黃的稻束》“思”與“詩”的完美結(jié)合
《金黃的稻束》寫作于20世紀(jì)40年代初。60年之后,詩人鄭敏回憶起她在寫作《金黃的稻束》時(shí)的情形:“一個(gè)昆明常有的金色黃昏,我從郊外往小西門里小街旁的女生宿舍走去,在沿著一條流水和樹叢走著時(shí),忽然右手閃進(jìn)我的視野是一片開闊的稻田,一束束收割下的稻束,散開,站立在收割后的稻田里,在夕陽中如同鍍金似的金黃,但它們都微垂著稻穗,顯得有些兒疲倦,有些兒寧靜,又有些兒寂寞,讓我想起安于奉獻(xiàn)的疲倦的母親們。舉目看遠(yuǎn)處,只見微藍(lán)色的遠(yuǎn)山,似遠(yuǎn)又似近地圍繞著,那流水有聲無聲地汩汩流過,它的消逝感和金黃的稻束們的沉思凝靜形成對(duì)比,顯得不那么偉大,而稻束們的沉思卻更是我們永久的一個(gè)思想,回憶40年代大學(xué)時(shí)的哲學(xué)課和文學(xué)課,它留在我心靈深處的不是具體的知識(shí),而是哲學(xué)和文學(xué),特別是詩,釀成的酒,它香氣四溢,每當(dāng)一個(gè)情景觸動(dòng)我的靈魂時(shí),我就為這種酒香所陶醉,身不由己地寫起詩來,也許這就是詩神對(duì)我的召喚吧,日后閱歷多了,思維也變得復(fù)雜起來,我的詩神也由一個(gè)青春的女神變成一位沉思的智者,他遞給我的不再是葡萄美酒,而是一種更濃烈的極香醇的白酒,我的詩有時(shí)有些不勝任,但生命是不會(huì)倒退的,正如江河,我只能向大海流去,永不返回。”(見2001年第6期《名作欣賞》)在這一經(jīng)歷漫長(zhǎng)時(shí)光洗禮的回望中,詩人的話樸實(shí)無華,并無后來批評(píng)家加在“九葉詩派”身上所謂的玄學(xué),但它卻坦白了《金黃的稻束》形成的秘密,它的生活與思想的源流以及當(dāng)時(shí)詩人在詩歌世界中的成長(zhǎng)。
由眼前所見的現(xiàn)實(shí)情景展開聯(lián)想飛越塵世的藩籬,由物質(zhì)的畫面走向精神的沉淀,可以說就是《金黃的稻束》從構(gòu)思到成篇的過程。這個(gè)過程既簡(jiǎn)單,又復(fù)雜。說它簡(jiǎn)單,它沒有復(fù)雜的隱喻,沒有隱晦的玄學(xué),短短十六行就完成了詩歌。說它復(fù)雜,它確定不移地呈現(xiàn)了一種生命的真實(shí),藝術(shù)的真實(shí)。這種真實(shí)恰如卡洛斯·威廉斯說的那樣:“不借助于任何神秘的力量,而是以一種實(shí)際的方式去理解,生活只有和我們自身融為一體,才是真實(shí)的。”
從標(biāo)題到畫面的形象構(gòu)成,這首詩會(huì)讓我們自然而然地想起19世紀(jì)法國畫家米勒的著名油畫——《拾穗者》。《拾穗者》表達(dá)出的是人和大地的親密關(guān)系,散發(fā)出野草和土地的氣息,表現(xiàn)了鄉(xiāng)村生活的質(zhì)樸平凡。在畫面上人類凝重的身軀似乎也預(yù)示著生存的重壓。這一隱含的寓意在《金黃的稻束》中就化為一種通過文字來負(fù)載的信息——“肩荷著那偉大的疲倦,你們/在這伸向遠(yuǎn)遠(yuǎn)的一片/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詩歌與繪畫在這一意義上,它們獲得了相當(dāng)?shù)男Ч督瘘S的稻束》與《拾穗者》一樣,凝重質(zhì)樸、簡(jiǎn)約深遠(yuǎn),展示了人與大地和歷史的澄明關(guān)系——親密而又深遠(yuǎn)。
生活中最為尋常或最為細(xì)瑣的時(shí)刻都能成為創(chuàng)造的一個(gè)標(biāo)識(shí),在這個(gè)標(biāo)識(shí)的引導(dǎo)下,藝術(shù)家通過練習(xí)他的所聞所見、所體驗(yàn)、所感動(dòng)甚至所丟失的事物,使它們交融沉淀,給它們塑形,賦予它們生命。在路上,詩人看到“一束束收割下的稻束,散開,站立在收割后的稻田里,在夕陽中如同鍍金似的金黃,但它們都微垂著稻穗,顯得有些兒疲倦,有些兒寧靜,又有些兒寂寞”,這時(shí)金黃的稻束依然屬于沉睡的庸常事物,它經(jīng)由詩人之手,提升了它與世界本質(zhì)的聯(lián)系,亦即是里爾克所言的“藝術(shù)家應(yīng)該將事物從常規(guī)習(xí)俗的沉重而無意義的各種關(guān)系里,提升到其本質(zhì)的巨大聯(lián)系之中”。這些本質(zhì)的聯(lián)系正是詩人在作品中需要展示的主旨——雕像、偉大的疲倦、靜穆、歷史、河流以及思想。可以說,《金黃的稻束》是“思”與“詩”的完美結(jié)合。
作為技藝領(lǐng)域里的詩歌,也許微不足道,任何有志于詩歌寫作并有相應(yīng)天賦的人都會(huì)在此范疇內(nèi)實(shí)現(xiàn)自給自足。通過閱讀、模仿、練習(xí),一名學(xué)徒會(huì)成功地掌握寫詩的技藝。有了技藝并不能保證你能寫出優(yōu)秀的詩作來。但是沒有技藝一定是無法完成的,假如詩人鄭敏還沒有完成技藝上的磨煉,那么即便她有千言萬語、滿腔感懷又何從下筆呢?狄蘭·托馬斯說:“優(yōu)良的技術(shù)總是在詩的構(gòu)件中留有空隙,以便詩外的什么能夠爬進(jìn)來、溜進(jìn)來、閃進(jìn)來或闖進(jìn)來。”因而我們總是需要儲(chǔ)備好“優(yōu)良的技術(shù)”,以期在某一刻實(shí)現(xiàn)詩。鄭敏先生的那些記憶、經(jīng)驗(yàn)、哲學(xué)、文學(xué)等一系列的儲(chǔ)備在見到“金黃的稻束”的那一刻全部涌現(xiàn)了出來,那些獨(dú)特的意象在那一特定的時(shí)刻全都闖了進(jìn)來。顯然,她更是在“優(yōu)良的技術(shù)”的幫助下實(shí)現(xiàn)了詩。我們知道,里爾克與馮至是她擁有“優(yōu)良技術(shù)”的導(dǎo)師,在西南聯(lián)大時(shí)期,鄭敏先生近受馮至先生的熏陶,遠(yuǎn)受偉大德語詩人里爾克的深刻影響,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創(chuàng)作手段對(duì)于她而言已不是阻礙。
在詩人探尋生活發(fā)源的深處之時(shí),金黃的稻束既給予了詩人問題,也藏匿了曖昧的答案。詩人不急于解決問題,也不急于說出答案。因?yàn)檫@兩個(gè)方面都不是詩歌直接要承擔(dān)的任務(wù),詩歌要承擔(dān)的是一座似有非有的橋梁的作用,有時(shí)候更像一首漂浮在文字與本質(zhì)湖面上的小舟,它肩負(fù)起擺渡作者表達(dá)與讀者理解的重任。詩人輕逸而機(jī)智,并沒有在字面意義上將“金黃的稻束”直接比作“母親”,或是直接比喻為“雕像”,而是閃躍與滑動(dòng),在“稻束”、“母親”和“雕塑”之間建立起動(dòng)態(tài)的感觀,把讀者帶入到更為深入的沉思之地。它們透明無礙地并呈在我們的眼前,各自成峰,而又相映生輝。“金黃的稻束”成為“靜默的雕像”。而偉大的疲倦、偉大的母親、歷史與生命又激發(fā)起我們對(duì)時(shí)間和生命的無盡遐思。但這些事實(shí)總有些晦暗不明,詩人鄭敏深深知曉這一秘密,就像知曉我們自己生命中晦暗的秘密一樣。她不徐不疾,《金黃的稻束》被輕輕地展開,如清風(fēng)拂面,它展示而不說教,它深入而不冗長(zhǎng),它遠(yuǎn)行而不喧囂。它自然形成,如山澗溪流,穿越意義和歷史的叢林,攜帶著它那無可比擬的生命力一直走到今天。
金黃的稻束
鄭 敏
- 金黃的稻束站在
- 割過的秋天的田里,
- 我想起無數(shù)個(gè)疲倦的母親,
- 黃昏的路上我看見那皺了的美麗的臉,
- 收獲日的滿月在
- 高聳的樹巔上,
- 暮色里,遠(yuǎn)山
- 圍著我們的心邊,
- 沒有一個(gè)雕像能比這更靜默。
- 肩荷著那偉大的疲倦,你們
- 在這伸向遠(yuǎn)遠(yuǎn)的一片
-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
- 靜默。靜默。歷史也不過是
- 腳下一條流去的小河,
- 而你們,站在那兒,
- 將成了人類的一個(g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