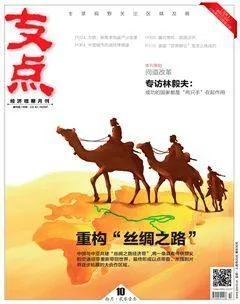林毅夫:成功的國家都是“兩只手”在起作用
核心提示:在每個經濟發展階段,市場是最有效的分配資源方式,傾向發展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但進行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政府既要發揮市場不到位時的監管、協調作用,又要發揮因勢利導的助推作用。
《支點》記者 何輝 楊向明
即將于今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引發全球關注。
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歷次黨的三中全會上,都會提出對中國經濟社會至關重要的政策決議。如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去年11月,黨的十八大已經明確了下一步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即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中,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值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關鍵時候,會提出哪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舉措呢?日前,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用“新結構經濟學”解讀了他對未來中國改革的期待。
三波思潮
某種意義上講,新中國成立后60多年的經濟政策,就一直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中反復調節。
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實行的是完全計劃經濟政策,經濟體制完全由政府控制,幾無市場的空間。1978年至今,中國逐步探索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國家經濟政策從十二大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演進到十二屆三中全會的“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到后來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核心就是在不斷探尋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經濟增長,是以政府為主導還是以市場為主導,不僅在中國是個難題,近400年來在全球經濟學界和政府決策層中也爭論不休,甚至在發展經濟學這一領域還形成了多個流派。
不過,林毅夫更愿意將其稱之為發展經濟學的三波思潮。
第一波思潮叫結構主義。當時的學者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貧窮落后,是因為沒有發達國家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背后的原因則指向市場失靈,是市場無法把資源配置到位,應以政府為主導直接配置資源發展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但實際上結果都很差。
由于前一波思潮的失敗,學者們又認為是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造成資源錯配,還是應該相信市場,于是形成了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應以所謂休克療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等激進改革措施在內的“華盛頓共識”,來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但結果仍然很糟糕,甚至比結構主義時期還要差。
結構主義經濟學強調政府的作用,忽略市場的作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強調市場的作用,忽略政府的作用。“反思前兩波思潮的教訓,我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林毅夫將新結構經濟學看作是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思潮,也被稱之為發展經濟學3.0版。
他說,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制度等經濟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新結構經濟學認為要動態地觀察每一個發展階段的比較優勢,而不能簡單地歸結于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
比較優勢
一直以來,林毅夫都致力于研究發展經濟學,這或許跟他的導師——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有很大關系。因為舒爾茨是發展經濟學家,對發展經濟學及農業經濟有獨到的見解。
在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中,林毅夫非常推崇比較優勢理論。在他看來,發展經濟學前兩波思潮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他們違反了比較優勢的規律。
“任何一個社會在每一個時點上所能配置的資源,也就是其要素稟賦實際上是不一樣的。”林毅夫用通俗的語言詳細解讀比較優勢與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從要素稟賦來看,發達國家的資本相對多,也相對便宜,而勞動力則較少,且較貴。反之,發展中國家資本相對少,也相對較貴,而勞動力相對多且相對便宜。
在競爭的市場中,企業從營運角度來講,一定會用便宜的要素去替代昂貴的要素,所以發達國家要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但結構主義卻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貧窮,是因為市場失靈沒有去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他們通過政府手段強行配置資源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其結果是產品成本太高,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力。
“政府干預過多,資源一定會錯配,效率就會變低。”顯然,林毅夫認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調節作用,但這并不等于說新自由主義的做法是正確的。
的確,市場是對資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但在林毅夫看來,這種有效性是有限制條件的。即在同一個發展階段內,市場對資源能達到最優配置。但經濟發展是動態的,當從一個階段升級到另一個階段的過程中,市場可能無法解決為創新升級而必須配套的外部條件,比如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金融制度的完善、產業群的形成等,這些往往無法通過市場途徑解決,需要政府“有形的手”協調不同企業來投資,或由政府自己提供。
簡單地說,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觀點是,在每個經濟發展階段,市場是最有效的分配資源方式,傾向發展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但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政府既要發揮市場不到位時的監管、協調作用,又要發揮因勢利導的助推作用。用林毅夫的話說就是,經濟發展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但政府更多的角色應該是“助產士”而非“永久保姆”。
因勢利導
新結構經濟學的問世與爭議幾乎是并存的,贊成他的人跟反對他的人一樣多。特別是當他提出中國經濟未來20年還具有可以保持每年8%增長潛力的時候,有人稱他是在“放衛星”,甚至還有人稱他為“林增長”。
“現在有一種觀點,只要是有政府參與的經濟活動,他們就認為是政府在干預市場,這是不對的。”面對質疑,林毅夫依然堅定自己的觀點,語氣平和。
他說,幾乎所有成功的國家都是“兩只手”在起作用。在發達國家,政府的“手”也沒有完全放開,它主要用于新技術的創新和研發,因為在發達國家,技術創新需要有政府支持的基礎科研作支撐,政府可以用于基礎科研的資金有限,因此,必須對基礎科研的項目有所選擇,這種選擇也就左右了商業技術研發的方向。在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是在現有技術產業鏈的體系內進行,不同產業所需的基礎設施、人力資本、金融配套不完全一樣,政府的資金有限,政府也同樣必須對其有限資源的配置做出選擇,政府的因勢利導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
那么,對當前的中國來說,政府該如何因勢利導呢?
林毅夫擅于類比性調研,喜歡用類似或相似的經濟現象對比,然后找出其中的規律或異同點。這種風格跟他的導師舒爾茨一脈相承。林毅夫曾這樣評價自己的導師:“他治學強調經驗事實,并以解決現實的貧困和發展問題為出發點來研究經濟理論。”
從世界銀行回國之后,他到全國各地深入調研。在浙江,他對溫州與臺州這兩個城市印象深刻。
溫州和臺州是浙江省兩個相鄰的地級市。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發展較快,其中溫州更為迅猛,創造了令全球震驚的“溫州模式”,而臺州更多的時候被人稱之是“溫州邊上的城市”。
不過,自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后,兩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有了很大的變化。在浙江省公布的2012年16項經濟指標中,溫州市有9項指標全省墊底。如GDP增幅比上年回落2.8個百分點,虧損企業比上年增加82%。反觀臺州市,各項指標均處于回升狀態,GDP增幅不僅比上年回升1個百分比,就連形勢最嚴峻的外貿出口總額也比上年增長1.2%。
“溫州為什么會出事?臺州為什么發展得還不錯?背后的原因值得研究。”林毅夫認為,溫州的問題就是因為完全相信市場。在競爭的市場中,企業家開始賺錢。當企業家資產普遍達到5億元、10億元、20億元的時候,城市的產業升級沒做好,導致升級不成功,企業家只能投機,導致泡沫越來越大。這是因為產業升級需要政府來協調很多外部性的問題,這些問題不是企業家能做好的。而在臺州,其經濟也是民營企業為主,但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和之后,政府在產業升級方面做的事比較多,比如引導結構轉型、完善金融制度、協調產業集群建設等,其產業升級相對做得要好一些,所以經濟回升態勢好。
回歸本質
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面對人民不斷提升的各種期望以及過去粗放發展帶來的各種問題,中國必須要繼續深化改革。
但此時的改革已進入到“深水區”,沒有“石頭可以摸”。未來的中國經濟往哪個方向走,已成為眾多有識之士關注的焦點話題。
有觀點認為,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相比歐美發達國家,必然有很多體制的不完善,可以向發達國家學習他們的理論來解決這些問題。
但林毅夫并不完全認同這種看法:“外國經濟學家大多并不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他們的理論都是來自發達國家的經驗,而用發達國家作為參照來看發展中國家,大部分看的都是問題。即使是成功的經驗,他們往往也會看成是問題。西方的理論可以作為參考,但不能拿來當藥方。”
林毅夫不僅是在為中國經濟“把脈”,而且在世界銀行工作期間,他也將這種觀察問題的方法帶到了非洲的發展中國家,指導他們如何發展經濟和升級產業。
林毅夫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還是要由發展中國家自己來總結。如何總結?最重要的一點是要回歸發展的本質,“我們要用的是亞當·斯密的方法,而不是亞當·斯密的結論。”
在新結構經濟學看來,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這樣的:經濟增長是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和制度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每一個階段都有其比較優勢。當新的技術不斷替代老的技術,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時,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生產費用不斷降低。同時,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基礎設施要不斷完善,制度也要不斷完善,這樣交易費用才能不斷降低,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才能越來越高。(支點雜志2013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