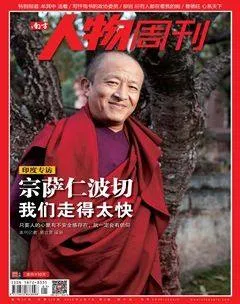怪我們想太多

上周,吳彥祖先生在微博發了張歡天喜地的照片,附之以老婆懷孕3個月的消息。在狂亂的轉發和評論中,許多女青年心碎了。盡管羞于承認,但不得不說,我在轉發途中也萌生了一種“男神生娃、人生蒼茫、這可咋辦”的悲喜交加,如此不堪入目的內心令我深感焦慮:一把年紀了,還在把“瑪麗蘇吳彥祖”當正經事來做,實在太叫人悲傷。
真不能怪我們,對于吳彥祖的精神意淫,上世紀的電影人是始作俑者。1997年,楊凡用《美少年之戀》里別有用心的鏡頭,講述了一個獵奇做作的同性戀故事,電影很普通,但我們跟老色鬼導演心有戚戚,都感受到了吳彥祖羞澀的懵懂和無知的性挑逗。
奧斯卡·王爾德說過:“把事物區分成好和壞是荒謬的,只有迷人與乏味之分。”這句話可以作為粉絲的座右銘,任何一種狂熱的迷戀都能給人生做乘法,而引領我們走入別樣人生的往往是一些事先毫不知情的名字。如今轉頭看看21世紀的頭10年,銀幕上處處都有吳彥祖的名字,香港電影剛剛開始不堪入目和掙扎北上,比起前輩演員們對不合時宜的長吁短嘆,新入行的吳彥祖顯得相當“不自重”,他奇形怪狀的表演頻繁流竄在各式坑爹搞笑又不知所云的電影中,販賣著美貌和身材,成為了香港影壇最有光澤的男花瓶。
《特警新人類》里他演一個沒用又傻帽的反派,赤裸上身穿著皮馬甲,說著大多數人聽不懂的普通話,死時涕淚橫流,一點兒都不酷。到了《新警察故事》,他依然是反派,卻滿面猙獰地出挑了,以爆烈偏激又心理扭曲的表演拿到了當年金像獎最佳男配角獎。之后,《新扎師妹》里的白馬王子、《知法犯法》中毒辣卑劣的背叛者、《妖夜回廊》里的性侵受害者、《門徒》中淡定復雜又沉重的毒品臥底……他端整到多一步就萬劫不復的樣貌,在各種極端、出位又出軌的角色里,一邊不以為然一邊閃閃發光,而圍觀在旁的女青年則一邊激蕩得口水橫流,一邊欣慰得心中竊喜。當時有個不足為人道的遠大理想:等姐有錢了,一定投資電影請吳彥祖來演,光是他赤裸上身擦車的鏡頭就要拍100遍!
那10年,一直覺得我們與吳彥祖的位置是分垂直階層的,他英俊得所向披靡卻從不傲慢,有名模女友、不鬧緋聞,照顧一群帥哥好友,講著流利的英文和可愛的中文,穿發皺的襯衫,還懂得在南非來一場雞犬相聞的大自然婚禮。他高高在上的工整完美比100萬種人生都要令我們艷羨、垂涎和遙不可及。
2011年,《竊聽風云2》的采訪中,我見到了吳彥祖。他依然帥得死去活來,走起路來虎虎生風,像華爾街精英一樣坐在對面,平靜親和分毫不差,答題系統是全英文的,講出的中文像事先背好了答案,無論怎樣逼問都沒有多一分心聲可吐露。那時候忽然明白,對于吳彥祖,是我們想太多了——他沒那么傳奇激蕩,自我定位也從不是健康英俊、性格完美的男性幻想體,他的人生就是把各式中文劇本標注上拼音背好完成,賺錢回家,做飯陪老婆,和好友搞搞惡作劇,翹首期盼閨女的誕生,像每一個普通男人那樣享受成就感,繼而與世界和睦相處。
不怪吳彥祖,都怪我們想太多,可是,人生都是越走越慢的,每老去一點都要回看慢鏡頭的此去經年,于是有那么一些時候,忽然能夠明白《美少年之戀》結尾的意味所在——在我的那10年里,每一段驀然回首的美好歲月,眉間都酷似1997年的吳彥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