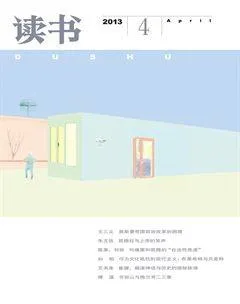后發展的政治
現代化發軔于西歐卻傳播于全世界,以其巨大的力量裹挾了幾乎所有的政治共同體,并將其置于一種相似的地位,即“后發展國家”。“后發展國家”只是對特定國家所在的發展階段和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所處位置的一種籠統描述,其實不同的后發展國家有著不同的發展道路和經濟表現,戴維·瓦爾德納的著作《國家構建與后發展》為解釋后發展國家之間的差異提供了新穎的見解。
瓦爾德納具體考察了土耳其、敘利亞、韓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發展歷程,他的分析發現,盡管土耳其、敘利亞、韓國都屬于“后發展國家”,而且都試圖利用戰后的發展機遇,但是經濟增長現象的背后三個國家之間存在深刻的差別。土耳其和敘利亞的制造業實現了快速的發展,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們的工業化程度與韓國相比已經遠遠落后,甚至可以說起初微不足道的差距已經擴大成為一道幾乎無法逾越的鴻溝。韓國不僅在制造業產出、產業多元化和工業增長方面超過了敘利亞和土耳其,而且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即使在轉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部門時,韓國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同樣具有相當的競爭力。
出現這樣的發展差異的原因何在呢?瓦爾德納認為發展存在固有的集體困境,不同的國家解決集體困境的能力不同,因而發展自然呈現差異;國家解決集體困境的能力,受制于國家從間接統治向直接統治轉型過程中精英之間沖突的程度,不同程度的精英沖突導致了不同的國家制度和政策。
發展意味著經濟結構和過程的變化,這種變化提高了創造價值的能力。可以將發展變成一個分析性的概念,它包含四個層面的內容:創造人均國民收入的實際增長的新投資,部門和產業關聯的建立,任何既定產業部門中生產過程的生產效率的提高,轉向較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一個國家的發展路徑涉及其中每個層面的變化,如果不能按照發展的多維層次前進,一個國家要想實現持續的繁榮無異于以沙建塔,其理由很簡單,這就是發展有其固有的困境,并不是每一個國家都能夠克服困境實現多維度的發展。
發展中的困境早已為很多學者所注意到,奧爾森有意識地針對亞當·斯密所提出的“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的理念,認為個人的理性行為將造成集體行動的困境,他在探源國家興衰時就認識到經濟的增長、效率的提高、普遍的繁榮對社會成員而言是普遍有利的,然而多數社會成員或由其組成分利集團,不是選擇將增長的財富投入發展,而是選擇將增長的財富進行再分配,于是國民經濟將不得不停滯下來。為何社會成員會做出此種集體非理性的選擇?投資于發展總不免存在風險,其關鍵點是不能預料自己能否以及何人將會獲得收益,特別是其他人能夠在不承擔風險或者成本的情況下獲得收益,甚至可能比那些承擔了風險和成本的人收益更大,因此理性行動的個人自然會避免從事有風險但是對社會有益的行為。
瓦爾德納將后發展國家遭遇的發展中的集體困境歸納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格申克龍集體困境,另一種是卡爾多集體困境。格申克龍集體困境是誘導資本家對新項目進行投資的難題,解決這種集體困境會帶來粗放型的增長;卡爾多集體困境是使現有的工廠更有效率并在產品周期中向上爬時遇到的難題,解決這種集體困境會帶來集約型的增長和創新。土耳其和敘利亞政府解決了格申克龍集體困境,但是兩國對格申克龍集體困境的解決是以加劇卡爾多集體困境為代價的,但是韓國政府則成功地應對了格申克龍集體困境和卡爾多集體困境,因此韓國實現了經濟的起飛,一躍成為新型工業化國家,而土耳其和敘利亞則陷入發展困境,難以實現國家的長足發展。
同是后發展國家,何以在解決發展中的集體困境時出現如此大的差異?其基本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后發展國家的國家制度能力和政府政策存在極大的差異,而一定的國家制度能力和政府政策構成了區分后發展國家類型的基本尺度。土耳其和敘利亞屬于早熟的凱恩斯主義國家,所謂早熟的凱恩斯主義意指國家還處在工業化初期之時就已經執行了高水平的轉移支付政策;韓國則屬于發展型國家,此種類型的國家執行低水平的轉移支付政策,政府政策的核心目標是推進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具體來說,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分析早熟的凱恩斯主義國家和發展型國家之間的差別:首先在國家與社會關系方面,早熟的凱恩斯主義國家是一種支持—庇護主義關系,而發展型國家則是一種控制關系;其次在官僚系統方面,早熟的凱恩斯主義國家缺乏獨立于政治的官僚系統,而發展型國家則具有高效率的獨立的技術官僚系統;第三在財政政策方面,早熟的凱恩斯主義國家執行以高水平的轉移支付為內容的分配性的財政政策,而發展型國家則以低水平的轉移支付為其財政政策的基本特征;最后在國家干預經濟的模式方面,早熟的凱恩斯主義國家是出于維持社會集團對政權的政治忠誠的需要,保護政權的支持者不受市場變化的影響,而發展型國家則是出于經濟發展最大化的目的,支持企業在競爭性市場中不斷提高生產效率、推動產業升級、更新經濟結構。要言之,早熟的凱恩斯主義國家是國家制度的自主性很弱的國家,因此此種類型國家的政府政策嚴重地受制于政治,必須通過執行高水平的轉移支付政策來換取社會集團的政治忠誠;而發展型國家的國家制度具有很高的自主性,所以它的政府政策是去政治化的,財政支出無需顧慮社會對轉移支付的需求,只需專注于推動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
后發展國家呈現出的不同類型,是國家構建的不同過程導致的。國家構建意指一個政治共同體從間接型統治走向直接型統治的過程,在間接型統治的國家,國家精英通過與地方權貴的聯盟進行統治,而在直接統治型的國家,制度和機構取代了權貴的中間作用,并把國家、經濟和社會聯系在一起。伴隨著從間接型統治向直接型統治的轉型,舊的制度被重新定義,新的制度建立起來,政治共同體的成員獲得了新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認同,國家擴大了供應公共物品的責任以回應新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認同。
后發展國家的國家構建存在兩種路徑:一種是統治類型的轉型與下層階級的吸納同時進行,另一種是統治類型的轉型先于下層階級的吸納。國家精英在統治轉型的同時是否進行下層階級的吸納,取決于國家精英內部沖突的程度,如果國家精英內部存在高強度的沖突,那么想要把握住國家統治權的精英群體將把目光轉向下層階級,以建立跨階級聯盟的方式來贏得下層階級對統治權的支持,若是國家精英內部只是存在低強度的沖突,那么相對統一的國家精英無需向下層階級尋求支持,而只需要維持小范圍的聯盟就可以掌握住統治權。瓦爾德納認為從十九世紀開始精英沖突的三種來源削弱了精英的統一并且不斷地刺激了更深刻的精英沖突和分化:第一是經濟的發展要求國家的干預,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帶來建立新的國家機構和征收新稅種的要求,這就會導致激烈的分配沖突;第二是傳統的農業精英和新興的工業精英將在國家的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上發生沖突;第三是在如何應對日益自信的下層階級問題上,精英集團內部也發生了分裂。
雖然精英集團之間的沖突不斷且來源多樣,但是沖突的存在并不意味著精英群體之間的合作難以為繼,也不意味著精英集團無法延續其對統治權的掌控,只有精英內部的沖突發展到高強度的時候,精英集團的某一群體才會將結盟的戰略從精英內部的小范圍結盟調整到跨階級的結盟。高強度的精英沖突意味著激烈的沖突帶有毀滅性質,也就是說沖突不僅威脅到精英的短期物質利益,而且威脅到精英維持其精英地位的長期能力。如果說獲得剩余的權利暫時減少了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將來獲得剩余的權利也遭受威脅則是忍無可忍的,因此相互競爭的精英群體必須尋找盟友來增強自身的力量,以維護其精英地位,欲達此目的,除了把眼光轉向下層階級建立跨階級聯盟之外別無他途。
總結來看,瓦爾德納力圖解釋存在于國家構建、國家類型、經濟發展之間的因果關系,這種因果關系建立在兩種機制的基礎上,一種是存在于國家構建與國家類型之間的機制,另一種是存在于國家類型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機制,前者是精英沖突的程度及由此決定的結盟方式,后者是國家制度和政策克服后發展的集體困境時具備的能力。
(《國家構建與后發展》,戴維·瓦爾德納著,劉娟風、包剛升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二零一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