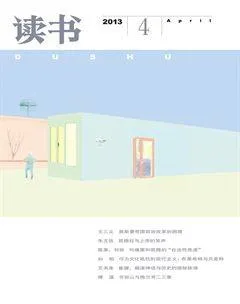桑德爾的魅力與局限
在美國導演伍迪·艾倫調侃哲學、政治乃至俄羅斯文學的電影《愛與死》中,一段類似的對話出現過兩遍。對話的引子,是關于一個行為是否道德的這個問題。由此,兩個對話者就有如對口令一樣,進行了大概是這樣的一段對話:“××是不道德的”;“但是道德是主觀的”;“可是主觀性是客觀的”……接下來,對話者就開始用更多晦澀的哲學術語,無厘頭式地接著對口令。比如,在這個對話第二次出現的時候,其中一個對話者說道:“道德概念隱含著實體(substances)的屬性,這種屬性只在關系二元性中存在。”而其回應者說道:“(但是它們)不是作為本體的存在的一個本質的外延(而存在的)。”說到這里,與第一次對話不同,其中一個對話者終于忍不住了,說道:“我們能不能不這么多地談性了?!”
這是我看到的對學究式的哲學最妙的調侃,也是對哲學本來是什么的一個也許是不經意的揭露。哲學問題起自日用常行。但是,很多時候,被一層層哲學術語與理論遮蓋著,我們忘了或是根本不知道本來我們是要談什么的了。這一點,在當代中國教育中可能更加明顯。新中國成立之后種種運動,造成了教育的斷裂。失去了自己的傳統,我們很多學者不僅僅是食洋不化,更是食中也不化。并且,因為很多年唯一正確的哲學只有一種,所以其他哲學至多也只能當作博物館里的物件兒來研究。多年沒有通識教育的要求,大學里哲學也成了一項專家的學問。這種失去了土壤、失去了根基、死了的、由經常是講者也不懂的詞匯堆積起來的東西,又怎么能對學生有任何觸動?這時,一個叫桑德爾(Michael Sandel;按其名字的發音,譯成“散代爾”更好些)的洋教授出現了。他不是一般的洋教授,是哈佛的洋教授。他也不是一般的哈佛教授,是那里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他居然可以把那些晦澀枯燥的哲學理論講活,與我們日用常行結合起來。這樣的講座能風靡,應該也不是太讓人驚訝的事情。我想,桑德爾的流行,除了“美國”、“哈佛”的光環外,除了他的口才與不錯的外表,與他能讓哲學直指人心的能力有很大關系。
筆者在波士頓大學就學時,也曾到哈佛旁聽過桑德爾的課。不過不是后來為他贏得大名的那門公開課,甚至不是完全由他自己教的課,而是與美國知名保守派政治學家曼斯菲爾德(Harvey Mansfield)與保守派政論家威爾(George Will)合開的。桑德爾是左派,后兩者是右派。但是他們能在一個教室里,結合美國的政治,闡明自己的觀點,并在理解對方的基礎上批評對方,同時又保持著學者(或者紳士)的基本風度,不但讓我這個學生受益,并且,當我想到中國的各式左派和各式自由派熱衷于互貼標簽,在簡單化、丑化對方的基礎上相互攻訐,甚至采用厚黑的手段,意圖置對方于死地時,我不由得非常感慨。
當時,我對他們講課的印象不錯。不過,在我回國后,聽說桑德爾的公開課在中國非常流行時(基于這門課的書的中譯本《公正:該如何做是好》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還是驚訝了一下。上網查查,中國觀眾最常提到的,是他講的“電車問題”(the trolley problem),即如果我們只能從讓電車軋死一個人或是五個人中選(這個選擇的情境在不同版本中有不同),我們應該如何選擇的問題。我看到這兒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為中國的教育感到悲哀。電車問題,是很多美國大學哲學老師(尤其是有分析哲學背景的老師)在教通識類道德哲學課程時必然要提到的問題。可是,在中國的觀眾和讀者中,卻成了新奇的東西。當然,即使在哈佛、在美國,桑德爾還是有他的魅力。前面提到,這來自他的口才和讓哲學直指人心的能力。不過,另外一點,是他一遍遍地重復教同一門課。這種做法,對提高課程本身的質量很有幫助。但是,從學術角度而言,這未免有些懶惰,或者是對學生歡迎的在乎超過了對學術本身的追求。并且,如果教的是某一本哲學經典本身,重復教授可能也可以讓講者發現新的、深刻的東西。但是,桑德爾的課程是基于現實案例,摻雜了從各個哲學家的著作中摘取的觀點。重復這樣的東西,恐怕有礙于教課者的學術水平的提高。
并且,用現實案例,可以讓學生知道哲學不是空中樓閣,而是源自日用常行。但是,過多局限于這樣的案例(和對哲學經典的東摘西錄),卻有使人沉淪于日用常行的危險。可能是反感于美國主流哲學家沉溺于這樣的案例與撇開經典的“獨立”思考,筆者的老師羅森(Stanley Rosen)曾在課堂上調侃道,現在道德哲學家總是考慮,如果我的老婆和我的情人都在一條船上,我應該把誰推下水去。我的答案是把她們都推下水去,再換個新的。嚴肅地講,這種現實案例,可以激發學生的興趣。摻雜了一些哲學經典的摘錄,也使得這種討論有了哲學的味道。但是,哲學經典之所以是經典,是因為它們是兩千年最聰明的人的思考的結晶。對它們的東摘西錄,無法讓我們真正全面理解經典中的深刻思想。而理解這些思想本身,才是真正能挑戰我們,讓我們的思考深化的。當代美國推崇的獨立、批判性思維,蔑視“死了的白人的書籍”(dead white men’s books)。其結果是講課往往淪落為學生已有的個人成見的宣泄,因而可能是最不具有批判性的。反而,尊重經典的權威,可能最有利于培養批判性、創造性思維。
因此,桑德爾課程的最大缺陷,是缺乏對經典文本的尊重與細心。哪怕在他自己的研究中,這恐怕也有所反映。他在學界成名,是對羅爾斯《正義論》中的一些基本觀念(比如原子式的自我)的批判,這在后來被歸入所謂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批判。但是,在《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的“社群主義”詞條中,本身受社群主義訓練出身的貝淡寧(Daniel Bell)指出,社群主義者對原子式的自我的批判并不適用于羅爾斯的自由主義。在《正義論》的第三部分中,羅爾斯自己其實對有助于做出正義承諾的、自由的自我(liberal selves)之形成的心理與社會條件非常重視。接著,貝淡寧不無調侃地指出,很少人讀到了《正義論》這本厚書的第三部分(這一點,與這一點下隱藏的幽默,我想讀過《正義論》的人恐怕都能理解——羅爾斯可能絕不算是一個文筆好的人,說話有時啰里啰唆,但是很多一流的哲學家都不是一流的作家,反過來也一樣)。因此,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的原子式自我(即與社會、歷史、心理脫離的自為的自我)的批判很有影響,但是這一批判并不成立(桑德爾好像對“社群主義”這個頭銜有抵觸情緒,但是他對羅爾斯的批判之一確實是圍繞著后者的所謂原子式的自我的概念)。
總而言之,桑德爾講課方式的優點,是將哲學帶入生活。但是,我們不能只停留在那里。也許讓我們超出生活之一般的最好辦法,是再從生活回到經典,看看那些歷史上最聰明、最深刻的人是如何處理只要有人就要去解決,但又似乎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桑德爾式的課程,是個有用的拐杖。但是,到時候了,我們要學會把它扔掉。
上面這些評論,是對桑德爾課程的一般評論。下面,我還想說幾句針對中國讀者的話。像我提到的,桑德爾在中國的流行,襯托出了我們教育的可悲處境。這里,食洋不化還情有可原,但是我們連自己的傳統都忘掉了,或者是丟到了一邊去,而被外人的思想忽悠來忽悠去,這更令人悲哀。桑德爾觸及的,或是政治哲學的一般問題,其實我們的老祖宗都是想過的。哲學問題嘛,之所以是哲學問題,就是要超越時間與地域的。如果一個問題只是一個時代的人、一個地域的人在想,那它就不是哲學問題,而是特殊的文化與習俗。比如,桑德爾在其學術研究和公開課中討論很多的,是對原子式個人的批判和對人的社會性的強調。而中國的儒家的一個重要認識就是人的社會性。這種認知,是桑德爾整個政治哲學體系的基礎。桑德爾在他的《公正》一書的第九章里,討論了個人是原子式的還是社會性的問題,并由此引申出了很多疑難,比如一個人是應該將對家庭的關愛還是將對國家的忠誠放在前面。這個問題,也恰恰是儒家有過豐富討論的問題,并有著與西方近現代主流學派不太一樣的思考。從《論語》中關于親親互隱的討論到《孟子》中關于舜與其父、其弟、其國之間關系的種種辯難,乃至《孔子家語》中對曾子與其父曾點的關系以及由此引發的孔子對舜與其父關系的評論等等,與《公正》第九章里的討論既有關聯,恐怕又深刻得多。這些問題的細節,我不能在這么短的一篇文章里討論。只是很一般地講講,西方近現代哲學中,主流的傾向是將家與國,或者更一般地講,私與公,表現為一種截然對立,再在這種對立中,做一個原則性的優先選擇。儒家當然也明白私與公的對立,但他們也意識到私于公的正面作用,即所謂能近取譬、推己及人。我們只有自己愛財愛色,才能理解別人也是愛財愛色。我們只有愛自己的父母子女,才能理解別人類似的情感,并從我們的自然情感中外推到他人身上,即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儒家希望,用這種公私的互補,去克服公私的沖突。這就意味著我們要學會對沖突各方排序。但是,儒家又不覺得有一個現成的序列,而它只能從現實摸索中求得。這使得儒家能在特殊情境與一般原則之間找到中庸之道。這些想法,對當代主流的公私對立思想以及對現成原則的過度強調,都是一種很好的修正或替代。比如,在《公正》第九章里,桑德爾提到了民族主義與博愛之間的矛盾。在當今的中國,也頗有學者強調民族國家的思想是現代化的標志,意圖發展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與以前的國際主義思想對抗。但是,這恰恰又是忘了傳統、盲目模仿西方的一個例子。這是因為,儒家乃至受儒家影響的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恰恰試圖超出這種對抗。那種基于民族國家的、以國界(民族)劃界的敵我分明的權利政治(realpolitik)顯得太過冷漠,并將國與國的沖突永久化,而基督教式的博愛又顯得太過幼稚與空想。與此相對,儒家承認一個人對本國的關愛超出對外國的關愛(即等差之愛)的正當性。同時,人之所以為人,恰恰在于我們有不忍人之心。如果我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罔顧他人的利益,即使我們可以茍活,但我們就不再是人了,而是惻隱之心泯滅了的禽獸。因此,我們就必須對外國人也要有關愛,而不是將他們當作我們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筆者多次說過,儒家的這種方式,比民族國家的想法更理想,但是又比基督教式的泛愛更現實。“華夏”至少從先秦思想家孟子開始,就是個文化概念,而不是西方近現代民族國家中的血緣概念。它比以血緣為基礎的民族更具有包容性,這恐怕也是中國歷史上能吸收、同化很多狹義上的民族的基礎,通過這種柔性的文化擴張來達到天下大同。這本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對世界政治的獨特貢獻。但現在,卻有著被東施效顰式地模仿西方中,又被湮沒的危險。筆者只能希望,我們能夠脫離那種忘了祖宗卻又食洋不化的尷尬境地,自信地回到自己的傳統。在當代與西方兩重參照下,真正地明白中國傳統的獨特之處,以對世界政治做出我們的貢獻。在這里,最中國的,與最世界的,就可能找到了匯合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