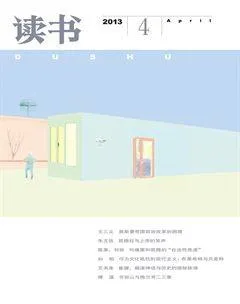知識人的黃昏
自從美國學者拉塞爾·雅戈比在一九八七年出版其《最后的知識人》一書以來,西方學術界基本上一致接受了他提出的論點,即以自由撰稿為生的獨立自由的知識人時代已經是黃鶴一去不復返了。知識人從此進入了一個日益專業化的時代,一個特定領域的博士文憑成了任職于任何學術機構不可或缺的敲門磚;那些以有教養的公眾為生的白雪陽春刊物在大眾文化的沖擊之下,也日漸成了明日黃花。在雅戈比看來,導致美國文化中知識人衰落的致命因素是一切向錢看的商業文化,以及知識日益專業化的趨勢:戰后高等教育的“爆炸”把知識人的身份從獨立的變成了依賴的,從自由撰稿人轉變成了拿薪水的大學教師(參閱Russell Jacoby : The Last Intellectuals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 1987, New York,14頁)。
但雅戈比首次創用了“公共知識人”這一語詞,來概括那些超出自己的專業之外,而向普通公眾闡述一個民族國家的道義問題和公共關懷的文化。差不多與此同時,隨著法國知識巨人薩特在一九八零年去世,福柯在一九八四年英年早逝,法國的后現代哲學家利奧塔德(Lyotard)也發出了“知識人已經死去”的驚呼。當然,這樣的知識人時代概括和驚呼只是一種文化隱喻,標志著那種像伯特蘭·羅素和薩特那樣代表“社會良心”,為“社會公正”和“世界和平”奔走呼吁,以及像丹尼爾·貝爾、歐文·克利斯托、萊昂內爾·特里林和加爾布雷斯這樣解剖和批判美國社會的公共知識人,以及那些靠自由撰稿為生的獨立知識人,不是壽終正寢,就是銷聲匿跡了,同時也標志著公共知識人擁有“一呼百應”影響的時代已經終結了,簡言之,標志著“知識人的黃昏”。
作為一個小插曲,美國上世紀的知識巨人丹尼爾·貝爾在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仙逝,享年九十一歲。他的名著《意識形態的終結》(一九六零)和《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一九七六)影響了整整一代的西方學人。對中國讀者來說,那本《后工業社會的到來》(一九八零)可能更有點像當年赫胥黎的《天演論》在中國的轟動:想當初,八十年代末的中國學人看了貝爾的書之后,曾放言“小心被開除球籍”,也不知那種“憂患意識”究竟對今日中國的轉型起過多少作用。那種意識今天看來,已經恍若隔世了。但貝爾在美國則是一位典型的“最后知識人”,最后一個不靠博士學位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做教授的獨立學者。他的去世更標志著美國獨立知識人時代的終結。
無獨有偶,二零零一年,美國的一位上訴法院的法官理查德·波斯納也寫出了一本題為《公共知識人的衰落》的書。波斯納沿襲了雅戈比所創用的“公共知識人”的界定,然后以美國社會科學學術界慣用的實證方法,用一個知識人學術著作的被引用數、上媒體的頻率和網頁點擊率,來衡量一個公共知識人的影響力。他以為現在公共知識人的主要社會作用與其說是為“社會公正”呼喚吶喊,還不如說是給公眾提供“娛樂消遣”;公共知識人的頭上早已失去了“道義良心”的金色光環,他們對公眾的影響力也愈益減弱;現在公共知識人出現在媒體上主要是提供專業知識方面的資訊,而不是社會應該如何運行的高見了。媒體之所以看重公共知識人,是因為知識人提供的娛樂和鼓舞作用要大于普通的記者(參閱Richard Posner: Public Intellectuals-A Study of Decline. 200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46頁)。在波斯納看來,這種公共知識人“娛樂化”和“知識化”現象的一個根本原因,是現代學科專業的劃分日益瑣細和狹隘,任何知識人都難以跨越分工精細的專業鴻溝。
就社會商業化的總體趨勢而言,雅戈比和波斯納的分析基本上也適合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知識人命運的演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可能還有不少靠稿費為生的文人學者,或者沒有博士學位而當上大學教授的,但從新世紀開始,在社會商業化和學科專業正規化的大潮之下,上述兩種昔日的知識人已經越來越像是鳳毛麟角了。中國知識人的“道義良心”作用也正在逐漸喪失,而“娛樂消遣”的味道則愈益明顯。從前國內流行的“報告文學”的體裁現在已經基本上消失不見了,代表“道義良心”揭露社會黑暗面的作者大都也改用了專業性比較強的現代新聞報道,而讓“道義良心”的評判功能主要留給了讀者和觀眾自身。知識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道義良心”的化身,而同樣是充滿“七情六欲”的世間凡人。在一個法律秩序趨于日漸正規運作的社會里,知識人與普通有教養的公眾之間的距離愈益縮小了,而作為社會“道義良心”代言人的知識人已經是銷聲匿跡了。
但是自柏拉圖和孔子的時代以來,“社會公正”和“道義良心”一直是知識人的核心關懷,或者說是知識人的烏托邦。柏拉圖認為一個“理想國”最好是由注重知識的哲學王統治的社會;對孔子來說,一位“賢君”則是“行天下之道者”。但是現代知識人的正式形成則要到十九世紀末法國的“德雷弗斯事件”,以作家左拉為代表的一批法國知識人紛紛挺身而出,抗議政府當局誣陷猶太人德雷弗斯。直至今日,文藝評論家愛德華·薩伊德對知識人的定義,仍然是“擁有自由精神的‘終身牛虻’”。他們的職責在于公開地提出令當局難堪的問題,抗拒正統和教條,以道德勇氣對抗當局。在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看來,知識人就是用激烈的辭藻為受到侵犯的權利辯護的人,他們也為受到壓制的真理、被延誤的社會進步而奮斗;他們的存在則有賴于一個能夠隨時回應,并且資訊充分的公共領域,以及那些得到人人確認的普世價值。按照卡爾·曼海姆的經典定義,知識人的職業是自由飄浮,獨立不依的,他們屬于社會秩序中相對無階級的階層,屬于社會上不依附于人的階層。
紐約大學的一位自由派歷史學家托尼·賈特(Tony Judt)在二零一零年初出版的一本新著《沉疴遍地》中指出,美國人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以來愈演愈烈的物質主義崇拜和貧富之間鴻溝的擴大,已經像一種病魔侵入了這塊曾經是神顯的國土。這種病魔便是物質主義的貪婪和喪失了公共美德的極端個人主義。它在侵蝕著美國社會的神經系統——體現社會公正和公平的種種機制;而且病魔早已使得美國社會在社會公平方面遠遠落后于歐洲的福利國家,也落后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亞。賈特引用了詩人奧利佛·哥德斯密的一首“荒村”的小詩,來作為他全書命題的隱喻:
財富聚集之地,蕓蕓眾生危亡,
病魔肆虐無忌,國土病入膏肓。
(參閱 Tony Judt: Ill Fares the Land, 2010, New York, 扉頁)
也是在二零一零年,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佛大學教授阿瑪蒂亞·森在其新著《正義的理念》一書中,指出了羅爾斯以公正制度描繪絕對正義的正義論的不足。在森看來,正義原則不應是由體制來界定的,而是由改善人的生活和自由界定的;體制正義論沒有考慮到人的行為的偏差可以在正義體制下同樣造成極端的不公正(參閱Amartya Sen:The Idea of Justice, 201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XII頁)。因而森的正義論更加關注于“可糾正的明顯不正義”,而不是從一種假想的社會契約演繹出絕對公正的抽象正義原則;從而這種多元的正義論也就更多地帶有社會批判的色彩。
托尼·賈特在其二零零五年的一部杰作《戰后歐洲史》中便講到了歐美公共知識人的命運。在最后一章“歐洲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中,賈特說道,公共知識人在二十一世紀的歐洲已經愈益成為一個瀕臨滅絕的物種,那些上世紀留下來的著名知識人也都陷于日益邊緣化的境地(Tony Judt: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The Penguin Press, 2005,785頁)。二零零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歐洲一些最為著名的領軍知識人,為了反對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在一些最有影響的報刊上,發起事先計劃好的聯合行動:德國的哈貝馬斯與法國的德里達,兩位歐洲最為著名的哲學家和公共知識人,在《法蘭克福匯報》上聯合發表了一篇文章:《歐洲的再生:我們在戰后的新生》。他們指出,美國最新的危險途徑給歐洲敲響了警鐘,歐洲人應該重新思考他們的公共認同,吸取他們共享的啟蒙價值,在世界事務中采取一種獨特的歐洲立場。
在同一天,歐洲一些同樣著名的公共知識人也發表了類似的文章,意大利哲學家兼小說家艾柯在首屈一指的《共和國日報》(La Republica)上,他的同事哲學家法蒂默(Gianni Vattimo)則在意大利最為著名的《新聞日報》(La Stampa)上,瑞士的“日耳曼藝術學院”主席阿道夫·默奇(Adolf Muschg)在《新蘇黎世日報》上,西班牙哲學家費爾南多·薩瓦特(Fernando Savater)在西班牙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國家報》上,以及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在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南德意志日報》上,都發表了類似的文章,做出了相應的呼吁。賈特說,在上個世紀的任何時刻,由如此出眾的社會著名人物發起,同時發表在這樣大型的報刊上,這樣一種規模的知識人呼喚,注定會是一個特殊的重大事件:一種會沖及政治和文化社區的宣言和宣戰書(同上書,787頁)。
然而這一“哈貝馬斯—德里達倡議”,盡管澄清了許多歐洲人所共享的愿望,但是卻靜悄悄地過去了而未受到人們的重視。首先歐洲各國的新聞記者并沒有報道這一“事件”,各國的政治領導人也根本沒有想到邀請這些名人學者去出謀劃策,而廣大的民眾更是當其為專家的奇文怪談而充耳未聞;即便是同情者竟然也沒有積極響應。當年左拉和薩特時代的知識人登高一呼,公眾群起響應的日子,仿佛已經是非常遙遠的過去。公共知識人的影響力早已為足球明星和搖滾歌星所取代了。“哈貝馬斯—德里達倡議”的命運恐怕更為明顯地顯示了他們已經是瀕臨滅種的最后公共知識人了。
公共知識人在其專業之外起到了“指導民意,激揚文字”的作用。然而隨著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斗爭的消亡,就是“公共知識人”也缺乏一種可以號召民眾的社會目標,從而出現了熱血的公知與冷淡的公眾所形成的鮮明對照。今日的公眾已經成了政治上“冷淡的一代”;然而可怕的是,冷淡與狂熱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昔日的狂熱曾產生了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今天的公眾冷淡癥同樣可以造成各種日常生活中的無形專制,以及貧富差別所帶來的社會不公。
《知識人的黃昏》這本書收集了筆者在跨世紀二十年時間里所寫成的一些有關知識人與文化批評的論文和隨筆。那些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寫成的論知識人的文章在當時仍屬于領風氣之先,打破了當時國內知識界依然彌漫著左傾激進主義的神話,引發人們重新反思知識人的社會作用;也引發人們重新反思“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人偏重破壞遠遠超過注重創新的偏向。現代以來中國知識人創造性的貧乏某種程度上要歸咎于對傳統文化的破壞。本書的后三分之二的文章則大都是一些文化隨筆,是作者在美國經受了十多年的洋插隊之后,以切身之體會,對歐美社會做出的一些思考和感悟。如果說九十年代在國內寫成的論文主要批判了國內知識人的文化激進主義偏向,那么近幾年有關歐美社會和知識人的隨筆則重新祭起了一個知識人“道義良心”的旌旗。
伯特蘭·羅素在《西方哲學史》緒論中說:“每一個社會都受著兩種相對立的危險的威脅:一方面是由于過分的講紀律與尊敬傳統而產生的僵化,另一方面是由于個人主義與個人獨立性的增長而使得合作成為不可能,因而造成解體或者是對外來征服者的屈服。一般說來,重要的文明都是從一種嚴格和迷信的體系出發,逐漸地松弛下來,在一定的階段就達到了一個天才輝煌的時期;這時,舊傳統中的好東西繼續保存著,而在其解體之中所包含著的那些壞東西則還沒有來得及發展。但是隨著壞東西的發展,它就走向無政府主義,從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種新的暴政,同時產生出來一種受到新的教條體系所保證的新的綜合。自由主義的學說就是想要避免這種無休止的反復的一種企圖。自由主義的本質就是企圖不根據非理性的教條而獲得一種社會秩序,并且除了為保存社會所必需的束縛而外,不再以更多的束縛來保證社會的安定。”(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一年版,23頁)羅素并說,自由主義是一種企圖既尊重傳統,又保持個人獨立的嘗試。由此想到,一個知識人的立場也在于尊重傳統和維護個人獨立之間保持一種平衡。在尊重傳統和個人自由之間保持一種平衡,也就是認識到世界上的“社會公正”都是相對的,終結的“社會正義”只存在于哲學家和詩人的想象之中,而且有眾多的版本;那些最基本的普世價值的實現都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因而一個知識人的職責,就像法國學者雷蒙·阿隆所說的那樣,在于評判各種政治體制下的相對非正義時維持一種適當的道德責任感,做一個帶著卑微公民角色的獨立觀察者。
最后就本書所用的“知識人”一詞做一點說明:二零零八年五月的一天,余英時先生到寒舍來與紐約讀書沙龍的朋友們座談,講起大陸至今仍沿用革命氣息濃重的“知識分子”一詞來指稱知識從業人員,為什么不用比較中性的“知識人”一詞。仔細想想,“知識人”作為一個翻譯詞語,與本土的“文化人”一語相當接近,不過是指帶有公共關懷對大眾答疑解惑的專業知識人士,某種意義上他們是用文字和言語替天行道者,有時頗像一種縮小了的“蝙蝠人”或“蜘蛛人”,因而將“Intellectual”譯成“知識人”更加具有形象的魅力。所以本書將以前文章中所用的“知識分子”一語一律改成了“知識人”。
(《知識人的黃昏》,傅鏗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