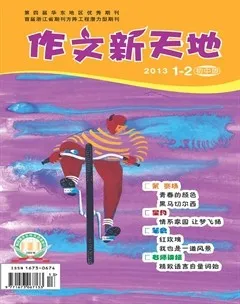Tomorrow is another day
每每去圖書館借書,總不會去看《飄》,它很顯眼但讓我很害怕,因為它的厚度。第一次決定讓《飄》離開書架是在觀看了電影《亂世佳人》之后,近4個小時的電影正如其近千頁的著書,只要你開始邁入,開始欣賞,其長度或者說厚度便讓你的膽怯之情消失殆盡。我向來最怕看外國名著,難記的人名、多線的人物關系以及復雜的故事情節,總是讓自己放棄接受外國著作熏陶的機會。不過,《飄》是除《巴黎圣母院》之外,又一本讓我喜歡上的外國文學。
說《飄》“厚實”,一點也不為過。不僅是指它的頁數多,更是指其覆蓋面的廣——政治、經濟、道德、愛情等諸多方面都有涉及。《飄》是美國女作家瑪格麗特·米切爾十年磨一劍的作品,也是唯一的作品。小說以美國南北戰爭為背景,以莊園主小姐Scarlett(斯嘉麗)與幾個男人之間的愛恨情仇的糾纏為主線,伴隨戰爭發生后的各種變遷,奏響一曲人類愛情的絕唱。其堪稱有史以來最經典的愛情巨著之一,由費雯麗和克拉克·蓋博主演的影片亦成為影史上“不可逾越的”的最著名的愛情片經典。
相對于《飄》,它有個更為熟悉的名字——《亂世佳人》,不過,后者的命名過于直白,且直指主人公斯嘉麗;而前者更具內涵,更富想象力。無論愛情、夢想,還是一種文明,乃至一個生命,都終有隨風而飄、而消失的一天。
主人公斯嘉麗的前兩段婚姻,一個是出于妒恨,搶先嫁給了Melanie(梅蘭妮)的弟弟查爾斯,查爾斯很快就在戰爭中死去了,斯嘉麗成了寡婦。另一段是為了重振破產的家業,由此騙取本來要迎娶她妹妹的暴發戶弗蘭克和自己結婚。這兩段婚姻中,斯嘉麗都是不幸福的,因為她的心里一直都藏著一個人——Ashley(艾希禮)。盡管艾希禮已經與梅蘭妮結婚,斯嘉麗還是抱著“艾希禮是愛我”的幻想,導致真正愛她的和她所愛的Rhett(瑞德)離她而去。小說中艾希禮的愛對于斯嘉麗來說,就像一個“逝者”,已經飄遠,遠得那么縹緲、虛幻、不真實,卻一直被斯嘉麗追隨,空虛地緬懷愛情。她感情的悲劇,提示我們:總說逝者如斯,當不舍晝夜地來到的那么一天——夢想被現實打破,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我們的夢想;抑或是愛情面臨抉擇,我們不得不靜下心來仔細掂量和權衡;抑或是突然發現原來死亡離我們那么近,我們不得不思考人生的意義的時候。我們是選擇看清一切然后悲觀空虛不知所以地活下去?還是拋開死亡這一終端,“盲目”地積極活下去?面對“逝者”,是在緬懷中活下去?還是拋棄過去,重新上路?
或許,這就是《飄》這本著作,除去愛情、政治、社會、道德之外,更深層的思考。
小說塑造的斯嘉麗是剛強的、堅韌的、虛榮的、貪婪的、殘忍的、自私的女人,但時代的變遷,讓我們看到了她的成長。她勇于承擔責任,她敢愛敢恨,讓我實在佩服瑪格麗特·米切爾女士能將她塑造得那么鮮活,那么有血有肉,不愧是十年磨一劍的作品。
小說結尾寫道:“……無論如何,明天總已換了一天了。”在開頭,斯嘉麗的父親曾經對她說過的一句話:“世界上唯有土地與明天同在。”所有的愛,所有的恨,很可能只需一縷陽光就可以消融,也很可能像平行線永不相交。所以,我們能做的,唯有珍惜擁有的人,因為我們總是并不確切知道我們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太多的人只有在失去的時候,才知道去珍惜。泰戈爾有一句詩說:“如果錯過太陽時你流淚了,那么你也將錯過星星了。”歷盡滄桑,才學會忽略過去,因為——“Tomorrow is another day”。
《飄》實在值得一看,每看一次,就會有新的感慨。
(作者為浙江外國語學院中國語言文化學院大三學生)
《飄》精彩片段
思嘉·奧哈拉長得并不漂亮,但是男人們像塔爾頓家那對孿生兄弟為她的魅力所迷住時,就不會這樣想了。她臉上有著兩種特征,一種是她母親的嬌柔,來自法蘭西血統的海濱貴族;一種是她父親的粗獷,來自浮華俗氣的愛爾蘭人。這兩種特征混在一起顯得不太協調,但這張臉上尖尖的下巴和四方的牙床骨,是很引人注意的;她那雙淡綠色的眼睛純凈得沒有一絲褐色,配上烏黑的睫毛和翹起的眼角,顯得韻味十足;上面是兩條墨黑的濃眉斜在那里,給她木蘭花般白皙的肌膚畫上十分分明的斜線,這樣白皙的皮膚對南方婦女是極其珍貴的。她們常常用帽子、面紗和手套把皮膚保護起來,以防受到佐治亞炎熱太陽的暴曬。
1861年4月一個晴朗的下午,思嘉同塔爾頓家的孿生兄弟斯圖爾特和布倫特坐在她父親的塔拉農場陰涼的走廊里,她的美貌顯得更明媚如畫了。她穿一件新綠花布衣裳,長長的裙子在裙箍上舒展著,配上她父親從亞特蘭大給她帶來的新綠羊皮便鞋,顯得很相稱。她的腰圍不過17英寸,是附近三個縣里最細小的了,而這身衣裳更把腰肢襯托得更完整,加上里面那件繃得緊緊的小馬甲,使她的只有16歲但已發育得很好的乳房便躍然顯露了。不過,無論她散開的長裙顯得多么老實,發髻梳在后面顯得多么端莊,那雙交疊在膝頭上的小手顯得多么文靜,她的本來面目終歸是藏不住的。那雙綠色的眼睛生在一張甜美的臉上,卻仍然是任性的,充滿活力的,與她的裝束儀表很不相同。她的舉止是由她母親和嬤嬤的嚴厲管教強加給她的,但她的眼睛屬于她自己。
她的兩旁,孿生兄弟懶懶地斜靠在椅子上,斜望著從新裝的玻璃窗透過來的陽光談笑著,四條穿著高統靴和因經常騎馬而鼓脹的長腿交疊在那里。他們現有19歲,身高六英尺二英寸,長長骨骼,肌肉堅實,曬得黑黑的臉膛,深褐色的頭發,眼睛里閃著快樂的神色。他們穿著同樣的藍上衣和深黃色褲子,長相也像兩個棉桃似的。
外面,陽光斜照到場地上,映照著一簇簇的白色花朵在綠色的背景中顯得分外鮮艷。孿生兄弟騎來的馬就拴在車道上,那是兩匹高頭大馬,毛色紅得像主人的頭發;馬腿旁邊有一群吵吵嚷嚷一直跟隨著主人的獵犬。稍稍遠一點的地方躺著一條白色帶有黑花斑的隨車大狗,它把鼻子貼在前爪上,耐心等待著兩個小伙子回家去吃晚飯。
在這些獵犬、馬匹和兩個孿生兄弟之間,有著一種比通常更親密的關系。他們都是年輕、健康而毫無思想的動物,也同樣圓滑、優雅,兩個小伙子和他們所騎的馬一樣精神,但都帶有危險性,可同時對于那些知道怎樣駕馭它們的人又是可愛的。
雖然坐在走廊里的人,都同生在優裕的莊園主家庭,從小由仆人細心服侍著,但他們的臉顯得并不懶散。他們像一輩子生活在野外、很少在書本上的鄉巴佬一樣,顯得強壯而畗有活力。生活在北佐治亞的克萊頓縣,與奧古斯塔、薩凡納和查爾斯頓比較起來還有一點粗獷風味。南部開化得較早的文靜居民不遜內地佐治亞人,可在北佐亞這兒,人們并不以缺乏高雅的傳統文化教育為恥,只要在那些在他們認為重要的事情上學得精明就行了。他們心目中所關注的事,就是種好棉花,騎馬騎得好,打槍打得準,跳舞跳得輕快,善于體面地追逐女人,像個溫文爾雅的紳士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