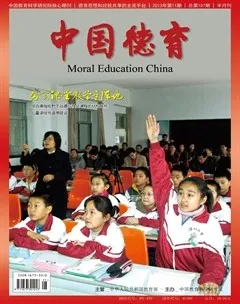兒童讀經與道德建設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發軔并持續至今的兒童讀經,主要是民間自發的活動。由于沒有統一的擘劃,因而眾說紛紜。單就名稱而論,就有“兒童讀經教育”“傳統文化素質教育”“國學育德工程”“中國古典文化教育”“兒童國學經典導讀”“兒童經典育讀工程”“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兒童中國文化導讀”等多種稱謂。至于兒童讀經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樣的意義和價值,倡導和參與這一活動的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更是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徑庭。但對于讀經有助于道德建設、有益于兒童的為人處世這一點,則是眾口一詞。
讀經活動的許多倡導者,雖然強調經典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雖然一再要求人們撇開現實的功利目的,要著眼長遠而不是汲汲于當下,要注重隱性功效而非顯性功效,但在論及讀經具有超越具體效用之上的“大功利”時,往往與道德建設關聯。如,蔣慶說:“兒童背誦中華文化經典,從小在心中埋下中國圣賢義理之學的種子,長大成人后自然會明白中國歷代圣賢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即懂得內圣外王、成己成物、知性知天的道理,從而固守之、踐履之、證成之,將圣賢的教誨融入自己生命成長的歷程。”很多人認為讀經不僅能增進道德信念,升華道德情操,優化道德行為,而且還能從整體上改良社會風氣,阻止社會道德滑坡,療治社會亂象。
中小學教師之所以熱衷于推廣讀經,則主要是因為相信并希望通過讀經,能使學生性格和氣質發生變化,守紀律,懂禮貌,溫良恭儉,凡事謙讓,馴服野性,變得文明。“不少老師反映,原來學生中不乏自私、任性、不懂禮貌等現象,孩子們在接受國學教育之后,漸漸學會謙讓、團結同學、尊敬師長了。”不少家長也以孩子在讀經之后,能主動承擔一些家務,懂得體貼關愛父母,諸如給老人洗腳、端茶等事例來說明讀經的意義和效果。可見,把讀經和當今的道德建設聯系起來,認為讀經有助于世道人心的改善,有助于和諧社會的建構,進而將讀經的目的歸結為道德建設,是現今很多倡導和參與讀經活動的人們的主要目的和用心。正因為如此,有人干脆將時下的讀經活動,稱之為“國學育德工程”。對此,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的確,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極為厚重的倫理色彩。最為典型的表現形式就是,作為這一文化重要載體的歷史文獻,都有著不同程度的道德說教。關系世道人心、著眼教育感化,從來都是傳統人士著書立說時,必須首先予以考慮的一點。學者們視為名山事業的“不朽之作”,固然是“千秋法鑒”,即便文人們“識小”的游藝之作,也要歸結為“養心之一助”。
閱讀這樣的典籍,體味其中的道理意蘊,會對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特別是古人提倡學、思、行的結合,注重知行合一,強調閱讀要引歸身受,學習要見諸行事,這就勢必會使書中的義理浸潤自身,從而改換氣質,變化性情。比如,明代學者章懋,就是一個強調要將朱熹的《小學》“熟讀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極精微,務使其理貫徹于胸中,一一體之于身而力行之”的人。在他八十歲的時候,一個已經考中了進士的人來向他請教“為學之方”。鑒于新進士舉止間的志得意滿和不時流露出的輕佻,章懋告訴這人要讀《小學》。這個進士不服氣,對章懋說:“這書我年幼的時候就讀過了,現在已經中了進士,還有必要讀嗎?”章懋告訴他,年幼時只是記誦,并沒有真正理解,算不得讀。進士回家后,聽從章懋的告誡,開始閱讀《小學》,覺得越讀越有興趣,越讀越有味道。三個月后,他又去謁見章懋。章懋一見他就問:“你最近是不是在讀《小學》?”進士十分驚奇地反問:“你怎么知道的呢?”章懋回答說:“看汝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與前迥殊,吾固知讀《小學》有得也。”聽了章懋的話,進士驚異于《小學》神奇的功效,“乃大欽服而退”。像《弟子規》《童蒙須知》那樣的讀物,對兒童日常生活行為的各個方面,諸如衣服冠履、言語步趨、灑掃涓潔、讀書寫字等雜細事宜進行嚴格規定,讀后對于兒童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乃至鑄就所謂“圣賢”的“坯墣”,無疑是有助益的。
然而,我們也要客觀看待、審慎評估古代經典在當代道德建設中的作用,不能過高估計,不能過分夸大,不能對它寄予過高的期望,好似讀經就可以解決我們現在的一切問題一樣。當然,也不能不顧變化了的情勢,不分辨其一般原則和具體內容,不加轉化地生搬硬套,原封不動地拿來就用,更不能把經典教育的意義,完全歸諸道德建設這一個方面,把經典的價值片面化和狹隘化。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中國古代社會簡直就可以稱之為讀經的社會。儒家經典,特別是《四書五經》,在全社會占有絕對崇高地位。沒文化或少文化的大眾信從它,兒童啟蒙識字是為了接近它,府州縣學和書院里講習它,各級科舉考試考它,文人學者研究它,皇帝經筵日講的還是它。讀經是所有人的義務,尊崇信奉經典是全社會的氛圍。在這樣的社會里,經典是神圣的,是人們不必懷疑,也不容懷疑的研讀對象。
但是,即便是在這樣一個“讀經社會”里,在所有文化人都在誦讀經典的時代,讀經并沒有提升人們的道德境界,沒有能凈化社會風氣,也沒有能解救社會的亂象。即便是在承平時期,在治世、盛世時期,感嘆人心不古、道德淪喪,指責教化不行,批評社會不公,悲憫百姓窮苦,揭示社會危機,也是所在多有。如賈誼在《論治安策》中說的“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的“盛世危言”,至于時當衰世、亂世、末世,那就更是“瘡痍滿目凄涼甚,深盼回春國手醫”。可是,再高妙的國手,都沒有能阻止中國歷史上一個又一個王朝的興亡生死。
讀經在歷史上沒有解救社會的紛亂和王朝的危亡,甚至也沒有能提升個體的道德品質和行為。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在現代歷史上,飽讀詩書、滿腹經綸而大節有虧的不乏其人。日本在中國建立偽政權,其搜羅的大多是清朝遺老和北洋軍閥時期的官僚政客,這些人都曾致力于讀經,有很高的國學素養,可稱得上是積學之士。但他們不僅在政治上賣身投敵,喪失民族氣節,在個人私生活上,也多有貪財如命、納妾嫖妓、吸食鴉片等丑行。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事例,現實生活中也有類似個案。
可見,無論是在經典具有絕對崇高地位的傳統社會,還是經典不再具有神圣性的近代社會,歷史的結論都彰彰在目,單純地讀經既不能提高國民素質,挽救世道人心,也不能療治一個社會的亂象,更不能挽救一個王朝的覆亡。希圖通過讀經來達到這樣的目的,不過是一些人不切實際的一廂情愿,是一種虛妄的想法。除了給讀經的反對者留下口實、提供批判的標靶,沒有更多積極的意義。
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它關注的不是具體的問題,而是關乎人的根本問題,蘊藏在經典中的常理常道具有普遍的永恒的意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期閱讀,都能獲得新的體會和感悟。正因為經典具有這樣的屬性,所以它是一個民族文化立足的基礎和根本,對經典的敬畏和研讀,也就成為使文化歷久彌新的源頭活水。在民族文化遭遇重大挑戰、發生轉型的關鍵時期,回到傳統中獲取應戰的資源,回歸經典領受啟示,是中外歷史上常見的做法。一方面,經典具有普適性,無論什么時候,無論什么人都能從中受益,另一方面,經典也具有民族性和時代性。這也就是說,任何經典都是特定民族的經典,都是特定民族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具體到我們民族的經典來說,它產生于2500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產生于我們民族文化奠基的“軸心時代”。它對后世的著述固然具有匡其趨向、示以準繩的意義,但后來一代又一代的詮釋,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它的精神和風貌。在時過境遷之后,特別是在中國社會正發生著結構性變革的今天,古代的經典當然可以用作道德建設的資源,但絕不能原封不動,生搬硬套,而要經過一番創造性轉化之后,才有可能成為我們現代建設有用且有效的資源。
所謂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是旅美華裔學者林毓生先生提出的一個概念。簡單地說,就是“把一些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符號與價值系統加以改造,使經過轉化的符號和價值系統,變成有利于變遷的種子,同時在變遷過程中,繼續保持文化的認同。”這個命題既反對徹底否定傳統,全盤移植西方文化,認為這種極端的、非此即彼的思想邏輯,不過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在現代條件下的變種;又反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認為以傳統文化為本位去同化西方思想,本質上也屬于“天朝大國無所不有”的自大和狂妄。它主張在深刻了解東西方文化的基礎上,立足于傳統,又不固守傳統,讓傳統和未來對話,使傳統在適應現實的基礎上獲得發展和創新。
有必要說明的是,古代經典中寄寓的道德,是與傳統社會相契合的倫理準則,其中許多內容和現代社會的公民道德不相吻合,甚至完全背離。有人希圖通過所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方法,擷取其中的優長,摒棄其負面成分,這實際上是一種毫無操作性可言的虛幻原則。因為在傳統文化中,精華和糟粕從來不是截然二分,而是水乳交融的,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從一個側面看是精華,從另一個側面看可能就是糟粕;一個人眼中的精華,在另一個人眼中可能就是糟粕;今天看是精華,明天就有可能會變為糟粕。再退一步說,即便能夠做這樣的區分,那么,糟粕同樣也是傳統文化豐富性和完整性的有機組成部分。沒有“糟粕”的傳統文化,不是一個真實的存在。糟粕與精華相需為用,相輔相成,相互滋養,相得益彰。糟粕的一方一旦被廢棄,精華也會隨之瓦解。所以,對待傳統文化,即便是能區分為所謂的精華和糟粕,那應有的態度也該是“取其精華,存其糟粕”。正因為如此,對待傳統文化,唯一正確的態度就是促成它的創造性轉化。這也就是說,要有效地利用傳統文化中的道德資源,把經典中的道德資源用于現今的道德建設,就必須對現今的公民道德有較為深入的了解,對人類文明成果有一個總體的把握,這是創造性轉化的前提條件。
顯然,兒童還不具備這樣一種對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的能力,甚至不具備起碼的理解能力,在這個年齡段,單純地讓他們背誦、記憶一些道德的規范和教條,并要求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實踐,那就應驗了批評者所說的“食古不化”,會桎梏兒童的世界,抑制兒童的想象,湮沒兒童的靈性。孩子們鸚鵡學舌般掌握的一些規范和教條,多與大人們的行事原則背離,對此兒童看在眼里,驚愕在心上,這些都會造成他們對道德失去敬畏感,變得疏離和冷漠。這樣一來,反倒造就了下一代對道德的輕忽和褻玩。不適當的道德教育導致的道德虛偽,其惡果甚至比道德教育的缺失還嚴重。
最后,有必要指出,在我們當代社會急劇轉型時期出現“讀經熱”,有著多重意義和價值。經典是連接我們和歷史傳統之間的一座橋梁,缺乏經典教育,我們就無法踏上回到自己精神家園的道路,只能成為文化上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我們倡導經典教育,是出于對自己傳統的“溫情和敬意”,是基于經典對我們民族歷史和社會生活具有深遠影響這樣的認識,是我們對自己是過去的子孫并且不想也不能割斷這種親緣關系的承認。只有接受國學經典教育,才能使我們的后代掌握優雅、精致的祖國語言,成為一個既有知識又有文化的現代中國人;只有接受國學經典教育,才能使我們的后代走進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親近、認同這個家園,并有能力參與到這個家園的建設過程之中;只有接受國學經典教育,才能讓我們的后代將自己生命的根須,扎植于傳統文化的豐厚土壤,把自己從一個自然的生物學意義上的中國人,變成一個自覺的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僅僅把讀經與道德建設關聯,將讀經的意義和價值落在道德建設這一點上,不僅過于狹隘,而且流于表淺。
責任編輯/苗 培
徐 梓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育歷史與文化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出版有《現代史學意識與傳統教育研究》《蒙學讀物的歷史透視》《中國文化通志·家范志》《元代書院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