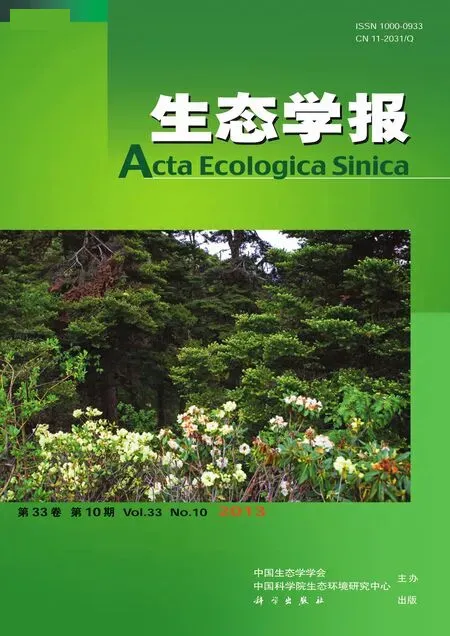黃河口鹽地堿蓬濕地土壤-植物系統重金屬污染評價
王耀平,白軍紅,肖 蓉,高海峰,黃來斌,黃 辰
(北京師范大學環境學院 水環境模擬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875)
黃河三角州河口濕地是中國及至世界暖溫帶唯一一塊保存最完整,最典型,最年輕的濕地生態系統;該濕地具有豐富的植物資源,同時也是多種珍稀瀕危鳥類的棲息地,因此,黃河三角洲濕地保護和管理一直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1]。近幾十年來,大規模石油開發和農業開墾等高強度人類干擾和氣候變化的綜合作用已經導致黃河三角洲濕地生態系統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退化,而重金屬污染則是該區濕地退化的一個重要驅動因素[2]。在河口環境中,污染源排放的重金屬可能吸附在懸浮顆粒物上并發生沉積,另一方面,河口區咸淡水混合導致pH值和鹽份等變化時,水體中的重金屬也會通過混凝、絮凝、共沉淀等途徑進入沉積物或濕地土壤[3],濕地土壤/沉積物中累積的部分重金屬可被植物根系吸收富集或轉移到植物地上部分[4],從而改變重金屬在濕地沉積物中的含量和分布特征并對濕地生產力和生物棲息生境產生不利影響。因此,重金屬在濕地土壤-植物系統的遷移轉化能夠直接影響濕地生態系統的健康及其穩定性。
已有研究表明重金屬的遷移轉化過程受土壤理化性質[5]、水文條件[6]、海水和河水的混合過程等[7]多種因素的制約。國內學者對黃河三角洲濕地沉積物重金屬污染特征進行了系列研究[8-9],但很少研究涉及河口區沼澤濕地土壤和植物系統中的重金屬污染的綜合研究,尤其缺乏考慮不同濕地水文條件下濕地土壤-植物系統重金屬污染特征方面的研究。本研究對黃河三角洲鹽地堿蓬濕地的重金屬污染程度進行了評價,對比研究了不同水文條件下(淹水和不淹水)濕地表層土壤中的重金屬污染水平及其在土壤-植物系統中的遷移特征,該研究有利于深入剖析重金屬在河口區沼澤濕地重金屬的生物地球化學過程,可為河口濕地土壤重金屬污染防治和退化濕地恢復提供科學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概況
黃河三角洲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地處北緯37°40′—38°10′,東經118°41′—119°16′,位于我國山東省東營市黃河入海口,總面積15.3 萬 hm2,主要分為故道保護區和現行流路保護區兩部分。該區屬暖溫帶季風性氣候區,具有明顯的大陸性季風氣候特點,四季分明,冷熱干濕界限極明顯。研究區年平均氣溫12.1 ℃,無霜期196 d,年均降水量551.6 mm,年均蒸發量為1962 mm。區域內地勢平坦,生態格局時空變異大,形成的濕地類型多樣。黃河三角洲濕地土壤形成時間相對較短,機械組成以粉砂為主,土壤質地以輕壤土和中壤土為主,土壤類型以潮土和鹽土為主。研究區地下水位較淺,水質礦化度高[10]。該區天然濕地植被以草本為主,主要植物群落有蘆葦(Phragmitesaustralis)、鹽地堿蓬(Suaedasalsa)、荻(Triarrhenasacchariflora)和穗狀狐尾藻(Myriophyllumspicatum)等;普遍存在的灌木為檉柳(Tamarixchinensis);天然喬木為旱柳 (Salixmatsudana),僅在黃河河道兩岸少量分布[11]。
1.2 樣品采集與分析
于2007年8月在黃河三角洲自然保護區內部的入海口附近區域 (北緯37°52′— 38°11′,東經118°41′ —119°10′),根據淹水條件不同選擇兩個典型鹽地堿蓬群落分布區:樣區1(非淹水區,主要受較淺的地下水補給)和樣區2(淹水區,受海水潮汐補給),在每個分布區內根據淹水條件劃分為3個典型樣地,樣區1包括1-1(干)、1-2(濕)、1-3(過濕);樣地2主要包括2-1(淹水1—2 cm)、2-2(淹水5—6 cm)和2-3(淹水8—9 cm)。在每個樣地按0—10 cm和10—20 cm兩個層次采集土壤樣品,每個土層采集3個重復樣品并混合為一個混合樣,同時利用環刀采集土壤樣品用于測定土壤容重和含水量;所有土壤樣品帶回實驗室后,放置陰涼處風干2—3周,去除植物殘體和石塊,磨碎后過0.149 mm的土樣篩后裝袋備用。在采集土壤樣品時同步采集鹽地堿蓬植物樣品,3次重復,洗凈后分地上和地下兩部分,在105 ℃烘箱內殺青30分鐘后再在60 ℃溫度下烘至恒重,磨碎裝袋待測備用。
植物和土壤樣品在聚四氟乙烯罐內經HClO4-HNO3-HF高溫消解定容后采用原子吸收(法國,JY-ULTMA)進行測定total phosphorous (TP)、As、Cd、Cu、Cr、Pb和Zn含量;土壤pH值和鹽分分別采用pH計和電導率儀測定(土∶水=1∶5);土壤含水量在105 ℃烘箱內烘24小時至恒重;土壤可溶性鹽含量采用重量法測定;總氮 (Total nitrogen,TN)采用碳氮自動分析儀;土壤有機質(Soil organic matter,SOM)使用重鉻酸鉀熱容量法[12]。實驗土壤基本理化性質如表 1。

表1 樣地土壤基本理化性質
1.3 數據統計與分析
通過計算Pearson相關系數來分析土壤基本理化性質參數間的相關性;運用單因素ANOVA分析不同樣地或不同土層土壤重金屬含量差異的顯著性;采用采用SPSS12.0和Excel 2010對數據進行數據處理、分析和繪圖。
2 結果與討論
2.1 黃河口鹽地堿蓬濕地土壤重金屬污染評價
表2表明了黃河口鹽地堿蓬濕地兩個樣區內土壤重金屬含量測定值和不同地區的土壤/沉積物質量標準值。由表2可知,非淹水區濕地土壤Cr(P<0.05)和Zn(P<0.01)含量顯著高于淹水濕地土壤,Cu含量則顯著低于淹水濕地土壤(P<0.01);而兩樣區間其它重金屬含量差異不顯著(P>0.05)
根據國家土壤質量標準,黃河口非淹水區鹽地堿蓬濕地土壤樣品中As和Cd含量超過三級標準的分別占83%和67%,而Cu、Cr、Pb和Zn含量平均值均低于國家土壤質量一級標準,整體低于二級標準,表明非淹水濕地土壤As和Cd污染嚴重,而未受到Cu、Cr、Pb和Zn污染;這與Bai 等[2]研究黃河三角洲潮溝濕地土壤重金屬污染時所得結論一致。對淹水區濕地而言,土壤樣品的As含量超過或接近國家土壤質量三級標準,土壤Cd含量全部超過國家土壤質量二級標準但均低于三級標準,Cu含量基本都超過國家土壤質量一級質量標準但低于二級標準,而Cr、Pb、Zn基本都低于國家土壤質量一級標準,表明淹水區濕地土壤As和Cd污染較為嚴重,Cu次之,而Cr、Pb和Zn等未達到污染水平。
基于安大略湖沉積物標準,淹水和非淹水區濕地中50%以上的土壤樣品超過了As的嚴重效應水平,而Cd、Cr、Cu均超過最低效應水平但未超過嚴重效應水平,Zn則未超過最低效應水平。對于Pb而言,非淹水區濕地土壤Pb含量未超過最低效應水平,而淹水區濕地土壤Pb含量則超過最低效應水平但低于嚴重效應水平。這表明黃河口鹽地堿蓬濕地土壤As污染嚴重,Pb、Cd、Cr和Cu也呈現一定程度的污染,而Zn含量則未達到污染水平。根據加拿大沉積物質量標準,非淹水區和淹水區濕地中均有50%以上土壤樣品 超過As的閾值效應水平,甚至有個別樣地As含量超過了可能效應水平。淹水和非淹水區濕地土壤Cd、Cr、Cu和Pb含量均介于閾值效應水平與可能效應水平之間,而Zn含量則都低于閾值效應水平。根據香港沉積物分類標準,淹水和非淹水區濕地土壤As含量均處于化學物質低濃度值和化學物質高濃度值之間或是高于化學物質高濃度值,除非淹水區濕地中67%的土壤樣品Cr含量超過化學物質低濃度值外,研究區濕地土壤所有樣品的Cd、Cu、Pb和Zn含量均未超過,表明該區濕地土壤受到一定程度的As污染,且非淹水區濕地出現一定程度的Cr累積。通過與不同地區的沉積物質量標準進行對比分析發現,非淹水區濕地土壤已經遭受嚴重的As污染和一定程度的Cd和Cr污染;而淹水區濕地土壤As和Cd污染嚴重,并呈現一定程度的Cu和Pb污染。

表2 實測重金屬含量與標準值對比
*顯著性差異(P< 0.05);** 極顯著性差異(P< 0.01)
2.2 淹水和非淹水區濕地不同積水深度對重金屬含量的影響
圖1顯示了黃河口淹水和非淹水區鹽地堿蓬濕地土壤重金屬含量隨積水深度的變化特征。在非淹水區濕地中,除As外,較濕的樣地1-2和1-3的土壤重金屬含量高于較干的樣地1-1,表明該區積水可能導致重金屬在土壤表層發生積累。該區土壤As、Cd和Cr含量呈表層(0—10 cm)<亞表層(10—20 cm),而土壤Cu、Pb和Zn含量則呈表層>亞表層的趨勢。淹水區濕地土壤As含量隨積水深度增加而呈下降趨勢,且樣地2-1表層土壤As含量低于亞表層土壤,而積水相對較深的樣地2-2和2-3表層土壤As含量高于亞表層土壤。但是3個樣地間和各層土壤間Cd、Cr、Pb、Zn、Cu含量均變化不大,表明除As外,淹水積水深度對濕地土壤重金屬含量的影響不大。
濕地在淹水條件下形成還原狀態,大多數重金屬易形成硫化物沉淀,活動性小,從而更容易在表層累積,但是As的環境行為與其它重金屬相反,不會形成硫沉淀,并且在強還原狀態下,還可能被微生物活動轉化為AsH3進入大氣[15],因此積水較深時濕地土壤As含量較低。相反,淹水區濕地土壤pH值較高(8.76,高于非淹水區8.10),而pH值高于8時金屬硫化物沉淀的穩定性減弱,因此氧化還原電位的影響減弱[16],并且淹水區的氧化還原電位會因為漲退潮而發生變化,不會出現永久的還原性條件[3]。此外,由于淹水區受到潮汐海水的影響,海水對表層沉積物的混合作用導致積水深度的影響不顯著。
非淹水區和淹水區濕地土壤重金屬含量存在差異(表2,圖1),可能與濕地淹水狀況密切相關。其中,As含量在各樣地間變化較大,受淹水和非淹水條件影響不顯著。淹水區濕地土壤中Cr,Cd和Zn含量顯著低于非淹水區濕地(P<0.05),但非淹水區濕地土壤中的Cu、Pb含量較低。重金屬可以與海水中的Cl-形成可溶性絡合物,使其更容易發生遷移[17],同時海水中的Ca、Mg等離子也會與重金屬競爭吸附位點導致解吸[18]。Balls等[19]和Gerringa等[20]對河口沉積物的研究均發現水體鹽度增加時Cd會從沉積物和CdS沉淀中釋放出來。盡管非淹水區濕地土壤鹽分含量較高(表1),但其水分補給主要來自淺層地下水,且地表無積水,限制了金屬離子的遷移。因此海水中的離子和潮汐沖蝕可能是導致淹水區濕地土壤Cd、Cr和Zn含量偏低的原因。
海水中重金屬可以被沉積物中的粘土礦物或有機質吸附并富集,或是生成硫化物、碳酸鹽化合物等通過沉淀作用進入土壤[15]。以往研究表明,Pb、Cu與Cd、Zn相比具有更強的有機質的絡合能力[21-22],同時高pH值時,由于有機質呈現更強的電負性,也有利于有機質與金屬離子結合。本研究中,非淹水區濕地土壤pH值和有機質分別為8.10和5.73 g/kg,均低于淹水區濕地(8.76和6.52 g/kg)(表1)。因此,較高的有機質和pH值可能是導致淹水區濕地土壤中Pb、Cu含量偏高的原因。

圖1 黃河口非淹水區(樣地1-1,1-2,1-3)和淹水區(樣地2-1,2-2,2-3)鹽地堿蓬濕地土壤重金屬剖面分布(連線表示各樣地0—20cm平均值)
2.3 黃河口鹽地堿蓬濕地土壤重金屬含量與土壤理化性質之間的關系
由表3可知,鹽地堿蓬濕地土壤鹽分和pH值呈極顯著負相關(P<0.01),而TN和SOM呈極顯著正相關(P<0.01),這與丁秋祎等[11]研究結論一致。Cr、Cd和Zn含量之間具有極顯著的相關關系(P<0.01),說明三者來源和在土壤中的化學行為較為相似[23]。土壤Cr,Cd和Zn含量與土壤鹽分含量呈極顯著正相關關系(P<0.01),而與土壤pH值呈極顯著負相關關系(P<0.01)。這主要是由于非淹水區濕地地表聚鹽導致表層土壤鹽分含量高于淹水區濕地土壤,且限制了重金屬的遷移;而在淹水區受海水潮汐的影響,這3種重金屬易形成Cl-絡合物而發生遷移[15]。但是Lores等[24]發現鹽度增加會顯著降低沉積物有機質對Cd、Cr和Zn的吸附能力。這可能與淹水條件有關。而高pH值既可能導致金屬遷移性降低,也可能由于強堿性條件下形成OH復合物而導致Cd、Cr和Zn等重金屬的遷移性增加[25]。Seaman 等[26]發現堿性條件有利于使穩定的Cr(Ⅲ)氧化為易遷移的Cr(Ⅵ)。
除As外,有機質與其他重金屬均呈正相關關系,但僅與Pb的相關性達到顯著性水平(P<0.01),表明該區有機質對重金屬的影響不顯著。As與SOM呈現出弱的負相關性可能是由于As在非酸性土壤條件下,土壤有機質能夠促使As(Ⅴ)轉換為As(Ⅲ),導致As發生遷移和淋濾[25]。滕葳[15]報道了As不易被土壤有機質吸附,而主要吸附在粘土礦物上。Cu與土壤pH值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P<0.05),這是由于Cu在弱堿性土壤條件下不易發生遷移,其遷移性隨pH值下降而增加[25]。Pb和Cu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P<0.05),表明二者之間也具有共同的來源和相似的化學行為,尤其是二者與有機質的相關性要明顯高于其他重金屬。
3.4 鹽地堿蓬對濕地土壤重金屬的富集和轉移
通過植物體內莖葉部分重金屬含量與土壤重金屬含量之比,可以計算鹽地堿蓬對各重金屬的富集系數;根據植物地上部分與地下部分的重金屬含量之比可計算出植物對重金屬的轉移系數[27]。圖2表明了黃河口淹水區和非淹水區鹽地堿蓬對重金屬的富集系數和轉移系數。研究得出的河口區鹽地堿蓬對重金屬的BCF與TF值均低于高云芳等[28]報道的黃河三角洲濱海濕地鹽地堿蓬的富集系數和轉移系數,同時與朱鳴鶴等[29]報道的遼河潮灘鹽地堿蓬對Cu、Zn、Pb和Cd的富集系數也存在明顯的不一致。這可能是由于同一種濕地植物的富集系數和轉移系數受采樣時間、采樣地點等環境因素的影響。

圖 2 淹水區和非淹水區鹽地堿蓬對濕地土壤重金屬的富集系數及轉移系數
除非淹水區濕地中的Cr、Cu和淹水區濕地中Zn外,研究區鹽地堿蓬對重金屬的富集系數均小于1,說明重金屬未在鹽地堿蓬植物體內顯著富集。鹽地堿蓬對Cu、Zn的富集系數高于其它重金屬可能是由于Cu和Zn為生物體必須元素,植物需要大量吸收和消耗這些元素[30]。
根據BCF的大小可以看出,淹水和非淹水區鹽地堿蓬對Cu具有明顯的富集作用,且非淹水區鹽地堿蓬的富集作用更強(P<0.01),這與Gambrell[31]的研究結果一致,說明在淹水深度較淺的情況下,濕地植物對Cu的吸收可能會增強。淹水區鹽地堿蓬對Zn的富集作用要強于非淹水區濕地(P<0.01),這可能與非淹水區濕地土壤Zn含量較高有關(約是淹水區濕地土壤的3倍,表1),因為植物對Zn的富集能力會受到土壤中Zn含量的影響[4]。
非淹水區鹽地堿蓬對Cu,Cr和Pb的轉移系數大于2,而對As,Cd和Zn的轉移系數小于1,表明該區鹽地堿蓬對Cu、Cr和Pb的轉移能力較強,能夠在植物地上部分發生累積,并可能通過殘落物的形式歸還土壤[4]。淹水區鹽地堿蓬對As和Cu的轉移系數較大,而對其他重金屬的轉移系數較小,表明該區鹽地堿蓬對As和Cu具有較強的轉移能力;而非淹水區鹽地堿蓬對Cr和Pb的轉移能力較強(P<0.05),但對As的轉移能力較弱(P<0.01)。其原因在于植物對重金屬的轉移能力與植物種類、重金屬種類和環境條件有關,有些植物在高鹽分和低pH條件下對重金屬的轉移能力會增強[4]。與淹水區濕地相比,非淹水區濕地土壤鹽分較高、土壤pH較低可能有利于這兩種金屬從鹽地堿蓬地下部分向地上部分轉移。與另一種濕地植物互花米草(Spartinaalterniflora)相比,鹽地堿蓬對Pb、Cr、Cu和Zn重金屬的轉移系數均較高[32]。

表3 黃河口鹽地堿蓬濕地土壤重金屬和土壤屬性的相關性分析
顯著相關(P< 0.05);**極顯著相關(P< 0.01);n=12
3 結論
黃河口鹽地堿蓬濕地土壤重金屬整體污染程度較輕,其中As為主要污染物,Cd、Cr、Cu為次要污染物,Pb和Zn未達到污染水平。淹水區和非淹水區濕地的不同水文條件對土壤和植物中重金屬含量有一定的影響。無論是在非淹水區還是淹水區濕地,As的行為都主要受水深影響,水深增加導致As含量下降。對于其它重金屬(Cd、Cr、Cu、Pb和Zn)而言,在非淹水區土壤積水會導致重金屬在土壤表層積累,而在淹水區淹水深度對土壤表層重金屬含量影響不大。研究區域土壤表層Cr、Cu和Zn含量主要受土壤鹽分和pH值的影響;除Pb外,重金屬受有機質含量影響較弱;重金屬Cr、Cu和Zn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關系,表明存在共同來源。
鹽地堿蓬對重金屬的富集和轉移受到重金屬種類、淹水條件以及土壤重金屬含量和理化性質等因素影響。淹水區鹽地堿蓬對Cu和Zn具有相對較強的富集能力,而非淹水區鹽地堿蓬只對Cu具有最強的富集能力;非淹水區鹽地堿蓬對Cu、Cr和Pb的轉移能力較強,而淹水區鹽地堿蓬對As和Cu 具有較強的轉移能力。除Cr、Cu和Zn外,重金屬在鹽地堿蓬的根系內一般不存在顯著富集,且絕大多數重金屬都表現出地上部分的含量比根系高的現象。
[1]Xu X G,Lin H P,Fu Z Y,Bu R C.Regional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wetland in the Huanghe River Delta.Acta Scicentiarum Naturalum Universitis Pekinesis,2001,37(1): 111-120.
[2]Bai J H,Huang L B,Yan D H,Wang Q G,Gao H F,Xiao R,Huang C.Contami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eavy metals in wetland soils along a tidal ditch of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China.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2011,25(5): 671-676.
[3]Laing G D,Vandecasteele B,Grauwe P D,Moors W,Lesage E,Meers E,Tacka F M G,Verlooa M G.Factors affecting metal concentrations in the upper sediment layer of intertidal reedbeds along the river Scheldt.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2007,9(5): 449-455.
[4]Weis J S,Weis P.Metal uptake,transport and release by wetland plants: implications for phytoremediation and restoration.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2004,30(5): 685-700.
[5]Laing G D,de Vos R,Vandecasteele B,Lesage E,Tack F M G,Verloo M G.Effect of salinity on heavy metal mobility and availability in intertidal sediments of the Scheldt estuary.Estuarine,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2008,77(4): 589-602.
[6]van den Berg G A,Loch J P G,Winkels H J.Effect of fluctuating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on the mobility of heavy metals in soils of a freshwater estuary in the Netherlands.Water,Air,and Soil Pollution,1996,102(3/4): 377-388.
[7]Paucot H,Wollast R.Transpor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ce metals in the Scheldt estuary.Marine Chemistry,1997,58(1/2): 229-244.
[8]Guo D Y.Analysis on heavy metals distribu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ollege of China,2007,17(1): 88-89.
[9]Ling M,Liu R H,Wang Y,Tang A K,Yu P,Luo X X.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eavy metals in the soil ofTamarixchinensisforest farm in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 and its ecological significance.Transactions of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2010,(4): 41-46.
[10]Ding Q Y,Bai J H,Gao H F,Xiao R,Cui B S.Soil nutrient contents in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s with different plant communities.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2009,28(10): 2092-2097.
[11]He Q,Cui B S,Zhao X S,Fu H L.Niches of plant species in wetlands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under gradients of water table depth and soil salinity.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2008,19(5): 969-976.
[12]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Analysis.Shanghai: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ublishers,1987: 96-104,132-136.
[13]Ontario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Energy.Guidelin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Aquatic Sediment Quality in Ontario.(1993-8) [2011-9].http://www.ene.gov.on.ca/envision/gp/B1-3.pdf.
[14]MacDonald D D,Ingersoll C G,Berger T A.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consensus-based sediment quality guidelines for freshwater ecosystems.Archives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2000,39(1): 20-31.
[15]Teng W,Liu Q,Li Q,Liu Y B.Hazards and Risk Assessment of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Beijing: Chemical Industry Press,2010: 261-297.
[16]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Framework for metals risk assessment,Chapter 3.(2007-3-8) [2012-5-31].http://www.epa.gov/raf/metalsframework/pdfs/chaper3.pdf.
[17]Hahne H C H,Kroontje W.Significance of the pH and chloride concentration on the behavior of heavy metal pollutants Hg(II),Cd(II),Zn(II),Pb(II).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1973,2: 444-450.
[18]Tam N F Y,Wong Y S.Reten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heavy metals in mangrove soils receiving wastewater.Environmental Pollution,1996,94(3): 283-291.
[19]Balls P W,Laslett R E,Price N B.Nutrient and trace metal distributions over a complete semi-diurnal tidal cycle in the Forth estuary,Scotland.Netherlands Journal of Sea Research,1994,33(1): 1-17.
[20]Gerringa L J A,de Baar H J W,Nolting R F,Paucot H.The influence of salinity on the solubility of Zn and Cd sulphides in the Scheldt estuary.Journal of Sea Research,2001,46(3/4): 201-211.
[21]Baeyens W,Goeyens L,Monteny F,Elskens M.Effect of organic complexation on the behaviour of dissolved Cd,Cu and Zn in the Scheldt estuary.Hydrobiologia,1998,366: 81-90.
[22]Muller F L L.Interactions of copper,lead and cadmium with the dissolved,colloidal and particulate components of estuarine and coastal waters.Marine Chemistry,1996,52(3/4): 245-268.
[23]Callaway J C,Delaune R D,Patrick Jr W H.Heavy metal chronologies in selected coastal wetlands from Northern Europe.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1998,36(1): 82-96.
[24]Lores E M,Pennock J R.The effect of salinity on binding of Cd,Cr,Cu and Zn to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Chemosphere,1998,37(5): 861-874.
[25]Kumpiene J,Lagerkvist A,Maurice C.Stabilization of As,Cr,Cu,Pb and Zn in soil using amendments-a review.Waste Management,2008,28(1): 215-225.
[26]Seaman J C,Arey J S,Bertsch P M.Immobilization of nickel and other metals in contaminated sediments by hydroxyapatite addition.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2001,30(2): 460-469.
[27]McGrath S P,Zhao F.Phytoextraction of metals and metalloids from contaminated soils.Current Opinion in Biotechnology,2003,14(3): 277-282.
[28]Gao Y F,Li X Q,Dong G C,Liu F,Wang Y N,Ke H.Purification of several salt marsh plants to the coastal wetlands in the estuary of Yellow River.Meteor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2010,1(10): 53-57.
[29]Zhu M H,Ding Y S,Zheng D C,Tao P,Ji Y X,Gong W M,Ding D.Accumulation and absorption mechanism about the familiar heavy metals ofSuaedasalsain the intertidal zone.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Control,2005,27(2): 84-87.
[30]Gambrell R P.Trace and toxic metals in wetlands-a review.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1994,23(5): 883-891.
[31]Zhu D T,Li M H,Li X.Cycle and enrichment characteristics ofSpartinaalternifloracommunity on heavy metal elements.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s,2010,38(3): 1203-1205.
[32]Yang H,Shen Z,Zhu S,Wang W.Heavy metals in wetland plants and soil of lake Taihu,China.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2008,27(1): 38-42.
參考文獻:
[1]許學工,林輝平,付在毅,布仁倉.黃河三角洲濕地區域生態風險評價.北京大學學報: 自然科學版,2001,37(1): 111-120.
[8]郭德英.黃河三角洲重金屬分布狀況及分析評價.中國環境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7,17(1): 88-89.
[9]凌敏,劉汝海,王艷,湯愛坤,于萍,羅先香.黃河三角洲檉柳林場濕地土壤重金屬空間分布特征及生態學意義.海洋湖沼通報,2010,(4): 41-46.
[10〗 丁秋祎,白軍紅,高海峰,肖蓉,崔保山.黃河三角洲濕地不同植被群落下土壤養分含量特征.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09,28(10): 2092-2097.
[11]賀強,崔保山,趙欣勝,付華齡.水、鹽梯度下黃河三角洲濕地植物種的生態位.應用生態學報,2008,19(5): 969-976.
[12]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理化分析.上海: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 96-104,132-136.
[15]滕葳,柳琪,李倩,柳亦博.重金屬污染對農產品的危害與風險評估.北京: 化學工業出版社,2010: 261-297.
[29]朱鳴鶴,丁永生,鄭道昌,陶平,吉云秀,公維民,丁德文.潮灘鹽沼植物翅堿蓬對常見重金屬的累積吸收及其機制.環境污染與防治,2005,27(2): 84-87.
[31]朱丹婷,李銘紅,李俠.互花米草群落對重金屬元素的循環和富集特征.安徽農業科學,2010,38(3): 1203-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