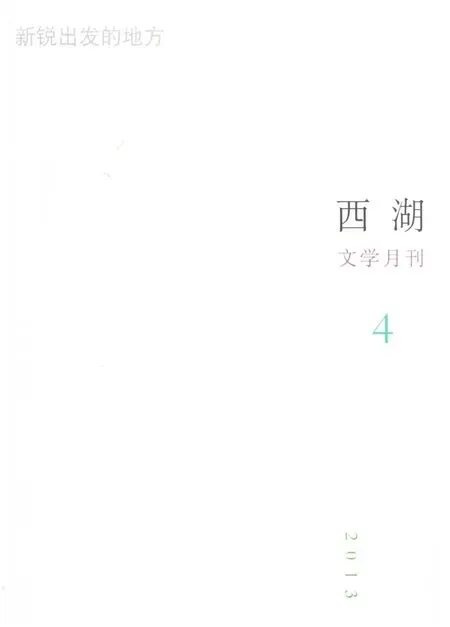“努力構建自己的文學地域”
胡學文 姜廣平
一
姜廣平(以下簡稱姜):很多人都看到了,故鄉在你作品中的特殊位置。當然,這是每一個作家都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故鄉與童年,都是文學中的重要母題。我想問的是,在你的寫作中,有一段時間似乎是有意回避故鄉。有意回避,倒反而可能是拋不開了。
胡學文(以下簡稱胡):故鄉與童年對作家的重要就像土壤對于植物,不僅是寫作者一生難以掘盡的礦藏,而且對寫作者的風格有著難以言說的神秘影響。加西亞·馬爾克斯如果不是生活在南美大陸,就不可能有《百年孤獨》。除了地域文化、地域歷史的浸潤,一定還有與童年有關的因素。馬爾克斯談過這個問題,但我認為,他沒有談徹底。有些東西,或許他本人都未意識到。故鄉是資源,對每個作家都是如此,但怎么處理,各人就千差萬別。我想尋找最佳的路徑。但哪條路徑最佳,我不知道,只有嘗試過才可以作出判斷。確實,有一階段,我竭力與故鄉遠些,但不是遠離,而是想濾掉情感因素,尋找路徑。
姜:你在剛剛開始創作時,似乎更愿意以一種新歷史的姿態出現。這是不是受到先鋒文學的影響?
胡:我非常迷戀莫言的《紅高粱》。初次讀這篇小說時,我正在師范讀書,那種驚喜難以形容。馬爾克斯讀了卡夫卡的《變形記》后感嘆:原來小說可以這么寫。我不敢自比馬爾克斯,但我揣測,他當時的感受與我讀《紅高粱》應該差不太多。我很愚笨,但任何作家都有野心,我試圖呈現一副狂野的面孔。對歷史的再認識可以使自己在寫作上有更多的自由。
姜:這里,我們不得不涉及到的一個話題是,先鋒文學給了你什么樣的影響?在我們這樣的年齡,先鋒似乎是我們所有“60后”作家的文學背景。
胡:影響肯定是有的,但不是很大。有一段時間,我只讀先鋒文學;為了讀懂,還給沒有標點符號的小說加標點。是不是很可笑?我想從先鋒文學那兒學習寫作技巧。我對先鋒文學認識不足,以為先鋒就是技巧,后來明白自己理解得太膚淺,那不是學來的,也不是技巧可以解決和涵蓋的。
姜:故鄉,其實是一個作家無法回避的。對作家而言,童年與故鄉,都是非常重要的資源。甚至,我們不能稱之為資源,因為,這兩樣東西,有著與生命同質的成分。你的寫作歷程也可以驗證這一點吧?
胡:你這句話很棒。甚至,我們不能稱之為資源。你寫評論,又寫小說,對此肯定有著切實的體會。確實,故鄉是資源,但又不那么簡單。我回顧自己的寫作,多數與故鄉有關,確實難以掘盡。就算我停下來,也非遠離它,而是為了把它看得更清晰。別的也可以寫,有不少構思,我在本子上記著,但遲遲沒有動筆。常常是寫一篇與故鄉有關的小說,再寫別的,不然,就感覺斷了根基。寫到鄉村,腦里便會呈現完整的圖景:街道的走向,房屋的結構,煙囪的高矮,哪個街角有石塊,哪個街角有大樹。如果寫到某一家,會聞見空中飄蕩的氣息。真的,幾乎不需要想象,是自然而然的呈現。如果僅僅以資源論,怎么能涵蓋呢?故鄉提供了可能,但萬物都有兩面性,我在利用這些可能的同時也有不安。寫作需要難度,輕松獲得或許對寫作是一種傷害。我已經意識到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姜:作家的寫作,其實,就應該從有機體角度論。評論家真的不必為作家寫了什么與怎么寫瞎操心。你盡可以評,但還是管不了人家怎么寫。但我們也發現,你在最初創作時,總是把小說背景放在清末民初。這種拉開時間的努力,是不是想要回避故鄉和童年的追逼呢?或者說,你想以一種陌生化的努力,來營造自己的文學世界?
胡:寫歷史沒有禁忌,隨意,大膽,是一種沒有邊界的創造。寫土匪喝酒、往酒壺撒尿,是豪野的表現,寫農民往酒壺撒尿,就是胡扯。后來,我覺得自己的理解有偏差,文學必須有分寸。文學沒有邊界,文學也必須有邊界。更重要的,在寫歷史時,我無法獲得寫作的愉悅,無法準確觸摸人物的內心,所以放棄了那種寫作。
姜:當然,你總算是回來了,帶著《天外的歌聲》、《秋風絕唱》、《極地胭脂》、《一棵樹的生長方式》等回到張垣。你這樣寫作的時候,是不是有受到沈從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等的啟發,或者是受威廉·福克納的影響?
胡:使自己的寫作獨樹一幟,是作家畢生的追求。也許所有的努力都是枉然,但一旦選擇寫作,努力就成為宿命。我想打上屬于自己的獨特印記。威廉·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郡成為世界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文學地域之一,沈從文、莫言也成功地構建了文學版圖,成為他們獨有的標簽。很多作家都在努力構建自己的文學地域。
姜:所以,你的作品,雖然遵從現實生活的真實,刻畫和描寫老百姓的悲苦與災難,但卻不能以所謂的“底層”論。你應該不是著力寫底層的作家。何況,“底層”這個詞,多少帶有一種對實際上屬于這一群體的人的輕狂與傲慢。
胡:講到“底層”,我愿意多談一些。我曾寫過一篇創作談《人物之小與人心之大》。我喜歡寫小人物,我的情感凝聚在此,關注停留在此。農民,農民工,教師,工人。這些小人物,他們進入我的視野,我的血液和他們流在一起。過去,現在,將來,我都愿意寫他們。這不是宣言,而是我無法更改。寫小人物不代表作品的內涵小,也不能說明作品的容量小。作品的分量與人物的身份、職業、級別沒有關系,完全在于開掘的深度與廣度。
“底層”這個詞沒熱起來的時候,我就在寫;轟轟烈烈時,我仍如是。我覺得底層也好,小人物也好,只是從某方面對小說的分析,或許是偏重分析了人物的境遇。這沒什么錯,作家的寫作方向不同,評論家的關注點也不會相同。作家的寫作多樣化,評論家的評論也應該多樣化。怎么寫是作家的權利,怎么評是評論家的權利。李云雷可能是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評論家。但我認為李云雷沒什么錯。他有權從自己感興趣的角度去關注和分析。底層動靜大了,一些作者就往這個方向靠攏,仿佛與底層掛上就不會落伍。作家寫得怎么樣,都要靠作品說話,作家不應喋喋不休地聲明或解釋。
再來說說對底層的棒喝。批評是自由的,只要出于真心,出于對文學的熱愛。我敬重這樣的評論,哪怕我不認可某些看法。如果出于文學以外或與文學很遠的原因,就讓人感覺不舒服。有時候,我讀到的不是論點,而是文字的憤怒。何至于此?確實,苦難被某些人過度地渲染了,就算如此,也沒必要夸張地憤怒。我尊敬的好多批評家是從文本的角度分析的,是出于對文學的摯愛。
姜:真正的文學,應該是悲天憫人的,是柔軟的。同時,我還認為,說出所謂“底層”這類字眼的人們,其實,也仍然是悲天憫人的對象,宿命與恢詭、天理與荒誕、生之何歡死之何悲等,都一直追蹤著每一個人。文學應該多在這里駐足停留。這樣的文學也才能引領一個時代。不知學文兄是否持此論。
胡:我完全贊同。你是納博科夫所說的優秀讀者,你和別的作家的對話我看過,你對作品的分析不是憑空的,很精準。在此,我表示敬意。
二
姜:你筆下的杜梅副縣長,是個極為豐滿的形象。可以說,在你這里,我們終于發現了一種向上的良知與悲憫,當然,這里也摻和進了你俯視的悲憫、大痛與大愛。這個人物身上,甚至帶上了某種悲壯與殉道的色彩,有著一種先入地獄、再出地獄的至善與純良。所以,這也是我多年來終于悟透的一種文學原則:文學,技術終究是末端、是小道,而本體論的意義,才賦予一個作家以真正的身份。
胡:我努力寫出她的復雜性,但還是有些遺憾,有些方面我沒做到或做好。如果現在重寫,或許會找到另外的方向,我會看得更“清”。杜梅這個人物,寫到最后,我有些痛,我能摸到她脈搏跳動的節奏。作家在寫他人,也是在寫自己。
姜:類似的人物,是不是還有唐英?你在塑造這個人物時,也動了差不多的心思?
胡:對,唐英也是一個讓我有痛感的人,我小心地揣測著她,時常與她融化為一體。寫作前,當然要考慮技術,對寫作者而言,技術是結構小說所必需的。寫作過程中還不斷自我提醒,往往寫著寫著,技術就退到身后,牽著或推動作家前行的是人物的命運及人物命運的走向。
姜:對了,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到了現在,你是完全刻意地在追求一種現實主義,默默地以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來進行自己的寫作?
胡:我喜歡的小說,是能夠接地氣,可能有著世俗的面孔,但同時長著羽翼,能夠飛翔于天空。一個方向往下,一個方向往上。往下扎得深,往上飛得高。這是我刻意追求的。至于什么主義,不重要。反正不是純正的現實主義。美國作家羅斯起初是現實主義,以后數年寫的是現代派作品,后來又回歸現實主義,但回歸后的現實主義與起始的現實主義已經不同,有了更“輕”的東西。進入并不困難,困難的是出口在哪里。重要的是能否寫出人物的“大”來。你談本體論的意義,我認同,但怎么呈現本體論的意義?與技術還是有一定關系。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大家,對技術不屑一顧,他的復調是探索人類命題“捎帶”出來的,是一種無意的技術,這樣的作家罕見。而另外一些作家,技術,也可以說風格即意義的一部分,如福克納,都了不起。
姜:李云雷發現你的小說中時常出現執拗的主人公,吳響、楊把子、唐英、麥子、荷子、蕎蕎、范素珍等等,都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你這樣設置人物,是不是首先將小說推入到一種極端狀態,然后在此種情境下展開寫作呢?
胡:我記得和姜兄初遇是在《人民文學》舉辦的青年作家論壇上,蘇州。那個晚上,我們幾個去喝茶,也說到這個話題。寧小齡說一般愛寫執拗人物的作家往往也有偏執的一面,還說血型往往是A型。果然,我,姚鄂梅,還有在場的另一個作家都是A型。與偏執和血型可能有關系,但關系應該不大吧?人有日常的一面,也有非常的一面。日常的一面我們能看到,非常的一面往往看不到。并非個體的人有意掩飾,而是他或她自己都沒有意識到。我喜歡把人物推到一個特定的環境中,打破慣常的生活秩序,使其和世界建立新的關系,逼出他身上不為人知不為己知的一些特質。可以說他執拗,或說他一根筋,但我決不是為表現或突出這種性格,我最大限度地逼,是想看清或確認那種新關系的可能。
姜:《命案高懸》里“混混”吳響一個人去追尋尹小梅死亡的真相,這樣的情節設置,你是出于什么考慮的呢?他那種執拗,是你寫之前設定的,還是在寫作中逐漸明晰起來的呢?當然,我說“明晰”是不到位的,因為這里,確實也有連吳響也說不清的前因后果。
胡:我在寫作中常有失控的時候,明明是往某個方向走,寫的過程中會出現意外,結果往另外的方向去了。出現這種狀況,我也不再控制。失控意味著別樣的風景,有驚喜。這篇小說,我讓一個混混式的人物去追尋真相,可以說,也只有這樣身份的人,才有膽識“跳上跳下”,而他作為混混的追尋也才更具意義。一個村痞,但頭腦靈醒;如果腦袋也渾,就沒什么意思了。起初,我想讓他搞清真相,隨著寫作的推進,我明白“搞清”是錯誤的,填得太實會削弱小說的表達,于是成了現在的樣子。
姜:這個中篇,你是想展現底層還是想展現一種混亂呢?你在這兩方面都用了足夠大的力氣,都有一種攫取人心的力量。特別是黃寶的死,我覺得意味深長,你是否想借黃寶之死隱喻什么呢?譬如逃避或者回避?
胡:寫作這篇小說的最初意圖,只想度量吳響這個人。我想探究吳響和這個世界的關系,一個女人因他死了,他和世界的關系發生改變。改變應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外在的。我竭力把這種改變寫出來,寫透。吳響是鄉村混混,但也是普通人,其心理軌跡應該具有普遍性。但在寫這種軌跡時,我發現心理分析必須基于他和現實的關系。現實的復雜性是吳響“帶”出來的。寫黃寶,既為寫吳響,也為寫黃寶本人,同樣,我想描畫他的心理軌跡。他的死不是現實逼的,是自己逼的。作品發表后,許多評論談到小說中的現實世界如何如何,其實,我的重心在于與現實碰撞后的心理世界。
姜:這部小說的理性力量是強大的。這讓我想到一個話題:你與這樣的題材為什么結合得如此有力?在我看來,現在多數作家其實已經面對現實失語。
胡:很簡單,我喜歡接地氣的作品。我竭力讓自己的作品有著人間煙火。小說的兩極——行走與飛翔,其中一極我基本做到,另一極是我努力的方向。
姜:《小說面面觀》里談到了司各特式的誠實和磊落。但福斯特隨即說,其實,這里有一種司各特做夢都想不到的忠誠。我們現在,且不談司各特做夢都想不到的忠誠吧,委實,那種誠實與磊落,我們也不期求了;總覺得當代作家,眼睛向下的還是少了。如果有,大多數也是擺的一種姿態。
胡:每個作家的追求不同。有的作家不屑于眼睛向下,似乎向下作品就打了折。確實,輕盈可以使作品格調不俗;但沒有重,輕盈可能會成為輕飄。作家是個體勞動,有選擇的自由,應互相尊重。
姜:你選擇吳響這個近乎無賴與流氓無產者的角色來探究尹小梅之死的迷障,是不是想做一次小說的智慧與炫技的表演呢?以這個人物來叩問一些東西,應該是你的有意設定吧!
胡:確實是有意設定。他身上能承載更多的東西。一個無賴與流氓對真相的追尋,對自己心靈的叩問要比一個“純粹”的農民有力。而且,他有追尋和叩問的可能和能量。這種預設也可以算技術的范疇吧。
姜:另一個饒有意味的話題肯定是悲劇問題。尹小梅之死帶來吳響的挫敗和黃寶之死,肯定是一個悲劇話題。關鍵問題不在這里,關鍵是,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悲劇?有人說你這篇小說“與其說是一個悲劇倒不如說是對傳統悲劇的一個戲仿”。對“戲仿”之說,我不太贊同,但是將吳響納入到后悲劇時代,當作這個時代的悲劇人物,我還是比較認可的。畢竟,戲仿一說,多多少少便是對吳響的否定。
胡:一次會上,評論家王力平說的話,我印象極為深刻:對喜歡的人要審視,對不喜歡的人要尊重。確實,作家要剔除某些感情因素,因為情感會遮擋作家的視線,甚至影響到用詞。但要百分百剔除,站在“公正”的立場,也很難。文學畢竟是關于心靈的,關乎心靈就難免被情感左右。起初,我只是站在旁觀者的立場;寫作中途,有些喜歡上這個家伙,常常與他重合在一起。悲憫是肯定的,但似乎比悲憫更復雜一些。
姜:我覺得真正獲得悲劇意味的是《飛翔的女人》。但更有意味的是,荷子與吳響,竟然都是在尋找,而且都那么執著。吳響尋找真相,荷子尋找女兒。荷子從南方省份找起,“現在輪著這個省了”,且在尋找女兒的過程中,荷子從來沒有失去信心,認為總能夠找到女兒。她無論遭受怎樣的凍餓、勞累、呵斥、詬罵、侮辱,對女兒的癡情思念從沒有一絲動搖,尋覓女兒的剛性與韌勁從不消退。這樣的悲劇,實在應該是后悲劇時代或者娛樂至死的時代的新狀態。
胡:《飛翔的女人》起初就想在兩個方面用力:強大的現實,現實對心靈的逼迫。如果說《命案高懸》的現實世界是帶出來的,那么《飛翔的女人》則是有意的呈現。《飛翔的女人》雖然也重視心理,但重點是外力對心理的作用,而不是心理的自我逼迫。這兩篇小說寫心理的重心不同。吳響有被壓垮的趨勢,是現實,更多是他被自己的心理壓垮。而荷子沒有,強大的現實只能讓她更堅忍,讓她的剛性以瘋狂的不可思議的方式生長。她沒有找到孩子,她失去家庭,從這一點說,確實是悲劇。寧小齡說,小說發表后,還有讀者打電話給他,問為什么沒找到孩子。另一個角度,她成功了,有喜的一面,是悲中之喜吧。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情感點,我的情感點在小人物,與自己的經歷有關。我周圍的人,目之所及,都是小人物,所以更能觸及這類人物幽暗隱秘的心理。
三
姜:我們勢必要談到你的苦難敘事。無論一個人的性格多么執拗,譬如荷子,她終究不得已走上賣淫這條路以解救自己的女兒。這樣,痛苦敘事中,人被脅迫、被劫持的意義就凸顯出來了。
胡:寫小人物的處境,“無奈”是難以繞過去的。面對無奈,選擇唯一的路。但絕境重生,已經這樣,還能再怎樣?現實的可能預設著人物的可能,現實的邊界也是心理的邊界。李敬澤在我的作品研討會上,說這篇小說的現實沒有完全打開。沒有完整丈量出荷子的心理世界。
姜:但我覺得你小說的意義,正是在這樣的層面上向文學母題逼近與抵達。
胡:我也試圖從別的方向抵達。路徑很多,方法很多,我努力尋找最適合的路徑和方法。在哪兒?能否找到?我不清楚。也許沒有意義,但設置難度,追尋本身就是意義吧。很糾結,但也找到了樂趣。這也是文學吸引我的地方。
姜:你的很多中篇,都似乎有著長篇小說的含量。這樣一來,我們是不是覺得,這樣的中篇,張力過大呢?為什么不把它處理成長篇呢?
胡:或許是可以寫成長篇的,像《一棵樹的生長方式》,我曾有過改成長篇的打算,后來沒有著手做這件事,一是當初寫中篇時的激情損耗,二是我懷疑自己難以拓展出新的屬于長篇的空間。
姜:除了張力的飽滿以外,我發現你的小說中視角也是非常有意味的。像《一個謎面有幾個謎底》,你選取的“我”是主人公老六的妹妹喬小燕的男朋友。這一來,“我”與老六之間的距離,就拉長了。
胡:寫這篇小說,我有一種敘述的沖動。以“我”的視角敘述他人,在我好像是第一次。“我”與老六有關,又有如你所說的距離。這為“我”的推測與探索提供了可能。有著想象的空間。
姜:我在這篇小說里發現雙線結構,或者,用我自己喜歡的說法叫做耦合結構。老六的城市經歷,與“我”來城市打工的目的,竟然如出一轍;而且,結果也驚人一致。老六所愛的人,在城市這種社會環境里丟失了;本來屬于“我”的喬小燕,也成了教授的情婦。更有意味的是老六,成了這兩部分的綰結點,且又成為兩種角色,受害者(其實是雙重受害者)、同時是這種悲劇的制造者。當然,說是制造者肯定不確切。畢竟,這一切,既不是老六能制造的,也不是老六能夠逆轉的。
胡:你讀得很細,完全深入到了小說肌理。小說各個角落的埋設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埋設常常是一個作家最得意的地方,當然也是最猶疑的地方,生怕讀者略過。怕識破,又怕輕易識破。我很高興你看得這樣清。有作家說,作品是寫給自己的,我不是這樣。雖然在寫作中沒有從讀者角度考慮,但仍有朦朧的讀者在。是有,而不是數量。沒有聽眾,演講會喪失激情,哪怕只有一個聽眾。你看清了,我想,你是能夠理解老六這個人物的。
姜:我覺得,耦合結構很有意味,它至少呈現了世界的某種相似性。這樣,張力在此又出現了。
胡:是啊,相似中有不同,不同中有相似。如果只寫老六,似乎太單薄了。“我”作為敘述者,是獨立的,也是老六的映襯。或者說是一棵樹投下的影子,這種立體感是我在這篇小說中想達到的。
姜:我時常在考慮一個社會性的問題:我們這樣的時代,是不是可以用狄更斯的《雙城記》的話來表述呢?“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講信用的時代,又是一個欺騙的時代;這是一個光明的時代,又是一個黑暗的時代。”我得承認,人們是在作著改變命運的努力,但這里,你是否又在暗示著人們要用哪一種方式去改變命運?
胡:我小說中的人物很少有原型,但有故鄉人物的某些影子,或者說,有時是某些故鄉人物,促成我一篇小說的誕生。我的村莊有一半以上的人以各種方式進入城市,他們在城市的情況我不僅是了解,而且是相當清楚。這個群體這種現象不能不讓人思考。有一個時期,也就是寫《一個謎面有幾個謎底》的時候,我的目光久久停駐。改變命運是任何一個時代的人都不會放棄的努力,是任何文學都繞不過去的話題。但作家的著眼點不同,有的著眼信仰,有的著眼文化差異,我想呈現的是他們改變命運的方式和可能。怎么改變?怎么改變才符合尺度?該不該符合尺度?那個尺度又是什么?我和小說中的“我”一樣迷惘。
姜:但是,畢竟,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一切皆有可能的時代。這個時代,其實為一切人準備好了一切。至少,當城鄉之間的樊籬終于被打破以后,這個社會為一切人準備了一切機會。所以,我現在發現,你這里的悲劇敘事,我們倒不妨可以沿用關于莎士比亞 “性格悲劇”的說法,是一種欲望悲劇。人們因為有了欲望,因而產生了悲劇。你筆下的人物,大多是因為欲望的存在而被扭曲的。
胡:放眼世界,哪里又有誰沒有欲望呢?有欲望沒有問題,也不是小說的重點,小說的重點在于審視欲望是怎么來的;在和欲望的對峙、抵御或在欲望的追趕中,人物如何處理自己與自己、自己與他人、自己與世界的關系。我最近重讀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簡單地說,這部小說就是寫欲望的。但閱歷不同,過去我讀出強大的欲望,現在則更多讀出不安和痛惜,欲望反而退后了。可以說,納博科夫的《洛麗塔》也是寫欲望的。納博科夫的偉大在于超越感官和道德,審視人們彼此的可能。所以,怎么寫欲望是一個很重要的,當然也是很難的問題。
姜:所以,我一直覺得,讀你的小說時,一個讀者的情緒,不可以被你裹挾。否則,我們很多價值判斷與分析,就會產生偏差。這樣看來,我們也就發現,作家看來是分為好幾種的。你可能就是那種力量型的作家,甚至可以說是暴力型的。你有一種強大的力量。這當然可以說明,你有一種強大的對社會的判斷與認知,這種判斷與認知,構成了你寫作的一種龐大底座。
胡:有些作品,我是有價值判斷的。不是為了更有力量,而是寫作中的不由自主。現在,我在想一些問題。作家在作品中應處于什么位置,作家該發出怎樣的聲音,這聲音是否有意義,暫時的意義還是持久的意義。我有了懷疑,或者說警覺。以后我會調整,嘗試別的寫作方式。
姜:當然,我還是承認,你這種力量的存在,是必要的。畢竟,這樣的時代,雖然為一切人準備了一切機會,然而,弱勢群體的存在,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社會或者社會中的強勢者對這些群體的侵犯,有時候竟然是在一種集體無意識與集體失語的狀況下產生的。這樣看來,你的清醒與良知,便于此產生出亮光與意義。
胡: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的演講,有一句話我特別欣賞。他說在雞蛋與石頭之間,肯定站在雞蛋一邊。這與道德無關,用良知來概括也不是十分準確。是作家的判斷,也是作為人類的判斷。對弱勢群落,人的基因中或許就有傾向性。當然,我并不是說,作為弱勢肯定是善的,必須同情,而是說在弱者與強者之間,在微弱光亮與炫目光芒之間,我更傾心于前者。
姜:你筆下很有幾個能立起來的女性。看來,一個真正的作家,還是應該以能寫好女性作為標志。呵呵。
胡:相比較男性,女性的情感更為復雜,與現實的對峙中女性也更容易被傷害。女性身上有著與文學更近的特質,再進一步說,沒有女性的文學世界不完整。關注女性的命運,更能看清我們及她們,更方便探尋生存的意義。
姜:看來,女性問題,你所思甚深。也說明,女性問題,是我們這個轉型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面。過去是,現在也是。只不過,角度各自不同而已。對了,你的這些女性形象與祥林嫂這樣的女性形象的區別何在?畢竟,時代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啊!
胡:如果從被侮辱的角度說,有相近處。但我的重點不是寫被侮辱的過程,而是寫退到極點之后女性和世界關系的變化,不是退縮,是一種柔軟卻堅忍的反擊。
姜:也許、可能有特定的地域,才有了這樣特定的女性群體。或者,你將這一群體的極端狀態呈現出來了?
胡:與地域有關嗎?可能是這樣。但說她們極端,似乎用詞重了些,好像她們不該如此。如果從現實的邏輯和角度分析,她們“這樣”咄咄逼人可能沒法存在。但文學應有自身的邏輯,在文學世界中,她們是可以“這樣”,也可以“這樣”存在的。這可以說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正常。成為常態,就不覺驚異了。
姜:我發現,你寫小說時的狀態,是不是與我們讀小說時感覺到的狀態一致呢?我一直覺得,你在寫作時非常用力。
胡:是想用力的,但用得不好,常常覺得不是寫作的料;特別是讀到好小說的時候,這種感覺更強烈。但有什么辦法呢?喜歡寫嘛,寫作也是向大師致敬的方式。
姜:《斷指》有人已經指出了,是一個類似于《羊脂球》的故事。然而,在我看來,這篇小說倒是寫出了底層社會的荒誕。
胡:荒誕無處不在,過去、現在,將來也會如此。任何歷史任何國度,荒誕都以不同的面目存在著,我的“發現”其實是存在,而不是真正的發現。我過早地預知了結局,因而失去了開掘的力度,有些遺憾。
四
姜:現在,市場經濟時代,鄉村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生態呢?我總覺得,現在,人與人的聯系與聯結不像過去那樣緊密了。客觀上,即使是在鄉村,現在不再像大集體時那樣處在一種非常關聯的人際關系圈子中。當然,現在,人與人之間,關系也還是有的。然而,我現在看出來的是,你的這么多鄉村小說中,似乎一個人的行動與行為,頗受旁人的關注與物議。事實上的情形是不是這樣的呢?
胡:鄉村散亂了,也可以說農民有了空前的自由,可以待在這個地方,也可以待在那個地方,互相離得很遠,但遠離并非不搭界,仍然有關聯。與便捷的通訊沒有直接關系,只能說通信提供了便捷的方式。至少,在我的故鄉是這樣。天南海北,那么多人,只要想知道,總能知道他們的消息。有時不想知道,也會無意中知道。鄉村秩序變了,倫理走了形,但仍存在著。這種存在像一根看不見的線,串著散落的珠子。而且,鄉村里聚集的方式很多,婚喪嫁娶、節假日等。
姜:也有人注意到另一個問題,就是你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一根筋”的比較多。
胡:我筆下有不少執拗人物,但不是為了執拗而執拗,執拗是他們叩問世界的方式,也是小人物常可依賴的武器。如果沒有這一點,只剩下被侮辱被損害的形象,還有什么光亮可言?
姜:當然,我承認,你寫出了現實主義的作品。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問題是,現實主義的形態是不是一定要寫出極端狀態下的人性?
胡:呈現極端狀態下的人性是一種方式。人有不同的面孔,只有這種方式才能看到他的另一面,或許,這反而是他真正的被遮掩的面孔。這就像觀一個人的球技,平時看不出什么,只有在賽場上才能看出真正的水平。當然,這不是唯一的方式。你提醒了我,必須尋找更多的路徑。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這個理論并不過時,而且有著相當的難度,但已不是現實主義唯一的形態。美國評論界把羅斯后來的作品冠以新現實主義,意義也在于此吧?任何主義,沒有新內容,都會喪失生命力。
姜:你寫出了極端狀態下的人性,寫出了人生的荒誕與悖謬,寫出了一次次追尋真相的努力,已經呈現出一種現實主義的新品質。我們可不可以認定,你對典型環境里的典型人物有了一種新的詮釋呢?
胡:我在努力,堅守著一些東西,也改變著一些東西。我的一位寫作朋友說,有時改變一個詞都是相當難的,確實如此。甚至在標點的運用上也是如此。但必須改變。為了尋找更大空間,也為體味探索的快感。效果如何,意義如何,我不知道,由他人去評價。我只知道,“典型”在這個紛雜的速度感極強的世界,很難很難。
姜:當然,我們也看到,在你的筆下,一些執拗的女性,其實可以說成執著更為恰當。像《極地胭脂》里的唐英,有一種固守自我的堅持,守住自己的一方天地,守住內心的潔白。《血色黃昏》里也開始有關于精神層面的展示。這種堅持與堅守,這種信念,已經超越其他人物的精神層面,抵達到一種對社會、對信仰層面的叩問。
胡:對精神層面的開掘是寫作的努力方向。畢竟,文學關注靈魂與精神。而且,對抗世界的速度,也只有憑借精神的力量。生活方式很難一成不變,但信仰是可以的。堅守,在某種程度上是姿態,也是對話方式。
姜:在你的小說寫作中,體驗與經驗看來是占很大比重的。與之相關的是,你覺得你現在的體驗與經驗靠得住嗎?你現在寫作過程中的體驗與經驗,是不是與現在的鄉村過于疏離了呢?
胡:我每年回鄉居住,沒覺得疏離。當然,在看鄉村的角度和著眼點上,與過去比較有了變化,也有新的思考。我的問題不在于疏離,而是能否找到合適的處理經驗的方式。角度有變化,不代表方式恰當與否。有些時候,我故意疏離,想站得遠一點,制造陌生感。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走近吧。
姜:在你看來,體驗、經驗與想象的關系是什么樣的?《從正午開始的黃昏》,可能是你刻意使用文學技巧的一個中篇。但這篇小說,看來偶然間離開了你一次。或者說,你這次離開了你善于寫作的領域,甚至也離開了“故事”。當然,有故事,只不過,這次的故事,是著意在隱藏故事。這部小說的敘述話語并沒有停留在“底層”的物質性空間,是不是意味著你將會實現真正的轉型?
胡:是否真正的轉型?說不好,我在尋求變化。其實,每篇寫作都試圖求變,只是有時變化太小,沒人察覺,或那種變化比不變更沒有力量。也許一生都尋不到最佳的寫作方式,但總算有找的愿望,所以也樂在其中。如果過去的小說偏重經驗,以后的小說想象的成分會大一些。
姜:最近讀你的中篇《隱匿者》,發現你的轉型的實現。應該說到了這里,已經實現華麗轉身。這篇頗有點卡夫卡味道的小說,是那么逼近我們生活中最為荒謬卻又最為真實的層面。這一篇小說是在什么情形下萌發的靈感?
胡:我是笨人,鮮有靈感,呵呵。有時閃過些念頭,我會及時記下。在我的本子上,有對一個詞的描述、對一個人物形象的勾勒,或者是某種敘述方式的運用,也有的是較為完整的想法。隨著時間推移,我慢慢確認哪些是種子,哪些已經成熟,應該動手完成。
姜:有人歸納得好:車禍讓那個瘦長的遇難者不存在了,20萬塊錢的賠償金讓“我”不存在了,叔叔的稱呼讓女兒的爸爸不存在了,三叔的侄子不存在了,妻子的老公不存在了;“我”近似瘋狂的暴力還擊讓趙青不存在了,騙子讓楊苗的老公不存在了,“我”對真相的主動尋找讓無數隱匿者不存在了。還有人稱,第一人稱的使用,連作者都不存在了。
胡:存在是事實,不存在也是事實。往往我們只注意存在、吃喝享用,試圖發出自己的聲音,直至生命凋零。沒了、不存在了,是生命意義上的消亡。另一種不存在不是生命的消亡,這種“不存在”存在著,橫亙在人生中,橫亙在世界上,可能被我們忽略了。
姜:其實,隱匿或者不存在,在小說中是故事層面的,然而,卻無意中揭示了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即我們現在這樣的社會生態里,不存在或者某一群體的被忽略、被遮蔽,是多么令人觸目驚心的事實。但是,我們很多作家卻在這里閉上眼睛。
胡:我的初衷沒想寫某一群體被忽略、被遮蔽,這太社會化了。在我的小說中,這些是被帶出來的,不是敘述重點。我的重心是借助“我”來打量周圍,揣度和家人和社會關系的微妙變化。特殊的身份,特殊的思維。一個活著的死人在看,不是正面看,是背面審視觀察。我選擇的不只是視角,還有“我”思考的方式。我特別在意“我”的這種不存在的思考。
姜:問題還有,這樣的隱匿或不存在,還更為強烈地揭示了諸如身份焦慮、生存焦慮、職業、符號意義(名字)、金錢、尊嚴、幸福、生存意義與價值追問等許多重大問題。這些問題,看似是現代城市綜合病,是歐洲19世紀奧匈帝國卡夫卡時代就流行的一些病,然而,卻在當下中國客觀存在著。這里,就有了厚重的分量。無論是從內容到形式,還是從形式到內容,都是那么直擊心靈。而與小說這種體裁的匹配程度,又是那么渾然天成,巧妙無比。
胡:謝謝你的肯定。寫作是需要動力的,你給了我信心。我總覺得一篇小說完成后,作家就該退后。對作品的解讀由評論家和讀者完成,正讀反讀誤讀,都是可以的。是評論家和讀者的權利,作家不應對作品作過多闡釋,因為所有的表達都在作品里。強力的自我闡釋有吆喝和辯解的嫌疑。前一陣子,我們幾個朋友在去北京的途中聊天,李浩說,如果能寫出一部拉什迪《午夜之子》那樣的作品,死也值了。寫出自己滿意、別人驚羨的小說,是每個作家的夢想,我當然不能免俗。或許終生都寫不出來,但我走著,能做的只能這樣了。我中篇寫得多些,短篇也寫。如鐵凝所言,短篇是節制的藝術,寫短篇更見功力。長篇也寫過,很不滿意,有幾年沒寫了,覺得寫好中短篇,再去寫長篇。
五
姜:你是如何走上文壇的?
胡:我三十七歲前是在鄉鎮及縣城度過的,當教師,邊教學邊寫作。寫作沒有任何可炫耀的地方,但教學上,我敢說,自己是不錯的教師。像蝸牛一樣慢慢往前爬,就這樣。我沒有明晰的自小就當作家的愿望,也沒有其他作家戲劇性的機遇。因為少年時代對閱讀的饑渴,參加工作后我把多半工資用來買書,讀書成癮,慢慢開始寫。在白紙上起草稿,再抄到稿紙上。我最初工作的鄉鎮沒有郵局,寄稿子需要到另一個鄉鎮。那是難得的享受,稿子投進郵筒,感覺整個世界都裝進心里。郵差一周來一次,摩托聲響起,心就狂跳。寫作讓我的生活有了光彩和期待,我堅持,沒有放棄。就這樣。
姜:在你走向文壇的過程中,哪一些作家給了你決定性的影響?
胡:說不上哪些作家給了我決定性的影響。我喜歡的作家很多。最早喜歡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果戈理、契訶夫,他們的書是早些年買的,幾塊錢的事。后來喜歡上歐美作家,像福樓拜、福克納等。當下的好多作家,我也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