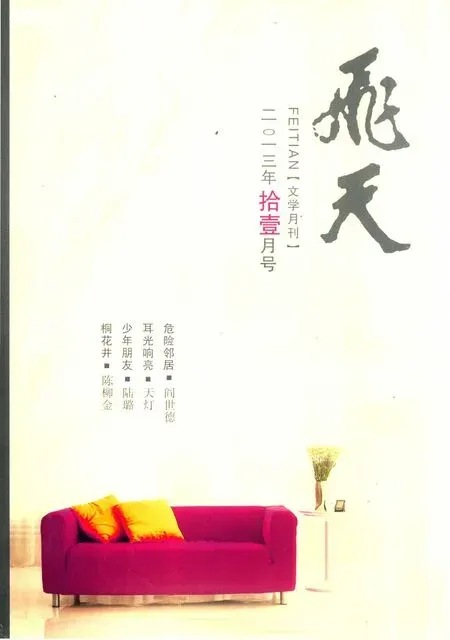石厲:建立在三維坐標上的詩論詩評
陳德宏
以前每每讀石厲的詩論詩評,總有一種特別的感覺:厚重、深刻、獨到、清新,似空谷足音。但由于閱讀的匆忙,加之缺乏定量的比較分析及整體的把握,因此認識僅止于印象。近讀40余萬言的皇皇巨著《詩學的范式》(石厲著,中國文聯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得窺全豹,茅塞頓開:深厚的國學修養,哲學美學理論的燭照,朦朧后詩人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創作體驗,構成了石厲詩論詩評獨樹一幟的貼近詩歌本質的鮮明特色。
我常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文友說,石厲不是生不逢辰,亦不是懷才不遇,而是某種“人生的錯位”。比如說對于古典文學,他受家學傳統的影響,自幼飽讀詩書,頗有心得,也頗有建樹——他的《中國遠古詩歌思想》、《先秦人文精神史綱》、《中華五千年史演義》、《春秋公羊家思想考略》,都堪稱學術專著。若在高等學府“厚古薄今”的文史院所,僅憑這幾部專著就足以奠定他的學術地位了。可惜他供職于“厚今薄古”的文學界,因此,這些磚頭般厚重的著作,充其量只能算他的“小秋收”。好在他將國學淵源引入他的詩論詩評,猶如疏浚了一條河流,將因五四白話詩的興起而中斷了的我國詩歌傳統融會貫通了起來。
中國詩歌的起點在哪里?它的產生與人類的實踐活動與情感有何關系?遠古詩歌的所指與能指是什么?……這些基礎的又是基本的問題,直接關系到詩歌的發生、發展,過去、今天及未來。石厲的《緬懷遠古詩歌》對此進行了追本溯源的研究。“認識事物的開始,特別是認識事物如何開始,將永遠影響著認識事物的全部”;“所以在歷史的探索中,起點永遠誘惑我們,它就像真理一樣,它和將來的意義是同等重要的,甚至有時候二者合一”。
進入古典文獻領域,石厲顯示出了縱橫馳騁如魚得水的獨特優勢。他征引《吳越春秋》中的《彈歌》,《禮記·郊特性》中的《伊耆氏·蠟辭》,以及郭沫若《卜辭通纂》載有的《癸卯卜》……指出“上古詩歌的雛形在有文字記載的殘片里已基本形成”。同時對《帝王世紀》載“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及《尚書·大傳》所載《卿云》歌詞“卿云爛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給出了自己的闡釋:前者“是對人類原初生活特征本身的歌唱”,后者表達“對美麗天空的深情厚意,來感念永恒”。
關于詩歌起點的探求,由于它在歷史方面的不可追溯性和它終極性的困惑,任何研究都只能接近而不能抵達。于是石厲又把詩歌的起源從解釋的角度轉向詩歌的發生方面,從發生學原理出發,旁征博引,指出詩歌的發生與人類的情感,與音樂、舞蹈、繪畫藝術的互通,與勞動的關聯,與覡巫與靈魂的通性……等方面進行了論證。
石厲關于古典詩歌研究的收獲,猶如獲得了一把打開詩歌之門的金鑰匙,令他開啟了一座又一座詩歌的奧秘之門:“詩歌的歷史,是人類精神的歷史,詩歌的本質也是人類精神的本質。甚至一言以蔽之,詩歌史是成年人的精神史,但是詩歌又不斷地承擔起孩子們的啟蒙任務,所以孩子們在不斷學習詩歌的過程中長大成人。”(《中國古詩與文化啟蒙》);“真正的文化是超越物質利益或政治派別的最純粹最通透也是最有普遍性的人類精神形式,它是能夠讓人類共同理解、共同認同的意志表達,它能夠讓不同語言的人類互相諒解、互相寬容。比如優秀的詩歌,就是數千年來人類一直信奉的重要文化形式”(《寫在中國現當代詩歌的邊上》);“謝靈運以前,山水在我國詩歌中,只是一種點綴或背景,而到了謝靈運,山水不僅是詩歌的表現對象,山水還是詩歌的象征本體。山水就像謝靈運的內心世界一樣,在他的詩歌中也是翻江倒海。從此,山水成為了中國詩人抒情寫意最好的載體,也是寄放情思最好的處所”(《詩島讀詩》)……
有詩人撰文宣稱,詩是不可發聲“讀”的,只能在心里無聲地“念”。石厲及其他一些研究中外詩歌起點的學者告訴我們,詩幾乎是與人類的語言同時產生的,是與人類的勞動相伴而生的。如果詩不能讀,在語言與文字之間的“空窗”期,人類如何將詩一代一代傳承的呢?民族英雄史詩也許更有說服力,有的民族沒有文字或者他們的文字出現得較晚,但他們的英雄史詩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經口口相傳了,不發聲讀可能嗎?再說了,詩與歌是密不可分的,詩與音樂舞蹈甚至祭祀都有關聯,而這些關聯的部分都有聲音,惟獨詩不能發聲嗎?
石厲詩論詩評另外的鍥入口是哲學美學。
哲學美學是石厲所受高等教育的專業。在他被大學哲學系錄取之前,已經熟讀了黑格爾的《小邏輯》《精神現象學》、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等大部頭的哲學著作,還手抄過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和柏格森的《時間與自由意志》……用功用心之深之勤,可見一斑。不僅如此,更在于他如饑似渴地癡迷哲學美學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恰逢如周揚所說的我國歷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是風云激蕩美學激辯思想碰撞火花四濺的年代,他所師從的著名美學家高爾泰、韓學本等正置身其中。激辯令石厲避免了接受坐而論道的經院哲學,讓他見識了也學習了哲學美學的精粹與真諦,信手拈來,便形成了對于詩的真知灼見。
高爾泰有句名言:文學是人類伸向未來的觸須。石厲繼承了高爾泰的思想并有所發展,在他的詩論詩評中不厭其煩地反復論述詩與詩人乃至整個人類的生命關聯。他說:“在詩歌史上,將詩歌自身當作目的和將詩歌當作簡單的工具都是極端的認識。詩歌必須是對于對象世界(包括自我生命)的澄明關照,詩歌不能與具體的世界無關,它至少應該與民族的命運、個人的生死有著秘密的詩歌式的通道。至于有人將詩歌又推入另一個極端變成某種簡單的、可以操控的工具,那只能是另外的問題,與詩歌所承擔的社會歷史道義或時代精神并無太大關涉。”(《李瑛:從歷史深處走來的詩歌巨匠》)據此,他在大量征引并分析了李瑛創作于不同時期的詩作之后予以定評:“詩人李瑛年輕時的詩歌雖然已經達到了一個高度,中年時以《一月的哀思》一詩蜚聲海內外,但他這前后的詩歌,教條的激情遮掩了普遍意義上人生的抒情,也遮掩了他用詩歌的方式認識世界認識生命。進入晚年后,他的詩歌正如古代圣哲所描述的那樣,他才完成了他的一系列‘大器’之作。”
在汗牛充棟的關于李瑛詩歌的研究著述中,石厲的論評切中腠理,雋永清新,深刻獨到,卓爾不群。
彝族詩人吉狄馬加一直用笫二母語漢語寫詩,此種狀況一直困繞著糾結著評論界,有人回避這一話題,以免尷尬,有人則不無憂慮地認為母語的消失(或棄用)勢必會削弱作品的民族特色及生命信息的傳遞。石厲則不然,他認為吉狄馬加詩歌創作的主要成就主要特色恰恰源自他的第二母語漢語——詩歌對他的第一母語彝語——民族記憶的呼喚與應答:“遠山成為他詩歌中一種最令他憂傷、最讓他一往情深的呼喚,在那里,有他民族的歷史,有將要熄滅的篝火,有他丟失的銹花針,有在黑暗中傾訴憂郁的口弦,有那些永遠埋葬在土中朝左邊睡去又朝右邊睡去的祖宗,有在深夜喝醉了酒的民歌,有在陽光下突然老去的一堵土墻,那是他的夢想、是他‘一個彝人的夢想’組詩永遠的象征。”(《遠山的召喚——論吉狄馬加早期的詩歌》)為此,石厲征引了海德格爾的學說及李白的實例:“而用海德格爾的話說,語言是與人的存在一起降臨的存在。后世傳說李白熟悉中國北方少數民族文字,那可能是李白的第一母語。正是第二毋語語境中的詩歌創作,竟讓李白占據了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個峰巔。”
新世紀以來,“詩歌到語言止”不絕于耳,以至發展到散文、小說也“到語言止”的泛濫。可究竟什么是“到語言止”?論者大多語焉不詳,聞者則如墜五里霧中。石厲對吉狄馬加詩歌創作的語言學闡釋,也許能給我們某種啟迪——“可以這樣說,與母語保持一種適當距離和陌生感的語言環境不僅能夠醞釀創造的激情,而且有助于抵達語境中更深層次的表達,可以達到一般的語言表現難以企及的高度。保持孤獨的語境狀態能夠使語言的創作者深入到語言表現的深處,使他和語言表現的對象之間更加純凈和清晰,沒有過多習以為常中迷霧的干擾。所以優秀的詩人在面對自己的母語時,都是母語逼迫下的流浪者、異鄉人,甚至是遠逝而自疏者。”
真是善莫大焉。石厲不僅闡明了“詩歌到語言止”的深刻內涵,更在于為數量可觀的以第二母語創作的詩人、作家,消除了起碼是減弱了他們的心靈自慚,阻擋了起碼是弱化了庸常社會投來的“白眼”。
有的評論家名氣很大,搞了一輩子評論,出了很多書,到頭卻落了個“有評論無理論”的定評。石厲則不然,他的詩歌評論沒有短平快的應景之作,洋洋大觀,是研究性的專論,是把詩人詩作放在時代的社會思潮中,予以動態的宏觀的美學與歷史的評價與判斷——闡釋著生發著也校驗著他的詩學理論。據此,他用《鄭敏的〈詩集1942——1947〉:超越客體的跡象》、《用客體指向自己:更加直接因而更加玄學的風格》、《鄭敏近觀:走向自然》評價了我國九葉派著名女詩人鄭敏的幾乎是一生的創作成就;他將女詩人匡文留與美國詩人惠特曼比較,寫出了《裸露——匡文留詩歌中的兩性情結》;他以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及深厚的詩學修養,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田海的9000行長詩《〈激情中國史〉的兩難境地》……
石厲不僅是“第三代”詩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還是他們的理論代言人,因為他就是創辦于1983年秋的校園詩歌刊物《第三代》的始作俑者者。他寫于26年前的文章《詩歌第三代》既可看作是這個詩歌思潮的宣言,也可看作是這個思潮的總結,因此也就具有了親歷性及史料價值。他說:“建國以后真正的詩歌第一代是北島他們,北島的那些追隨者們是第二代,我們是第三代。”北島之前無詩歌無詩人?有些狂妄!這就是他們亮相時的叛逆姿態。不過,他們的批判可不僅指向解放后的十七年,也指向了北島們,而且對北島們的批判還更為犀利深刻——“我們知道,北島他們的詩歌最顯著的特點也是最致命的地方,那就是以理性為詩歌本體。什么現象,什么生命里程都在理性的統攝中進行詩歌式的分析回答。他們反對人之外有一個上帝存在,但當他們創造作品的時候,卻把自己填充成上帝的形象,并且不惜以上帝的扮相與讀者對話……這就從一個角度糾正了錯誤,又從另一個角度犯了這種錯誤。”批判的鋒芒夠尖銳了,但石厲的如下幾句話也許更能擊中北島們的要害:“我并不試圖反對理性,但我反對用理性來堆積作品。本來在康德美學中,這種錯誤早已被澄清了,康德以后西方的一流藝術家絕不會犯這種錯誤了。”
猶如哲學上的否定之否定,對北島們的否定反而凸顯了“第三代”詩人的實踐與理論的許多優點及其合理性:比如表現一般人的人生狀態以及表現廣普意義上的人類感情;比如絕對安于大的現狀,不對政治和時代輕易發表那些不成熟的見解;比如去探究人生或生活的細節,發現那些真正支配我們生命與生活的普遍性內核;藝術上主要關心作為人類普遍意義而存在的人的情感和人生經驗,在形式上追求節奏的口語化,語言的口語化;作品試圖尋求一種自然而然的東西,盡量尋求更高意義上的真實……
作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闖入文壇的“詩歌憤青”,石厲對于“第三代”詩歌的論述,已相當冷靜而客觀了。
將一本厚重的文藝評論集以《詩學的范式》名之,足見詩論詩評在石厲心中的分量與位置。如果作者將自己一以貫之的詩歌理念定為規范自己詩歌創作的圭臬,本也無可厚非,但是作為公開出版發行面向廣大讀者的書,《詩學的范式》就不僅值得商榷而且令人生疑。五四以降的新詩發展已近百年,應該承認中國的新詩仍在探索試驗中,離“范式”尚遙遙無期(也許永遠不會有范式)。環顧國際詩壇,也無“范式”可言,如果硬要找一種“范式”,那也只是深藏于每一位詩人、詩評家內心的“個人版本”,示人可也,交流亦可也,統一則不可,亦不能。有人曾要建登天的“巴比”,連“上帝”都不同意。道理很簡單,世界需要多樣性,詩歌更需要多樣性。
不過,石厲建立在中國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哲學美學思想、詩人創作的直感體驗這“三維坐標”上的詩論詩評,在喧嘩嘈雜的當代詩壇,應該說還是獨樹一幟的——它比學院派的文章多了些直感多了些體驗多了些鮮活,它比某些詩人不靠譜的囈語般的“創作談”多了些科學多了些理性多了些人間煙火,它比某些職業但并不專業的評論家的大作多了些理解多了些感悟多了些對詩質詩藝的抵近。
這是石厲詩論詩評的獨特價值。
這正是石厲詩論詩評的獨特貢獻。
這也正是石厲詩論詩評的獨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