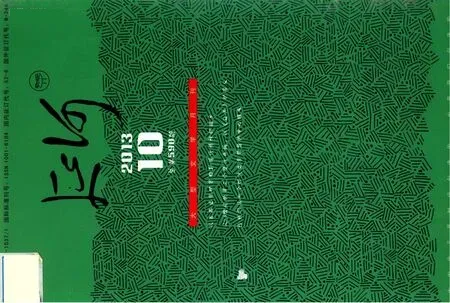神話“重述”的集體潰敗
朱嫣然
《碧奴》是蘇童為“‘重述神話’寫作計劃”而作的長篇小說。“重述神話”是全球包括英、美、中、法、德、日、韓等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知名出版社參與的全球首個跨國出版合作項目。由英國坎農格特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發起,委托世界各國作家各自選擇一個神話進行改寫,內容和范圍不限。
這是一個頗具意義的寫作項目,已加盟的叢書作者包括諾貝爾獎、布克獎獲得者及暢銷書作家,如簡妮特?溫特森、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斯蒂芬?金等。中國作家中,蘇童、李銳、葉兆言、阿來等受到邀請,用自己的方式對中國神話進行了重新解構。遺憾的是,在這一系列的神話寫作中,先鋒作家們保留了自己的語言優勢和敘事能力,同時也暴露出其根深蒂固的無神論意識形態。用無神論去書寫神話,導致了這些作品中“神性”的集體缺失,直接拋卻了神話寫作的靈魂。
相比于李銳的《人間》、葉兆言的《后羿》和阿來的《格薩爾王》,“人氣作家”蘇童的《碧奴》受到了更多的批評與關注。蘇童用優美的語言打造了一個神話,如同打造一個華麗的神殿。但是神的缺席制止這場神話敘事,這是一個致命的缺陷,猶如“碧奴”背負的那塊頑石,壓垮了整部作品的精神指向。
眼淚的生存哲學
《碧奴》故事的敘述是由眼淚開始的,最終又由眼淚結束。極具想象力的“眼淚敘事”,是這部小說最引人入勝,卻也是唯一精絕的地方,構成了整部小說虛無而蒼白的支架。
一個叫信桃君的貴族來到了北山,對他的敘述,卻從遺忘開始。“人們已經不記得信桃君隱居北山時的模樣了,他的草廬早就被火焚毀,留下幾根發黑的木樁,堆在一片荒蕪的菜地里。”顯然,信桃君是開頭時一個模糊而黯淡的影子,蘇童用了煞有介事的語氣,將這個孱弱的落魄貴族焚燒成一團黑色的記憶。整個故事的背景,因此被放置在了一片鬼魅而疏離的土地上。將死的信桃君,他隱居到了北山,同時也把死亡的宿命帶到了這里。北山的人們因為為他“哭靈”,而遭遇了一次殘忍的集體謀殺。這是“眼淚”在故事中的首次出場,它的出場帶來了與死亡有關的恐怖記憶。從此,“北山下的人們至今不能哭泣”,哭泣不被允許,它成了死亡的圖騰。要生存,就不能哭泣,這成了北山下人們的生存哲學。
“眼淚等同死亡”的哲學觀第一次被打破,是碧奴出現在五谷城時。她的眼淚被城門口的官兵發現,并被認為極具藥引價值,可以奉獻給達官詹刺史的藥爐。淚水在關鍵時刻救了將死的碧奴一命,將象征著死亡的外衣成功脫下,被賦予了與生存有關的星火希望。這是一次依賴“眼淚”的互救,詹刺史需要用眼淚入藥救活老母,碧奴需要將眼淚交出以換得生存。
蘇童當然不會讓碧奴在這種情況下流淚,如我料想的一樣,在面對著接淚的壇子時,碧奴一滴眼淚也無法流出。我們無法樂觀地認為,她是有精神潔癖或某種覺悟。這個美麗而愚蠢的村婦,她暫時離開了與苦難無關的情境,以至于失去了反應。這是一次遺憾而尷尬的轉折,眼淚并沒有擺脫自身的宿命。
眼淚最后一次大規模出場,是在故事的結尾。大燕嶺上搬磚的男人們,他們同北山下的人們一樣,不被允許哭泣。而碧奴的哭聲像風一樣回蕩在大燕嶺的上空,堅硬的城墻外,是灰黃而空曠的遠方。蘇童用優美精致的語言,著力刻畫了碧奴這最后一次的哭泣。這哭泣是如此宏大而悲傷,整個天地都因此荒蕪。在這次哭泣中,碧奴終于拋卻了桃村的女兒經,放肆地改用眼睛哭泣。她的哭泣有了作用,山崩地裂中,長城塌了。
眼淚至此完成了它的三次主要出場,蘇童也通過這三場“眼淚”完成了敘事。在故事的敘述中,眼淚始終與恐懼和死亡有關,直到一個看似樂觀的結局到來。但這結局又是如此牽強,它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新問題,碧奴是如何靠著最后的眼淚,哭倒長城的?僅僅是因為她拋卻了眼淚帶來的死亡恐懼,向“不能用眼睛哭泣”發起了反抗?
被忽略的心臟
哭泣本身是一種情感表達的方式,北山的人們顯然失去了這種直接表達情感的權利。但是蘇童給了他們全新的排淚秘方,桃村女孩的眼淚,從眼睛以外的手指和腳趾、頭發、乳房、陰部等所有孔竅流出,漫過蒼涼的大地,成為小說的章魚式結構的邏輯支點。
“耳朵大的女孩從母親那里學會了用耳朵哭泣的方法,那眼睛和耳朵之間的秘密通道被豁然打開,眼淚便流到耳朵里去了,大耳朵是容納眼淚天然的好容器,即使有女孩耳孔淺,溢出的淚也是滴到脖頸上,脖頸雖然潮了,臉上是干的。厚嘴唇的女孩大多學的是用嘴唇排淚的方法,那樣的女孩子嘴上經常濕漉漉的……”顯然,只有身體最飽滿的部位,才會流出豐富的眼淚。蘇童給碧奴的,是一頭烏黑濃密的長發,碧奴從那里流出眼淚,流得比所有其他女孩兒都多。在她背著冬衣尋夫的途中,她的腳趾也新增了流淚的功能。這大抵可以推斷出,長途的跋涉,讓碧奴的雙腳也變得更加厚實有力。
但是,奇異的是,在蘇童筆下,眼淚可以從所有孔竅流出,唯獨沒有心。在故事的開頭,北山的人們由于為信桃君哭靈而紛紛葬送性命,因此得出“哭靈人都死于一顆感恩之心”的結論。當北山下的人們為了生存不再流淚時,他們也就放棄了有心靈有關的事物。
這是一處絕佳的隱喻,可惜的是,蘇童似乎刻意地將其忽略了。在之后的敘述中,從身體各處流出的眼淚洶涌不絕,而心臟依舊保持著被忽略的姿態。我原本以外,在碧奴流亡的途中,被忽略的心臟會被重新喚起,流出清澈透明的眼淚,完成“眼淚敘事”與“神話敘事”的雙重轉化與升華。遺憾的是,直至結尾,碧奴以及蘇童本人都沒有從中蘇醒。他們沿著“眼淚敘事”的奇詭開端漸行漸遠,終于走向不歸的末路。
故事在哭倒長城處戛然而止,似乎暗示了眼淚和碧奴的最終勝利,卻因此讓整個故事顯得蒼白而虛弱。沒有心的眼淚,如同沒有靈魂的肉身。因此,碧奴的眼淚是沒有精神指向的,它無法支撐起這則神話的價值與信仰體系。眼淚在蘇童的筆下,如同一個刻意打造的、極具神秘感的儀式,卻最終成了一個虛晃的影子,在碧奴一路的流亡中,逐漸黯淡下去。
受虐與施虐的狂歡
在“眼淚敘事”的主線之外,“自虐與他虐”的母題,如同一條暗夜里的蛇,固執地爬行在渾濁敘述的表層。碧奴在給丈夫送冬衣的流亡途中經受的種種,看起來像是一場紛繁吵嚷的苦難匯演,和不可思議的虐待狂歡。
碧奴如同一個舊式的自虐英雄,悲情泛濫,自我凌遲,享受著浸淫其中的快感。她行走在充斥著血和淚的路途上,遍嘗人間苦難,卻似乎并不自知。蘇童的敘事保持了先鋒小說家一貫的冷淡,卻在《碧奴》中得到了極為失敗的效果——如同沒有心的“眼淚”,碧奴成了一個沒有心的殉道者。
在自虐以外,一系列更嚴重的他虐事件混入了小說的敘事中。碧奴一路上從未遇見善意的人事,在樹林中,她被一群年輕的男孩猥褻,隨后被釘在死人棺木上為陌生男子哭喪……施虐的高潮發生在碧奴被當做刺客,被關在鐵籠里示眾的時刻。那是一場真正的嗜血狂歡,在蘇童冷酷卻又沉湎的描述中,其場面的暴虐程度令人發指。“人們轉過了臉,很自然地去看籠子里碧奴的手,她的手被套在木枷洞里,看不清楚,她的發髻已經散成亂發,亂發滴著雨水披散下來,遮住了她的臉,她的臉也看不清楚……”這是一個瘦削而蒼白的女子,但人們關心的,只是她的臉看不清楚,影響了自己的窺視。而碧奴本人呢,在骯臟的囚車和滂沱的大雨中,她安然入睡,對一切命運的不幸坦然接受。這或者就是蘇童在序言中所說的“樂觀的故事”,我們甚至可以由此推斷,蘇童本人也陷入了這種施虐的狂歡中,不能自拔。
蘇童是一個模糊的影子,隱藏在看似冷漠實則興奮的敘述背后。他與碧奴之間,構成了精準而對立的“受與施”關系。對碧奴施暴者,正是蘇童本人。他用了一場又一場的暴力狂歡,蓄意打造出一個女子的悲慘形象,如同在腐爛傷口上雕刻出的精美繁花。
苦難的巨大籌碼,推動著蘇童小說的敘事。一個女子的眼淚和痛苦,通過極端的虐待和摧殘,赤裸裸地呈現在了讀者面前,從而喚得震動和同情。這是一種笨拙的方式,它使故事本身失去了一個飽滿的精神內核。
缺乏說服力的出走者
碧奴是在一個晴朗的日子里出走的,在那個溫暖的季節里,她固執地要去為丈夫送一件冬衣。碧奴出行的目的是如此單薄,單薄得有些愚笨。當然,在故事的開頭,碧奴的這種愚笨是可愛的,至少她是帶著頑強的信念離開桃村的。我們可以期待,這模糊的信念,會隨著這場固執的出走,而逐漸清晰和明朗起來。
從出走的層面來說,碧奴身上具有反抗者的精神氣質。她的愚笨和固執,使她充滿了一往無前的勇氣。與懼怕眼淚的北山人不同,碧奴似乎是不忌憚死亡的,她試圖用一只青翠的葫蘆,提前埋葬自己的肉身,像埋葬一件冰冷的器物。她對待自身是冷漠的,這種冷漠反襯出她在出走時的堅決,以及后來路途中的熱情。在這場漫長而痛苦的行走中,碧奴對自己遭遇的一切磨難選擇了盲視,沒有任何痛感,同時,她又有著不可思議的,不抵達大燕嶺絕不罷休的堅韌信念。對肉體的極端漠視,和對目的地的極端狂熱,構成了一個精神分裂的女性形象。
碧奴出走的唯一目的,就是為她遠在大燕嶺的丈夫萬豈梁送一件冬衣。如此我們便可以看出,整部小說就是在講述中國古代,一個極其普通的“千里尋夫”的故事,其本身不具備任何新意。蘇童利用了神秘主義和傳奇性等工具,為整部小說編織了一個巨大的圈套,以掩蓋故事本身的單薄。如同一件高貴柔軟的外衣,勉強地遮掩著空洞的內核。
作為出走者,碧奴是缺乏說服力的。碧奴沒有自己的守護神,也沒有自己信仰的教義。她惟一的跟班是一只同她一樣愚頑的盲眼青蛙。這是一種苦行僧的姿態,需要用身體語言去表達信念。但是,在《碧奴》中,我們無法找到支撐這種苦行的精神力量。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究竟什么東西在支撐碧奴承受如此巨大的苦難。是愛?宗教信念?還是某種神奇的巫術?蘇童在敘述中沒有給出有力的解答。
這一切使得碧奴的出走變得毫無說服力,她不是一個朝圣者,而作為殉道者,她又是沒有光環的。碧奴整個人,連同她的故事,都是如此黯淡而單薄。她是一個缺乏說服力的出走者,從另一個方面折射出中國男權文化的陰郁一面。
蘇童用一部長篇小說的筆墨描寫了碧奴這樣一個女人,美麗,愚笨,隱忍,同時有著無可救藥的癡心與貞潔。這顯然是蘇童心中華夏女性的最高典范。整個故事的主線是這個叫碧奴的女人,而男性角色則是故事中一個個輪番出現卻又面目模糊的配角,男主甚至只是一個與名字有關的蒼白代號,它看上去很像是一份女性主義文本,實則完全相反。那些面目模糊的男人們,兇狠、狡詐、對碧奴的苦難境遇毫無憐憫,反而更加肆虐地加以踐踏,而碧奴卻對此毫無知覺,繼續圣母般地對他們表現出天真的良善。碧奴穿越了所有非人的苦難,只為完成對丈夫的堅貞。而她是否愛自己的丈夫呢?在蘇童的小說中,對此似乎絲毫沒有涉及。
傳統的中國男權文化,要求女人成為模范的受虐者,這一受虐倫理,從貞節牌坊開始,一路浩浩蕩蕩地延伸下去,最終凝結在先鋒小說家的筆尖上。蘇童肯定并謳歌了碧奴的勝利,重塑了傳統的貞操美學。而面對孟姜女故事中可能包含的儒教歧視女性因素,蘇童并沒有給出必要的質疑或批判。《碧奴》的整個敘事,就如同一曲高昂的女性受虐之歌,從兩千多年前的秦漢,一直回蕩到今天,如同碧奴那風一般的哭泣。
“神”與“性”的雙重缺失
作為神話寫作文本,《碧奴》在處理最關鍵的“神性”時遭遇了慘敗。整部小說用華麗的語言打造了一個精美的神殿,卻連冠冕堂皇的神像都不曾塑起,只留下空蕩蕩的閱讀現場。“神”與“性”的雙重缺失,暴露了蘇童根深蒂固的無神論意識形態,同時宣告了這則神話寫作的失敗。
小說沒有任何直接的性描寫,這從側面襯托出愛的退場。“他們守在溪邊,隔水談論著信桃君狀如孩童的生殖器官,躲在巖石后面的牧羊人說王公貴族就是不一樣,連那東西也長得那么精致文雅,灌木叢里的樵夫則懷疑那樣的器官是否能夠傳宗接代……”這是小說中為數不多的對生殖器官的直接描摹,它是纖細而脆弱的,仿佛隨時可以被折斷。某種意義上,信桃君的死亡,暗示了“性”,或者是男性的陽具在整部小說中的缺場。這也許是蘇童刻意打造出的貞節。在后文中,即使碧奴被一群年輕的男孩猥褻,蘇童的語言也控制得干凈節制,一筆帶過,有著不可思議的纖弱美感。
而在碧奴與丈夫萬豈梁之間,也沒有太多的情感描摹。只有一段描述碧奴對丈夫的回憶,涉及隱秘而歡愉的性愛,短暫而甜蜜。可是這段追憶是如此單薄,根本無力支撐碧奴出走背后的強大精神信念。
脫離了性和愛的根基,《碧奴》故事中的情感變得單薄起來,經不起任何推敲。而整個故事中,我看不到神的存在。除了結尾處出現的山神淡弱的影子,冷漠地看著背著重石上山的碧奴。那些亡靈變成的青蛙、百春臺河五谷城外的馬人和鹿人等,生硬而軟弱,失去了神話敘事的透明和清澈,也與神話應具有的神性毫無瓜葛。
蘇童在序言中說,“神話是飛翔的現實,沉重的現實飛翔起來,也許仍然沉重。但人們籍此短暫地脫離現實,卻是一次愉快的解脫,我們都需要這種解脫。”遺憾的是,讀完《碧奴》全篇,我并沒有得到解脫,甚至更加沉重。我們并沒有從碧奴的眼淚中,尋找到解決人類普遍困境的終極方法,反而陷入到一種更無力的絕望中。神的缺失,讓讀者和碧奴一樣,最終只能走向神話的窮途末路。
蘇童妄圖通過對民間神話的瑰麗想象,建造一套自己的情感哲學。但是毫無疑問,他失敗了。在這次“重述神話”的嘗試中,中國作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包括李銳的《人間》、葉兆言的《后羿》和阿來的《格薩爾王》在內。一群心中無神的作家,無法正確闡釋神話遺產。碧奴的道德眼淚,摧毀了孟姜女的偉大信念,同時宣告了這次神話重述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