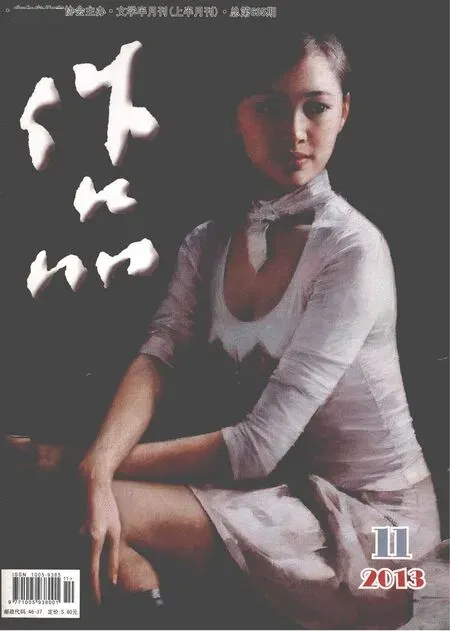緬懷
◎諾 諾
火車(chē)過(guò)了張家界站不遠(yuǎn),我又夢(mèng)見(jiàn)小蕁給我發(fā)來(lái)了短信。短信界面沒(méi)內(nèi)容,空蕩蕩地,好像只是一個(gè)錯(cuò)按的意外。于是我在夢(mèng)中又迷迷糊糊地睡過(guò)去,隱約聽(tīng)見(jiàn)滴滴響兩聲,分不清虛實(shí),便胡亂地拍了拍亂成一團(tuán)的被單,佯作解釋。
直到迷迷糊糊地醒來(lái),對(duì)著頭頂?shù)拇舶宄錾竦臅r(shí)候,在完全沒(méi)有意識(shí)到的情況下接到了她的電話(huà)。
我沒(méi)有應(yīng)答,她也沒(méi)有說(shuō)話(huà),雙方屏息凝神地沉默著。最后她掛斷了通話(huà),耳邊手機(jī)輕微地“嘟”了一聲,便再?zèng)]有發(fā)出聲響。
深夜才醒過(guò)來(lái),燙了速食面,在窗口旁的椅子上神思恍惚地坐著。列車(chē)員經(jīng)過(guò)的時(shí)候,遠(yuǎn)遠(yuǎn)對(duì)著另外幾個(gè)清醒的乘客壓低了聲音說(shuō):“再過(guò)十五分鐘就要到站了。”經(jīng)過(guò)我身邊,似乎稍微遲疑了一下。我側(cè)過(guò)身騰出半條過(guò)道,他便徑直走了過(guò)去。
我漸漸失去了睡意,等著下一站的停靠,下車(chē)買(mǎi)一些深夜和清晨用的飲用水。又記起煙已經(jīng)在登車(chē)前用完了,把原子筆從口袋里翻出來(lái),借著桌子下的應(yīng)急燈光在掌心上添了一個(gè)“煙”字。但最后還是沒(méi)有買(mǎi)到,只在即將關(guān)門(mén)的站臺(tái)商店里買(mǎi)了些礦泉水和冰棒。這樣的站臺(tái)小店里,其實(shí)也沒(méi)什么能買(mǎi)的了。
這讓我想起和小蕁在一起的時(shí)候,深夜突如其來(lái)地走出家門(mén)想找點(diǎn)熱乎的夜宵,卻發(fā)現(xiàn)亮著燈的只剩下了賣(mài)零食的便利店。
白天的時(shí)候,誰(shuí)也不想出門(mén)。除了每周固定一次出門(mén)補(bǔ)給,大多的時(shí)間是兩個(gè)人裹在被子里,一言不發(fā)地看小說(shuō)和漫畫(huà)書(shū),上網(wǎng)。彼此已經(jīng)很習(xí)慣沉默,時(shí)間久了,就像身體里不可分割的一大部分。水端兩杯,碗洗成對(duì),規(guī)避所有可能尷尬的瞬間。
小蕁從菜市里買(mǎi)回來(lái)的金魚(yú)就在這靜悄悄的某一天里悄無(wú)聲息地死了,浮在用礦泉水的大瓶子剪成的簡(jiǎn)陋魚(yú)缸的水面上。春天過(guò)去的時(shí)候,不見(jiàn)了翻過(guò)來(lái)的鼓脹肚皮,也沒(méi)了空洞膨脹的魚(yú)眼,變成一缸藏在陽(yáng)臺(tái)的角落里的死水,生機(jī)勃勃地泛著綠。卻也并沒(méi)有腐爛的臭味。我刷牙的時(shí)候總能見(jiàn)到它,每回都想著,也許可以往里面插株綠蘿,或者別的什么。但刷完牙后總會(huì)迅速地忘記,任由它一日日干涸、腐爛,不可避免地成為一些不為人注意的小秘密繁衍生息的溫床。
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之后,我們又開(kāi)始說(shuō)話(huà)了。像很久沒(méi)有開(kāi)過(guò)口了似的,她用一種平靜的語(yǔ)調(diào)說(shuō):“去超市的時(shí)候,買(mǎi)點(diǎn)酒回來(lái)吧。啤酒。”我“嗯”了一聲。她又說(shuō):“我今天有點(diǎn)肚子疼,就不去了。”
原來(lái)有的時(shí)候,真的是可以靜到只有“吱呀”的一聲,除了被風(fēng)推動(dòng)的百葉窗的窗葉,再無(wú)任何聲響。我走出樓道的時(shí)候,路邊停著一輛發(fā)動(dòng)機(jī)在夜里起了火的小轎車(chē),車(chē)主和保險(xiǎn)公司的人圍著它大聲地爭(zhēng)論著什么。回來(lái)的時(shí)候車(chē)卻不見(jiàn)了,地上只留下了一塊燒焦的深色痕跡。一片四方形淺一些的區(qū)域,勾勒出車(chē)頭原先的輪廓。我描摹著深夜里那場(chǎng)隱秘的燃燒,提著袋子在原處發(fā)了一會(huì)兒呆,什么都沒(méi)想出來(lái),慢慢地走回去了。
那天晚上我們凍了冰塊,兌進(jìn)啤酒里喝,相互依偎著,枕在同一個(gè)枕頭上絮絮地說(shuō)著話(huà)。
她說(shuō):“我小時(shí)候第一次坐火車(chē),興奮得整個(gè)晚上沒(méi)睡著,一直把腦袋伸到窗簾里頭去看外面的風(fēng)景。后來(lái)經(jīng)常跟母親一起坐火車(chē),就開(kāi)始斤斤計(jì)較為什么不能再早一點(diǎn)到達(dá),為什么不能少晚點(diǎn)幾個(gè)小時(shí)。橘紅色的路燈還在,可是看不見(jiàn)了。”
我仰著頭看著天花板角落里結(jié)出的蛛網(wǎng),她靜了一會(huì)兒,摸索著握住了我的手。而那一個(gè)動(dòng)作,激起的反應(yīng)竟然不適。像是左手握左手,自然而然地,有一種無(wú)所適從的排斥。
“小的時(shí)候不喜歡數(shù)學(xué)課,被逼著去補(bǔ)習(xí)奧數(shù)。我媽問(wèn)我,你要不要去上這個(gè)課?我說(shuō)不要。她也沒(méi)說(shuō)什么,隔天就拿了本奧數(shù)練習(xí)冊(cè)回來(lái),讓我寫(xiě)。寫(xiě)不出來(lái)就不能做別的事情,只能聽(tīng)她講奧數(shù)題。她一道題要講十分鐘,講完了問(wèn),你看懂了嗎?我說(shuō)懂了,就讓我復(fù)述。說(shuō)不出來(lái),她就重新講一遍。她就這么坐在電腦房的椅子上,我站著聽(tīng)她講,燈光都是白晃晃的,腿都要站得麻掉,時(shí)間卻仿佛一直凝固著。”
“高中的有段時(shí)間,我不斷跟她吵架。有一次我把神經(jīng)癥的確診病歷拍到她面前,那是吵得最嚴(yán)重的一次,她一邊流著淚一邊對(duì)我吼,我給了你這么多,你什么都不想要,也不說(shuō)究竟想要什么。你究竟想要什么!”
“那差不多是我們最后一次吵架,后來(lái)學(xué)校開(kāi)家長(zhǎng)會(huì),我陪她走到學(xué)校去。她忽然問(wèn)我,病歷上開(kāi)的藥,你要買(mǎi)嗎。我過(guò)了一會(huì)才說(shuō),不要。她沒(méi)再說(shuō)什么,就這么走到了校門(mén)口。她跟我說(shuō),回去的時(shí)候注意安全。我的眼淚忽然就掉下來(lái)了。”
“嗯。”
“空調(diào)的溫度好像太低了。”
“……”
可是她已經(jīng)睡著了,蓋著過(guò)膝的空調(diào)被,迷迷糊糊地發(fā)出了一聲短促的敷衍。我爬起來(lái)想去摸地板上的空調(diào)遙控器,牽動(dòng)了被她捏著的手,竟然很輕易地就抽出來(lái)了。我關(guān)掉空調(diào),從雜物柜里翻出了另一條空調(diào)被蓋著,躺到她身邊,慢慢睡著了。
后半夜,火車(chē)減速停了下來(lái)。我睡不安穩(wěn),干脆從床鋪上下來(lái),對(duì)著窗外流動(dòng)的黑影發(fā)呆。這種時(shí)候竟然也有別人醒著,經(jīng)過(guò)我身邊的時(shí)候慢慢從煙盒里抖出一根煙,看著我說(shuō):“要嗎?”我看著他,搖了搖頭。他便從我旁邊的過(guò)道過(guò)去了。
我看了一會(huì)兒,站起來(lái),也朝抽煙口走過(guò)去。他竟然還在,抽煙口彌漫著一股淡掉了的煙味。
“能給我一根嗎?”
他有些吃驚地看了我一眼,從上衣口袋里翻出煙盒,抽出了一支煙和打火機(jī),然后稍微挪出了一點(diǎn)位置給我。我謝過(guò)他,點(diǎn)著了煙,深深吸了一口,然后朝著窗口一點(diǎn)點(diǎn)地吐出來(lái)。將煙捏在手里,也并沒(méi)有吸第二口的意思。
“年輕人不要抽煙,對(duì)身體不好。”
“嗯。”
他又找了話(huà)題:“我女兒和你差不多大。”
我興味缺缺,斷斷續(xù)續(xù)地接了幾句,便沒(méi)再說(shuō)話(huà)了。后來(lái)他也回去了。我蹲了一會(huì)兒,聽(tīng)見(jiàn)“吱呀”的一聲,火車(chē)在一聲綿長(zhǎng)的口哨后,慢慢地發(fā)動(dòng)起來(lái)。樹(shù)影開(kāi)始流動(dòng),死寂的深夜?jié)u漸有了規(guī)律的哐哐當(dāng)當(dāng)?shù)穆曇簟T谝?guī)律的嘈雜后,心底竟然溫溫吞吞地安靜下來(lái)。
送小蕁回北方的時(shí)候還是夏天,同一班列車(chē),從南至北貫穿了大半個(gè)中國(guó)。她在武漢下車(chē),車(chē)廂里的冷氣開(kāi)得昏昏沉沉。我倦意連天,打著哈欠,不時(shí)陪她到站臺(tái)上買(mǎi)一些飲用水和消磨時(shí)間的零嘴。她把裝水的袋子抱在懷里,小聲說(shuō)著在我睡著的時(shí)間里她看見(jiàn)的沿途風(fēng)景。其實(shí)那只是些掠影匆匆的山和樹(shù),一閃即逝的漁火,還有些橘紅色路燈的街道。
“對(duì)廣東人來(lái)說(shuō),兩廣、福建以北的都叫北方?”
“嗯。”
“我在雜志社實(shí)習(xí)那會(huì)兒,做校對(duì)的時(shí)候,看見(jiàn)編輯把一個(gè)河南人說(shuō)成‘生在北方’。我去跟他說(shuō),河南怎么能算北方呢?他說(shuō),河南冬天那么冷,怎么不是北方呢。我心里忽然變得很難過(guò),眼淚都涌上來(lái)了,也不知道為什么。”
“……”
掛在兩排臥鋪包廂間的電視屏幕不知道什么時(shí)候開(kāi)了,嗡嗡地放著廣告。我睡在最上面,明明暗暗的屏幕光非常晃眼,伸出手摸了幾下想把它關(guān)掉,卻沒(méi)有找到開(kāi)關(guān)。我心煩意亂,打開(kāi)一瓶礦泉水,坐到小蕁的對(duì)面,把頭倚在窗邊的白色窗紗上,眼里是窗外連綿起伏的山,過(guò)不久昏昏睡去。
我做了一個(gè)夢(mèng)。夢(mèng)里我們還停留在暑假里,生活無(wú)限循環(huán),仿佛可以就此這樣下去。我們終日地沉眠,抱在一起像樹(shù)熊一樣從清晨睡到下午。睡醒了趴在沙發(fā)上看漫畫(huà),澆花,翻出冰箱里剩余的食材燉成混亂的湯。食材一日日浪費(fèi)殆盡,就牽著手去超市買(mǎi)回新的食材,一袋袋地塞進(jìn)冰箱里。再一日日地取出袋中的肉、蔬菜、燉湯的輔料,最后剩下一只只結(jié)實(shí)透明的塑料袋,隨手塞到冰箱旁的空余儲(chǔ)物柜里,雜亂無(wú)章地放置起來(lái)。
那時(shí)候超市的塑膠袋已經(jīng)開(kāi)始收費(fèi)。我們常用的大號(hào)塑膠袋兩毛一只,后來(lái)漲到了三毛一只,因此我們總要帶上一些零錢(qián)去超市。偶爾忘了帶,誰(shuí)也不想要找回來(lái)的零票,懷里抱滿(mǎn)了分裝的肉、熟食和蔬果。有些溫?zé)幔行е鶝龅睦淠椤O嗷ネ泼撻_(kāi)門(mén)的責(zé)任,直到最終站在門(mén)前。我說(shuō):“你幫我拿著,我來(lái)開(kāi)門(mén)。”
她說(shuō):“我拿不下了,放到地上吧。”
門(mén)不知道是誰(shuí)打開(kāi)的,窗戶(hù)出門(mén)的時(shí)候沒(méi)關(guān),餐桌上落著幾片油綠的葉。
我睡得很晚,第二天的中午時(shí)分才醒過(guò)來(lái)。車(chē)廂里的人已經(jīng)陸續(xù)地收拾好了行李箱準(zhǔn)備下車(chē),因?yàn)榇哼\(yùn)客流高峰的緣故,到站時(shí)間推遲了三個(gè)小時(shí),大約要到傍晚的時(shí)候才能到武漢。
這節(jié)車(chē)廂里的乘客也大多都是要在武漢下的。從一號(hào)到十號(hào)臥鋪,桌子上擺著某某旅行社的紅色團(tuán)帽,有些則已經(jīng)被戴上去了。導(dǎo)游打開(kāi)了擴(kuò)音器,在叮囑些最后的下車(chē)注意事項(xiàng)。別的小隔間里,游客用的大多也是與普通話(huà)語(yǔ)調(diào)相近的湖北話(huà)在交流。他們說(shuō)得快了些,其實(shí)我聽(tīng)得也不是很懂,只能隱約辨別出幾個(gè)“襪子”、“舅舅”之類(lèi)沒(méi)有太大意義的詞,猜不出語(yǔ)義。
我送小蕁回武漢的時(shí)候,夏天還未完全過(guò)去,開(kāi)著冷氣的出租車(chē)?yán)锏淖鴫|還冒著滾燙的熱氣。有一天下午好不容易下了點(diǎn)毛毛雨,天是陰的,但地上還嘶嘶地冒著熱氣。出來(lái)的時(shí)候記得去吃一碗熱干面,店主錯(cuò)放了辣,沒(méi)好意思指正,只好一邊大口呼著氣一邊慢慢地吃。最后還是沒(méi)堅(jiān)持下來(lái),只吃了不多的一點(diǎn),付了錢(qián)離開(kāi)。
她打來(lái)電話(huà)說(shuō):“去黃鶴樓嘛,你一直沒(méi)去過(guò)。”這時(shí)候她母親在電話(huà)的另一端招呼了她一聲,她用武漢話(huà)答了兩句。我聽(tīng)不懂她們的一應(yīng)一答的對(duì)白,耐著心等著。她又切回來(lái),換了普通話(huà)繼續(xù)跟我說(shuō):“也許明天就出太陽(yáng)了呢。”
我說(shuō):“噢。”
她說(shuō):“那你等等,我過(guò)去接你。”
雨淅淅瀝瀝地下大了,公交車(chē)外面其實(shí)已經(jīng)是一片水霧了。我看不清窗外的景象,明晃晃的一片深綠色不斷地落到后面去,透著石灰水的輕微的灰白色。在某一條不知名的公路上,因?yàn)閺澋赖膽T性,我的右手碰到了她順勢(shì)下滑的左手。她并沒(méi)有縮回去,但同樣的,也并沒(méi)有更多的動(dòng)作。我注意到她有些尷尬地,想要不動(dòng)聲色將它抽回去。她最終做到了,現(xiàn)在它溫順地蜷在她的大腿上。
“剛到Z城的時(shí)候,”她說(shuō),“有一次去菜市場(chǎng)買(mǎi)菜,我用那種口音很正的普通話(huà)跟他們說(shuō),白菜多少錢(qián)。菜販說(shuō),三塊錢(qián)。我有點(diǎn)吃驚,以為這里的菜價(jià)貴,但也只好付錢(qián)了。結(jié)果我才轉(zhuǎn)身,他就賣(mài)給另一個(gè)本地口音很重的男人一斤白菜,男人就給了他一塊錢(qián)。當(dāng)時(shí)我差點(diǎn)就沖上去了,但知道沒(méi)用,什么也沒(méi)做。”
我將目光移開(kāi),感覺(jué)到所有突如其來(lái)的尷尬與不適漸漸轉(zhuǎn)化為悲哀,也只能裝作沒(méi)有注意到這些細(xì)節(jié)。其實(shí)那時(shí)候我們已經(jīng)很久沒(méi)有做愛(ài),接吻也慢慢變?yōu)閼?yīng)付公事般的潦草功課。我有一次突如其來(lái)想要深吻,她只是稍微地偏了一下臉就躲了過(guò)去,說(shuō),你不要這樣。
我看不見(jiàn)她的表情,也完全辨別不清自己的感受。我們只是默默地躺在床上,面朝天花板,無(wú)聲地睜大著眼睛,了無(wú)睡意。過(guò)了一會(huì)兒,她撐著身子從床上起來(lái),說(shuō),我去倒杯水。她徑直地開(kāi)了門(mén)出去,我聽(tīng)見(jiàn)打火機(jī)咔嚓的聲音,過(guò)后又是一片壓抑的沉默。
我漸漸地陷入了睡意中,過(guò)了不知多久才隱約聽(tīng)見(jiàn)她用鑰匙開(kāi)門(mén)的窸窣聲。她把煙放到床頭柜上,爬到我身邊蜷縮起來(lái),背對(duì)著我,到此為止便沒(méi)有了剩下的記憶。第二天醒來(lái)的時(shí)候,我側(cè)著身面對(duì)著墻壁,將被子團(tuán)成一團(tuán)緊緊抱在懷中。我們像兩只不再坦誠(chéng)相待的刺猬,背靠著背,只能漸漸地,越來(lái)越疏離。
要下車(chē)的時(shí)候,車(chē)廂里的人已稀疏了。隔三岔五地才能見(jiàn)到一只佇在地上的旅行箱和三五疊放在下鋪床上的提包。在這站下去,連乘務(wù)員都要換下一半,提著壺去裝開(kāi)水時(shí)看見(jiàn)乘務(wù)室里打包好的一只提包,心底一絲絲地拔涼。
走到門(mén)口時(shí)倒是意外地遇見(jiàn)了之前的大叔。他哐哐當(dāng)當(dāng)?shù)匕研欣钕淅介T(mén)口的時(shí)候,我搭了把手幫他提著旅行包。他順其自然搭了句話(huà):“小姑娘也是到武漢去?”
我說(shuō):“啊。”
他問(wèn):“回來(lái)過(guò)年的?”
我對(duì)這樣接踵而至的問(wèn)題無(wú)所適從,又想了想,不愿繼續(xù)這個(gè)話(huà)題,于是點(diǎn)了點(diǎn)頭,算作默認(rèn)。他兀自開(kāi)始感慨,零零散散夾雜著一些女孩子外出謀生的不易,興許是源自于切身的體悟,像對(duì)著自己的女兒,言語(yǔ)間有了長(zhǎng)輩式的溫情。我假裝不在意,余光卻時(shí)不時(shí)地掃到他的神情,也竟然可以如此陶醉其中。這么想著,心里竟然有些柔軟起來(lái)。
火車(chē)漸漸靠站,我心神不寧,于是回去提了袋子,同他一起站在下車(chē)隊(duì)列的最前端等待。聽(tīng)見(jiàn)排氣的聲音,應(yīng)該是停下來(lái)了。我竟然有些想要退縮。我在心里構(gòu)思著繞一個(gè)最短的路程,到售票廳去,買(mǎi)一張最近的火車(chē)票到全國(guó)各地任何一個(gè)城市去,然后回家,或者繼續(xù)走下去。
但是這個(gè)時(shí)候小蕁跳上了車(chē)。近兩年翻新的武昌站已經(jīng)不再需要老式的扶梯,所以在列車(chē)緩緩?fù)7€(wěn)后,隨著車(chē)門(mén)的開(kāi)啟,一陣短促的腳步后,我們打了個(gè)短暫的照面。就在那一個(gè)短促的照面間,我看見(jiàn)了她新剪了短發(fā)的模樣,細(xì)碎的滴水溫順地垂在耳邊。于是我說(shuō)……
但我最終還是啞口無(wú)言。身后隱約聽(tīng)見(jiàn)她喊爸的聲音,于是我記起來(lái)那年電話(huà)里男人的聲音,說(shuō),我女兒要結(jié)婚了,你們這些狐朋狗友就不要跟她往來(lái)……而最后連說(shuō)出來(lái)的機(jī)會(huì)竟然也沒(méi)給我,嘟嘟兩聲,電話(huà)就隨著一句尖銳的“爸——”被掛斷了。我手里捧著電話(huà),心底一片靜悄悄的荒涼。
而這荒涼竟然也逐漸散開(kāi)了。一列列到站的列車(chē),春運(yùn)時(shí)交替的客流,摩肩接踵,擦肩而過(guò)。就好像異鄉(xiāng)的人流永遠(yuǎn)不在意他鄉(xiāng)人的感受,鬧鬧哄哄的,一切又沒(méi)影了。我最終還是沒(méi)買(mǎi)到回程的車(chē)票,在武漢訂了家快捷旅店住下來(lái)。大年初一的時(shí)候,收到了小蕁的短信。
“新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