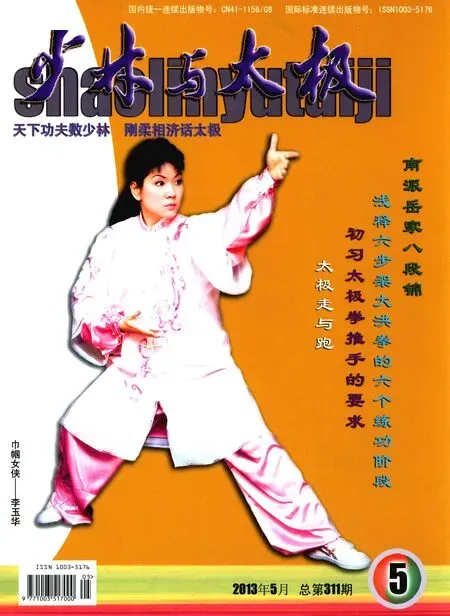龍刺
文/岳 勇
龍刺
文/岳 勇

第七章 惺惺相惜
“噗”的一聲,火光一暗,又有一支火把燃燒殆盡,終于一閃而滅。筏子上,已只剩下最后一支備用的火把,還在一閃一閃地燃燒著,發出半明不滅的火光,照亮著前方十余丈遠的河面。
一名正在撐篙的“龍刺”急道:“這最后一支火把也快燒到盡頭了,怎么辦?如果沒有火把照明,在這黑咕隆冬的地下河道里航行,一旦撞上石壁,人仰筏翻,那可就糟了。”
拓跋猗也意識到情況不妙,正自皺眉無計,忽見野利仁手指前方,嚷道:“快看——”
拓跋猗急忙執起火把,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卻見前方百十丈開外,頭頂的鐘乳穹壁忽然矮了下來,呈坡狀斜斜插入水面,一眼看去好像河道已到盡頭,前方只有石壁,再也無路可行。
野利仁道:“老二,這可怎么辦?原來這地下河道竟是一個死胡同,根本行不通的。再往前去,咱們的筏子可就要撞上那石壁了。”
拓跋猗目視前方,仔細觀察著前面的河道,道:“沉住氣,別慌,如果這真是一個死胡同,那自上游源源不斷流下來的河水,又是自哪里冒出來的?兄弟們,把筏子劃近點,讓我看看清楚。”
四名撐篙的“龍刺”一齊用力,木筏向前一躥,又前行了十數丈。拓跋猗將火把舉過頭頂,極目望去,忽然喜道:“看,河水是自那石壁下流出的,如果我所料不錯,那石壁下面,必有洞穴出口,而且河水流量如此之大,那出口必定不小。”
待筏子又向前劃出數十丈,眾人果然都瞧見了,那河道盡頭的石壁下面,水聲嘩啦啦作響,正有大量河水汩汩向外冒出。河水白晃晃的,似乎有光自河底透出來。
拓跋猗喜道:“那石壁下面有個大洞,河水便是從那洞中涌進來的。咱們已在這地下河道里航行了近十個時辰,根據行程計算,應該已從橫山腹地來到了山腳邊沿,那洞穴必然與外面的河流相通,咱們只要自那洞穴中潛出,就可以到達山外的無定河了。”
野利仁不由睜大了眼睛,道:“難怪這條地下暗河與山南山北兩河相連,卻沒有人發現,原來暗河兩端的出入口都潛藏在水底深處。”
拓跋猗突然躍到木筏邊沿,奪過兩根竹篙:“老三,接著!”手臂一振,拋過一根竹篙給野利仁。野利仁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接過竹篙道:“好,下面就看咱們的了。”兩人已經休息了大半日時間,氣力早已完全恢復,值此關頭自是全力以赴,兩根竹篙往河底一撐,筏子猛然一震,劃開水面,宛如離弦之箭向前駛去,一瞬之間就已行到河道盡頭的石壁下。
拓跋猗拔出腰間長劍,嗖嗖聲中,盡數挑開狄青等三十三名宋將身上的藤索,又解開他們臉上的蒙眼布條,道:“前面已到出口,請狄將軍與諸位鐵血營的兄弟,和咱們一起自那水底通道潛出去。”又對野利仁道:“我在前探路,你跟兄弟們在后面護著狄將軍他們,咱們大伙一起出去,千萬不能落下一個人。”
野利仁知道他是怕狄青等人雖然解開了藤索和蒙眼布,但身上仍有幾處大穴被封,真力不繼,萬一在水中出現危險無法自救,所以才囑他相護,當下點頭道:“二哥放心,老三明白。”
見眾人都已準備妥當,兩人將手中竹篙往河底用力一撐,長長的竹篙先是一彎,緊接著猛然彈直,木筏受巨力推動,閃電般向前一沖,砰的一聲撞在前頭石壁上,頓時竹釘松動,藤索斷裂,數十根木頭四散漂開,順水流走。
就在木筏撞上石壁前的那一剎那,拓跋猗大喝一聲:“走!”眾人張開嘴巴,猛然吸口大氣,一個魚躍,齊齊跳入水中。
河水冰冷刺骨,灌進衣服里來,大伙忍不住激靈靈打了個寒戰。好在河水雖冷,卻還清澈,睜開眼睛能看清兩三丈外的水底事物。眾人在水中略作調整,便在拓跋猗的引領下,一齊向那透光的河底洞穴潛游過去。
那洞穴隱隱透著白光,在水面上看來,仿佛近在咫尺,但真正身處水中潛行過去的時候,卻發現相距自己入水的地方竟有十數丈之距。
眾人迎著迎面噴涌而來的河水,吃力地向前潛行。野利仁走在最后面,發現有誰被急涌的河水沖出了隊伍,便立即上前拉上一把。好不容易才接近到洞口,欲往那洞中鉆去,卻不料越接近洞口,河水的沖擊力越大,剛至洞口便被疾涌的河水沖了開去,連試數次皆不得過。
眾人雖然陸上功夫了得,但水性卻很一般,能在水下潛行全憑一口真氣懸著。“龍刺”等人尚好,狄青等一眾宋將穴道被封,真力不繼,在水中潛得半炷香的工夫,便覺眼冒金星,胸口憋著一口濁氣,幾乎要爆炸開來。
那醫官實在憋不住了,張嘴欲喘,誰知嘴巴一張,河水便毫不留情直灌進來,嗆得他直翻白眼。拓跋猗回身瞧見,情知不妙,用手托住那醫官后腰,向著大伙把手朝上一指。眾人心領神會,跟著他掉頭游回去,箭一般躥出水面,大口喘氣。
野利仁抹抹臉上的水花,吐了口唾沫道:“二哥,咱們在水中潛行還行,可一到洞口,洪水暴涌而入,要平衡身體、讓自己不被急流沖走都十分困難,就更別說自那洞口逆水鉆出去了。都到這個關口了,卻沖不出去,這可怎么辦?”
拓跋猗點頭道:“是呀,洞口水流湍急,根本不可能迎著水流鉆過洞去。讓我想想,看有沒有其他法子。”四下里瞧瞧,河中除了凹凸不平的石壁,再無其他,忽然心中一動,道:“咱們不能正對著那洞口行進,那樣的話,河水暴涌,沖擊的力量太大,一不小心就會被沖出好遠。咱們應該避其鋒芒,自洞口兩側水流較緩處潛近,雙手攀著石壁上突起的巖石,穩打穩扎,一步一步自那洞穴中走出去。”
他這幾句話是用漢語說的,眾人都聽得明白。狄青吐出口中濁水,道:“這個主意不錯,值得一試。”
眾人稍歇片刻,又深深吸了口氣,左右分開,分做兩隊,沿洞穴兩邊再次潛下。一入水底,河水自山外暴涌而入,又險些將大伙沖散。拓跋猗打個手勢,眾人急忙靠近石壁,手攀巖壁,先穩住身體,再手足齊用,一步一步朝那洞口靠近。
潛行不遠,水勢突變,一股潛流自背后反涌回來,竟一下將眾人向前推進了數丈距離。原來那洞穴出口頗大,約有數十丈方圓,洞中河水暴涌進來,沖擊正中,兩側卻各形成一股回旋的水流,正好把大伙輕而易舉地送到洞邊。
眾人憋著一口氣,定定神,跟著拓跋猗一起,雙手抓牢洞壁上的石頭,迎著那股急劇涌進的水流,一步一步,往洞中鉆去。
入到洞穴中,因有拓跋猗在前擋住水流,水勢往兩邊分流,后面眾人反覺阻力較小,行動反而更加迅速。卻只是苦了拓跋猗,他一馬當先走在前面,洪水襲來首當其沖,臉上被急流撞得隱隱生痛,身上的衣衫也被流水撕裂,一片一片漂了開去。
在拓跋猗的帶領下,一行人連攀帶爬,終于出得洞來,正暗自松下口氣,不想洞外水流更是湍急,而且在洞口形成一個巨大的旋渦,攪得眾人團團亂轉,像是那漏斗形的旋渦中隱藏著一只無形巨手,拼命把眾人又朝那洞穴中倒拖回去似的。
眾人大驚,急忙往旋渦外掙扎,可是那旋渦速度奇快,力量奇大,竟將眾人深深吸引住,越往外掙扎陷得越深,只一會兒眾人便被轉得頭昏目眩,分不清東南西北了。眾人張嘴欲叫,河水倒灌入口。眾人嗆了幾口水,雙手雙腳亂劃亂蹬,腦海中嗡嗡作響,卻已漸漸失去知覺……
烈日當頭,晃得人眼睛生疼。
不知昏迷了多久,拓跋猗猛然睜開眼睛,發現自己衣衫碎裂,渾身濕漉漉的,正躺在山腳下一條大河邊的沙灘上,半截褲腳還浸在水中,光著兩個腳板,一雙靴子早已不知去向。
他皺皺眉頭,想起自己昏迷之前發生的事,頓時一驚而起,四下一瞧,卻見空曠的沙灘上,“龍刺”和數十名宋將,就像擱淺的魚似的,橫七豎八地躺在沙地上,任由河水拍打、烈日暴曬,卻一動不動,宛如死尸一般。
他不由心頭一沉,拽了一下身邊的野利仁。野利仁咳了一聲,肚中咕嘟作響,猛然張開嘴巴噴出幾口濁水,這才漸漸緩過氣來,翻身坐起,茫然地瞧著他:“老二,怎么了?”
拓跋猗這才松下口氣,道:“咱們潛出那水底洞穴之后,被那旋渦轉暈,胡亂撲騰,反倒被河水沖到了岸邊。快去看看其他人怎么樣了。”
野利仁爬起身,逐個看過去。還好,大家都只是被水嗆暈過去,并無大礙,被他在肚子上踩上兩腳,噴出幾口濁水,也就清醒過來了。再一點人數,九名“龍刺”與三十三名宋將,一個不少都出來了。
拓跋猗一屁股坐在沙地上,正要喘口氣,野利仁卻突然跳了起來,一面四下看著,一面搖頭大叫:“不對不對。”
拓跋猗皺眉問:“有什么不對?”
野利仁道:“這地方不對。”
拓跋猗怔了一下,這才注意查看四周環境,但見近處的河流山巒,遠處的城郭景致,都是那么陌生。他敢肯定,這絕不是他所熟悉的橫山北麓夏國地界的風景。那么這里是……
他心中一個念頭尚未轉過,就聽得遠遠的有人呼喝道:“呔,什么人在那河邊?”說的卻是漢語。拓跋猗扭頭望去,卻見遠遠的大路邊塵沙揚起,一隊騎兵正向這河灘疾馳而來。
拓跋猗手搭涼棚,遮住刺目的陽光,定睛看去,只見那隊騎兵約有一百來人,皆胯乘甲馬,肩披鎖子甲,腰懸弓箭,甚是英武,卻并不是夏國軍士的裝扮。
他不由臉色大變,驚道:“那是宋軍,咱們走錯了方向,這里是大宋國境。”
野利仁差點跳了起來:“什么,這里是宋國?怎么會這樣,老王爺不是說逆水而上,就能抵達夏國么,怎么……”
拓跋猗略略一想,便已明白過來,嘆口氣道:“倒不是王爺有意說錯。他發現這條地下水道的時候,河水是由北往南流的,那時逆水而上,確實能直抵夏國。但他卻不知這條地下暗河的流向,是隨兩端連接的河流的水位高低而變化著的。當北方雨季時節,橫山北麓夏國境內的無定河河水暴漲,水位比南邊的里水河高,所以地下河道里的水就是由北往南流的。而現在正值南方多雨時節,橫山南麓宋國境內的里水河水位超過北邊的無定河,地下河道里的水自然就會由南往北流。王爺只在三十年前觀察過那條地下暗河的水勢流向,被‘風隱者’軟禁之后便再未離開過那山洞半步,自然不知其中的變化。”
說話之間,那隊騎兵已風馳電掣般奔至近前,眾人舉目望去,果然是一隊宋軍。宋軍騎兵潑喇喇涌上來,四面散開,將眾人團團圍住,人人端弓搭箭,向中間瞄準。
那領頭的騎兵隊長一眼瞧見狄青,不由一怔,問:“這不是狄將軍么?”
狄青站出來微微一笑,道:“正是狄青在此。”
那騎兵隊長在宋軍中的職銜,遠比狄青要低,一見果然是他,神情一肅,急忙跳下馬來,伏身拜倒,行了一個軍禮。狄青上前將他扶起,道:“不必多禮。”
那騎兵隊長瞧清形勢,急令手下將被圍在中間的宋軍醫官及三十一名鐵血精騎放出來,指著拓跋猗等九名作夏軍裝扮、不明身份的人問:“狄將軍,他們是……”
狄青回頭瞧了一眼,道:“他們就是夏國鼎鼎大名的‘龍刺’。”
騎兵們一聽“龍刺”這兩個字,立時如臨大敵,拉緊弓弦,一齊對準“龍刺”。
野利仁等人臉色一變,嗆啷啷拔出兵器,就要上前硬拼。拓跋猗把臉一沉,喝道:“老三,別沖動。我可不想兄弟們都被射成刺猬。”眾人不由一呆,知道敵眾我寡,力量懸殊,若真的動起手來,縱能殺得了幾個宋軍,也無法抵擋住從四面八方射來的箭雨,悻悻地瞧了宋軍一眼,只得還刀入鞘。
那名騎兵隊長見“龍刺”放棄抵抗,松了口氣,喝道:“韓元帥正在綏德城中視察軍情,把他們全都押回去,交由元帥處理。”又轉頭瞧著狄青,詢問:“狄將軍,你意下如何?”
狄青朝不遠處的城郭望了一眼,點頭道:“既然元帥就在左近,自然應該交給元帥發落。”
騎兵隊長道聲:“是。”一揮手,一隊騎兵仍然端弓搭箭對準“龍刺”,另一隊人馬卻手提繩索一擁而上,將拓跋猗等人按倒在地,反轉雙手,捆了個嚴嚴實實。
綏德城,離橫山南麓僅三十余里,為宋夏邊境一座重要的軍事重鎮,宋國在此增設綏德軍,統轄米脂、懷寧、克戎、臨夏、永寧關等十城兵馬。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本來坐鎮延安,總領西北軍務,這一日正好在綏德城中督察軍務。
天色漸晚,一輪孤月高懸天際。
綏德城大校場內,宋兵環列,劍戟森森,當中燃燒著三堆熊熊大火,火堆上架著三口大鐵鍋,鍋里是滾滾翻騰的青油。高高的臺階上擺著一張虎皮大椅,中間坐著一位年過半百、身形微微發福的大將,身披戰袍,長須及胸,虎目生威,極是威嚴。這便是宋軍元帥韓琦。狄青及那三十一名自橫山生還的鐵血精騎早已換了裝束,腰懸兵刃,背負雙手,環立在韓琦身后。
拓跋猗等九名“龍刺”被五花大綁著,剛被推進校場,就立即感覺到了籠罩在校場里的那股濃烈的殺氣。
二十四級高的臺階上,韓琦虎目一睜,居高臨下地掃了一眼,問:“堂下何人?”
拓跋猗不卑不亢地道:“大夏國‘龍刺’,拓跋猗。”
韓琦聽到“龍刺”二字,眼中殺機一閃:“拓跋猗,看見眼前那三口油鍋了嗎?”
拓跋猗道:“看見了。”
韓琦道:“從現在開始,本帥問你什么,你就老老實實回答什么,若有半句隱瞞,本帥便立即將你丟進這滾燙的油鍋。你可聽明白了?”
拓跋猗“哼”了一聲。
韓琦身子朝前一傾,虎目中精光閃動,向他咄咄逼視過來:“聽說你們‘龍刺’找到了那條傳說中能橫穿橫山山脈的秘徑,是么?”
拓跋猗冷冷地道:“是。”
韓琦道:“這次你們從橫山中出來,走的就是這條捷徑,是么?”
拓跋猗道:“是。”
韓琦忽然回過頭去,瞧了狄青一眼,又緩緩扭過頭來,目光釘子一樣落在拓跋猗臉上:“狄將軍和這三十一名鐵血營的兄弟,雖然是跟你們走在一起,但這一路上他們的眼睛被蒙上了,什么也看不見,所以并不知道那條秘徑的具體位置。說到底,其中的秘密,只有你們九個人才清楚,是不是這樣?”
拓跋猗抬眼朝狄青望去,卻見狄青在臺階上也正朝他望來,兩人目光一交,拓跋猗忽然明白過來,心中一陣感激,又把目光轉向韓琦:“確實是這樣,除了咱們‘龍刺’這九個人,再也沒有第十個人知道這秘徑的所在。”
韓琦盯著他道:“很好。那本帥現在問你,那條秘徑究竟在什么地方?”
拓跋猗道:“在山上,在橫山上。”
韓琦臉色一沉,道:“在橫山上的什么地方?”
拓跋猗直盯著他的兩只眼睛,毫無畏懼地與他對視半晌,忽然微微一笑,道:“你的油鍋燒熱了么?在下可等得有些不耐煩了。”
韓琦臉色一變,神情難看至極:“你的意思是,寧肯下油鍋,也絕不將那秘徑的具體位置說出來,是么?”
拓跋猗昂首道:“是。”
“好!”韓琦忽然長身立起,“本帥相信,你不說自有其他人會說出來的。既然你自己想下油鍋,本帥便成全你。來人,將這位大夏國的拓跋將軍丟進油鍋。”
話音未落,早有四名如狼似虎的刀斧手一擁上前,將他抬起,直往那滾滾翻騰的油鍋邊走去。
野利仁雙目怒瞪,幾乎噴出火來,叫聲:“二哥!”就要沖上前來,卻被兩名宋軍死死按住。拓跋猗回過頭來,剛毅的目光在眾位兄弟臉上一一掠過:“好兄弟,咱們來世還做兄弟!”
眾人眼眶一紅,一齊點頭,誰也沒有開口說話,只將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韓琦在臺階上頗不耐煩地揮揮手,四名刀斧手手臂一撐,竟將拓跋猗高舉起,大步走到油鍋邊,正要用力將他往那滾燙的油鍋中扔去,忽然聽得一聲大喝:“且慢!”說話的,卻是狄青。
狄青大步跨出,走到韓琦跟前,拱手道:“元帥,這拓跋猗乃是夏帝曩霄身邊的心腹大將,曩霄對我中原虎視眈眈,久有南侵之意,只因兩國修好多年,苦無借口毀約出兵。值此一觸即發的關鍵時刻,咱們如果斬殺夏國大將,只怕正好遺人口實,給了曩霄出兵開戰的絕好理由。”
韓琦眼皮一抬,瞧著他道:“你的意思是叫本帥放了他們,主動向曩霄示好,是不是?”
狄青忙低頭垂首,道:“屬下不敢,屬下只是提醒元帥要三思而行。”
韓琦目光一閃,仿佛要盯到他心里去:“本帥看來,只怕是你自己想救他們吧?”
狄青臉色微變,道:“元帥明察秋毫,屬下不敢有絲毫隱瞞。在橫山深處,曾經有人要殺屬下等人,是拓跋猗一句話,救了屬下等三十三個人的命。知恩不報,實非大丈夫所為。所以屬下斗膽請元帥放他們九個人一條生路。至于那條秘道,屬下略略聽得懂幾句黨項話,從他們的交談中已獲知其大概位置,相信只要屬下帶領鐵血營的兄弟再上山一趟,總能找得到。”
韓琦沉下臉來,眼中殺機一閃,道:“本帥如果一定要殺他們呢?”
狄青臉色蒼白,沉聲道:“那屬下就只好對元帥無禮了。”鋼牙一咬,突然躥上幾級臺階,一道冷光自衣袖中閃出,一柄尺余長的短劍已抵近韓琦咽喉。
韓琦臉色突變,頓時僵在虎皮大椅上,瞪著他道:“狄青,你想造反么?”
狄青冷聲道:“屬下不敢,屬下只是不想欠‘龍刺’的人情。假若他日宋夏交兵,屬下定當于兩軍陣前,親斬拓跋猗的人頭來見您。”
韓琦臉色鐵青,咬緊牙關道:“如果本帥不放他們呢?”
狄青道:“那就莫怪屬下冒犯了元帥。”手臂輕輕朝前一遞,劍尖頓時刺入韓琦頸上肌膚,一縷鮮血沿著他的脖頸流了下來。
韓琦本是文官出身,不比武將,用手一摸,滿頸是血,頓時臉色煞白,再也堅持不住,恨恨地瞧了狄青一眼,咬牙道:“好,本帥答應你,暫且放過他們九人。”
狄青并不撤劍,道:“請元帥即刻下令。”
韓琦瞧著“龍刺”,無奈地道:“好,拓跋猗,看在狄將軍的面子上,本帥且放爾等九人一條生路。限爾等一個時辰之內離開大宋國境,一個時辰之后,本帥再下令追擊,若再被本帥生擒,立即格殺。”
狄青對四名刀斧手喝道:“元帥已經下令放了他們,還不替他們松綁。”
四名刀斧手面露難色,一齊望向韓琦。韓琦略一點頭,四人這才放下拓跋猗,又利索地解開了九人身上的繩索。
拓跋猗仰頭看著狄青,沖著他略一點頭,忽然朗聲道:“狄將軍,我曾救過你和你一眾兄弟,此回你救了咱們兄弟,你我之間算是扯平了。他日戰場相見,我拓跋猗可不會對你手軟。”
狄青自然明白他說這話,旨在于韓琦跟前撇清與自己的關系,免得連累自己,不由苦笑一聲,只是繃著臉喝道:“少說廢話,拓跋猗,元帥既已答應放你們走,就絕不會食言。爾等只有一個時辰逃命,還不快走,更待何時?”
野利仁卻是個直人,不明白兩人間惺惺相惜之意,瞧著他問:“那你呢?”
狄青瞧了韓琦一眼,眼含敬意,苦笑一聲道:“狄某本是一個刺配充軍的罪犯,今日之所以能成為統領千軍的戰將,全賴韓帥一手栽培。韓帥于我,猶如再生父母。今日竟然以下犯上,執劍相迫,這宋軍營中,豈還有我狄青的立足之地。”
狄青凄然一笑,驀然回劍,劍鋒一閃,徑往自己頸間抹去。一抹鮮血濺出,人已倒在韓琦腳下。
眾人臉色大變,為之一呆。
韓琦蹲下身探他的鼻息,急忙大叫:“還有一絲氣息,快抬下去請醫官急救!”數名鐵血精騎擁上來,抬起倒在血泊中的狄青,急急退出校場。
“狄將軍……”拓跋猗大叫一聲,聲音已有些哽咽。
韓琦虎目一瞪:“還不快走,莫非是嫌本帥給你們的時間太過充裕?”
拓跋猗眼眶微紅,沖著狄青被人抬下去的方向遙遙抱拳一禮,領著八位“龍刺”兄弟,頭也不回大步而去。
瞧著九人的身影越去越遠,一名虬髯宋將忍不住站出來道:“元帥,難道真就這樣放他們走了?”
韓琦瞧著拓跋猗九人身影消失的方向,冷聲一笑:“世上哪有如此便宜之事。此處離宋夏邊界尚遠,他九人若想在一個時辰內逃離宋境,除了走那條秘道,別無他法。你快帶人跟蹤他們,一旦知道了秘徑之所在,便立即……”話至此處,忽然以手為刀,做了個殺人的動作。
虬髯宋將心領神會,道:“元帥放心,末將明白。”一拱手,領命而去。
第八章 尾聲
半個時辰后。
綏德城外十里遠的一處密林中,虬髯宋將找到了拓跋猗一行。只不過他找到的,只是九具尸體。
九名“龍刺”,每個人都拔出自己腰間的兵器,刺入了前面一人的胸口。九個人,被九件兵器連接起來,雖然已經氣絕,卻仍屹立不倒。九具站立的尸體,形成了一個極其詭異的陣勢。
虬髯宋將不由一呆,良久,才嘆口氣道:“原來他們早已識破元帥的計謀,寧愿死,也絕不肯泄露那條秘徑的位置。果然是一群好漢子!”
收檢尸體的時候,一個用獸皮縫制的信封自拓跋猗胸前的衣襟里掉了出來。拆開信封,里面是一封用指尖鮮血,一筆一筆寫在一張獸皮上的短信。信上盡是黨項文字,喚來懂黨項文的士兵譯成漢語,則內容如下:
嵬理吾兒:
為父尚在人間,勿念!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山中秘徑,可用于侵略殺人,亦可用作南北交往之通道。是殺人,還是救人,全在當權者一念之間也。
宋夏一旦開戰,死的是將士,苦的是百姓,無論是贏是輸,夏國必將大傷元氣,東北有契丹虎視,西南有吐蕃雄踞,若趁機來襲,汝將如何?
三十年來,吾日日自省,悟得為君之道不一定要開疆擴土、一統天下、四海賓服、八方來朝,能將一方小小土地治理得井然有序,國泰民安,亦可成為世人景仰、萬世稱頌的帝君。
是戰是和,望吾兒三思!
父:李德明
可惜的是,這封信永遠也送不到曩霄手中了。
不久之后,夏宋開戰,戰爭綿延百余年,雙方消耗無窮財力,軍民更是死傷無數……(8)(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