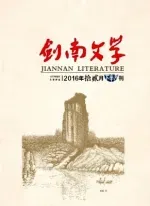杜甘反戰小說中的女性形象
■喻佩瑤
法蘭西民族崇尚自由。為了自由,他們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斗爭,尤其是在國家面臨危難、大敵當前的緊要關頭,英勇的法國人民奮起反抗,眾志成城,由此產生的反戰小說熠熠生輝,璀璨奪目,是法國現實主義小說最為重要的部分。
法國的反戰小說題材豐富,歷史悠久。回顧這些反戰小說,我們可以發現反戰小說的形式雖然在不斷地發生變化,但是現實主義小說的傳統從未中斷。20世紀末出現了一批優秀的反戰小說,其中馬爾克·杜甘的作品不多,但成就突出,其風格獨樹一幟,尤其引人注目。為了表達對在戰爭中負傷而毀容的祖父的敬意,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發表了視角獨特的處女作 《軍官病房》,前所未有地把毀容軍官這一特殊群體作為寫作題材,探索戰爭帶給個體從肉體到心理造成的巨大創傷。1998年這部小說在拉泰斯出版社出版,印了35萬冊,獲得了書商獎、尼米埃獎和雙猴獎等18項文學獎,還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并且被著名導演弗朗索瓦·杜貝隆搬上銀幕。這部影片入圍第54屆戛納電影節,“獲第27屆法國電影凱撒獎最佳影片、導演、男主角、男配角、攝影、服裝等八項提名,獲最佳男配角、最佳攝影獎”。總的來說,不管是小說還是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杜甘的第三本小說《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國》于2002年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更是一篇反戰杰作。小說描寫了一個普通青年的冒險經歷和感情生活,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反映了戰爭的殘酷和荒誕,表達了人們對戰爭的厭惡和對幸福生活的向往。“出版后,評論界大聲叫好,不少人甚至認為它肯定會贏得一項文學大獎”。或許這是因為這部作品觸及了“合作分子”這一敏感話題,引起了爭議,所以無緣法國文學獎。但是,“墻內開花墻外香”,這部小說獲得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聯合評選“2002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獎,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和好評。 “這是我第一次因為小說在國外獲獎!”,杜甘在來京領獎時說道。 “在領獎后致的答詞中,他動情地感謝中方授予他的這個獎項,使他能夠在將近40年后實現他舅舅的遺愿,完成這次他們都極為向往的旅行”。
一位蘇聯作家曾說: “戰爭讓女人走開”。戰爭的血腥和暴烈的確為柔弱的女性所不堪,但這就意味著戰爭完全是男人的事,與女性毫無關系嗎?答案是否定的,戰爭從未讓女人走開過。 “一次次的戰爭奪去了多少女性的生命?毀滅了多少女性的家庭?又有多少女性因為戰爭被迫拿起武器走向了硝煙彌漫的戰場?女性從來沒有擺脫過戰爭陰影的籠罩”。杜甘的小說《軍官病房》和《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國》中,有著不少有血有肉、形象豐滿的女性形象,讓人印象深刻,為之動容。本文試圖以杜甘這兩部小說為藍本,緊扣戰爭與女性之間的關系這一主題,闡釋戰爭對女性命運的影響,凸顯反戰這一主題。
(一)戰爭對女性命運的影響
戰爭是人類的災難。古往今來,人類為了搶奪領土和自然資源等爆發了大大小小無數次的戰爭。這其中有正義的戰爭,也有非正義的戰爭,但不管是哪種,這些戰爭都使無數戰士戰死沙場,無數難民流離失所,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使人類遭受巨大損失和破壞。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對人類文明造成了巨大的摧殘,帶來了難以想象的可怕后果。
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性,歷來被視為柔弱的象征,是被保護的對象。可戰爭卻不會因此而格外眷顧她們,使她們免遭傷害和苦難。相反,無數女性以各種形式被迫卷入了戰爭當中,所受傷害相比男性更為嚴重。 “戰爭迫使男子上了前線,使婦女不得不忍受難以言說的相思煎熬的痛苦;戰爭不可避免地奪去了許多男子的生命,使婦女不得不經受失去親人的巨大痛苦;戰爭的不斷繼續、戰場所需物資的不斷增加,使婦女不得不承受沉重的賦稅和徭役負擔,加上叛軍的燒殺擄虐,使婦女身心遭受更大的摧殘”。在杜甘的《軍官病房》和《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國》這兩部小說中,有不少鮮活的女性形象。她們有的是作為志愿者在后方擔任護士搶救傷員,有的是參與抵抗運動中的情報工作。戰爭對她們的命運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在《軍官病房》這部小說中,美麗的女護士瑪格麗特雖然是一個富有的金銀器商人的女兒,她卻主動要求作為當時緊缺的護士去前線的急救醫療隊,成為了一名志愿者。可就在她去醫療隊的第四天,一顆德國炮彈落在幫傷員止血的瑪格麗特的帳篷里,她被毀容了,耳朵也失聰了。從此,她的一生因為毀容而定格,決定了她在以后的人生當中的種種艱難。相比在戰爭中其他缺胳臂少腿的傷員,面部損傷所帶來的影響遠遠要大得多。斷了四肢還可以裝上義肢,穿上了衣服也不會把傷口赤裸裸地暴露在外。可是如果是面部毀容,該怎樣示人?瑪格麗特不僅要經受身體上的痛楚,還要備受世人冷漠的眼光,在社會生活中受挫,經受精神的折磨。她出院之后回到家中,女仆竟然不認識她,而正在參加晚會的父母和兩個哥哥也沒有流露出絲毫溫情。直到最后她的幾個男性同伴都成功地結了婚,她卻仍然是個例外,“因為她是一個女人,而一個被毀容的女人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生物”。就這樣,她終身都未能享受到愛情和婚姻,把一生都無私地奉獻給了他人。對于一個女人來說,還有什么比這些傷害更加痛苦的嗎?
《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國》中的米拉是一個西班牙猶太女人,是主人公加爾米埃的上級。作為情報人員,接頭碰面、四處搜集消息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僅得膽大心細,而且在遇到緊急情況時要冷靜果敢。米拉每次與加爾米爾接頭時,都是那么冷漠,壓抑著自己的情感,不被人看出任何蛛絲馬跡。可是后來她還是被抓捕了。她始終沒有屈服,接著被流放,“他們在精神上要遭受甚于死亡的折磨、屈辱,否定自己的存在。納粹分子將向人類表明,他們能夠做出比使人們死亡更恐怖的事情,這就是他們所能留下的一切”。她在集中營所受的苦難必然是駭人聽聞,從集中營被解救出來后她來到了以色列。最后,深愛她的加爾米爾在她定居的地方——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找到了她,而這時的她微笑著,熱情、親切,跟之前冷漠、高傲的形象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米拉在加爾米埃的陪伴中于1964年3月去世,她就這樣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人類永恒的事業——和平。
克洛狄娜是加爾米埃剛開始參加地下工作不久留宿過、掩護過他的戰友,后來成為了他有名無實的妻子。加爾米埃并不喜歡她,只是因為覺得孤獨才與她結合。戰爭結束以后,克洛狄娜仗著加爾米埃父母的善意在他家里住下,最后如愿和他結婚。可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我們很少說話,我們的共同生活的滋味就像煮過的生菜,我們結婚就像別人拿到了一張黨證,以便確認一種立場”。這種無愛的婚姻就像一把枷鎖把他們生硬地綁在一起,對于兩個人來說都是一種折磨,但這又何嘗不是克洛狄娜命運的悲劇?
《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國》中有一個剛滿19歲的妓女叫阿特加,她的父親從戰爭開始就被俘虜到德國,母親拋下她跟人私奔了,留下她獨自面對命運的無情擺弄。她善良單純,毫不知情地成為了臥底,卷入了這場紛爭。直到最后被捕,她也是 “目瞪口呆地跟在后面”。這樣一個花季少女,本該在父母親的庇佑下,幸福快樂、無憂無慮地生活著,可就是因為戰爭她不得不為了生活淪為妓女,陷入多么危險的境地而毫不自知。她的悲慘命運正是對殘酷戰爭的無聲控訴。
戰爭這個怪物給這些女性帶來的苦難絕不比男性少,相反,她們的悲慘命運更是凸顯了戰爭殘忍的本質,發人深省。“對于那些仍然相信戰爭是一種偶然事件的人,我希望這本書能夠使他們意識到一切沖突都只是人類新的失敗,任何理由都不足以使人相互屠殺”。杜甘向我們展示了無情的戰爭對女性命運造成的巨大影響,從側面凸顯了反戰這一主題,觸動人心,引起了讀者的共鳴。
(二)女性形象的塑造
杜甘的兩部小說視角獨特,題材新穎。他選擇了細微的角度作為切入點,作品中出現的人物在戰爭這樣的大背景下都顯得平凡而微不足道,但是我們細細觀察就可以發現,這些都是一些非類型化的人物。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形象更有鮮明的個性特征。
《軍官病房》中美麗的女護士瑪格麗特是一位令人欽佩的女性。她有著美麗的長發,苗條的身材,藍色的眼睛,甜美柔和的聲音,熱情的微笑。但這樣一位美人兒卻被毀了容,鼻子和顴骨被炸彈擊中,姣好的面容當中有一個窟窿,耳朵也失聰了。她呆在巴黎榮譽軍人醫院這座白色監獄里,接受著魔鬼般的器械的折磨。這里的病人們面對著病友嚇人的傷口,就像看到自己厄運的鏡子,在別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這所醫院里,有一個名叫路易·勒沃舍勒的毀容者,在他的妻子和兩個兒子來探望他之后,不能承受親人們看到他被毀面容之后的反應而自殺。確實對于毀容者來說,面對生活需要多么大的勇氣和多么堅強的內心,一個這樣的大男人尚且不能做到,更何況是一位女性!可是瑪格麗特卻做到了,她沒有選擇自殺,而是毫不躲避,樂觀積極地面對生活。當佩納斯特出現在她的面前邀請她加入軍官俱樂部時,“她的全部回答就是給了我們一個熱情的微笑,一張像她的眼睛和前額一樣未受損傷的嘴巴的純潔的微笑”。但在獲準休長假回家之后,等待瑪格麗特的卻是正在參加晚會的父母和哥哥們的驚慌失措和冷漠無情。都說家是溫馨的港灣,即便受到再大的傷害,只要回家就能得到慰藉。像瑪格麗特這種境地更是需要家人的關心和鼓勵,可是她沒有看到這些,相反還受到嫌棄。最后她毅然離開了家。作為一個女性毀容者,獨自面對著自身的痛苦、他人的眼光、親友的拋棄卻依然頑強地生活下去,她的勇氣和堅強令人折服。
更令人敬佩的是,在經過了這些苦難之后,她依然在兒童醫院工作。后來除了在部里上班之外,還在一家精神病患者衛生院里工作。她終身未婚,把自己的一生無怨無悔地奉獻給了他人。她的舍小我為大家的奉獻精神讓我們為之感動。此外,她與住院期間結識的三位病友之間建立了同甘苦、共患難的珍貴友誼。在醫院那段難熬的日子里,他們相互扶持、鼓勵。一直到最后出院,他們都是最親密的朋友。瑪格麗特雖然失去了親情,也沒有享受到愛情,但她收獲了珍貴的友情,她的大愛精神贏得了他人對她的敬重,她的形象熠熠生輝。
《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國》中的女上級米拉有著茶色的皮膚,優雅、苗條、柔軟,卻一直對瘋狂愛上她的加爾米埃保持著距離,故作冷漠和傲慢。或許這樣一種冷峻的態度、有原則、有分寸的工作作風正是她的魅力所在,深深地吸引著加爾米埃陷入愛河不能自拔。米拉被捕之后,在三天的期限里,她并沒有在嚴刑拷問下出賣加爾米埃,供出聯絡網。在生死攸關的時候,她為了保護同伴和組織,以自己的柔弱之軀獨自冒著生命危險,沒有吐露半點消息,使得加爾米埃安然無恙地度過了最危險的幾天。在這樣危險、特殊的環境里,他們之間這種默契、信任豈是一般的情感所能承受的?
戰爭結束之后,加爾米埃對米拉日思夜想,千方百計地找到她之后,米拉與戰時的態度截然相反——親切、熱情,帶著開朗的微笑,努力打消加爾米爾的靦腆。像與多年的老朋友重逢一般,她說起了她的經歷,卻對被捕、被流放的日子避而不談,這是她人生中灰暗的日子,足可見她當時受了多少苦難和折磨,她不想讓加爾米埃難過。米拉還談到了她畢業之后照顧精神病人、領導基金會、為爭取獨立而斗爭等經歷,這是一位有思想、有膽識、有信念的女性,她在戰爭中勇敢地站起來,主動地承擔責任,為人類的幸福而貢獻自己的力量。難怪加爾米爾說: “我很快明白了我永遠有那么多理由愛她”。
在杜甘的這兩部小說中,除了瑪格麗特和米拉這兩位主要的女性形象之外,還有一些女性形象同樣讓我們為之動容。《軍官病房》的克雷芒絲在戰前送別她的情人后,顯得迷人而憂傷,卻與主人公阿德里安·富爾尼埃發生了關系,成為阿德里安魂牽夢縈的情人、煎熬歲月中的精神支柱。之后她拒絕了阿德里安卻又抱怨他的沉默。給人以飄忽不定、茫然無知的感覺,這與戰爭時期人們心靈受到創傷,對未來感到迷茫、困惑是分不開的。戰友雷米的母親是一個“將近六十歲的美女”,目光堅定,也是一名抵抗運動成員,最后被抓到集中營里再也沒有回來。作為一名老婦,她本可以躲在安全的地方繼續生活,不問世事。可她沒有,她毅然地加入反抗的行列,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相比以前的反戰小說,《軍官病房》和《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國》兩部小說中出現了更多個性鮮明、形象豐滿的女性。杜甘把殘酷無情的戰爭與女性的柔弱卻又堅強的形象放在一起形成強烈的視覺效應,更能凸顯反戰的主題和贊美這些偉大光輝的女性。
老舍曾說,作家描寫戰爭“不是為提倡戰爭,頌揚戰爭,而是為從戰爭中挖掘出真理,以消滅戰爭”,老舍先生這句話道出了作者寫作戰爭小說的意義,這也是作家應有的一種博大情懷和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杜甘正是這樣的一位作家,他以這兩部出色的小說從不同角度給我們展現了一戰和二戰的冰山一角,警醒著世人要防患于未然,遠離萬惡的戰爭,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