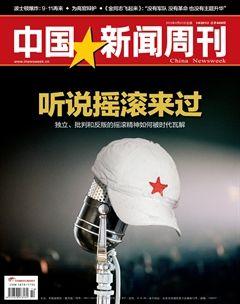溫州戶外廣告的生死場
韓永
最近一年多,朱小瑚很少回溫州,“有種走不出來的傷痛”。有時候會從夢中驚醒,在夢里,一塊塊廣告牌轟然倒下。
徐建康和麻麗芬也有類似的經(jīng)歷。由于睡眠不足,40多歲的麻麗芬長了一臉痘痘。《中國新聞周刊》接觸的這幾位溫州的廣告商,都是一臉倦容。他們三人都是溫州市戶外廣告行業(yè)的領軍人物,但兩年前,溫州開始了一場針對戶外廣告的整肅運動,一塊塊廣告牌從現(xiàn)實一直坍塌到他們的夢境里。
從30%到100%
故事要從2011年3月中旬說起。
此間,溫州市100多家戶外廣告企業(yè),陸續(xù)前往位于寬帶路的市城市管理與行政執(zhí)法局(簡稱“城管局”),辦理一年一度的審核。朱小瑚任董事長的珊瑚廣告公司,在溫州的戶外廣告牌最多,有300多塊。按照以往的經(jīng)驗,這種審核“就是走個流程”,不通過審核者寥寥。
但這一年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市城管局有關人員說,從即時開始,停止戶外廣告的審批與續(xù)批,理由是為了改善市容,政府將會對戶外廣告進行整頓。
最初下達的指標,是拆除戶外廣告的30%。溫州市城管局副局長谷一超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介紹說,這大致就是溫州市違法戶外廣告的比例。所謂違法,就是指沒有經(jīng)過審批的廣告牌。
當時,鹿城區(qū)城管局局長姜益祥召集了轄區(qū)內戶外廣告企業(yè),分配拆遷指標。這一次的溝通并沒有遇到困難。畢竟對于戶外廣告企業(yè)來說,30%的比例并不傷筋骨。當時,很多戶外廣告企業(yè)從以往經(jīng)驗出發(fā),想當然地認為,這只是歷次整治的重演。
但他們未曾想到,一場“大清洗”才剛剛開始。30%的任務完成后,溫州市政府又提出了50%的拆遷目標。姜益祥再一次召集轄區(qū)內戶外廣告企業(yè),分配指標。
與前一個階段主要“拆違”不同,要完成50%的拆遷指標,就要對經(jīng)過審批的合法廣告牌動手。于是,政府在停止審批戶外廣告之后,又在戶外廣告的年審環(huán)節(jié)上做工作,不允許一些廣告通過年審。
拆遷還在繼續(xù)。在50%的目標達成后,溫州市對戶外廣告牌展開了“殲滅戰(zhàn)”。記者看到了一份今年1月實施的《鹿城區(qū)戶外廣告節(jié)前攻堅拆除行動實施方案》。其制定的目標是,“全面拆除城區(qū)各類違法戶外廣告設施與到期戶外廣告設施”。由于政府停止審批已近兩年,在主管部門看來,溫州市所有的戶外廣告牌均能列入非法的黑名單。
到了此時,溫州市原有的2000多塊廣告牌,只剩下了72塊。《方案》要求對這72塊廣告牌“全力攻堅”,“以強拆、助拆為主,確保節(jié)前拆除完畢。”
“末日危機”
溫州市城管局副局長谷一超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一直在強調,政府所拆廣告牌均為非法。
但對于這一點,廣告商們并不認同。他們認為據(jù)《行政許可法》第三十八條規(guī)定:申請人的申請符合法定條件、標準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作出準予行政許可的書面決定。也就是說,只要戶外廣告企業(yè)提供的材料符合原有的審批條件,溫州市城管局就應當批準延期,不批準屬違法。
溫州市停止審批戶外廣告的背景,是該市基于環(huán)境整治的出發(fā)點,欲提高審批的門檻。浙江五聯(lián)律師事務所徐利平律師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提高門檻要有法規(guī)依據(jù)。而即便有依據(jù)提高審批的門檻,對于這種情況,《行政許可法》有“信賴利益保護”的規(guī)定,即“行政許可所依據(jù)的客觀情況發(fā)生重大變化的,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jīng)生效的行政許可。由此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造成財產(chǎn)損失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補償。”
也就是說,像溫州這種由于政策的變化導致無法審批的,應該給予一定的補償。但溫州市政府基于“拆違”的邏輯,不提供任何補償。
作為溫州市戶外廣告專業(yè)委員會主任,徐建康曾作簡單的測算,說這次整治給溫州市廣告企業(yè)帶來的損失,在5億元左右。
這個算法,是基于每塊廣告牌的合同收益,谷一超對此并不認同。他說,因為每年都需要年審,戶外廣告牌有效期只有一年,而廣告商卻和客戶簽5年的合同,這不能算是合理的預期收益。
今年1月11日,感受到“末日危機”的溫州市多家廣告公司,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請愿行動。王朝大酒店附近的十字路口因此堵塞。但請愿并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在平陽縣,16位參與者被拘留。
在對《中國新聞周刊》提起三個月前這段往事之時,徐建康突然間激動了起來。“這觸動了我的傷疤,激發(fā)了我的憤怒。”作為溫州市戶外廣告專業(yè)委員會主任,他組織了多輪與政府的談判,每次談判的路徑都如出一轍:區(qū)里表示同情,說只負責執(zhí)行;副市長也表示同情,也說只負責執(zhí)行。于是,最后全都指向溫州市最高層級的官員:市委書記陳德容。

政府的邏輯
陳德容是在2010年7月從嘉興調任中共溫州市委書記的。在公眾眼里,他的執(zhí)政和說話風格都別具一格。溫州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陳德容是一位很講究效率的官員,他經(jīng)常去基層,叫得出街道書記的名字,習慣從基層著手倒逼政府的效率。
在2010年,溫州市人均GDP列浙江省倒數(shù)第三,發(fā)展水平指數(shù)和發(fā)展速度指標分別居倒數(shù)第一和第二位。很多企業(yè)在發(fā)展壯大后遠走他鄉(xiāng),把稅收帶到遠處,把“低、小、散”留給家鄉(xiāng)。
溫州的企業(yè)為何“墻內開花墻外香”?土地的價格或許能說明問題:2010年上半年,溫州工業(yè)用地的招拍掛價格,已經(jīng)是200萬元/畝,在浙江省可謂“一騎絕塵”。對于企業(yè)來說,這是個讓人望而生畏的價格。
2012年7月,新浪地產(chǎn)公布了一個內地主要城市房價排行榜,溫州市在這個榜單上名列第二,僅次于三亞,每平方米單價高達2.5萬元。
而大多數(shù)慕名而來的外地人,會對這個城市產(chǎn)生很大的心理落差:城市缺少規(guī)劃,沿街綠化貧乏,道路坑坑洼洼。坐在顛簸的出租車上,會對投資和生活在這座城市的性價比有更為直觀的體會。
溫州的“拆違”,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開始的。它被賦予了兩個將對溫州的前途影響深遠的功能:一是騰出發(fā)展的空間,降低投資和生活的成本;二是讓城市脫繁至簡,清爽宜人。
拆除戶外廣告牌,只是這一聲勢浩大“拆違”活動的一部分。溫州市城管局副局長谷一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前一屆市委領導的思路就是“以環(huán)境促發(fā)展”。“這既包括硬環(huán)境,也包括軟環(huán)境。”谷一超說。
對“軟環(huán)境”進行治理,也是此次清理戶外廣告的另一個背景。
溫州市鹿城區(qū)城管局局長姜益祥說,溫州的戶外廣告過去缺少規(guī)劃,遍地開花,這個行業(yè)資源的分配,不是依據(jù)市場的原則,而是一種“權力分配”。
“批不批廣告牌,就看你能不能找到幫自己說話的人。”他坦承,作為鹿城區(qū)城管局長,也有一些人找過他。
在改革開放以后的很多年,戶外廣告的繁榮,被視為一個地區(qū)經(jīng)濟發(fā)展的象征,審批的標準非常寬松,主管部門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這種權力與行業(yè)巨大的利潤結合,滋養(yǎng)出肥沃的腐敗土壤。
在這樣的土壤里,未經(jīng)正式審批的廣告牌拔地而起,雖然身份可疑,但也向主管部門繳納管理費。此外,城市的公共空間,如道路和綠地被大量占用;而一些樓頂?shù)摹⑽唇?jīng)安全評估的廣告牌迎風搖曳,每年都制造出廣告牌墜落傷人的事件。
何去何從?
谷一超介紹說,這一次整治,主要的對象主要有兩個,一是樓上的受風面較大的廣告牌,二是占用公共空間的廣告牌。前者是基于安全考慮,后者則是基于公共空間的重新規(guī)劃。
他說,政府正在制定城市公共空間的使用規(guī)范,一批之前被無償使用的公共空間,將會進入招拍掛程序。
而之前對戶外廣告牌的市場需求,將會被引導到墻體和LED廣告上。姜益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已有4塊廣告按照新標準獲批。
新標準的變化體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審批的流程上,將由之前的城管一家審批,變?yōu)?個相關部門會審;二是在內容上,廣告的效果要對城市的環(huán)境是個“增量”。這也就意味著審批過程延長,同時讓通過審核的難度加大。
但廣告企業(yè)最為擔心的,是按照現(xiàn)有的戶外廣告規(guī)劃,資源量嚴重不足。徐建康和朱小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新標準下的戶外廣告資源量,不及原有空間的一個零頭。
溫州市城建設計院副院長方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溫州市的樓房多是商住兩用,給廣告留出很少空間,這讓溫州市適合做墻體和LED的空間捉襟見肘。
方嵐認為,按照現(xiàn)有的空間,溫州很多戶外廣告公司將會倒閉。徐建康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兩年整治后,目前能堅持下來的戶外廣告企業(yè)不足20家。
為了應對可能的不穩(wěn)定因素,主管部門也在努力協(xié)調資源。姜益祥說,在按照新標準獲批的4塊戶外廣告中,本來有兩塊屬于王朝廣告公司,她便說服王朝負責人將其中一塊讓給了泰山廣告公司。
而對于廣告商而言,未來充滿不測。他們還在等待政策的松動,甚至還在期盼政府對他們的損失“給個說法”。溫州高速公路廣告公司總經(jīng)理李玉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這次整治中,他的公司有近40塊高速公路廣告牌被拆除。“當年賣房借錢做這個公司,什么風險都計算過,就是沒有計算過這個(強拆)風險。”
由于廣告牌被拆,對客戶不能履約,徐建康已經(jīng)輸?shù)袅艘粓龉偎尽K嬖V《中國新聞周刊》,自己今年51歲了,天命之年卻還可能不得不遠走他鄉(xiā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