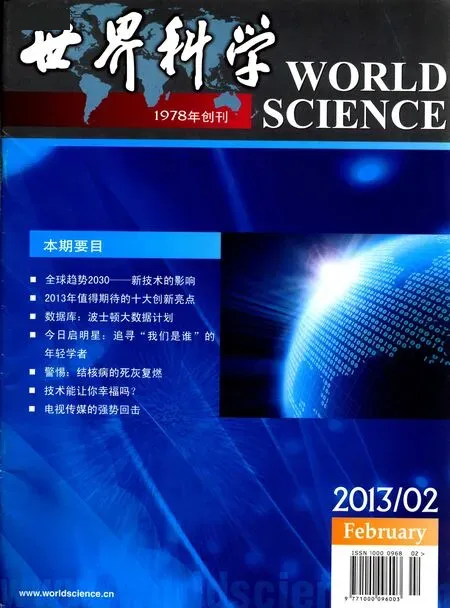技術能讓你幸福嗎?
蔡立英/編譯

是的,而且技術能讓你的辦公室變成一個更舒適的工作場所
●電腦和手機有時會讓人抓狂,電子設備把你拴在了辦公室里,新收到的電子郵件和手機短信沒完沒了地讓你分心30秒。這些情景是不是聽起來很熟悉?
計算機和通訊技術的進步使生產率大大提高的同時,也給職業人士的工作生活帶來了不幸。難怪現在很多人的夢想甚至是把手機扔到山澗里,這樣就完全不受干擾了。但是,如果技術不是給人們制造壓力,相反是使人們更加享受生活又會如何呢?
建造幸福并沒有聽起來那么不可思議,過去十年來,工程師、計算機科學家、心理學家和其他研究者已經表明他們能做到。具體來說,通過監測和分析睡眠類型、運動和飲食習慣,再加上像體溫、血壓和心率這樣關鍵的統計數據,他們就能準確找到一個人日常作息中存在的問題,然后提出能從可測程度上改善健康狀態和精神面貌的建議。建立在這些研究之上,現在上市的一系列消費品讓你在家就可以嘗試這些東西,其終極目標是讓你更健康、更幸福。
幫助人們改善個人生活的技術同樣也能在工作場所產生積極的作用:在組織的各個層面上都會帶來更好的交流,更好的團隊合作,以及更大的工作滿意度。也許最引人入勝之處是,它能幫助員工獲得無論做什么事都完全沉浸其中并且精力充沛、感到幸福的那種滿足感。似乎太美好了而不會是真的?事實上,這完全是有可能的,不是魔術。但是要達到最好的結果,需要工程學和心理學的適當結合。
技術層面
從技術層面來說,驅動這個活動的是三種趨勢的融合:小型化、無線通訊和更好的電池。只需現成的硬件你很容易就可以組裝一個能記錄十億字節行為數據而只有幾十克重的小型傳感器,所以它不會給使用者帶來負擔或是打亂其日常活動。
21世紀初,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亞歷克斯·彭特蘭(Alex “Sandy”Pentland)是最早提議使用可佩帶式傳感器來研究人們幸福度的研究者之一。那個時候,傳統的想法認為測量一個人的思想精神狀態的最佳方法是使用訪談或書面調查。但是研究結果表明絕大部分的人類交流是非言語的。非言語的信號,例如語調、姿態和手勢可能比正式語言還要重要得多。譬如說,你正在聽同事說話,即使你不置一詞,你的面部表情也會立馬泄露你是否感興趣、厭倦或者完全不滿意。
彭特蘭的想法是用一個包含麥克風、加速計和紅外發射機的可佩帶式傳感器(他稱之為“社會計量儀”)來檢測一個人的音調以及他或她的運動,從而管窺到佩帶這個傳感器的人的經歷、社會型和交流質量。然而,那時的電子技術還不是非常能勝任這項任務。早期的傳感器重達200克,并且沒有多大的存儲和處理容量或是很長的電池壽命。

日立可佩帶式傳感器能監測員工的活動和互動
后來,彭特蘭的研究組與雅諾(Yano)以及他在日立公司的團隊合作,來擴展這些裝置的可用性。然后日立把它們商業化并整合成一個叫 “商業顯微鏡”的社會經濟傳感器,于2009年發布。
最新的日立商業顯微鏡(HBM))大約只有一個姓名牌那么大,重33克。你用鏈子把它戴在脖子上,就像你在會議上把一個姓名牌掛在脖子上一樣。在它那個塑料殼里面是6個紅外收發機、一個加速計、一個閃存芯片、一個麥克風、一個無線電收發機和一個能讓這個“社會計量標牌”一次性工作兩天的可充電的鋰離子電池。
日立商業顯微鏡測量佩戴者的身體運動和音高,以及周圍的空氣溫度和照明強度。它記錄身體運動——包括點頭、揮手、伸手、指點和其他非言語的交流——就像計步器記錄一個人的步數一樣。也就是說,加速計會測量X、Y、Z軸方向上的每一次移動。隨后,這些測量結果會被轉化成一個單一數值,表示你在空間中移動的程度。
這個傳感器能通過它的6個紅外收發機告訴你什么時候兩個或者更多的佩戴者相鄰很近,這6個紅外收發機指向不同的方向,從而覆蓋佩戴者前面和側面的廣闊區域。當這些收發機發現另一個社會計量標牌在2米以內,這兩個社會計量標牌會交換ID號碼。然后每個社會計量標牌會記錄互動的開始時間、持續時間和地點。為了確定地點,社會計量標牌會聽取來自最近的“信號站”的信號,信號站是一個持續播送其位置ID的紅外裝置;信號站被有策略地放置在被監測空間的周圍——會議室的桌子上、使用者的書桌上等等。每個社會計量標牌的小型LCD屏顯示時間、溫度、你今天見過的其他日立商業顯微鏡佩戴者的號碼,以及你的身體的活動程度。
社會計量標牌也會收集所發生的交流類型的有關信息。例如,和同事坐在會議室里聽一個報告者嘮嘮叨叨地說幾個小時與圍坐在咖啡機周圍生氣勃勃的談話是非常不同的。日立商業顯微鏡能鑒別這種不同,還能通過監測人們的運動并測量他們的聲音能級。
每天離開辦公室之前,使用者把社會計量標牌放在一個“搖籃”里,它會給電池充電并且下載所儲存的信息。這些測量結果通過因特網傳輸到日立的數據中心做分析和長期存儲。系統周期性地給使用者提供關于所監測到的運動的報告。
自從三年前日立商業顯微鏡上市以來,數以百計的機構,包括銀行、信息服務公司、設計公司、研究機構、呼叫中心和醫院都已使用它來收集大約10兆兆字節的行為數據,總計達50萬人天次。當然,要理解人們的主觀體驗,不僅僅需要記錄他們如何移動或是他們跟誰說話。而且,為了使所有這些數據有意義,你需要有一個關于人類行為的科學框架。
行為影響因子
每個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動機,感覺和目標——所有這些都會影響行為。但是這些潛在因素可能對于臨時的甚至是受過訓練的觀察者而言并不一定是顯而易見的。一個人不規則的運動是表示痛苦呢,還是輕浮呢?少于一天正常的社會交往次數意味著那個人抑郁呢,還是意味著那個人只不過是專心致志于一個有吸引力的活動呢?工程師需要一種把傳感器數據提取為有意義的精神狀態的方法。
為此,我們求助于新興的積極心理學領域。不像傳統的心理學專注于心理問題——舉幾個來說,壓力、抑郁、焦慮、困擾和情緒波動——積極心理學關注值得擁有的精神狀態(包括幸福)和廣受歡迎的性格特點(比如自制和慷慨),以及有助于幸福的內部和外部因素。

你也許會認為幸福是一種不可言喻的東西,一種難以捉摸的存在狀態,不可加以量化和分析。但是過去十年來,柳博米爾斯基(Lyubomirsky)和她在加利福尼亞大學里弗賽德分校的合作者們進行了許多研究,表明實際上可以對幸福進行系統地測量。
這些研究結果可能是違反直覺的。例如,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傾向于相信當我們結婚、買房或是得到提薪時會更加幸福。然而,結果卻是,這種外部情況對我們長期的幸福水平而言貢獻甚微。類似地,許多人以為關系受挫、職業失敗或是金融危機會使他們更加不幸福,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結果是大多數人都比他們預期的更快地適應積極的或是消極的情況。
互動分析
在左邊的“投手-捕手”關系圖(上圖)中,深色圓圈代表 “投手”——更加健談的那些人——淺色圓圈代表不太愛說話的“捕手”。在這項研究的開始階段,辦公室交流主要是單向的,正如箭頭所顯示。到最后,雙向互動成為了標準的行為模式。在右邊的空間利用圖中,圓圈大小顯示了員工在辦公室的不同地點逗留的時間,顏色與活躍度相對應(淺色表示主動,深色表示被動)。
對幸福確實有影響的是人們的習慣和活動。即使諸如表達謝意、表示善意之舉這樣簡單的行為也能使你可測程度上感覺更好。那么,結論是:改變行為而不是固戀理想情況,才是增進幸福的最佳方式。
幸福的好處遠非僅僅是感覺良好。在2005年,柳博米爾斯基和她的同事記錄了幸福和積極的感覺如何改善人們的私人生活和職業生活。例如,幸福的人們往往更加有創造力,工作時更富有成效,從而賺取更高的薪水。你解讀得很正確:得到提薪并不能使你更幸福,但是如果你已經幸福了,更多的錢很可能作為一個附帶的好處出現在你面前。關于這些積極結果的堅實有力的統計數據——更高的薪水、更好的績效評價和更長的壽命——幫助他們戰勝了質疑幸福研究價值的懷疑者。
在工作場所,感到幸福的一項指標是獲得一種全身心投入的狀態或稱為“心流”的狀態,這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克萊蒙研究大學心理學家米哈里·齊克森米哈里(Mihaly Csikszentmihalyi)用來描述這種現象而創造的一個術語。當心流產生時,幾個小時的時間快得就像幾分鐘似的,你完全忘記了身外的煩惱。幾乎每個人都會在這個或那個時刻體驗到心流,包括知識型工作者比如工程師和科學家,他們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全神貫注的創造活動和解決問題的努力。正如結果顯示的,技術能幫助人們識別這種寶貴的精神狀態。
小型研究
在一項小型的但是引人入勝的研究中,雅諾和他的同事亞拉浩二以及米哈里所考察的是,能否量化人們何時達到那種特別的“在狀態中”的感覺。在這個實驗中,要求參與者記錄他們一天中的感覺和相應的活動。然后,把他們的日立商業顯微鏡數據——尤其是加速計所測量到的他們的運動節奏——與他們的日記作對比。并沒有一個運動或者一種活動與心流的狀態相對應,一天中也沒有一個特定的時間,工作者能以這種方式更加集中精神。考慮到人們的個人風格和癖好,這個結果是有意義的。
經過研究,心流的關鍵指標原來是運動的一致性。對一些人而言,那種一致的運動很慢,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則很快。一些人喜歡早晨活動,另一些人則偏愛下午或是夜間活動。無論何者,當參與者體驗到心流時,他們的運動變得更加規律,他們全神貫注于一項有挑戰性的但是引人入勝的活動中而忘我了。當他們把日立商業顯微鏡數據與他們的日記作對比時,參與者常常驚奇地發現他們的精神狀態竟然如此明顯地被識別。一旦人們意識到他們的日常行為模式,他們就能更好地安排他們的工作日程以利用他們最可能處于這種精神狀態的時間。我們在工作場所使用可佩帶式傳感器的一種更直接但也是更有啟發性的方式是記錄社會互動。例如,你可以檢查辦公室的哪個地方可能進行最頻繁和最活躍的討論,哪些區域又是未充分利用或是傾向于消極互動的。基于這些檢測結果對辦公室重新布局可以推動更富有成效的合作。
在許多情況下,這些社會計量儀的監測數據會揭示出非常不同于你從公司的組織結構圖中可能推斷出的交流模式。譬如說,你正在試圖估計一個公司合并的各種影響。理想情況下,你希望這兩家公司完全融合成一體,盡管兩家公司的文化和工作過程可能并不同。傳感器數據能告訴你曾經是兩個不同的團體實際上在何種程度上能合并在一起,因為數據顯示誰真正跟誰交談以及交談的頻率。在一個早期的實驗中,日立商業顯微鏡被用來研究一家公司內的兩個生產設計部門的合并。合并后一個月,新團體就絕大部分而言,仍然是兩個分割的實體。甚至連團體的領導,起初也是繼續主要與他的老同事交流。確實,情況是如此糟糕,在一般員工和大老板之間足足有6度的會話分隔度。這很令人震驚,因為社會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最先在20世紀60年代研究的現象——分隔隨機選擇的兩個人的相識步數是6步,這兩個結果驚人的一致 (斯坦利·米爾格拉姆的這項研究后來催生了派對游戲“六度凱文·培根”)。

如圖,兩個部門合并一個月后,雇員(顯示為上下兩部分結點)仍然高度分隔,他們的社會互動遵循了一種等級模式。組織領導和普通員工的分隔度,憑日常對話聯系來判斷,大約是6。即使是合并后團體的領導(黑色圈出的結點)也主要與他老部門的同事交流。在管理者收到這些模式的反饋并采取措施增進交流之后,合并后的團體更加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在圖中顯示為上下兩部分結點有更多連接和一種扁平化的組織機構,結點之間的平均距離縮短到四步以下
所以,這樣一個功能失調的辦公室怎樣更好地運作呢?作為這個實驗的一部分,管理者和雇員定期收到社會計量儀的監測報告,包含顯示誰和誰交談的圖示,然后鼓勵每個人做出調整,從而把人們凝聚到一起。為期三個月的實驗結束時,團隊的領導和其他人與他們的新同事能更加緊密地合作了,社會等級也扁平化了。而且,員工報告了更大的滿意度和生產率。
在另一個小型研究中 (這是我們三個人的第一次合作),我們關注的是提升員工的滿意度。我們也測量了人們的運動以探尋幸福和體力活動是否相關。我們的研究進行了6周,涉及到有32個雇員的一個日本辦公室。半數參與者進行了一項促進幸福運動——即寫下那周在工作中發生的三件積極的事。剩下的參與者僅僅只需列出他們那周完成的工作任務。為了控制安慰劑效應,所有參與者都被告知給他們設計這個任務是為了讓他們更幸福。
和控制組比較起來,講述積極事件的參與者報告了更大的幸福、內發動機、生活滿意度和與他人的聯絡性。這些好處在研究結束后持續了一個月。考慮到這項運動的簡單性,這些好處就更加顯著了:僅僅用10分鐘寫下好的事情就會造成明顯的不同。
我們還尋找參與者的日常活動的不同之處。我們發現練習回憶積極事件的雇員開始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通過測量他們的運動可知),并且在白天更早地達到他們體力活動的峰值。此外,他們花費更少的時間與同事交流。換言之,當參與者感覺更好時,他們投入更多的時間到工作中,花費更少的時間參與社交活動,變得對他們的工作更加主動、投入和勤奮。當然,一個健康的組織需要一定程度的社會互動,正如我們在上述的公司合并實驗中所見。但是這項研究強調了平衡會面時間和個人成就的重要性。

這些研究結果還表明了社會計量儀的監測數據和更多的主觀調查結果是如何相互補充的:客觀測量記錄的是行為的具體變化,而主觀測量則從人們的思想和感覺層面解釋了這些變化。
合作剛剛開始
工程師和心理學家之間的研究合作才剛剛開始。我們滿懷期望,隨著可佩帶式傳感器的使用更加普及,更多的數據得以積累,人們將發現運用這些計量生物學監測器的新途徑。
當然,沒有一個幸福傳感器將會是完美的。但是,無需如此。當溫度計在四個世紀以前被發明出來時,非常不精確,但仍然帶來了有價值的信息。隨著時間的推移,溫度計的設計更精細了,現在它已變得不可或缺。我們相信幸福傳感器將會沿著相似的路徑演變。盡管在評估人們的精神狀態時總是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可佩帶式傳感器已經比測定幸福度的傳統工具好多了,因其相對不顯眼,使用起來不費力,而且制造起來相對不貴。
到時,更多的企業將使用這些傳感器來測量員工行為和滿意度,來研究新實踐、新工序的有效性,可能甚至用來培養心流。以這種方式,雇主將能夠營造出促進員工積極投入工作和提升總體生產率的工作環境。的確,那將會是一個幸福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