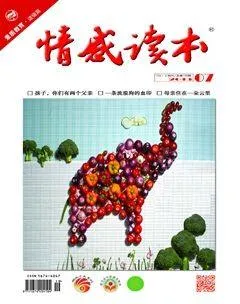我妹林月
岑桑
一
我叫林強,林月是我的妹妹。她從小就被我欺負。揪她辮子,給她畫花臉,都是常有的事。開始她會向爸告狀,但后來就不會了,因為她想做我的“跟班兒”。
少年時代的我,還是很拉風的。我是那一片孩子的“老大”。罵過人,打過架,每天放學,都會帶著一幫兄弟,騎上自行車,按著車鈴,呼啦啦地穿過大大小小的胡同。
那時,林月會死命跳上我后座,抱住我的腰不放。我說:“放開,干嗎總纏著我!”她就會堅定不移地說:“我不放,我要做你的跟班兒!”
我和林月是在京城胡同里長大的孩子,大概也要一輩子住在那里,它們是永遠不會被拆遷的,因為它們是文物。知道文物什么意思嗎?就是它們破成渣,也得戳在那兒。
高考那年,我落榜了。其實是在意料之內的事。我在家里窩了半年,爸決定送我去學廚師。他認為有手藝在身,一輩子餓不死。我們家只有他這一個家長,他的想法就是“圣旨”。后來,我被送去了河北一家很有名氣的廚師學校,那里的一位老師是爸的朋友。
我在那里學習了一年,寒暑都忙著實習。最后考到證書,才回到北京。那天林月來車站接我。我問:“爸呢?”
她說:“在家等你呢,不過你得有點心理準備啊。”
我一聽,心里就有種不祥的預感。結果回去才知道,爸中風了,整個人半癱在床上。我忽然就有種天塌下來的感覺,整個人都蒙住了。我愣了半天想起問:“什么時候的事?”
林月說:“你走沒兩月,他就癱了。”
“那你怎么不告訴我呢?”
“告訴你有什么用啊?你學費都交了,難道讓你回來啊?”
“那我一年的生活費都哪來的錢啊?”
“我打工唄。”
這一年,我爸49歲,我20歲,我妹16歲。我們一大一小兩個男人,靠我妹整整養了10個月。她每天到快餐店賣8小時漢堡,然后回家給爸做飯,幫他擦身,換尿布,最后再去小區里的黑網吧,做半宿網管。有時候回想起來,真不知道她一個女孩子,是怎樣撐過來的。
那天,我拉著她瘦巴巴的手問:“你不上學了?”
她說:“那怎么辦?咱們家存折里就剩500元了,我不打工,都喝西北風啊?”
二
回到北京后,我在一家飯店里找到了工作。有了固定的收入,生活也就穩定了許多。我讓林月回校復讀了高二。其實,她的成績并不好,但我覺得至少要讀完高中。我爸的身體,在第二年開始有了好轉,能說清楚話,還能拄著拐杖,簡單地走幾步。
我覺得命運終于向我們家露出了善意的微笑。
林月高中畢業后在一家公司找了個電話客服的工作。她人長得不好看,但聲音特別甜,尤其是性子夠和善,不論怎么罵都不還口,還是笑嘻嘻地禮貌應答。上班第一年,就被評為優秀員工。拿到獎金那天,林月請我和爸吃飯,我說:“有我還用去飯店嗎?”
她說:“當然了,意義不一樣。”
我爸看著一兒一女都能掙錢養活自己,笑得口水都流到碗里了。那天從飯店出來時,剛好遇到了一個小學同學。我沒認出他來,但擦肩而過的時候,他認出了我。他說:“唉喲,這不是強哥嗎?”
看起來,他混得不錯,西裝革履的,渾身都是名牌。我和他簡單打了聲招呼,就扶著爸轉身走了。
然后,我聽到身后那位同學和他的朋友說:“看看,這貨以前是我那片霸主兒,現在混得特慘,聽說就在小飯店當廚子……”
我默默聽著,心里忍不住酸。照以前的脾氣,我非把他揪過來揍一頓不可。但是工作之后,那些往日的火氣,也就漸漸磨沒了。這個世界就是這么現實,你沒本事,別人理所當然地會笑你。
可是,我扶著爸剛走了幾步。林月就轉身回去了。她指著那個比她高一個頭的男人,大聲地說:“哎,你說誰呢!嘴巴放干凈點。今天我爸在這兒,我哥不愛理你,要不然你別想活了!”
那個同學嚇得連忙說了一串“對不起”,灰溜溜地走了。我和爸轉過身,驚訝地看著她。可林月卻跑過來,調皮地吐了吐舌頭說:“怎么樣,霸氣不?”
我哈哈地笑了,說:“就你這樣的脾氣,怎么拿的優秀員工啊?”
林月說:“那不一樣。別人罵我,怎么都可以,但是說你就不行!”
“為什么啊?”
林月挽住我胳膊說:“我是你跟班兒啊,哪能讓他們瞧不起我老大呢!”
那時已是12月,夜晚的北京,吹著凜冽的風,可是有我妹緊緊地挽著我,我就會感到一種踏實的,歷經風雨也不會消散的溫度。它不熱烈,卻持之以恒。
三
林月是家里唯一的女性角色,所以總是兼顧母親的職責。當我向30歲靠攏時,她開始催婚了。她說:“哎,哥,你是不是該談個對象了,怎么一直沒見你有動靜呢。”
我無奈地說:“現在的女孩活得多明白,像我這樣掙得不多,長得不帥,還拖一中風老爸的主兒,誰敢愛啊?”
林月撇嘴說:“切,那是她們沒眼光。”
不久,林月就私自做主把我的照片登在了相親網站上。于是相親電話,一個接一個地打進來。后來我認識了何麗。
何麗是丹東人,開朗熱情,在北京工作了4年,說一口爽快的東北話。我們在幾次見面中,都比較談得來。之后,她要來家里看看。
一直以來,我都沒說我爸中風的事。我只告訴她我和父親、妹妹住一起。因為我怕還沒開始就把人嚇跑了。
所以,帶何麗回來的周末,我如臨大敵。可是那天等在家里的只有林月,爸不在。
何麗問:“你們家就你們兄妹兩個啊?你爸呢?”
林月說:“這是我哥的房子。我和我爸不住這兒。”
何麗捶了我一拳說:“行啊你。還和我留一手。怕我為你家文物房子找你啊。”
我忙解釋說:“沒,沒那意思。”
那天何麗一走,我就追問林月,把爸弄哪兒去了。
她說:“我租了個房子,把爸接過去了。以后,你就不用怕女朋友突擊檢查了。”
“你一個人,能照顧得了爸嗎?”
“怎么不能呢?我租的樓房,可好住呢。等你把嫂子娶回來,我們再搬回來住。”
林月用她那種堅定不移的目光看著我。我知道,再勸也沒什么用了。
四
2007年我和何麗結婚了,那時林月帶著爸在外面已經住了一年多。何麗是個明白人,她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要我把爸接回來住。可是林月卻不同意,她說:“嫂子畢竟是外人,爸那么麻煩,久了肯定要抱怨。到時候鬧起來,誰都不好過。”
我把曾經她說我的話倒給她:“現在是你沒結婚,你帶著爸,有人要你嗎?”
可林月卻有了另一套說法。她說:“呀,就因為帶著爸就不要我,那樣的男人能嫁嗎?我爸就是檢驗男朋友的試金石啊!”
林月總是有這樣的本事,把不好的事,看成好事。把任何麻煩,都轉化成積極向上的正能量。
雖然何麗是直性子,但很會操持生活。家里在她的打點下,很快有起色。2009年,我們開了一家小飯店。我做大廚,她來管賬,日子辛苦卻也紅火。每個周末,林月都會推著爸回來。那時爸的身體開始走下坡路了,腦子也變得不太清楚。但一家人聚在一起,總是其樂融融。第二年,我和何麗有了兒子。林月這個小姑,高興得天天來看侄子。我看她喜歡的樣子,勸她說,“你該找一個了啊,哥看著都替你急。”
林月卻不在意地說:“瞎急什么啊,戀愛結婚是講緣分的。”
可我知道,她是為了照顧爸。那時的爸,已經完全像個小孩了。林月不忍心把他送去養老院。她在網上看了虐待老人的新聞后,害怕神志不清的父親被欺負。而我因為有了小孩,也無暇顧及到他。
有時,我很懊惱自己的自私,作為一個兄長,卻習慣了讓妹妹去承擔麻煩。我從沒想過,這些看似快樂的日子,卻掩藏了許多我從不知曉的秘密。
那是2012年的12月。林月突然在夜里打來電話,叫我快過去看她。我聽她的聲音都在發抖,頓時慌了。我連夜打車去她那。爸藏在床底下,嘀嘀咕咕地不知道在說什么。林月坐在電話旁的地上,頭破血流。
我連夜把她送去了醫院,替她包扎的醫生出來對我說:“你是林月的哥哥吧?”
我點點頭。他說:“你是怎么當哥的?你妹妹長期遭受家暴你不知道嗎?她渾身都是傷!”
我站在蒼白的日光燈下,霎時傻掉了。
林月說,早在半年之前,父親就已經開始有暴力傾向,有時只是粥不合口,就會動手打人。這一次林月替他蓋被子的時候,手指戳到他的脖子。他就拿拐杖砸了林月的頭。林月一直都不敢和我說。因為她怕我知道了,會把父親送去養老院。那天,我要她去醫院做個全身檢查。開始她死都不肯,直到我發了脾氣,她才答應。
一周后,我陪著她去醫院拿檢查報告。醫生說:“你這個哥,真夠可以的。你妹得肝癌了,知道嗎?”
我這才明白,她為什么不去體檢。她早就知道了,所以才不戀愛、不結婚。林月說,“我都這樣了,不能去連累別人。”
五
我和何麗商量,把爸和林月接回來住。她一邊點頭,一邊抹眼淚說:“這么多年,真是難為你妹了。都接回來,我伺候。”
那已經是新年的1月,我爸到家后,一上床就睡了。林月一直站在院子里。我說:“進屋吧。外面空氣太臟。”她卻轉身說:“哥,你答應我。以后什么情況,都不能把爸送去養老院。他是有兒女的人,不要扔下他一個人。”
我默默地點了點頭。
她像心里放下一塊石頭似的,微微笑了。
這就是我妹,一輩子沒做過什么驚天動地的感人事跡,也沒什么愛好和追求。在她善良單純的世界里,就是想讓她的親人過得好一點,好一點,再好一點;至于自己,一切都無所謂。
一天,林月看見靠在墻角的舊自行車說:“這老古董還能騎不?你再馱我去胡同里轉轉吧。”
我說:“行,哥帶你兜風去。”
那天北京下了糾纏不去的大霧,林月坐在后座上,像從前那樣,緊緊地抱著我的腰,說:“哥,你怎么還這么拉風,這么帥呢?”
我說:“你可真會哄我開心,哥的臉都老成長白山了。”
林月清爽地笑了。她把頭輕輕靠在我背上,說:“哥,我好想一輩子都做你跟班啊。可惜我這一輩子,有點短了。”
劉大偉摘自《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