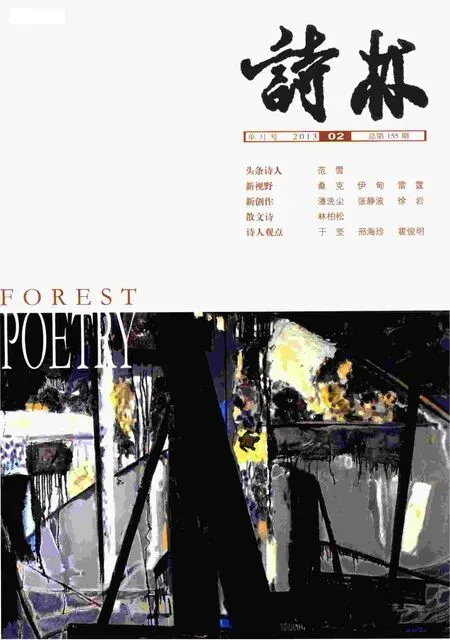寂靜是一劑五味子(組詩)
曹立光
山葡萄熟了
一只啄木鳥在樹洞深處,掏出
許多往事。母親仰臉端詳云霧繚繞的南山
被一面綠色的風引領上山,我坐在枯樹墩上
偷窺忙碌的螞蟻如何把一粒陽光從洞內搬出晾曬
溫暖、光滑、紅艷的五味子映著晴朗的天氣
手捧逐漸失去水分的夏天,母親用袖口擦了擦眼角
青春總是短暫的,有一天會破碎被采摘
甜蜜不是永恒,愛也不是唯一的行李,與溫暖
邁過螞蟻生存的疆場,我把過冬柴火
堆放在窗下,給母親攢足火苗
山葡萄熟了。母親說:你可以放心地走了
趁天暖,出山的路,風是干凈的,不絆腳
我再一次低頭走向南山,母親跟著我
她看到我又背起柴禾,她又悄悄地眼睛濕潤
寂靜是一劑五味子
我回來的時候,它們正離去
馬鹿攙扶著駝鹿,野豬肩膀上
扛著滿臉愁容的黃鼬
背包羅傘鉆出樹洞的黑熊一家子
在風又一次揚起沙塵的時候
跟隨東北虎、野豬、猞猁走出山口
轉眼 就不見身影
云還是十年前的模樣
只有天空 呈現中年病態的臃腫
水在上游被截流 那里正在建設度假村
只有羊 還在圍著一棵樹
啃食自己剩下的青春 都說命運是繩子
學會掙扎 還有機會瓦解生命的水分
站在院門外 我不敢去敲
小時候曾無數次被饑餓拍醒的門環
炊煙不是療傷藥 寂靜是一劑五味子
現在的我 像一句生銹的嘆息
在城市和山區之間 我徒有華麗外殼
竟難以
用胸膛焐熱一碗水 用雙手植綠一片陽光
一群梅花鹿穿過白樺林
一群梅花鹿穿過白樺林
像早春初綻的杜鵑花
風吹 單薄的身子搖搖
風再吹 脆弱的骨朵晃晃
陽光打濕它們眼里的青草
露珠用鳥鳴逐一清點它們的小名
途經的河水 用清澈
為前進的蹄音扯一面流水的旗幟
懷孕的母鹿和世界上所有的母親一樣
不放過每一聲鮮嫩的問候
更不會錯過聆聽來自腹中的呼喚
年輕的梅花鹿會像戀愛中的少男少女
懵懂著在河邊約會,在月光下親昵
逡巡的王鹿頭頂太陽的皇冠
用鹿角保衛愛情 捍衛自己疆土
站在瞭望塔上 我在望遠鏡中
看一群梅花鹿穿過白樺林
像一群思想者 慢慢把生活咀嚼
直至黃昏甩動的尾巴里
閃動著悲憫的光,和博愛的草汁
這些,大山心里都明白
在湯旺河畔 我曾無數次
看到野兔在猞猁嘴中
流出絕望的眼淚
又有多少個饑腸轆轆的夜晚
嗷嗷待哺的幼狼 用嘴去頂去拱
奶水稀少在虛脫中死去的母親
又有多少次草枯草榮 溫柔的綿羊
像收割機一樣把荒蕪留給板結的土地
而這些 大山心里都明白
又有多少次 我在獵人的槍上
看到奔跑的命運
誰攥緊自己的小命還不曾學會放手
在湯旺河畔 我曾無數次
看見祖父
躬身拉動歪把子鋸與一棵棵樹勢不兩立
沿著當年祖父上山的腳印 父親
提著嶄新的油鋸 像提著
自己锃亮的人生
消失在森林懂得尖叫的早晨
低下頭 我看見
我的下半身已被鋸齒掏空
我愛的 恨的 都被反復地推拉
回轉頭來 我年幼的兒子
在岸上提著陽光的手把鋸
面對一棵小樹揮舞自己的臂膀
他不知道那棵小樹 就是他
孱弱的 倔強的人生
狩獵者看著穿紅裙的火狐
一道月光從樹的指縫間跌落
濃霧像匹大馬在河邊靜靜飲水
閃著藍色鱗片的波浪 叼著凝固的雪花
在陌生的時光里蟄伏 并且閃爍
狩獵者看著穿紅裙的火狐走近
狩獵者看著穿紅裙的火狐靜默在岸邊
狩獵者看著穿紅裙的火狐瘦弱的肩膀在抽搐
狩獵者一整個晚上坐在樹下
此刻他聽不到空中流蕩著的微微水霧
此刻他聽不到樹葉上露珠凝結的輕響
這月光之夜呀 愛恨曾親昵地挨得那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