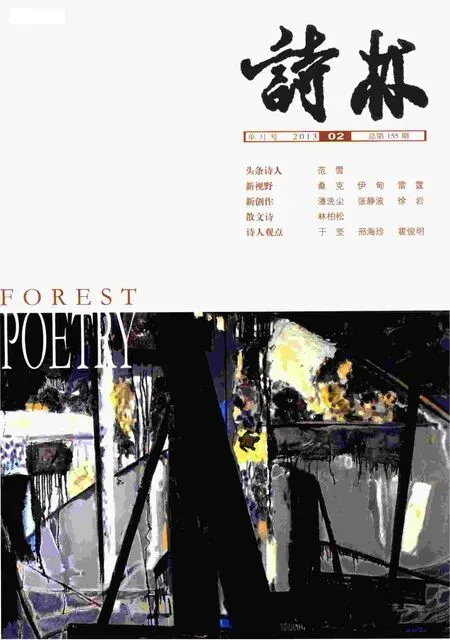陽光書(組詩)
傅 蘇
半月小夜曲
半只蘋果,悄悄擦傷了皮膚。接下來的十五天,會有十五個連續的阿嚏,把身體里的果糖崩出來。給藍色的托盤搪一層青瓷,給昏厥的男人輕輕的半個擁抱,給半圈以上的圓畫上虛設的線,再撲上秋天的粉末。化一個完美彩妝。一時間,留白都可能變成未來或新圖景。路上會遇到怎樣的一朵半開不開的花。陌生人為何總敲門不入。怎樣的一把鑰匙能打開半鎖不鎖。
死與凈化的問題
來。做一會兒小游戲。給我們的沙子洗澡,給泥土放電,給夢幻和迷霧選一組上乘的好材料。過濾細聲細氣的小耳語,擦除隱蔽的行蹤,動一動天上蓬松的云朵。我要鋸一截烏黑的椴木栽進泥土,建一座低矮的紀念碑。把頭骨折疊好放進樹洞,把心臟和一大串滴里嘟嚕的螺絲螺母都串成項鏈。邀請你們來,參加青草和苔蘚的派對。中途避過一會兒雨,在蘑菇傘下合影。
白嘴鴉飛來了
我看見了。一百年后,天很藍,綴著不帶修飾的白。空氣中有翅膀扇動著氣流,是的。關于冬天我總是在逃避,習慣性縮著脖子,習慣性把帽檐壓得太低,習慣性騎單車,摔倒在鏡子一樣清脆的冰面上。把有關寒冷和蕭瑟的話題,再往后拖延半拍。是的,半拍,是我從來都不曾預見到的。因而,我并不懷疑:曾有幾只白嘴鴉飛回來過。一些人說,春天來了。一些人不說,春天也來了。
肖申克的救贖
關門,誦經。熄燈,摳墻。摳落大片疤痕。刻一枚石子,刻平衡的時間。他穿梭于木頭箱子的兩端。身披影子的斑駁和光的白。晚間記賬,記響當當的黃金和白銀,記貪婪或暴虐。正反雙面的銀行家,在囹圄深陷的暗道中開采自由的鐵礦。雷電為之掩行,暴風雨為他刷洗身上的污垢。要用漫長來消磨,從第一道細微的劃痕開始,五百碼距離穿越國境,通往晴朗海岸。我要在黑玻巖孔縫下藏一封家書。然后磨砂,噴漆,拋光。翻新一艘廢舊的木船。
海角7號
起霧了。日光升起大霧。汽笛拉響,起錨了。船沿著既定航線全速移動。風吹過船舷,海有抹不干的淚水。七日,每天有霧。他在海面上畫出微痕,傷了眼睛和皮膚。海懷里抱著心臟,沉默的人躺在海里,不留下病根。頭發沾滿鹽巴,他假裝死去,假裝被遺忘,也假裝被歲月的真相袒露過。他還假裝在天空中種下了云朵。一場雨,搭起彩虹的長橋。收棉花的人,隔著海岸收信,收軟綿綿的觸角。她老了,所以她背向大海,她既不眼花也不耳聾。不遠的海里每天都有船只過往,每個甲板都站著流連之人。所以她背向大海,很忙的樣子。那信使來過,他繡了七朵藍色的浪花。
會旋轉的鏡子
大地上采集的河流倒退成向上的雨滴,天空中飄浮的閑云返回到幽藍的海洋。我還會站在那里,摘掉頭頂的禮帽,任由一個旋轉的上午或者下午,尾隨一位心靈手巧的銀匠,悄悄地把它展開。鏡子里微風吹不平褶皺,池塘里長出繾綣的水草。時光歸攏而來,遮掩了鐘擺走動的真相。大部分事件終將被人們淡漠,輕而易舉地像是一場誤會。那是空間和時間交織的布匹。而這世界,一直翻著漂亮的跟頭,一只魔方被打亂了秩序,而后傳來一排排巨浪拍岸的聲音。轟,轟。在旋轉的鏡子前,人們都心懸疑竇。試圖讓時間靜止或倒退的發條,像散開的麻花。為什么,一些人總是打著歷史的飽嗝,頭大而腳尖。
玻璃浴缸
水是干凈的,玻璃漸漸模糊掉。她凝固成兩三瓣。玻璃花包著玻璃紙。在氤氳的霧氣里。扒在玻璃上打著手勢的人,也許還梳著羊角辮,也許還沒盛開。那一刻,水滴是溫順的,溫順是透明的,透明是模糊的,模糊是時間綻放在記憶里的花灑,短暫地抱著夜色長裙。那一刻,全世界的水都停止了流動。包括江河湖海,水洼澤國,包括人類片刻的歡娛和悲傷,久發而未決的眼淚。像大臣給君王讓路。霧氣蒸騰而出,籠罩在雨林中。裸浴之人把時間碎片丟棄在平淡而模糊的光陰的杯中。斷開的掌紋,正打著各種奇怪的啞謎。
青銅騎士
他騎著青銅來接我。快上馬啊,騎士,騎士。棱角分明的一塊青銅,沖我大喊一聲。我還是有些愚鈍。有些幸福再也來不及適從。這些年來,竟還有這樣的人喊我。我還是有些愚鈍。或早已習慣慢慢被忘卻。只有帶我來的青銅,和我馬背上的兄弟連體。我還是有些愚鈍。馬蹄的蓮花沿返途的方向標記。一條山道,結滿了紅繩和青棗。馬只是站在青銅雕像的身后。噴響鼻,抖抖身上殷紅的汗血。于林中小客棧旁立穩。有人在替我啟樁。一壺燒酒還沒有燙好,囊中銀兩還未散盡。青銅,青銅,你稍事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