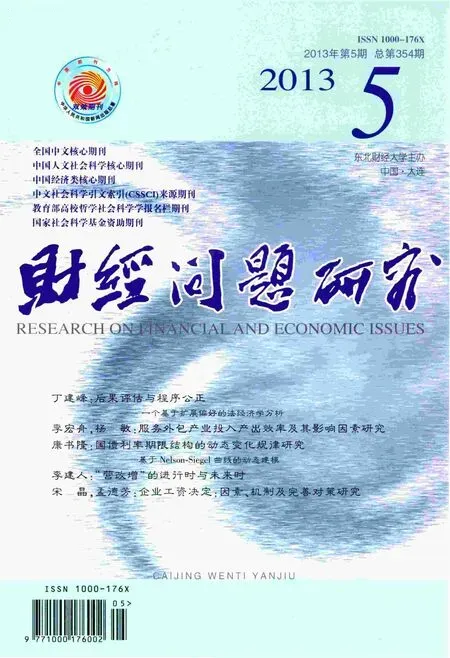就業向服務業轉移對經濟增長影響研究
曹亞軍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 統計學系,河南 鄭州 450002)
一、引 言
隨著服務業在各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不斷上升,與服務業就業結構、生產率等相關的問題一直是理論界關注的焦點。其中,最重要的研究結論被學術界概括為Baumol假說。Baumol[1]預測,在發達國家,服務業就業份額趨向增加,并且隨著就業份額向服務業轉移,人均實際GDP增長率將下降。他設想在經濟中有兩個部門:進步部門 (制造部門)和停滯部門 (服務部門)。他認為服務業生產率增加低于制造業,并假設制造業產出與服務業輸出的比率是不變的,盡管服務的價格相對于制造業持續上升,但是服務業需求持續增加,導致了服務就業份額的提高。生產率增加的差別和持續的需求比將帶來服務經濟的蓬勃發展。這一結論與發達國家就業持續轉向服務業這一經濟現象吻合。他指出,由于人均實際GDP增長是由制造業生產率的增長和服務業生產率的增長的加權平均,權重是相應的就業份額,那么低生產率增長的服務業的就業份額增加將帶來人均GDP實際增長率持續下降,并且最終收斂于服務業的生產增長率。因此,如果就業份額向服務業的轉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人均GDP實際增長率的下降也是不可避免的。
Baumol的研究激起學術界的廣泛探討。Pugno[2]認為按 Lucas[3]的說法,服務的消費增加了人力資本。比如保健消費和教育服務將會導致人力資本的積累。相應的,服務消費提高了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從而導致了制造業和服務業生產率的增加。這意味著生產率增長是外部效應的內生化。他將這種人力資本積累效應歸入Baumol的模型,結果表明如果這個效果較強,就業轉向服務業會增加人均GDP實際增長率,而不是減少。De Vincenti[4]得出與Pugno類似的結論。Oulton[5]顯示,如果服務作為制造業的中間投入,不作為最終的需求,就業轉向服務業會提高人均實際 GDP增長。相反,Sasaki[6]認為,如果服務既作為中間投入又作為最終需求,從長遠來看,就業轉向服務業會減少人均實際GDP增長。
上述理論研究注重來自于消費和服務產品所產生的外部效應以及生產率增長的向內發展。如果生產率增長是外生變量并且服務業的生產率增長低于制造業,那么就業轉向服務業一定降低了人均實際GDP增長。然而,如果生產率增長是內生決定的,那么就業轉向服務業就不一定減少人均實際GDP增長。比如,Kaldor[7]斷言,從長遠來看,在發達國家,人均GDP實際增長率幾乎是不變的,沒有下降趨勢。Kongsamut等[8]建立了三個部門 (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新古典增長模型,表明在廣義平衡增長路徑下,即使每個部門的就業份額是持續改變的,但是人均GDP實際增長率是恒定的。當他們推導結果時,使用了一個不同的偏好,這個偏好產生了一個內生結構變化。
綜上所述,對于就業轉向服務業與人均實際GDP增長之間的關系,有三種不同的看法,即增加、減少和不變。Hartwig[9]實證分析了1970—2005年期間18個經合組織 (OECD)國家,對于醫療保健和教育支出轉向服務是如何影響人均實際GDP增長率的,得出了支出的轉變降低人均實際GDP增長率,這與Baumol的陳述相一致。Nordhaus[10]對美國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類似結論。而Maroto-Sanchez和Cuadrado-Roura[11]對1980—2005年期間的 37 個 OECD 國家進行了實證調查,得出了勞動力轉向服務業對人均實際GDP增長率有積極作用。顧乃華和夏杰長[12]實證分析了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的崛起對鮑莫爾—富克斯假說形成的挑戰,并得出隨著人均GDP的提高,服務業比重與整體經濟增長速度之間的負相關關系會弱化的結論。
不同的實證研究結果截然不同,原因比較復雜。例如,服務業統計中存在的缺口和缺陷相對較多,我國目前就存在資料來源缺口和口徑不同、房地產業數據低估、保姆等服務未被計入以及服務價格指數缺失等問題。在各國經濟統計中,服務經濟遺漏都較多。從最近兩次經濟普查的結果看,我國常規統計的主要問題是低估了服務業的規模和比重。
本文提出Baumol服務悖論的擴展模型,同時吸取模型中有關技術進步的兩個想法:(1)服務消費促進人力資本積累;(2)制造業生產的“Learning-By-Doing”帶來技術進步,提出就業轉向服務和人均實際GDP增長之間有一種非線性關系,生產率增長在兩個領域都是外部效應的內生化,得出服務就業份額和人均實際GDP增長是一個u形關系。
二、模 型
1.基本內容
首先,我們設定企業行為。考慮兩部門經濟:制造業 (m)和服務業 (s),兩部門的生產只使用勞動投入。每個部門的生產函數如下:

Qi表示產量 (i=m,s);Ai表示勞動生產率,Li表示就業量。假設充分就業,Lm+Ls=L,這里L指勞動力人口。
假設勞動力在兩個部門之間自由流動,并且兩個部門的名義工資相等。工資表示為w。在利潤最大化和零利潤的條件下,得到下列方程:

價格等于單位勞動成本。接下來,我們設定消費者的行為。假設一個典型的消費者的最優化問題如下:

ci指人均消費 (ci=Ci/L);σ指兩種類型的消費之間的生產要素替代彈性,α指控制制造業消費支出權重的參數;γ指控制國內生產的確定的參數。當γ=0時,偏好相似,因此,制造業消費和服務業消費的收入彈性是1。當γ>0時,偏好不同,因此,制造業需求的收入彈性小于1,服務需求的收入彈性大于1。引入一種正數,對就業份額的動態影響不大。然而,它影響了動態輸出率。當得到就業轉向服務降低人均GDP增長的結論時,Baumol[1]假設了輸出比率保持不變。γ>0的假設符合Baumol的假設。
通過求解方程 (5)和(6)的最優化問題,得到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需求函數:


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市場出清條件如下:

將方程 (9)代入方程 (1)和(7),將方程 (10)代入方程 (2)和(8),我們得到每個部門的就業份額。

在這里,我們假定每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是由ri給定的外生變量,和Baumol[2]的理論一樣rm>rs:

以后,我們將變量x的增長率表示為gx,這里gx=(dx/dt)/x。然后,聯立方程 (3)和(4),我們發現服務的相對價格ps/pm無限增大(Baumol的成本疾病)。此外,通過檢查方程(11)和(12),得到以下命題:
命題1:假設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低于制造業。如果制造業消費和服務消費之間的替代彈性小于1,那么從長遠來看,服務業的就業份額Ls/L將會增加。
命題1和Baumol理論中的命題3是一樣的。Baumol假定產出比率是不變的。相反,我們使用一個CES和不同偏好。每個部門的輸出如下:

從這些方程,我們導出了輸出比率 (即消費比率):

命題2:假設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低于制造業,假設制造業消費和服務消費之間的替代彈性小于1,如果γ=0,從長遠來看,輸出比Qs/Qm將會下降。即使γ>0,但在適度的利率下,從長遠來看,輸出比率會下降。替代彈性越小,輸出比率的下降速度將會越適中。
命題2表述了輸出比率的長期趨勢。如前所述,Baumol假設產出比率不變,即Qm/Qs=常數。另一方面,我們指定效用函數,并假定σ<1和γ>0。這些假定與Baumol的假定大致相符。注意,我們的模型忽視了公共財政轉移的作用,這是Baumol所強調的。
2.人力資本積累和“Learning-By-Doing”
之前假定各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是外生變量。而這里,我們將兩部門的生產率增長內化。假設,每個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如下:

Tm表示制造業的特定生產率的大小,h表示人力資本的水平。因為人力資本積累到可以在兩個部門之間自由移動,人力資本h對兩個領域的生產率都有影響。從方程 (17)和(18),我們得出了生產函數Qm=Tm(hLm)和Qs=hLs。基于Pugno[2]的觀點,我們認為人力資本是通過服務業的消費積累的:

δ表示控制人力資本積累效率的參數。人力資本積累是積累的人力資本的線性函數,帶來可持續人均實際GDP增長。Pugno認為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下:第一種是服務消費無意中導致人力資本的積累,而另一種是有意消費服務來積累人力資本。在本文中,為了便于分析,我們采用了無意的人力資本積累。
我們假定制造業的特定生產率Tm是知識儲備Km的增函數:

Φ表示 Tm關于 Km的交叉彈性。根據Arrow[13]的觀點,我們假設知識儲備取決于迄今為止積累的生產經驗,界定知識儲備如下:

需要注意的是,生產經驗Km是由Lm/L測量的。即使當勞動力增長時,我們用制造業就業份額,而不是制造業就業水平,來判定動態模型有效。此外,我們用制造業就業,而不是制造業的產量,有以下兩個原因:首先,在我們的模型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然后,產量的增加與就業的增加有一對一的關系。因此,為了簡單起見,我們用制造業的就業而不是產出來衡量生產經驗。其次,依據我們的規定,每個部門的生產率增長形成了一個只取決于就業份額的函數。由此,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將模型與Pugno和De Vincent的模型相比,在我們的模型中,生產率增長是只取決于就業份額的一個函數。
從方程 (20)和(21)得出流量Tm導致:

將方程 (17)和(18)相對于時間取微分,代入方程 (19)和(22)的合成表達式,推導出各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如下:

從這些方程中,我們總是得出gAm≥gAs。

圖1 gAi和Ls/L的關系,當Φ>δ
在 Pugno[2]和De Vincenti[4]的理論中,兩部門的生產率增長率是服務就業份額的增函數。相反,在我們的模型中,制造業生產率增長要么增加要么減少服務就業份額。然而,這并不影響我們的主要結論。重要的是,生產率增長差數gAm-gAs減少了就業份額向服務的轉變。這一發現與Bosworth和Triplett[14]所顯示的實證數據相一致,他們計算了美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他們指出,兩個行業的生產率增長之間的差距隨著時間遞減。
3.人均實際GDP增長
現在,我們獲得了人均實際GDP增長率。考慮經濟實質增長,我們必須消除價格變化的影響。人均實際GDP增長率g可以定義如下:

這意味著g是每一個部門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加權平均,權重是相應的就業份額。因此,我們得到與Baumol的假設rm>rs相一致的結果。
服務業生產率增長是服務業就業份額的一個增函數。現在我們轉向制造業的生產率增長。如果Φ>δ,gAm是Ls/L的減函數。相反,如果Φ<δ,gAm是Ls/L的增函數。δ表示人力資本積累對服務消費的效率,Φ表示制造業的特定生產率對制造業生產的交叉彈性。因此,哪個影響占主導地位決定了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是否成為服務就業份額的一個減函數或增函數。圖1和圖2表明了gAi和Ls/L之間的關系。

圖2 gAi和Ls/L的關系,當Φ《δ

因此,g是關于服務就業份額的二次函數。檢驗方程 (27),我們得出以下命題:
命題3:如果2Φ<δ,那么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也跟著就業轉向服務而增加。如果2Φ>δ,那么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下降到服務就業份額(Ls/L)*=(2Φ-δ)/2Φ,從那時候開始,它隨著就業轉向服務而增加,最終收斂于g=δ。
證明:由方程 (27)可得g關于Ls/L的偏導數如下:

命題3表述了服務就業份額與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之間存在一個u形關系。假設服務就業份額的初值充分小。那么,隨著服務就業份額的增加,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下降。然而,當服務就業份額超過了由 (Ls/L)*給定的界限值,人均實際GDP增長率增加,最終收斂于g=δ。Ls/L和g之間的關系是否是一個u形曲線,取決于由于服務消費引起的人力資本積累效果的相對大小。如果這個效果相對較強,服務就業份額的轉變將持續使人均實際GDP增長率單調增加。另一方面,如果效果相對較弱,我們得到一個u型關系。圖3—圖5顯示了這兩種情況下服務業就業份額與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之間的關系。

圖3 g和Ls/L的關系,當2Φ<δ

圖4 g和Ls/L的關系,當2Φ<δ且Φ<δ

圖5 g和Ls/L的關系,當Φ>δ
在本文模型中,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總是大于服務業,這與Baumol的理論相一致。然而,存在一個就業份額向服務業的轉移提高人均實際GDP增長的階段。
正如前面解釋的那樣,Φ>δ或者Φ<δ決定了gAm是否為Ls/L的增函數或減函數。如果Φ>δ,制造業生產率的增長是服務就業份額的減函數。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求2Φ>δ,因此我們可以得到命題3中Ls/L與g的一個u形關系 (如圖5所示)。如果Φ<δ,制造業生產率的增長是服務就業份額的增函數。即便如此,我們有2Φ>δ,它產生了Ls/L和g的u形關系(如圖4所示),如果δ→0,g將成為Ls/L的減函數,這與Baumol的就業份額轉向服務的轉變降低了人均實際GDP增長的結果都是相同的。
重寫方程 (25),我們得到以下關系:

其他條件不變時,只要gAm>gAs,Ls/L的增長對人均實際GDP增長具有反作用 (見方程(28))。換句話說,Lm/L的下降對人均實際GDP增長具有反作用,因為由方程 (22)可得,制造業就業份額的下降會減少Tm的增長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們的模型中,生產率增長微分gAm-gAs是服務就業份額的減函數。因此,隨著就業份額向服務業轉變,Ls/L的增加對人均實際GDP增長率的反作用不斷減小。如前所述,右邊第一項gAm可以是服務就業份額的增函數或減函數。然而,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總能得到gAm>0。因此,當服務就業份額很小時,右邊第二項的反作用相對較大,因此就業份額向服務業的轉變減少了人均實際GDP的增長。另一方面,當服務就業份額較大時,右邊第一項的正作用相對較大,因此,就業份額向服務業的轉變增加了人均實際GDP的增長。使用相同的推理,我們可以解釋為什么從一個向下階段到一個向上階段的轉變速度在Φ<δ時比Φ>δ時快 (如圖4和圖5所示)。
三、充分的動態和數值例子
從上述分析,我們得到3個命題。然而,分析是不完整的。當推導命題1和2時,我們假設兩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是外生變量。當推導命題3時,我們假設服務就業份額隨時間增大。在我們的模型中,生產率的增長和就業份額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我們必須同時分析就業份額和生產率增長的動態。其動態概括如下:


將方程 (32)代入方程 (30)和(31),得到一個關于As(t)和Am(t)的兩個微分方程組成的體系。
因為上述系統是非線性的并且有些復雜,我們用數值模擬來分析其動態。通過檢查Am和As的動態可以知道其他內生變量的作用。在這里,只考慮σ<1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服務就業份額隨時間增大。在表1中,我們設置了參數。情形1,Φ>δ;情形2,Φ<δ且2Φ>δ。此外,我們設置了Am和As的初值是1。

圖6 服務就業份額動態化 (σ<1,Φ>δ)

圖7 實際人均GDP增長動態化 (σ<1,Φ>δ)

圖8 服務就業份額動態化 (σ<1,2Φ>δ,Φ≤δ)

圖9 實際人均GDP增長動態化 (σ<1,2Φ>δ,Φ≤δ)

圖10 產出比動態化 (σ<1,Φ>δ)

表1 參數列表
圖6—圖11表明了數值模擬的結果。當替代彈性每間隔0.10從0.10到0.90變化時,這些數字賦予每個變量時間路徑。

圖11 產出比動態化 (σ<1,2Φ>δ,Φ≤δ)
在情形1和2下,服務就業份額隨時間增大,人均實際GDP增長率先減小后增加。然而,圖7和圖9之間有明顯的區別。圖9中從一個向下階段到上升階段的轉變時間比圖7中短。這是由于界限值 (Ls/L)*在情形1和2下是不同的,在情形1中 (Ls/L)*=0.70,在情形2中 (Ls/L)*=0.38,這用圖6和圖8中的水平實線表示。從圖6和圖8可以看出,服務就業份額的時間路徑并無很大差別。然而,因為 (Ls/L)*在情形2中比在情形1中小,所以人均實際GDP增長率從一個向下階段到向上階段的轉變速度在情形2中比在情形1中快。
替代彈性的大小嚴重影響了輸出比率Qs/Qm的時間路徑。正如命題2提出的那樣,從長遠來看,輸出比率下降。然而,下降的速度關鍵取決于替代彈性的大小。正如圖10和圖11所示,在1和2這兩種情況下,替代彈性越小,輸出比率的下降速度越適中。
四、結 論
分析表明,就業份額向服務業的轉移減少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但在某一時點后,它逐漸提高人均實際GDP增長率。這個結論既與Baumol[1]的就業轉向服務業降低了人均實際GDP增長的觀點相一致,又與Pugno[2]的就業轉向服務業提高人均實際GDP增長率的觀點相一致。隨著服務就業份額的增加,制造業的“Learning-By-Doing”效果在下降。由于服務消費,人力資本積累效應在增加。這兩個對立的影響相互作用使服務就業份額和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之間產生u形關系。因此,服務業和制造業兩個部門的生產率增長是內在決定的。就業份額向服務業的轉移起初降低了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但在某一時間點,這種轉變開始提高人均實際GDP增長率。因此,從就業轉向服務業使經濟蕭條階段到促進經濟增長階段的轉變是一個內生的階段。如果服務就業份額不斷增長,那么從長遠來看,人均實際GDP增長收斂于服務生產率的增長。因此,為了促進經濟增長,我們必須提高服務生產率,這是出現在Baumol極富成效的貢獻之后所有模型共同傳達的思想。
[1]Baumol,W.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The Anatom of Urban Crisi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3):415-426.
[2]Pugno,M.The Service Paradox and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6,17(1):99-115.
[3]Lucas, R.E. On The MechanicsofEconomic Development [J].Journal of MonetaryEconomics 1988,22(1):3-42.
[4]De Vincenti, C.Baumol's Disease, Production Externalities and Pro ductivity Effects of Intersectoral Transfers[J].Metroeconomica,2007,58(3).
[5]Oulton,N.Must the Growth Rate Decline?Baumol’s Unbalanced Growth Revisited [J].Oxford Economic Papers,2001,53(4):605-627.
[6]Sasaki,H.The Rise of Service Employment and Its Impacton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7,18(4):438-459.
[7]Kaldor,N.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A].Lutz,F.A.,Hague,D.C.The Theory of Capital[C].London:Macmillan,1961.
[8]Kongsamut,P.,Rebelo,S.,Xie,D.Beyond Balanced Growth[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1,68(4):869-882.
[9]Hartwig,J.Testing the Growth Effects of Structural Change[DB/OL].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doi:10.1016/j.strueco.2011-09-01.
[10]Nordhaus, W.D.Baumol's Diseases: A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s[J].The B.E.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008,8(1).
[11]Maroto-Sanchez,A.,Cuadrado-Roura,J.R.Is Growth ofServicesan Obstacle to Productivity Growth?A Comparative Analysis[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9,20(4).
[12]顧乃華,夏杰長.生產性服務業崛起背景下鮑莫爾-富克斯假說的再檢驗——基于中國236個樣本城市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財貿研究,2010,(6):14-22.
[13]Arrow,K.J.The Economics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2,29(3):155-173.
[14]Bosworth,B.P.,Triplett,J.E.The Early 21st Century U.S.Productivity Expansion Is still in Services[J].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Monitor,2007,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