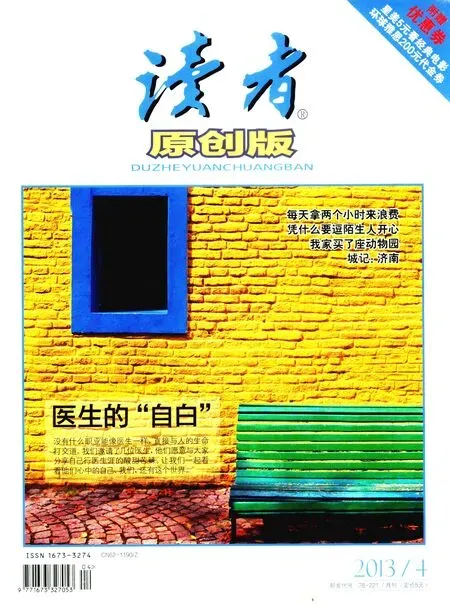戴口罩的春天
文 _ 紐西
戴口罩的春天
文 _ 紐西

10年前的那個春天,我們都戴起了口罩。那時,我們要對抗的不是風沙和霧霾,而是一場嚴酷的疫情。
那個春天,我和宿舍的兄弟們坐在去往廣州的火車上。那本是出游的好時節,但擠在硬座車廂的我們各懷心事。作為第一批擴招的大學生,我們背負著沉重的就業壓力,南下只是希望謀得一份工作。
27個小時之后,我們抵達廣州。隨著人流走出火車站,來不及感受羊城的春光和綠意,率先進入視線的是滿大街捂著口罩的人。其時,我們對于“非典”有所耳聞,卻不曉得它的厲害,只當是種較重的感冒。有人覺得南方人過于矯情,搞怪地將車票貼在鼻尖上,看著那薄薄的紙片隨鼻息翕動,大家一陣哄笑。
幾天后,我們無功而返。回到學校不久,“非典”疫情升級,感染病例大幅增加,恐慌情緒在人群中迅速蔓延。我們被關在學校里,想起那次旅行,后怕不已。
每一天,新聞中都會播報最新增加的“非典”病例,相關機構在四處尋找曾經乘坐各種交通工具的疑似病例和易感人群。我們喝著學校熬制的中藥,求得稍許心理安慰。
偶爾上網,看到一位大學生發的帖子:他的父母所在的醫院被指定為“非典”病人接收醫院,所有的醫護人員都將參與救治。這個消息無異于晴天霹靂,他下意識地勸說父母辭職,父母只是笑笑,說他太孩子氣。由于他們都在醫院工作,按照規定,可以只去一個人。他們幾乎同時說:“我去!”父親說,自己是一家之主,有責任承擔這個危險;母親說,如果只有一個人去,那一定是她去。“他們就在飯桌上這么平靜地爭著,而我的心卻像被刺破了一樣。我不相信我的家有一天會面臨這種生死抉擇。”
我猛然意識到,我的父母也是醫生,雖然那座城市還沒有報告“非典”病例,但他們也已經做好了準備,并可能面對同樣的危險。那一刻,我心中有什么轟然坍塌。
那個春天,多位醫護人員因抗擊“非典”殉職;那個春天,醫護人員被稱為“最可愛的人”。事實上,我從不認為某種職業具有天然的優越性,相比其他職業更接近崇高與神圣。我見識過庸醫,也曾被老師誤導。在那個非常時期,對于很多醫護人員而言,堅守崗位是最起碼的職業道德。正如那位大學生的父親所言,從業30多年,絕不能愧對“醫生”這個稱號。
這位醫生一定無法接受,10年之后,人們再次提起這個職業,首先想到的不是救死扶傷,而是紅包、回扣、醫療糾紛……新聞報道中,醫生和患者似乎已經勢如水火,即便我們平常所見未必如此。
一些媒體對負面新聞的刻意放大和渲染,讓很多患者在步入醫院之前就不自覺地提高了“警惕”。信任缺失,導致醫生的診斷屢遭質疑,為了免責,醫院增加檢查項目和簽字環節,這在無形中增加了診療成本,引起患者不滿。
抗擊“非典”的領軍人物鐘南山院士在接受采訪時曾說,10年來,自己最大的遺憾就是社會、公眾、政府及媒體對醫務人員的偏見。很多問題本是體制造成的,最終卻將醫生和患者推向了對立面。
10年,就像一個輪回。這個春天,當霧霾散去,風沙平息,我們終于可以摘下口罩,甜蜜地親吻,暢快地呼吸。只是,醫生依舊身處困境。類似的困境也同樣困擾著我們普通人,沒有人是旁觀者。
在做本期“特別報道”時,我們邀請了幾位醫生講述他們在執業過程中的見聞和體悟。這本是一份普通的職業,講求醫者仁心。醫生可以卸下光環,但不應背負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