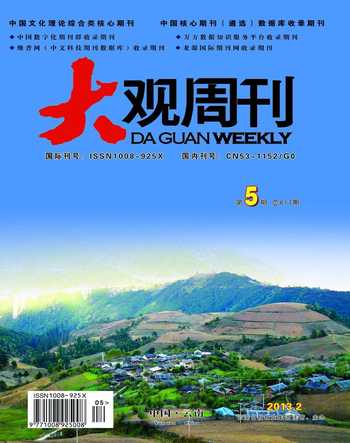李提摩太的教育傳教理念及其實踐
王京強
摘要:李提摩太通過介紹西方文化來影響和教育中國知識分子,在必要時,采用與中國的文化和宗教相妥協的傳教方法,在山西大學堂的創建過程中得到了貫徹和實踐。山西大學堂沒有被建成一所教會大學,但李提摩太興辦新式學堂讓晉省人接受近代教育的構想與實踐,對于山西擺脫保守走向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李提摩太 教育 傳教 山西大學堂
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是近代來華著名傳教士之一,在華長達45年之久,對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著重探討李提摩太在傳教過程中是如何運用教育傳教方式與近代西方教育理念指導山西大學堂創建的。
一
李提摩太于1870年到山東煙臺、青州傳播基督教。1876年至1879年間,因華北大旱,他攜帶12000兩賑災銀在1877年從山東來到山西,先后在臨汾、聞喜、洪洞、太原等地發放賑款,救濟災民,時人稱之為“洋大人”。賑災期間他在山西所到之處積極傳教、介紹西方科技知識,還曾向時任山西巡撫的曾國筌、張之洞提出修鐵路、開礦產等治晉方略,1886年離開山西。1890年7月,應李鴻章之聘,他前往在天津任《時報》臨時主筆,次年10月,到上海接替韋廉臣為廣學會的督辦(后改稱總干事)。在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期間,他積極活動于上層人士之間,多次建議將中國置于英國“保護”之下,聘請外國人參加政府,企圖影響中國政局的發展,結果均未能如愿。他主持廣學會達25年之久,出版《萬國公報》等十幾種報刊,創刊40年間共出版2000種書籍和小冊子,成為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1900年,他接受山西巡撫岑春煊邀請,重返山西解決教案問題,并參與創辦山西大學堂,被聘為山西大學堂西學書齋總理,同時還主持上海山西大學堂譯書院,往來于上海與太原之間。清政府賜他頭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并誥封三代。1916年因病回國,1919年在倫敦逝世。
與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的傳教方式類似,李提摩太也側重于以介紹西方文化來影響和教育中國知識分子,在必要時,采取與中國文化和宗教相妥協的方式。但這并非是李提摩太有意模仿利瑪竇,而是其在中國傳教、賑災游歷過程中逐漸摸索形成的。在山東萊陽,李提摩太曾會見過兩位佛教僧侶和一位學者,通過交流討論,他覺得通過講授自然哲學基本事實就可以引進比在中國占統治地位要好得多的宇宙知識。“這次出訪及其相關的決定,標志著李提摩太事業的另一階段。他已經看到,如果中國人享有更好的傳授知識的條件,那對他們就是一大恩惠,他現在邁出了導致建立山西大學的第一步。”[1]39可以說這是李提摩太在傳教過程中廣泛接觸各界人士,不斷調整自己的策略以尋求有效途徑的嘗試。此后,在山西賑災過程中,李提摩太認為“如果賑災是耶教的任務,教育人們避免災荒同樣是而且是耶教更偉大的使命。如果把幾千人從這場可怕的災難中解救出來是好事的話,使數以百萬計的人避免遭受這般驚慌就更加意義非凡。”[1]85 《李提摩太傳》的作者蘇慧廉為此這樣評價道:“經過這場浩劫,他把‘教育這個詞鐫刻在自己的靈魂里。這個詞成了他生命的基調”,決定其將來的傳教工作主要應該走教育的路線,“與受教育的階層廣泛接觸,因為他們接受事物快,而且是最能影響他人的階層。”[1]86
李提摩太不僅僅停留于思考或自己的實踐,而且還建議當時在華傳教團體應該聯合起來在中國18個省會,逐漸建立起高等學堂,希望能從此影響大清帝國的要員接受基督教,進而影響他們自己的同胞改變信仰。對于上層傳教路線,他直言不諱的指出“我就是緊追上流人士不舍”[1]122。《英國周刊》對其與眾不同的傳教錄像做了相關報道:“如果你抓住了上流人士,也就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中國相對來說,是由少數人統治著——官員們和受過教育的階層——人數約為10萬。我們今天最大的需要,是派出稱職的人員去引導,教育,這些正在思考的人士。當我們贏得了他們對基督的信任時,我們就贏得了全體民眾”[1] 122。由此可以看出,李提摩太用教育籠絡上層人士的路線,有意無意地符合了英國政府欲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思路,這也成為人們認為李提摩太是為英國侵略中國服務的主要依據。
從另一層面來看,李提摩太洞察中國社會的特點是相當透徹的。當時中國社會正是一個典型的士農工商的階層社會,士高居于上,入者高居廟堂,成為輔佐君王的官僚階層,退則為鄉里士紳,領導縣政權以下的地方社會。同時,他們擔負著對地方教化保護的職責,如果能將這些人或其子女教化皈依基督,或至少學習近代知識文化,將會大有利于傳教事業的展開。李提摩太的教育傳教思路是為了與中國這一特色的社會階層情況相契合,對這些人的籠絡將影響整個社會的思想傾向。李提摩太對教育傳教法進行著不斷努力地思考、探索和完善。
二
李提摩太的教育傳教法是從促成山西大學堂建立開始的。1900年,在全國義和團反洋教日趨高漲的形勢下,山西發生了殺害傳教士的教案,清政府派岑春煊接替毓賢任山西巡撫以圖速結教案。面對聯軍兵壓娘子關而山西又沒有滯留的傳教士能夠幫助解決教案善后的情況,1901年4月,岑春煊致電在上海的李提摩太邀“請閣下來晉任委員之職,負責解決晉省教案與商務問題”[2]1,邀請其赴晉協助解決,這為曾在山西有過慈善和傳教經驗的李提摩太提供了教育傳教的實踐機會。李提摩太收到電文后很快接受了邀請,并向李鴻章遞交了《上李傅相辦理山西教案章程》,提出解決山西教案的七條意見。其中除了懲罰和賠款要求外,第三條指出“共罰銀五十萬兩,每年交出銀五萬兩,以十年為止。但此罰款不歸西人亦不歸教民,專為開導晉人知識,設立學堂,教導有用之學,使官紳庶子學習不再受迷惑。選中西有學問者各一人,總管其事。”[2]12其意在將“庚子賠款”用于學堂建設上。這個章程既可緩解西方列強給清政府施加的壓力,也不致于使財源外流,還可推動地方教育的發展。綜合評估利弊,李鴻章代表清政府同意按李提摩太的提議解決山西教案。李提摩太的教育傳教法因解決教案方案的批準而邁出了關鍵性的第一步,開始著手籌建大學堂。
在依據章程解決教案之后,雙方就開辦大學堂事宜展開談判。岑春煊派洋務局候補知縣周之驤赴滬與李提摩太商談。周提出四個條件:一、晉省所出五十萬兩銀不稱罰款。二、西教士在校內不準宣傳耶教。三、學堂不得與教會發生關系。四、西教士不得干預學堂行政。很明顯,第一條只是措辭問題,容易解決;第二三條事關學堂性質,第四條關學堂主權歸屬。關于后三條較實質性的問題分岐使談判一度陷入僵局。李提摩太對此指出:“關于宗教自由的問題,中國在幾個對外條約中都已表示同意。如果岑巡撫現在獲得特別授權來更改并廢除這些條約的話,那我們就可以討論禁止講授耶教教義這一規定了。”[1]215李提摩太的反駁很有力,顯然作為已經形成的條約內容,一個地方巡撫當然無權更改了,中方只得不了了之。但是雙方均不愿商談破裂。在做出一定讓步之后,周之驤與李提摩太在1901年11月簽署了《晉省開辦中西大學堂合同八條》。該合同對中西大學堂諸如辦學宗旨、款項來源、歸屬期限及一些具體問題進行了明確規定。
然而,就在周李談判之時,清政府推行新政之一部——興學,“除京師大學堂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所有書院與省城均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州縣改設小學堂,并多設蒙養學堂”[3]P4719。山西省根據清政府興學詔書,將省城原有令德堂與晉陽書院合并為山西大學堂。岑春煊積極籌備并制定出《大學堂規則》,規定大學堂分中西學八科,即德行、言語、政治、文學、法科、文科、格致科、醫科,其中第四條規定:“各府廳州縣學堂一時未能多得西師,無由廣傳西學,況堂內學生中學根底尚淺,亦未便驟令馳域外之觀,只可先行嚴科中學,而以譯介西書作為余課”[2]3。很明顯在當時的條件下,新式學堂也只是貫行“中體西用”的實踐所,并非以傳授近代知識為目的。1902年2月,岑春煊《設立晉省大學堂謹擬暫行試辦章程》上奏朝廷提出籌經費、建學舍、選生徒、定課程、議選舉、習禮法六條意見。5月8日,光緒帝朱批云“選舉一條著管學大臣議奏,余著擬辦理”[4]7。不難想象,籌建山西大學堂很大程度上是山西官紳以既成事實來抵制正在談判中的中西大學堂,存在著地方士紳與西方傳教勢力在大學堂問題上的博奕。
當李提摩太按上年簽訂的《晉省開辦中西大學堂合同八條》,于1902年5月帶領新聘教習敦崇禮、新長富與華人教習以及儀器設備抵達太原后,發現晉省已成立了山西大學堂并開學上課。在這種情況下李提摩太認為若再辦一所大學堂會增加晉省人的抵觸,且又增加經費,即向巡撫岑春煊提議將中西大學堂與已成立的大學堂合并辦理,名稱仍為山西大學堂,但分為兩部,一部即已成立的大學堂教授中學由華人主持;一部即將要開學的中西大學堂,教授西學由西人主持。這個提議首先得到冀寧道沈敦和的贊同,并為此起名中齋與西齋。鑒于當時意見不統一,岑春煊以歸并與否詢問當時大學堂已招學生108人,結果68人贊成,13人反對,其余棄權[2]8。岑春煊在與地方官員士紳反復商討后,最終意見達成一致,同意將大學堂與中西大學堂合并辦理。隨之,《山西大學堂創辦西齋合同二十三條》簽署,同時原《晉省開辦中西大學堂合同八條》即行作廢。“二十三條”中值得注意的有第六條,西齋作為山西大學堂一專齋而具有“中國國家學堂”[2]12的性質,而減弱了其賠款意味。正是在這種“一校兩制”的模式下山西大學堂初步開始運行。
1903年《奏定學堂章程》頒布后,由于山西大學堂具有與西方傳教士簽訂合同的特殊背景,也由于山西大學堂的科目設置基本符合了《章程》中關于大學堂設置標準的要求,所以,山西大學堂作為壬寅辦學的唯一幸存者保留下來。1904年,山西大學堂新校舍建成,中西兩齋師生整體遷入,新任學臺(提學使)寶熙借此機會,對學堂進行了重大改革,特別是根據新學制的規定,對中齋的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作了較大的調整,增設了英文、日文、法文、俄文、代數、幾何、物理、化學、博物、歷史、地理、國文、圖畫、音樂和體操等許多新課程,舊課程除保留經學外,其他科目一律取消,并聘請了新教習分別承擔新課程的教學,從而,促進中西兩齋的融合,使兩齋的教學科目和教學方法漸趨一致。至此,一體化的山西大學堂基本形成,并步入了良性發展的道路。
山西大學堂在中西兩齋良性競爭融合下運營數年之后,根據二十三條合同之第三條“西學專齋經費除光緒二十七年付過銀十萬兩外,光緒二十八年再付銀十萬兩為開辦經費,下余三十萬兩于光緒二十九年起每年付銀五萬兩至光緒三十四年一律付清”[2]12的規定,李提摩太于1910年決定提前辭去總理職務,并將西齋管理權提前移交山西當局。因為他“深信近代教育已在全省深深扎根。”[2]12巡撫丁寶銓、咨議局議長梁善濟接受其辭呈,西齋正式收回,歸省辦理。傳教士影響一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才逐漸退出。
另一方面,近代中國開辦新式學校苦于缺乏教材,“二十三條合同”簽訂后.西學專齋首任總理李提摩太特從西齋每年經費中撥出10000兩白銀,在上海設立了山西大學堂譯書院以解決教材問題。山西大學堂譯書院初設于上海西華德路,后遷至江西路福慧里210號。最初譯書院由李曼教授負責,后又聘英人竇樂安(John Dorroch)博士主持,其中英、日譯員及校閱者前后l0余人。山西大學譯書院自1902年設立至1908年因經費緊張停辦,6年時間共翻譯印行多種教科書,根據行龍先生的考證,譯書院譯書共23種25冊[6](也許尚有遺漏者),其中如《邁爾通史》為1900年美國新版書,1902年即譯出發行。《天文圖志》1903年英文版出版,1906年即出中文譯本。譯書院的效率可見一斑。譯書院的一些譯本,民國以后,甚至到2O世紀40年代仍為同類圖書中的佼佼者。山西大學堂譯書院所譯各類教科書,為當時許多大、中學堂所采用,對解決學堂燃眉之急的缺乏教科書問題確實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也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積極的貢獻。1902年山西大學新共和學會出版的《新共和》刊物,其“發刊宣言中稱譯書院‘頗有貢獻于當時的社會國家確非虛語往事如煙” [6]。這些譯著便利了當時學術文化交流,傾注了李提摩太的大量心血。
三
作為一名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在華所為無疑是有著政治目的的,其用西方近代文化知識沖擊封建頑固思想,使培養的學生對外國在華勢力產生認同、助力英帝侵華,但從客觀上看,李提摩太為中國教育事業做出的貢獻不可小覷。“西齋取得的成就,當時在中國,是無可匹敵的。招收舉人、秀才為學子,從ABCD學起,從加減乘除學起,經過七年學習畢業之后,就掌握了他們各自所學的學科,這確實是一個大膽的辦學步驟。在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其他大學做得到。”[1]224
不僅如此,李提摩太在山西興辦教育客觀上推動了山西逐漸擺脫封閉走向近代,當時的《華北先驅報》有文:“從教育方面而言,山西是中國最為先進的省份……在山西50%的鄉村都有小學,所有男孩和決大多數女孩都有機會接受近代教育”[1]225。同一刊物上另一文章寫到“全省各地,在官府衙門和學校里,都有山西大學堂的畢業生。山西省的警務督辦和許多在任的地方官員都是大學堂的畢業生,這些人全力支持巡撫進行改革。無庸諱言,沒有他們的精神支持,巡撫將很難推行他的計劃。因此,將近二十年后,李提摩太博士的遠見卓識正在得到實踐的印證。”[1]225
參考文獻:
[1]蘇慧廉.李提摩太傳[M].香港:世華天地出版社,2002.
[2]山西大學百年紀事委員會.山西大學百年紀事[M].北京:中華書局.2002.
[3]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z]卷169 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4]清實錄 德宗實錄[Z] 卷498.
[5]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C](下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6]行龍.山西大學校史三題[N].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2).
[7]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序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