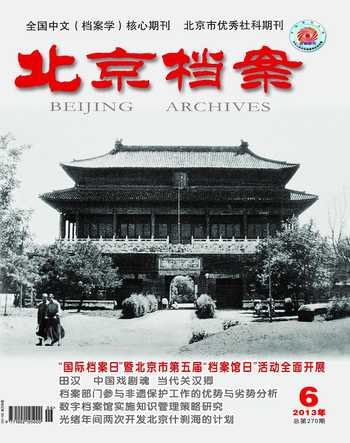西河鼓王趙玉峰
馬岐
凡是流派,都不是自封的。西河大鼓演員之多眾所周知,但西河大鼓的根基是說大書,一人一個風格,很難求其統一,所以始終沒有流派的分別。直到1961年5月,中國曲藝研究所在河北省成立曲藝工作室,召集京、津、河北、東北等地的西河大鼓同行,一起商討,才推出了西河大鼓“四大流派”:即朱派(朱大官派,當時由傳承人王書洋代表)、馬派(馬連登、馬增芬派)、趙派(趙玉峰派)和李派(李德金派)。而當時在場的西河名家頗多,如北京的王艷芬、劉田利、蔡連貴,天津的田蔭亭、艷桂榮、陳鳳云等等,百十來位都是西河界的大將、專家,都是從小學藝,說唱為生,具有相當叫座能力的、頗有藝術造詣的大家,但都沒被立成派。由此看來,一旦成派,也就是說,要成為“師”一級的人物,絕非輕而易舉。不但藝術風格要成熟,而且要有自己的代表作品,還要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有系統的傳承,得到行內外的公認,才能叫人心服口服,即藝術必須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本文所說的趙派,即趙玉峰先生創立的這一派藝術,在當時的西河界,就是百里挑一。那時,京、津、河北、東北一代唱西河大鼓的人恐怕數以百計都記不過來,但所有業界人士,不論男女老少,提起趙玉峰先生,全都高挑大指,稱贊其為“西河鼓王”。
我有幸見過趙老先生一面。他晚年落戶在遼寧鞍山。上世紀60年代,我曾奉父命到東北去看望這位老人。其實當時我并不了解他的藝術和為人,只是借演出的空暇,替父親馬連登給老先生帶一點兒煙之類的小禮品,還有一張趙先生要的我三姐馬增蕙的照片。據說老先生特別疼愛三姐,非要看看“三丫頭”大了長成什么樣了(當時我三姐已經20多歲了)。那次是楊田榮師叔(東北的評書大家)帶我到的趙老先生府上。記得老先生大高個兒,很黑,但是神采奕奕,精神矍鑠,見面就跟我說:“你爸爸都管我叫爺爺輩兒啊!你也別搗輩分了,就叫個師爺就成了。”因為趙先生輩分相當高,叫師爺還差著輩兒呢,應該叫師太爺。我見過了這位師太爺和他的老伴師太奶奶,重重地給二老行了禮,跟怹談了兩個多小時的話。他說,他到東北就落在了鞍山,曲藝團聘他當顧問,他教了很多小青年(其中就有現在的評書大家劉蘭芳以及王印權等)。他還說,組織上對他很照顧,吃住都好,也就不愿意再回京津了。我問他我們馬家的西河是怎么成長起來的,他反問我道:“你學西河了嗎?”我回答我從小就不喜歡西河大鼓,我喜歡京韻、梅花、單弦之類的。老先生笑了,又問:“那說書呢?喜歡說書嗎?”我趕緊回答我特別喜歡。他說:“那好,有機會我教給你說書,一個鼓書演員,說功和唱功都要好才對。”他給我講了一個我二姐馬增芬的小故事,這個故事我還真
不知道,因為故事發生時,我還沒出生呢。有一年趙先生在天津謙德莊上地,時不常地總有個小姑娘來聽書,還專門愛聽唱。有一天開書之前趙先生問:“你一個八九歲的小姑娘,懂得怎么聽嗎?”小姑娘回答:“我還能唱呢!”趙先生高興極了,說:“好啊,那今天開場你先唱一段,唱好了,打下錢來都歸你!”說完了,趙先生從弦師手里接過弦子來,親自操琴,這個小姑娘唱了一段《打黃狼》,贏得了全場喝彩,趙先生也頗為吃驚,問道:“你是內行的孩子吧?”小女孩這才說我叫馬增芬,我爸爸是馬連登,我母親叫吳書善。趙先生笑了,說:“好啊,原來你是我重孫女兒啊!我給你提提輩分,我收你做徒弟吧?”二姐趴地上就要磕頭,當時在場的觀眾都笑了(因為當時是不許這么隔著好幾輩兒收徒弟的)。趙先生說:“你真磕啊?這么著吧,每天你來我這兒一趟,我教你唱,你先別跟你爸爸說,等唱好了,再唱給你爸爸聽。”就這樣,二姐每天跟趙先生學,一共學了三個段子,一個霸王別姬,這段在30年代還灌了唱片;第二段是羋建游宮,第三段是馬前潑水。父親慢慢地發現了二姐的唱法上有了變化,越唱越好,突飛猛進,也就發現了是趙玉峰師爺暗中的栽培。在這個基礎上,后來二姐才慢慢地唱出了自己的藝術,唱成了名。趙先生說完了這段故事,我才知道,原來“馬派”西河的根源是“趙派”。那天出門時,老先生一再地叮囑我,一定要學西河,別忘了你是吃西河飯長大的!楊田榮師叔一笑,說:“您就隨他吧。”其實到頭來我也沒聽趙老先生的話,一輩子都在鉆研京韻、梅花、單弦,也說書,但沒唱過一天西河大鼓。
很可惜,我沒有親耳聽到過趙先生說書,更沒聽到過他唱西河大鼓。他也沒有留下影音資料,所以我所有的對他的了解,都是從其他前輩口中聽來的。
趙玉峰先生是西河界的正門正戶,按著“玉福起連增景祥”的輩分,他排在“福”字兒。他的師兄叫邦福蘭,邦先生收了耿起樹(就是父親馬連登的師父),還收了劉起林。劉起林就是天津評書名家張連仲的師父(張連仲是當今著名弦師張子修的父親)。趙先生本人收了朱起云、田蔭亭、田起山、張起榮等眾多高徒,這些位都是后來的書壇大將。而這些個傳承資料,都是田蔭亭師爺告訴我的。
我們說趙先生是書壇當之無愧的魁首,首先因為,西河大鼓是趙先生定的名。早先,西河大鼓從河北流入京、津、唐、奉(遼寧)等地,叫的是“河間大鼓”,也叫過“梅花大調”、“梅花老調”,還叫過“大鼓書”等名稱。再早,北京的焦秀蘭灌制過一張唱片,上面寫的就是“河間大鼓書”。趙玉峰年輕時,首到京津演出,聽人家說,京津兩地早就有“梅花調”(即南北板梅花大鼓),跟當時這個曲種的叫法重名了。他根據河間大鼓發源于子牙河以西,才把它定名為西河大鼓。20年代,在天津的四海升平戲院,由趙玉峰、王鳳永、劉寶全等人共同商定,正式在海報上貼出了“西河大鼓”四個字,從此這個名稱流傳并使用到了今天。其次,趙玉峰繼承的是前輩鼓書家朱大官、馬玉峰、何老鳳等,并把這門藝術推向了新的高度。從唱、彈、說、表四個方面,都推進到了新的藝術水平,因此,可以認為他是西河大鼓歷史上劃時代的代表人物。趙先生6歲學藝,12歲先后到天津、北京獻藝。他先學“怯大鼓”(就是京韻大鼓的前身),后改學河間鼓書,15歲就響名了,可以說是“挑簾紅”,名列當時的“京津書壇五虎將”之首。趙玉峰第一個在說書時摒棄了河間府的怯字音,改用北京話,使城里人能夠接受他的藝術;在書路的安排上,他主動向北京的評書界學習,使得長篇鼓書更有魄力;在唱腔上,他把當時河北柳子腔、京劇以及京韻大鼓的好唱腔都揉到自己的演唱中,多走“下把腔”(即三弦下把位的唱腔),對傳統的“一馬三澗”、“螞蚱蹬腿”、“雙高”都加以豐富,同時在伴奏上要求隨腔,而不再是簡單的“跟著走”,間奏中,豐富小過門的音樂;在表演上,學習戲曲中的身段,使出來好看……總之是把西河大鼓書推向了極致。
此外,很多現在的流行唱法,都是以趙派為基礎的,尤其是,有“趙”才有“馬”。父親馬連登和姐姐馬增芬都受過趙玉峰的傳授和指導。俗話說飲水思源,應該說馬派西河大鼓,是趙派西河大鼓的推進。
雖然趙先生的音響資料現在見不到了,但是,他的傳人田蔭亭先生的錄音還在。田先生嗓音條件好,又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因此,他繼承趙先生的藝術十分到位和正宗。內行的老先生回憶,田先生學的最像趙先生,同時又根據自己的理解和條件,有自己的更多發揮和再創造,他的藝術是內外行都贊譽的,現在基本上都公認他為“田派”了。田先生拿手的段子錄了不少,現在可以找到的有《馬鞍山》《九里山》《將相和》,還有長篇書目《三俠五義》等。從田先生的錄音中,就能領略到趙派西河大鼓藝術的精髓,他表現趙先生的沉雄剛勁、火熾動聽、韻厚腔濃、板俏聲圓等特點,都是十分到位的。
說到這里,難免有些遺憾。馬派西河還有人在學,因為那是女腔,多少還有幾位女演員在唱西河大鼓,或多或少地有所傳承。可是趙派是男西河,學者鳳毛麟角。西河大鼓在京津,男演員的數量已經基本是零了,再過幾年,別說是趙派,連男聲的西河大鼓都聽不到了,真是可悲可嘆啊!
(作者系曲藝世家、著名評書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