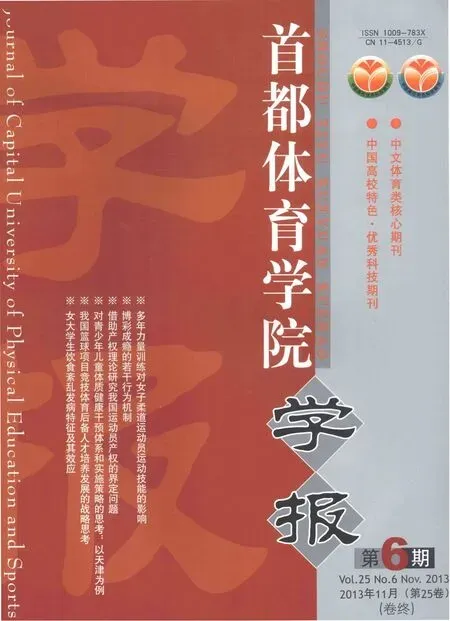對近代中國武術史研究中幾個問題的重新認識
摘 要:在中國近代武術史上有待于研究的空白點頗多,研究其中的5個問題,其創新點為:1)新近發現“武術”一詞在唐代就有使用,而不是普遍使用于清末之說;2)“精武會”從創立之初就有深刻的政治背景,與陳英士和農勁蓀2個關鍵性人物有關;3)“浙江國術游藝大會”上使用“游藝”一詞旨在減少比武的血腥味和走后門,選址于杭州與古時有“打擂”傳統有關;4)民國時期的“第2次國術國考”在項目設置上館長張之江與高官褚民誼有較大的分歧;5)抗日戰爭爆發后,武術界提出“國術救國”的口號,但也有少數著名的武術家走上了與人民為敵的不軌之路,負面影響頗大。
關鍵詞: 近代武術史;武術;精武會;國術;游藝;打擂;投敵媚敵;政治背景
中圖分類號: G 852 文章編號:1009-783X(2013)06-0494-07 文獻標志碼: A
Rediscovering Some Issues in the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Wushu History
CAI Baozhong
Abstract:There are many issues in the researches of modern Chinese Wushu history waiting to be studied.The present thesis sets to research on five issues whose innovative points are as follows:First,the word “Wushu” was newly discovered to be dated back to the Tang Dynasty rather than the late Qing Dynasty.Second,Chin Woo Athletic Association had a complex political background even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foundation and it had close relations with two key figures,namely,Mr.Chen Yingshi and Mr.Nong Jinsun.Third,the word “recreational” was used in “Zhejiang Martial Arts Recreational Assembly”,which aimed to reduce the bloody atmosphere and the opportunity to win a martial contest by using social relationship.Hangzhou was selected to hold the Assembly because of its “Da Lei (open Wushu competition)” tradition in old times.Fourth,there is a great divergence of views on the project settings of the Second State Examination of Martial Arts between Zhang Zhijiang,the curator,and Chu Minyi,a senior official,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Fifth,the slogan “Martial Arts to Unite the Nation” was moved forward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However,a few famous martial artists walked on a wrong road against the people,which brought great negative effects.
Key words:modern Wushu history;Wushu;Chin Woo Athletic Association;martial arts;recreation;Da Lei;pro-enemy collaboration;political background
收稿日期:2013-02-18
作者簡介:蔡寶忠,男,遼寧人,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武術史與文化。
近30年來,作為武術理論基礎性研究的武術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先后出版的7個版本的編年體《中國武術史》,反映了當今這個領域研究的主要成就。相比之下,古代武術部分研究得更加徹底,摸清了武術產生和發展的總體脈絡,而近代武術部分仍停留在對幾件大事的敘述或記述上,明顯缺乏對一些有爭議武術事件的研究與探索,這對澄清事實,還原歷史極為不利。另外,因忽視對武術一般性事件和小事件的闡述,出現了“斷代”或“斷層”現象,其理論也就難以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也正因為如此,至今尚未見到一部有關的“近代武術史”方面的專著。
借承擔國家體育總局武術運動管理中心基礎理論研究課題——“中國近代武術史研究”之機,在現有的條件下對近代武術史作了較為全面的梳理。近代武術史研究中的盲點和空白點頗多,需要研究的空間非常之大。本研究著重介紹以下5個問題。
1 “武術”及相關用語的變更本意都是為了突出主體思想
自古以來,“武術”一詞基本處于不斷更替的狀態,其代名詞多達幾十個,而近代只有武藝、武術、國術3個詞。習云太先生認為:“武術一詞的普遍使用,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事。”后有龔克先生提出的較早的具有現代意義的武術,其依據是以清人徐珂輯撰的《清稗類鈔·戰事類》中“馮婉貞勝英人于謝莊”記載:咸豐庚申(1860年)英法聯軍自海入侵,京洛騷然……中有魯人馮三保者,精技擊。女婉貞,年十九,姿容妙曼,自幼好武術,習無不精。這一說法比前者提前了50多年。
在研究“武術”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份頗有價值的唐代史料——《全唐文補遺·山西卷》,從中發現有2處出現了“武術”一詞。1)《大周故從善府旅帥上騎都尉董君(師)墓志銘并序》,這個墓志銘是“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歲次辛卯正月戊辰朔五月壬申記”。摘錄部分內容如下:董師“君弱齡好古,狀發勤書,王粲橫戈,俄從武術。班超入幕,忽預兵鈐。”[1]這里的“武術”,具有軍事、戰爭和謀略的寬泛意思。2)《唐太原郡夫人太原郡王氏墓志銘并序》,這個墓志銘是由“盍時署國子監慶文館進士”習軍撰書并篆。主要內容如下:“原夫執君子之風猷,合班超之武術,守職為政。”[1]這2處的“武術”,具有軍事、戰爭、謀略和文物結合的寬泛意思。這是國內迄今為止,最先公布的2份珍貴史料。這2個“武術”詞,早于“清末的說法”約1 169年,可見,唐代就有軍事意義上的“武術”稱謂。在唐以后的宋元明各代多使用“武藝”一詞。清末的“武術”又取代了“武藝”,它不僅是“術”與“藝”2個字的變更,更重要的是武術功能由軍事向體育的轉型。另一個動因來自于西洋火器的輸入,大大降低了武術的軍事實用價值,而凸顯體育的功能。這種功能上的轉型體現了近代武術與古代武術的本質差異,并成為我們研究近代武術史的邏輯起點。
辛亥革命以來,“武術”一詞多了起來。例如:1911年青島成立了“中華武術會”組織;馬良組織編寫了《中華新武術》教材;1917年北京創立了“武術傳習所”,同年,由吳志青等人籌備組織了“上海中華武術會”;1923年在上海舉行了“全國武術運動大會”;1926年正式定名為“中國武術”。在這之間仍有混用“武術”一詞的現象。
在后續的年代里,“國術”一詞悄然出現。最早見于唐豪的《武藝圖籍考》中,書中記載:“國術這一名詞,創始于李烈鈞注1,其何所取義?”推測如下:李僑居日本,日本的相撲稱為國技,所以中國武術改為“國術”更準確。1927年中央國術館成立,并采用了“國術”一詞。張之江之所以將“武術”改為“國術”,其意在于與國文、國醫、國畫、國樂等相提并論,既是國粹,又是國寶。就其文化含量而言,明顯地得到了提升,使得長期處于文化底層的武術,終于取得了應有的地位,并登上民族文化的大雅之堂。也有人這樣認識:國術,即中國武術之意,也可理解為“乃我國精粹之技術”,以提高武術的價值觀和在我國人民大眾以至上層人士中之社會地位。那么,張之江提出“武術”改為“國術”,除了有自己的上述想法外,與老友李烈鈞的影響是分不開的。現代人研究認為:“‘國術是一個綜合概念,是國民政府對民族體育(曾經被稱之為‘土體育)的官方稱謂……那么,張之江提出的‘國術則是一個相當明確的概念。張之江所倡導的‘國術,并不是一個單一的運動項目,而是一個以徒手與器械的格斗競賽為核心的民族體育體系。”不僅如此,“‘國術的結構是多元的,它包括了傳統武藝遺存在民間的多個獨立項目。有拳械套路表演,有徒手和長短器械格斗項目,又有自古以來與武術相輔相成的民族摔跤納入其中,還包括了與傳統武藝有密切關系的射箭、彈弓、毽子和力量測試等項目。這些項目都是各級國術館訓練與傳播的內容,也是學校國術活動的內容”。在當時,這個提法盡管還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但也不得不承認,它是當時歷史條件下一個力圖體現中國文化特色的民族體育體系,是民國時期我國民族體育存在與發展的主要形式。中央國術館的初創是以“國粹”的高度出現,以政府的行為、國家的意志來管理和控制國術,曾在20世紀末期、30年代乃至40年代,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從表面上看,由武藝→武術→國術→武術,只是名稱的變更,這種變更過程是非常漫長和微妙的,其實質已反映了武術質的變化與飛躍。
“國術”名稱一直沿用至解放前。至今港臺地區及東南亞一帶,仍稱武術為國術。如新加坡有“光漢國術總會”。這種稱謂與當時“國術館”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正式用“武術”一詞。1952年6月24日,榮高棠先生在《為國民體育運動的普及和經常化而奮斗》報告中,運用了“武術”一詞。1954年第44期《新體育》中解釋:“為什么不能叫國術?‘國術一詞,概念模糊,如果武術可以稱‘國術的話,那么我國固有的藝術和技術,如雕塑、繪畫、音樂、刺繡、針灸……都可以稱‘國術。只籠統地把武術稱為‘國術,顯然不夠確切。”如果用現代的觀點看國術,一是局限于本國,二是分不清哪國,缺乏科學性。1958年9月8日在北京舉行了全國武術運動大會,其后成立了中國武術協會。“武術”一詞真正顯現其本來面目。
2 “精武體操學校”從創立之初就有深刻的政治背景
著名的上海“精武會”是以愛國武術家霍元甲注2的社會聲望創建的民間武術組織。鴉片戰爭以來,西方體育以強勢的姿態涌入中土,1909年和1910年春,霍元甲在農勁蓀推薦下、應陳英士邀請到上海與西洋大力士奧皮音比武,2次未遂,消息見報后,元甲名聲大振。以陳英士為首的愛國志士及熱衷武術的一些熱血青年,想請霍元甲創辦精武體操學校。元甲欣然同意。
在以往的書籍中幾乎從未提及農勁蓀和陳英士2個關鍵性人物,以至于影響到研究結果,值得冷靜思考。在這里必須將農勁蓀、陳英士2個關鍵性人物交代清楚。農勁蓀(又稱農竹),本名許農(1864—1953),出身滿清官僚家庭,后來由于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惟恐株連家族,而改為姓農。他既是一個商人,更是一個革命黨人,為精武體操學校第一任校長。在天津南運河邊上開有懷慶藥棧,以此為保密身份、開展革命工作、結交武林人士、積蓄革命力量而設立的“招牌”[2]。農勁蓀認為霍元甲是將來為辛亥革命出力的一個好人選,平時對他進行一些關于辛亥革命愛國主義方面的熏陶和影響,并成為至交朋友。在奧皮音挑釁的關鍵時候,在民族危難的緊急關頭,農勁蓀積極舉薦霍元甲,并在日后創辦精武體操學校時起到了重要作用。
陳英士(1877—1916),又稱陳其美,革命黨人,是孫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中部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1906年夏,留學日本東京警察學校,學習警察,后改學軍事,1908年回到上海,經常往返浙滬及京津4地從事革命活動,加入青幫,成為大頭目[3]。1909年在上海接辦革命機關天寶棧,當年冬季有西洋力士奧皮音來滬挑戰,因當地武功不著,陳英士、農勁蓀等愛國志士遂延聘武術名家與之較量,以伸張民族氣概。霍元甲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被邀請來滬的,奧皮音聞訊而逃。“自此之后,滬人多知元甲武功,若不為之流傳,殊為可惜……有提議辦一間武術學校”。適時,陳英士與宋教仁、譚人鳳、楊譜笙等在滬組織中部同盟,擬策劃浙江起義。此時,陳考慮到武裝起義、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等事宜,正需要大量的軍事人員,擬定創辦一所學校加以培養。同時借以霍元甲的愛國熱情、社會聲望和非凡的武功,何樂而不為呢。志士的憂國之情與元甲的報國之心構成天然的契合。在陳英士的積極倡導下,在農勁蓀、陳鐵生、王一亭、楊譜笙、徐一冰(這些支持者都是學校的首批會員)的支持下,精武體操會于1910年成立了。特聘霍元甲主持武術技術訓練,并習軍事。計劃挑選志向堅定、體格強壯的青年50人作為骨干加以訓練,6個月為一期,畢業后分配到各地,開辦同類學校。“希望10年內訓練出千名有強健體魄,又有軍事技能的青年,以適應大規模革命運動和改良軍事的需要”。
至于陳公哲、姚蟾伯、盧煒昌[4]3人(亦稱三友公司),主要是在精武體操學校“越七十日,霍元甲卒”后的歷史關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作用時間主要是在1924年以前,共約15年。這一時期他們曾積極推動和支持精武事業的發展,精武體育會以其“愛國”和“武術”為感召力,迅速在南方各地及南亞地區建立了分會,并有效傳播了中華武術,洗刷了“東亞病夫”的恥辱。在當時影響力是極其重大的,所以“三友公司”的功績將永遠載入史冊。
精武體育會創辦人不提及陳英士原因有3個:1)隱其姓名,避其鋒芒。陳英士當時系中部同盟會主要負責人,追隨孫中山創立民國的革命運動,曾被袁世凱懸賞“七十萬兩金”換陳的頭顱,更何況倡辦精武體操學校會帶來滅頂之災,由公開轉入地下更為有利;但不幸的是1916年陳英士被袁世凱的部下暗殺,此后,精武體育會的活動更加謹慎。2)宗派之爭,影響聲望。上海光復后,各派為爭奪革命領導權,有人詆毀陳英士,如“偷兒成群,擁有都督”“風流都督”;有刺殺陶成章嫌疑,其社會聲望受到不良影響。3)社會團體,會員復雜。精武體操學校倡辦之初,“會員分子,極其復雜,其中陳其美(即英士)、旦冒申為國民黨員,陳鐵笙為同盟會員……”等。社會各界人士亦在其中,管理又較為松散,含而不露是最好的自我保護方式。
從上所有資料和情況分析看,可以認定:陳英士為精武體操學校的創始人。概括為5個方面:1)發起延聘霍元甲來滬比武;2)親自領銜創辦精武體操學校;3)親自租賃閘北黃家宅舊式平房為校舍;4)親授農勁蓀出任校長,親挽霍元甲任總教習;5)親自加入該會,并鼓勵同盟會員參加;6)親自在革命活動中宣揚精武精神,并鼓勵將士習武強身。
精武體育會是一個愛國團社組織,誕生于愛國聲中。雖然它明確表示不介入“政治斗爭”;但是,在歷史的重大事件中都自覺或不自覺地發揮了作用,因此,孫中山先生對“精武會”愛護備至,倍加推崇。在1919年特意為《精武本紀》作序,并親筆題寫了“尚武精神”的牌匾。這一舉動是有深刻時代背景和明確指向的。辛亥革命后,“土洋體育”之爭仍在繼續,孫中山針對當時有人想廢止武術,拋棄技擊,提倡純粹“洋體育”的做法提出批評,并告誡:“我國人曩昔,僅襲得他人物質文明之粗末,遂自棄其本體固有之技能,以為無用,豈非大失計耶!”強調體育關系到國力的強弱和民族的盛衰,是“于強種保國有莫大之關系”。為贊揚精武體育會的“成績甚多”,樹立“精武體育會”這面旗幟而鼓起加油。
孫中山認為“自衛之道”,若對國家而言是強種保國,若對人民而言是強我體魄,并將“尚武精神”視為救國的一種手段,通過“強種”來達到“保國”和“強國”的目的。精武會是以“愛國、修身、正義、助人”為指導思想的,在《精武本紀》的“大精武主義”中,明確表示“造成世界最完善,最強固之民族,斯即精武大希望也,亦精武之精神”。精武的意圖是組成強身的群眾社團,希望各地來仿效,則全民族的體質增強就會有希望。這一指導思想與孫中山的愛國主義思想是完全相吻合的。《序》中還指出:“精武體育會,成立既十年,其成績甚多,識者稱為體魄修養術專門研究之學會,蓋以振起從來體育之技擊術為務,于強種保國有莫大之關系。推而言之,則吾民族所以致力于世界平和之一基礎。”評價之高,前所未有。孫中山在這里強調的是“武術強體→強體為國→國強太平”的遞進關系。“強國強種”是一個綜合性指標,具有廣泛的社會性,與精武會章程規定的“提倡武術,服務社會”是一致的。
在研究精武體操學校創辦的過程中發現,學校的初創就得到同盟會的支持,而聯想到同盟會組織者陳英士和農勁蓀,以及財力方面的資助等。這種特殊關系便構成一個相對封閉的鏈條:陳英士追隨孫中山,成為中部同盟會的主要領導者,并與農勁蓀共同籌劃同盟會;農勁蓀曾在天津開設懷慶藥棧時,結識習武之人霍元甲,正因為有這樣一個情節,才特請霍元甲到上海與奧皮音比武,未遂后由陳、農二位撤霍元甲大旗創立了精武體操學校。透過這種現象反映出精武體操學校創立之初是有深厚政治背景的。從精武會的成員組成看,黨派眾多,比較復雜,有國民黨黨員、同盟會會員,而革命與維新黨員最多,正因為如此,精武會受到晚清政府的注意,所以陳公哲先生多聘商界人士任會長,以淡化政治色彩,保存壯大自己。對此,陳公哲先生在談及1910年他與孫中山先生的對話時是這樣回憶的:“精武一向不肯參加孫總理政治活動,常受彼部下指責……及對總理言曰:……蓋欲建立為純粹社會團體,提倡武術。若一旦參加政治,各處分會,易遭地方不同派系之官廳禁阻,所以潔會自好,非不贊同革命也……先生向革命一途邁進,余則向體育一途建設,未敢謂為分道揚鑣,然彼此相得益彰。先生頗然余說。”這些對重新認識與評價精武會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武術和俠義精神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起到了無可代替的作用。據統計,在1907—1911年間,孫中山連續組織并領導了8次武裝起義,主要是依靠會黨力量[5]。如1894年11月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建立興中會,并第一次鮮明地發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6]。為了實現起義的目標,便廣泛吸收社會各界人士,其中十分重視與會黨和江湖人士、武林豪俠的接觸,這些人在起義中直接或間接,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發揮了舍生取義、忠于信仰、勇氣為先的“尚武精神”。所以,孫中山贊賞精武會是有充分的理論依據的。
上述分析,并不是否定霍元甲的社會聲望,以及與精武體育會的關系。霍元甲是一位愛國武術家,在西洋拳師挑釁之時,挺身而出,以自己的愛國行動贏得了社會的高度贊譽。霍元甲雖然不是精武體操學校的創始人,但該學校的創立是以他的社會聲望為基礎的,必須承認霍元甲與精武體育會的血緣關系。
3 “游藝”一詞與打擂的選址問題是有時代性與歷史性的
在武術界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武術擂臺賽”,指的是1929年11月在杭州舉行的“浙江國術游藝大會”中的全國武術擂臺賽。這次擂臺賽的舉辦是有其深厚的時代背景的。1928年深秋南京“全國國術考試”之后,便成立了“中央國術研究館”,并很快改組為中央國術館。隨之,全國各地各級國術館相繼成立。它的社會基礎直接來自于之前各地所創立的武術會社,而且基礎雄厚;它的政治基礎直接來自于當時軍閥和政客的需要及控制,其導向性很強。各地各級國術館的成立,為武術的推廣和普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提高與門戶之見等問題沒能得到解決。由于武術界人員結構較為復雜,百年來相互詆毀、相互攻擊的現象始終存在。為了縱觀武術界全貌,了解“誰的本領好,誰的本領不好”,1929年1月7日,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委員長兼浙江省政府主席張靜江(1877—1950)致電國民政府,要求以當局的名義舉辦一次全國性的武術擂臺大賽。國民政府的幾位當權者最終礙于張靜江的資格和地位,同意以國府的名義向全國發出通告,并全權委托浙江省政府與國民政府直屬機構——國立南京中央國術館共同主辦。
通告一經發出,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反響,立刻得到各地國術館的贊同和響應,各門派好手都摩拳擦掌,躍躍欲試。這次賽會的宗旨是“遵循總理(孫中山)遺愿,提倡(昌明)尚武精神,力圖強國種,誓雪‘東亞病夫之恥,喚起民眾習武強身,練武御抵”。大會在籌劃的過程中涉及方方面面的事情,其中大會的名字和大會的選址問題是要率先考慮的,它直接影響著對外的宣傳工作。
在這里就“國術游藝大會”的定名和選址問題作一介紹:關于“國術游藝大會”定名的問題,一度在武術界和政界人士中大惑不解,人們普遍認為用“國術運動大會”或“國術比賽大會”更合適,但是當時為什么沒有采用,而是用“游藝”代替了“運動”和“比賽”這2個詞呢?原因有2個:1)“比賽”2字太刺眼,武術界門派較多,有的還有些成見,好勝心可能會使他們沖破武德的約束。另外,若用“比賽”2字,無人保送的和自動要求參加比賽的是否接待?這些人無單位(或名人)保送,約束力沒有,講規則不聽怎么辦?打出人命怎么辦?2)1929年,浙江省政府同時負責籌備召開一次全國體育運動會,一般簡稱運動會,在使用國術運動大會這一名稱時,已有好幾個省函電往來,聯系工作,尋找門子,打錯電報了。為此,省政府研究再三,決定將籌備階段的“國術運動大會”,改名為“國術游藝大會”。其根據是“游藝”2個字最早見于《論語·述而》中之“游于藝”。“游藝”的范圍在不同時期對它的認識也是有差異的。孔子所謂的“藝”,指的就是“六藝”,朱熹也有類似的解釋。1935年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由楊蔭深所著的《中國游藝研究》中,將游藝分為雜技、弈棋、博戲3類,其中射柳、角抵、相撲3項含有武術內容。在這之前的1915年,浙江省就創辦了《游藝》雜志,后來天津開辦了《游藝畫報》和《新游藝畫報》,北京創辦了《游藝報》等。以我們所見,在當時“游藝”算是個流行詞或時髦詞。
關于“國術游藝大會”的舉辦地問題同樣引起各方面的關注。為什么會選在杭州,其優勢有3個:首先,浙江省十分重視中央國術館及相關國術團體提出的符合民眾的良好倡議。省務委員會召開專門會議研究、論證“倡議”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其中還有鮮明的政治性。其次,杭州是我國的6大古都之一,傳統文化底蘊深厚,同時也是舉世聞名的風景旅游勝地,可以吸引更多的參賽者。再者,杭州有多處露臺爭交遺址,可供參賽者參觀和考證。據體育史考證:相撲比賽場地在“南宋臨安城著名的有3處,一處在霍山行祠,“廟上露臺爭交”。一處在護國寺,“南高峰露臺爭交”[7],還有一處在“南高峰頂榮國寺。有華光樓,旁有射亭,有角面坻臺”[7]。有人對后2種說法提出質疑,通過對大量的史書考證認為:南宋時,全國的相撲大賽有2個地點,有時在葛嶺山北麓黃龍洞的“護國寺”,有時在南高峰“榮國寺”塔院。研究還認為,吳自牧寫“護國寺”的可能性較小,如果是榮國寺,則文字上只須寫作“榮國寺露臺爭交”或“南高峰露臺爭交”即很明白。正因為杭州具有這些優勢,才順利地獲得了承辦權。
大會會場設在杭州鎮東清朝舊巡撫衙內的2 hm2大廣場上。其原巡撫衙在辛亥革命新軍起義攻打時被燒毀,擂臺(也是本次大會的表演臺)是在平整后的廢墟上用水泥建成的,高2 m、寬約17 m、長約34 m,臺子中間以白粉畫一直徑為10 m的圓圈作為比賽界限。會場門口樹起2座松柏牌樓,用紅綠綢做巨大橫幅,并寫有“提倡國術,發揚民氣”的大字。擂臺上方飄著“欲全民均國術化”的大紅橫幅,兩旁對聯為“一臺聚國術英雄,虎躍龍驤,表演一生功夫,歷來運動會中無此舉”“百世樹富強基礎,頑廉懦立,轉移千載頹風,民眾體育史上應有余思”。臺上懸中山先生像一幅,并聯云:“五州互競,萬國爭雄,丁斯一發千鈞,愿同胞見賢思齊,他日供幫家驅策”“一夫善射,百人挾拾,當今萬方多難,請諸君以身作則,此時且資民眾觀摩”。場中四周貼滿各種標語,使整個會場顯得隆重而熱烈,比武氣氛異常緊張。
4 “第2次國術國考”在項目設置上存在著2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在民國期間有2次“全國國術國考”。第1次于1928年8月發布《國術考試條例》之后的10月15—20日在南京公共體育場舉行。來自山東、河北、北平、南京等17省市和中央國術館的共330名應考者參加。其中獲得預試(單人徒手和器械表演)的有240人,參加正試(徒手與器械的對抗)的有150人。最終有15人獲得最優獎、37人優等獎、82人為中等獎。根據中央國術館當時召開的董事會會議記錄等相關資料記載,舉辦第1次全國國術考試的最終目的有3個:第一反對重文輕武,力主全民大眾習練國術;第二為征集散落與流傳在民間的武藝精華秘笈;第三為借此次國考之風,廣招學員以令中央國術館的學生隊伍壯大。此次國考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時隔5年的1933年10月20—30日第2次國術國考又在南京公共體育場舉行。來自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青島、重慶、漢口、浙江、福建、貴州、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江西、綏遠、南京及中央國術館共20個單位438人參加。這次“國術國考”比第1次隆重、壯觀,參加大會儀式的有蔣介石、汪精衛、林森、馮玉祥、李烈鈞、蔡元培、戴傳賢、于佑任、孔祥熙、何應欽、孫科、鈕永建等。考試委員會委員長由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傳賢親自擔任,何健、鈕永建、諸民誼、張之江任副委員長,張之江兼總裁判長,李烈鈞仍為裁判長,王子平、孫祿堂任裁判員。
這次考試基本按照《國術考試條例》和1931年11月修正的《國術考試細則》執行。與上屆相比有3點不同:一是設項略有不同。套路分5項:拳、刀、劍、槍、棍;對抗分4項:散打、長兵、短兵、摔跤。二是比賽規則有改動。預試有了評分細則,鑒于上屆“擂臺”形式易造成傷害事故,改為點到為止,并使用了防護拳套。三是有女選手參加,因而配備了3名女裁判(楊婉如、白素貞、翟漣源)助理。這次考試在項目設置上曾產生了2種截然不同的意見,而在以往內地所見到的武術史書籍中從未提及,這次我們利用臺灣方面的資料作了比較客觀的分析,使之更接近歷史的原貌。在當時,張之江注3倡導以“真功實力”的放開打,而禇民誼注4則強調“健身第一”的公平性。由于張、禇二人均為國民政府頗有地位的要員,對國術的推動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受到了全國武術界的關注。現將張之江與禇民誼的主要觀點概括為表1。
表 1 張之江與禇民誼爭論的主要觀點
從表面上看,張與褚的分歧似乎在考試方法上,其實,二者最根本的差異是在推廣國術運動的思想上。張之江所持的國術仍在于自衛衛國思想,禇民誼則立足于強身保健思想。也因為此種思想的差異,使得雙方的立論幾乎沒有交集。基本上,自衛衛國的國術技能理應以強健的身體作基礎,而強身保健的國民,必能適應自衛衛國的場合,二者似應相輔相成方是。這次分歧或爭論,以求同存異而告終。
這次正試采用雙淘汰制,決出應試者等次,分甲、乙、丙3級。凡一項勝6次者為甲等,甲等名額占應試人數的35%。勝5次者為乙等,勝4次者為丙等,每等之內,按學科成績排定先后順序。在重量級別中,參加人數相對少,勝2次者就可以獲得甲等。這次考試采用每項單獨評分,逐項分別入取前6名的方法。最終獲得甲等的有43名。其中拳術對試13名,長兵3名,短兵6名,摔跤3名,搏擊(拳擊)重、中、輕3個級別共9名。參加女子組正試的只有9名選手,皆取為甲等,以鼓勵女性習武。
客觀地講,2次國術國考,是對對抗項目競賽的有益嘗試,初步奠定了武術競賽的內容、形式、方法和規則,對近現代武術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中央國術館的影響下,一些地方性的“國術考試”也在進行。如繼1928年第1次“全國國術國考”之后,上海市國術館舉辦了上海市第1屆國術考試。應試者達500多人,試場規模宏大,每天觀看者達三四萬人。按照評定成績定銜為“國士、壯士、武士、勇士”和及格5個等級。遼寧省先后在1931年和1947年舉辦了2次國術考試。第1次由東北軍高級將領張學良主辦,在長兵對抗項目上特制了器材,增加了安全措施。第2次由東北抗戰烈士紀念會主辦,考試辦法采用先表演后對抗的形式,決賽入場卷上有本人照片,以防冒名頂替,實行無級別抽簽的辦法,獲得了極大成功。河南省國術館是成立較早的省份,輻射的面積較大,參與習武的人較多,每年舉辦一次國術考試,并積累了一些成型的經驗。如舊中國第7屆全運會武術比賽規則就是由河南省國術館提供的。各地國術館的建立,以及地方性的“國考”,有效促進了武術的普及與提高。
5 抗日戰爭時期個別“武術家”走投敵媚敵之路是賣國行為
抗日戰爭爆發以后,中國人民同仇敵愾,采用各種實際行動抗擊日寇的侵略行經。習武之人則堅持“國術救國”的基本原則,充分利用身上的武藝和手中的利器為抗日作出應有的貢獻。像東北軍、二十九軍大刀隊的將士們在武器相對不足落后的情況下,發揮武術的軍事作用。利用白刃格斗、夜間偷襲、誘敵深入、乘勝追擊等戰術,殺死砍傷無數的日寇,也涌現出眾多的民族英雄,為抗日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幾個民族敗類,這是近代武術發展中的特殊現象,很值得認真總結和反思。抗日戰爭中,出現了2個有名的大漢奸,一個是以提倡“中華新武術”馳名的馬良,一個是以提倡太極拳馳名的褚民誼。抗戰勝利后,馬良死在獄中,褚民誼被判死刑。這2個人在武術上都有一定造詣,也都曾積極推廣武術,在這點上的貢獻不可否認,因此他們的名字經常被武術界提起;但是,當國家民族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他倆竟投身日寇,甘當走狗,不僅自己成了千古罪人,而且各自影響了一批人,使南北一批民間武術人士追隨其后,也走上附敵和媚敵的道路。這是民國武術一段非常值得重視的現象,是一段令人痛心疾首的歷史。
褚民誼曾在德國獲得醫學博士,后棄醫從政。他深知太極拳的健身價值,而廣泛接觸武術界朋友,并創編了一套太級操,在當時影響很大。在政治上,褚民誼則一直與汪精衛走得很近,屬于國民黨內的“汪派”嫡系,因他倆是妯娌。抗戰爆發,汪精衛悍然投敵,組建偽政權,褚民誼置民族大義于不顧,緊隨汪精衛走上漢奸的道路,并成為汪偽集團的要員。他先后擔任過“駐日大使”“外交部長”“廣東省省長”等一系列重要職務,成了臭名昭著的“名牌漢奸”。在日本人的庇護下,他一邊大權在手,威風凜凜,腦滿腸肥,一邊還想著他的健身養生之道。在他擔任汪偽中國體育協會會長和偽教育部體育委員會委員長之時,曾憑借其社會關系和影響力,拉了一批“體育名流”和“國術名流”投身日偽懷抱,多次組織體育代表團到日本參加活動,向日寇大獻殷勤,丟盡了中國人的臉。1945年抗日勝利后,蔣介石假借廣州成立警備司令部“治安維持會”之機,派軍統首領戴笠和鄭介民負責解決廣州的漢奸問題,并順利活捉了褚民誼,于1946年8月23日槍決了褚民誼。
馬良正因為主持創編了《中華新武術》教材,才使得其名聲大振。實事求是地講,“新武術”在當時是個創舉,對武術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從綜合資料分析,馬良是一個典型的投機分子。具體表現在5個方面:1)投其所好。傳統武術本身脫胎于軍旅武術,許多招招式式有較強的實用性,無須增加“帶數口令”和步兵操典成分。馬良以自己的軍旅經歷與行武出身,編創“新武術”,簡化其傳統武術,以“馬氏體操”的形式出現,迎合了當時一部分人的從眾心理。2)借力發力。馬良為了抬高“新武術”的地位和影響,通過軍政關系和社會關系請到政府要員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張謇、梁啟超等,為“新武術”四書作序,以此來樹立自己的形象和“新武術”的影響力,近而達到借他人之名,揚自己之名的目的。3)王婆賣瓜。編創的“新武術”,本是“馬氏體操”,已失去傳統武術的特色,卻要打出推廣“國粹”的招牌,吹噓“新武術”就是“我國之國粹”,并企圖推行一種標志各級官階身份、共三等九級的“佩劍制度”。當即受到了輿論的譴責。4)抄襲他文。馬良除了主持創編“新武術”,其武術言論是比較少的。1924年9月曾在《體育與衛生》第3卷第3期上發表了馬良的《中華北方武術體育五十年紀略》的文章,它代表了作者的武術觀點和思想;但遺憾的是,“該文無論從題目到正文內容,都顯然是由麥克樂注5《五十年來中國之體育及武術》的‘中國武術一節搬抄而來”。通過具體文章的對比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文章結構是仿襲;文字內容是侵吞;此文抄襲無疑。5)親媚日寇。1919年8月5日,任濟南鎮守使馬良無故殺害了山東回民外交后援會會長馬云亭、朱春濤、朱春祥等3名愛國人士,制造了震驚全國的“濟南血案”。抗戰爆發后濟南失陷,善于投機鉆營的馬良再次投向日寇的懷抱,初任濟南維持會會長,后任偽山東省公署省長、又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跟著大漢奸王克敏當走狗。抗戰勝利后以漢奸罪入獄,在保外就醫期間病死。
馬良與褚民誼影響了一批武術名家,在這里可以舉例說明。正值抗日戰爭的關鍵時刻,馬良于1939年、1943年2次組織“中國武術表演隊”;褚民誼于1940年也組隊參加日本天皇組織的所謂“友善活動”,直接策劃附敵或媚敵行動,參與者有許禹生、吳斌樓、寶善林、王俠林、牛德海、王保英、龔玉福等。就這3次活動的參加者而言,不論出于何種原因,都是不足稱道的失節行為,是缺乏民族氣節的表現,根本談不到什么“振奮了國威”,更不是什么武術史上的“佳話”。幾十年后,居然將參加這些活動的照片公布天下,將活動的內容只做完全正面的描寫。這不但表現了民族氣節意識的淡漠和缺乏反省精神,而且還有欺蒙社會與誤導讀者之嫌,反映了武術人物評價標準的失范與錯亂。值得冷靜地反思。
抗日戰爭爆發后,還有一些習武之人走上了與人民為敵的不軌之路。如大成拳名家王薌齋,在北平淪陷后,經臭名昭著的賣國漢奸張壁介紹來北平授拳,自稱是來抗日,后成了北平偽市長袁良的保鏢,甘當走狗,專為日本人做事,被北平武術界同行所咒罵。不僅如此,其得意弟子姚宗勛仗勢欺人,曾帶著幾個日本憲兵,牽著幾條大狼狗,來到大興國術館,指名道姓地要和武培卿較量。無奈之下,武培卿與之放對。憲兵在后,狼狗在側,怎可出手?姚宗勛借機舉手將武培卿打傷,便揚長而去。此舉,激怒了整個北平國術界,矛頭直接指向姚宗勛的師傅王薌齋,而王此時正是北平偽市長的保鏢。其他徒弟又如何呢?在這里可以用一句武術諺語加以回答:心不正,拳則偏。另外,王向齋與齊純芝私交頗深,并與他狼狽為奸,以教拳為名網羅社會上的地痞流氓張敬堯和孫傳芳等人,通過齊純芝先后同川島芳子勾結成為漢奸。盧溝橋事變前后,齊純芝把川島芳子的住宅跨車胡同15號作為漢奸們勾結和破壞抗戰活動的黑窩。1937年平津失陷后,齊純芝任偽華北政府委第一任主任,楊秀真(齊純芝門生)任綏靖總督辦,胡杰(齊純芝門生)任工務總督辦,王向齋也曾任華北治安總署督辦。在日本特務的操縱指使下,又同偽滿州國溥儀互為勾結,并預謀同汪精衛的偽南京國民政府接觸來聯合反共。此言一出,不亞于對王薌齋從政治上判了死刑,也成了大成拳(意拳)是所謂漢奸拳的鐵證之一。最近10年以來,一直有人對此予以反駁和辯解;但是,由于缺乏強有力的史料證據批駁此說,事實真相究竟如何,可以說還在云霧之中。
另在《中國武術人名辭典》144頁有當代武術人物“李俊卿”的一條詞條,其中說李俊卿“曾任江蘇省省長李士群保鏢”。稍微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李士群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務,汪精衛漢奸集團“76號特工總部”的總頭目,一個十惡不赦的漢奸賣國賊。有“殺人狂”之號的李士群,雙手沾滿了抗日軍民和無辜百姓的鮮血,他以“清鄉”有功,于1941年12月出任汪偽江蘇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此后,更加變本加厲地圍剿抓捕抗戰軍民,尤其是針對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四軍和地方抗日力量,多少人慘死在這個魔鬼的屠刀之下。試想以李士群的陰鷙歹毒,能給他當保鏢的,恐怕只能是他親信可靠的“76號”分子,或是毫無良心可言的江湖打手之流。如果李俊卿確有這樣的經歷,照理,數十年后應該深自愧疚,摭之掩之猶恐不及,怎么還有人把這當作光榮經歷張揚出來。我們只能把這看成是對武德的公然蔑視,是對中華武術人文精神和價值標準的諷刺與嘲弄。
這種現象雖然只是個別的,但足以引起我們的反思。長期以來,我們對近代武術研究是明顯不夠的,特別是對民國時期的武術家或民間拳師缺乏考證。在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里,民間拳師的流動性較大,投其所好,不法之徒是存在的。以往的研究只重視對人物的正效應,忽視了問題的另一面,即負效應。以褚民誼和馬良為例,二人身居高官,影響一批人是必然的。我們對這批人應如何看待,限于資料的缺乏,暫不能主觀臆斷;但它的確需要研究,更需要突破。在最后還是要強調:習武崇德的優良傳統不能丟,應重人品、重民族氣節。
參考文獻:
[1] 全唐文補遺.山西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2] 他收過陳真這個徒弟嗎[N].遼沈晚報,2006-10-14.
[3] 王承仁,曹木清,吳劍杰,等.中國近百年辭典[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247.
[4] 張震海.漫談精武體育會簡史[J].中華國術,1992,1(3):42.
[5] 李誠.習武必讀[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1991:201.
[6] 李文海.“振興中華”口號的由來[N].人民日報,1982-04-30(5).
[7] 吳自牧,夢梁.角面坻:外郡行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8] 馬明達.應該重新審視“國術”[J].體育文史,1999(5):36.
[9] 馬賢達.中國武術大辭典[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90:1.
[10] 俞覺安.上海精武會首任會長農勁蓀[J].上海體育史話,1988(4):28.
[11] 韓錫曾.精武體育會創始人考辯[J].浙江體育科學,1995(2):49-52.
[12] 潘公展.陳其美評傳[C].陳英士紀念集,1985:192.
[13] 張重天.我所知道的陳其美[J].文史知識,1982(2):65.
[14] 陳公哲.精武會50年[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1:89.
[15] 范克平.舊時國立南京中央國術館寫真:9[J].中華武術,2005(3):28.
[16] 徐清祥.中國武林之謎[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113.
[17] 趙善性.關于“游藝”的補充[J].體育文史,1993(2):59.
[18] 張法清.南宋杭州露臺爭交遺址考[J].體育文史,1993(4):51.
[19] 陳心平.全國首屆武術擂臺賽前后[J].上海體育史話,1991(4):29.
[20] 陳順安,凌耀華.舊中國首次擂臺賽[J].浙江體育史料,1983(1):12.
[21] 范克平.舊時國立南京中央國術館寫真”:6[J].中華武術,2004(12):17.
[22] 徐元民.中央國術館舉辦國考采用拳械對試之論爭[J].國術研究,1997,6(1):32.
[23] 張宏然,張企凡.參加首屆武術國考記[J].江蘇體育文史,1988(1):38.
[24] 兩次擂臺賽[J].遼寧體育文史資料:武術專輯,1986(1):102.
[25] 馬廉真,張天罡.諸民誼伏法記[J].武林,2006(6):14.
[26] 周偉良.近代武術史上的一樁“剽竊案”[J].體育文化導刊,2004(10):66.
[27] 馬明達.民族大節不容含糊:抗戰勝利56周年紀念日感言[EB/OL].[2013-02-15].http://www.xici.net/d42731504.htm?.
[28] 席曉勤.偽國民政府紀事[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123.
注釋:
注1李烈鈞(1882—1946),原名烈訓,字協和,號俠黃。江西武寧人,父輩稍懂拳術,幼小學過一些武術基本功,還經常向鄉鄰中出色的武師求教。其中武舉人張坦奄、邱老茂、田建卿等都曾熱心指點過李烈鈞。從小習武,對他長期的軍旅生涯頗有裨益。1904年赴日學習陸軍,1907年加入同盟會,歸國后,在新軍和軍事學堂任職。曾任參謀長、安徽、江西都督。1915年奉孫中山之命,到云南昆明,參加護國戰爭,并任第二軍總司令,此時與張之江協同作戰。是辛亥革命云南起義的老戰友,也是云南起義的主力,兩人交情甚篤,感情深厚。
注2霍元甲(1867—1909),字俊卿,綽號“黃面虎”。祖籍河北東光縣,世居靜海小南村(今屬天津市西郊付村)。出身武術世家,父親霍恩第為鏢師,以保鏢為業。霍元甲排行老二,幼時體弱多病,其父考慮學武不成有損霍家聲譽,便命霍元甲攻讀詩書,而不準習武。霍元甲遭此摒棄后,立志圖強。每日窺摩父傳兄弟之技,潛心苦練于棗林避處。父知其行,嘉其志,乃悉心傳授。霍元甲經10年督教,秉承家學,通秘蹤藝,并旁參各派,益以內勁,技愈精湛。1890年有河南拳手,杜某聞霍恩第名前來較技,霍元甲與試并獲勝。名聞鄉里。1895年到天津賣柴,遭當地盤剝者10余人持械圍攻,霍元甲揮扁擔盡逐之。此后居住天津謀生。初掌“腳行”,繼為懷慶藥棧掌柜。曾以單肩擔走千斤藥擔,一腳踢開青石磙子,被時人稱為“霍大力士”。1901年和1909年分別在天津和上海嚇跑2個外國大力士,后來師徒又接連挫敗旅居上海的日本武技高手,名聲大震。在上海愛國人士陳英士的積極倡導下,以霍元甲的社會影響力,創辦了“精武體操學校”,霍元甲任總教頭,劉振聲任教練。在傳授武術數月后,因咯血病加重而逝,當年42歲。此后在陳公則等人的倡導下,將原“精武體操學校”改名為“精武體育會”(簡稱“精武會”),人們推崇霍元甲為“精武體操學校”創始人。
注3張之江(1882—1966),字子姜,號保羅。河北鹽山縣人。少時隨祖父攻讀四書五經,練過太極拳、八卦掌。成年后,赴東三省講武堂學習,并受業于陸軍大學將官班。1901年從戎,任軍職至國民軍總司令。1927年脫離軍界,在紐永建等協助下,創建“國術研究館”,翌年改組為“中央國術館”,任館長。1933年創辦以武術為主兼習各項現代運動項目的“國術體育專科學校”(后更名“國立國術體育師范專科學校”),任校長。張之江還曾于1920年率學員赴日本考察武技,學習柔道和劍道。于1933年和1936年間2次率團分赴兩廣、福建等省及香港、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表演、宣傳武術。著有《東游感想錄》《國術與國難》《國術與體育》等。
注4禇民誼(1884—1945),原名明遺,字重行,浙江吳興人,同盟會早期會員。后因與日本政府勾結,被國民黨政府以“通敵賣國”罪處死于江蘇。他出身醫生家庭,家教甚嚴,精通英法日語,獲法國醫學博士,但卻棄醫從政。1903年抵法后,與蔡元培、吳稚暉等人創辦《新世紀月刊》等刊物,還出版過許多進步刊物。1911年回到上海,經黃興介紹,結識汪精衛,并與汪妻之妹結婚,被迅速提升為中央委員兼行政院秘書長。褚雖官居要職,畢竟是學醫出身,深知健身之重要。1925年正是太極拳鼎盛之時,便從師于吳鑒泉,后又認識同門的徐致一、吳圖南等人,以較大的精力研究太極拳,拳藝長進很快,曾利用職務之便改組了中華國術協會,創辦了《大眾健康》雜志,極力主張國術大眾化、科學化。褚根據自己的練功體會,創編了一套“太極操”,并通過出版書刊、掛圖、培訓班等形式廣泛宣傳其健身價值。這套太極操在第11屆奧運會上,作為第一個節目,為柏林3萬觀眾做了集體表演。
注5麥克樂(1886—1959),美國人,1913—1926年間作為美國基督教青年會體育干事在華傳播西方近代體育。在華期間,他積極推行西方近代體育,編著、翻譯體育教材書,主辦《體育與衛生》刊物。此外還留下了不少有關體育研究方面的學術論文。其中《五十年來中國之體育及武術》一文是1922年麥克樂應當時《申報》館為紀念該館成立50周年計劃出版《最近之五十年》紀念刊之邀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