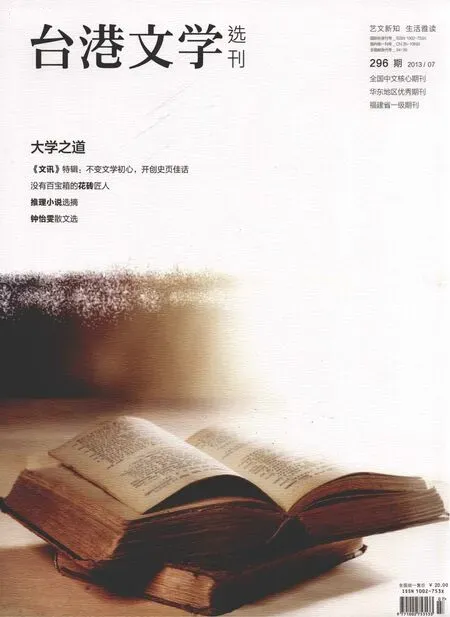時光的縫隙
鐘怡雯(馬來西亞)
出遠門最快樂的是回家。回家最幸福的是睡自己的床。出門愈久家愈可愛,床也愈溫暖。特別是長時間在外,從遙遠之處返家,疲軟身體撲倒床上,忍不住要贊嘆,哎,還是自己的床好。這柔軟美好的,屬于自己的床啊。旅館陌生的床雖然易于入眠,離家超過十天左右,就會開始想念自個兒的床,以及西門,一只二十一歲的玩具貓。回家的第一晚多半陷入混亂的睡眠,跟旅行時第一晚睡陌生的床一樣。醒來后,總有一段腦袋無法運轉的空白瞬間。輾轉幾個城市的長途行走之后最常這樣,這是旅行的真正終點。
那是時空的縫隙。
醒在自己的床,空氣清凈機的馬達高速運轉,被子床單混合房里無數難以辨識可是安心的氣味。再熟悉不過了,日常生活的氣息。所謂日常,便是教書開會家事各種瑣碎,以及偶爾失眠和低潮。有人美化為規律,有人說這是生活的本來面目。因為平凡,也就無奇。所有令人愉悅的驚奇或驚喜,都在日常之外,或者翻轉日常。說到底,日常生活的本質是無趣。
因此格外珍惜這瞬間即逝的旅行句點。時空的縫隙很快便縫合了,我回到日常,努力在每一個身份里恰如其分。玩也玩過,走也走得夠遠,痛快的花過錢,浪擲過寸金難買的時間。把兩條腿走瘦,把五花大綁的現實遺忘徹底,身體和腦袋同時變輕。再怎么不甘心,總也要回到日常。認命一點吧。
是的,最近開始認命,而且愿意接受日常,是三個月內數次往返中壢和怡保,以及中壢和吉隆坡之后。疲于奔命。終于對這四個字有了徹底體悟。
返馬不是回家也不是旅行,就只是出遠門。更準確的說法,出遠門探望親人。因此,離家比返家的意義大,我的床在中壢家也在中壢,不在馬來西亞。如果純粹開會住旅館,抗拒就小些。要住夫家或自家,我就努力縮短行程。然而母親開刀出了意外,我因此成了空中飛人。十九歲來臺后,從未有如此頻繁返馬的記錄。
睡在家人睡過的床,枕頭以及被子,連夢也難得。床是這么一種極端的貼身物品,要嘛完全熟悉,要嘛就全然陌生。要嘛睡自己的床,要不就睡旅館。不論睡怡保的自家或夫家,或吉隆坡的小妹處,我都開不了口,這床單被子枕頭套,換過嗎?
換過也不見得好睡。這種時刻,誰有心思伺候睡眠?
幾個月體力透支的超人生活,我用意志力撐著,母親也以她驚人的意志力,早早結束我的疲于奔命。最早大家都站在同一陣線,跟死神拔河。再后來,我與母親站在同一陣線,跟父親弟妹七人拔河。大家都希望她賴活,只有我希望她好死。要舍生取死,多么不容易。在最天人交戰的時刻,違逆感情用事。特別是面對自己的母親。
除了我,沒有人肯做這個困難的決定。老大難為。一個猶豫不決而脆弱的父親,必須有一個當機立斷近乎無情的女兒為他作主。無情到我必須發誓,下輩子,絕對不要跟這個男人有任何瓜葛。
不是第一次了。
祖母八年前過世,她比祖父多活的那兩年活得并不好。常常半夜驚惶大叫,排泄物抹得房間臭氣熏人。我們不了解她從前的過度潔癖,一如不了解她怎么會用這種難堪的方式折磨父母親折磨自己。我打了無數次國際電話強迫父親送她到療養院。一個月,你跟媽就休息一個月,不然到時垮掉的是你們。父親每天要上班,母親帶著小外甥女,兩人都竭力撐著。那時仍住南馬居鑾,弟妹在吉隆坡,出了事可是遠水救不了近火的呀!我不幫父親做決定,他絕對忍不下心。
祖母在療養院吃面噎死時,臺灣的sars疫情才結束,悶壞的臺灣人一窩蜂往外跑,問了四家航空公司,機票一位難求。父親沒要我回去,我亦無返馬打算。祖母跟祖父一樣火葬,是我拿的主意。父親在最后一刻還在考慮,火燒會痛,好嗎?
還好他是母親的丈夫,祖父母的兒子。
馬來西亞的華人習俗,人死了兩三天之內就要出殯,不論火化或土葬。不管六十或九十,再高壽也沒放上一個月的。祖父的喪事辦了三天,祖母兩天。回到家大概只來得及參加出殯。那就不要死別吧。
我一直以為參加的第一個,也是最后一個喪禮,會是我自己的。老實說,我對死別的場面畏懼又厭惡。我討厭淚水,生離夠傷心了,親人的死別是什么,我不想知道,或許也承受不起。十年前的節慶,在動物火葬場送別小女生的畫面和感覺還在。祖父死后一年,它也走了。初秋的雨已有涼意,天地灰蒙蒙。在雨里看著小女生裹著棕色毛衣送入焚化爐。兩個小時后,我捧著一個發燙的骨灰壇回家。再四天,把骨灰灑在靈鷲山一處飛蝶漫舞的面海小徑上,陽光明媚。這句點多美。我們的人間緣分在此結束。
如今我得幫父親,幫弟妹再做另一個痛苦的決定。
有一股力量把我分裂成兩半。白天我有忙不完的事,多虧這些日常,像張脆弱而強韌的蜘蛛網,把我勉強固定在軌道里運行。晚上躺在床上,我開始大大小小的盤算,各種無微不至的假設,在每一個細節里推論可能的影響或后果,反復問自己,這樣對嗎?那樣如何?追溯前因追問后果,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哪個環節出了錯?終至輾轉難眠。
難眠中繼續天問,為什么我沒有質疑到底。印度醫生很有把握,成功率九十五巴仙。這包票打得太滿。那么大的脊椎手術,決定得如此倉促。在我回家之前抵定,是誰答應了?我沒問后來也沒再追問。印度醫生在怡保很有名,手術經驗豐富,他簡短的解說沒有解除我飄渺的疑惑,可是,我也感受不到迫近的危險。這整件事情好像被一種詭異的決定性的力量設定過。向來不信任馬來西亞的醫療,這一回,印度醫生的鐵血判斷讓我無話可說。手術一定有風險,對吧?
母親的痛打亂了我。
年沒過完,母親背痛得無法站無法坐,第八第九節松脆的胸椎壓神經。我被家人告知,兩天后母親要動手術。母親很能忍痛。當她反復痛死了痛死了說個不停,那痛便弄亂所有人的生活,也擾亂父親。父親一亂,就會把我們全都煩死。手術能解除母親的痛,解決大家慌亂的根源。這巨大的期待,掩飾了手術的問題。
下飛機后跳上大妹的車,她飛車到醫院,兩個小時后,見到笑瞇瞇的母親一如往常。母親見到我很開心,笑瞇了眼。咦,你沒先轉去休息一下再來啊?上次見面,是去年年底,我在吉隆坡開會。我們在小妹家吃飯闔家大團圓,十六個大人十個小孩,一屋子鬧哄哄,亂糟糟,小孩滿屋跑,說話得拉開喉嚨。亂中拍照講話,真是耗神。好在我住旅館,吃完飯立刻逃走。自從家族成員多了小孩這種族類,家人的話題就圍繞著他們打轉。我這種沒小孩又不善跟小孩交際的人,就成了外星人。小妹挖苦我,跟小孩子說話那么難咩?大姨媽。我給她白眼,姨媽個頭,我還大姑姐咧。跟母親也沒機會說上話,我們習慣煲電話粥天南地北。
母親被醫生強迫臥床,嚴禁行走,吃飯也只能把床搖成十五度,免得壓神經。從入院開始到離世,她再沒下過床。
醫院的飯難吃,馬來人煮給各族病人吃的,沒豬肉更別談什么好料,母親仍是每一次送餐都要試兩口,看是什么味道嘛?三種菜各試一口,全搖頭。還是怡芬煮的好吃。三妹為她熬魚粥,香味撲鼻。母親吃得很開心。相比之下,更顯醫院餐的寡淡乏味。
一切都很尋常。手術后把打亂的現實重新排好,把睡亂的床單拉拉整齊,一切便都回歸從前。萬一呢?沒有萬一。母親才六十二,我們腦海里沒有也不允許萬一。對于死亡,我實在太天真了,而且缺乏經驗。祖父母離世都是八十好幾的老人了,二姑五十幾歲病逝,我的生命經驗里,死亡跟老跟病有關,跟意外無涉。
在這之前半年,我確實想像過父母的死亡。二十年以后,我六十好幾了,當他們八十幾老病在床,我得返馬照顧兩位老人。老人照顧老人的畫面我努力想了又想,搖搖頭。惟一能做的是,從現在起練好身體養足體力,等待那刻來臨。我演練過,借助電影和文學的想象。一群老去的兒女為父母送終,心智足夠成熟,風霜打過,應該不太難。況且,小妹懷胎三月,母親跟小妹感情那么好,一定會幫她坐月子,就像對每一個女兒那樣。母親很有把握地說,小妹懷的是兒子。
我們都錯了。我低估了死亡,太有把握。這是我生命最大的挫敗,輸得最慘也最不甘心的一次,甚至沒有機會還擊。母親也錯了,小妹懷的是女兒。
生命可以期待,它有形有體,而死亡不等,它是暗處的魅影,突然襲擊,防不勝防。沒有準備好這回事。死亡不能準備,而且沒有預兆。
在這最致命的時刻。有一股透明的膜把我過度發達的感官封住,阻絕了我對危險的感應能力。為什么沒有察覺到夢的預警?那預警非常細微,或許,我對死亡太陌生,我對死亡缺乏透視力。圣誕節前,有一天我打給母親,按捺住惶恐的語氣,你有沒有怎樣?關節痛嗎?夢令我不安,夢里母親縮著一張疼痛的臉,說不出話,背景灰暗,像中壢令人絕望的冬天。
沒啊,沒有怎樣。母親有點錯愕。這里很熱啊,圣誕節過完要過華人新年啰。她另起天氣的話頭。我放掉了夢。講完電話,疑惑和隱憂仿佛還在。后來妹妹跟我說,圣誕節后母親開始背痛。
我的夢預知了痛,沒有預知死亡。
開刀后臥床,最困難的事情不是照顧母親,而是伺候父親的情緒。妹妹們終于發現,父親令人難以置信的軟弱和暴躁。他的嘆氣和絕望表情讓人瘋狂,連最會甜言蜜語的小妹也訴苦。到底爸是怎樣養大我們的?他這樣子怎么做工?被父親氣得跳腳的時候,這變成我們的大問號。終于恍然大悟,原來,母親才是家里的支柱。母親一直是個有主見的人,父親的起伏情緒和猶豫多變從未改變,是母親扮演了海綿的角色,吸收了父親的強震,又給他出主意,讓他大多數時候看起來確實就是養大七個孩子,歷經人生風險的成熟男人,管理一個工廠,一人之下,數十人之上。
他背后的女人才是支柱。支柱一旦崩塌,我們都承受不住。
母親常昏睡,清醒時間不多。她說不出話,可是清醒時什么都知道,她看我燒水幫她泡腳,看我煮飯做家事。廚房本來是她的地盤,換我掌廚,她的無奈表情里還有很復雜的什么。自從我離家,她就再也不肯讓我近廚房,連碗也不給洗,好像我是客人。要是能說話,她一定揮手趕我像趕一只誤闖禁地的小狗,出去出去,沒你的事。喂她吃飯喝水,她眼睜睜望著我,吃一口停很久,也不嚼。媽麻,沒吃東西沒力,吃快快。我不叫媽,改口跟小妹一樣喊媽麻,帶著撒嬌的語氣。小妹在一旁煽風點火,博士煮的菜不好吃啊?母親瞪她一眼。媽,你好惡喔。我有講錯咩?小妹自問自答。母親忍不住笑了。母親一笑,時間剎時回到從前。我肩膀上的千斤重擔仿佛消失。幫她擦身換尿布,她立刻假寐。重擔又摔回我肩上。
她不要麻煩我們。
有時她會比手勢,張口發不出聲。這最讓我挫敗。跟母親講電話講習慣了,沒有聲音,我捕捉不到她的意思。我們雞同鴨講,溝通困難。痛得說不出話,那表情我夢里見過。許多次我咬著牙要他們滾,那些看不見的冤親債主。再也沒有機會煲電話粥了。這句話哽在我喉嚨,兩個多月來我喉嚨發炎牙齦流血,只有誦經時心情平靜,暫時忘卻肉身。
有苦說不出。我們都受著瘖鈍之苦。
有一次我住小妹家,床太硬冷氣太冷。小妹的黑鼻子常趁妹夫不注意偷溜到三樓打滾搞破壞,拿床墊磨牙在床單留下貓毛,然后在妹夫面前裝乖。他一直以為這只貓好家教。空氣中有灰塵貓毛的微塵懸浮。我的過敏鼻子癢心情亂,輾轉中聽到二樓的父親下樓又上樓,他固定三點左右幫母親翻身。等到他關了門,我提起腳跟也摸黑悄悄下了樓。
母親醒著。我指著自己的心說,痛。她也拍拍自己的胸口,伸手去擦淚。三更半夜的,我們母女趁沒人時比手劃腳掏心掏肺。我怕她傷心,趕快岔開話題。自顧自講了一陣在臺灣的日常,也不知道母親聽懂了沒,等累得迷迷糊糊語焉不詳準備上樓時,窗外天色已微明,便在那張硬墊上隨意打發黎明。后來我常在自己的床上,翻滾到這時間過了,才艱難睡去。
那陣子我負責做飯,一天兩頓。八人份的飯煮得虛火上升滿頭大汗,人沒睡好體內一座火爐在燒,熱天里煮飯又仿佛置身烤爐,內外夾攻。三菜一湯煮好,我食欲全無,湯倒碗連飯撥進嘴里,隨便應付肚子。每天都期待放平過勞的酸痛身體。有一晚我早早上樓準備休息管他睡不睡得著。樓下小妹跟妹夫看電視,母親有人陪。
終究放心不下,又拖著腳步下來。
母親一見我就笑了。湊過臉去,她伸手來摟我,摸我的臉我的發。打從有記憶來,母親從沒主動抱過我,我是難以親近的遠距女兒,跟父母親太近總是不自在。不像小妹,從小到大都屬于摟媽族,沒斷奶似的。這是跟母親最親近的一次。惟一,也是最后。她笑得沒病沒痛,背后那條從頸子開到尾椎的傷口仿佛不存在,那場手術最后仿佛并沒有開成。笑完她還要起來煮飯喂雞,收衣服切水果。下次我打電話回去,照例她又會說,雯啊,是你啊,按得閑啊。
時光一逝永不回。
半夜聞到神秘的莫名臭味,一下把我驚醒。另一個世界給我捎來訊息,是告別的時候了。心酸難耐,就是無淚。
兩天后母親開始發高燒,拒食。大妹哭著求她,半逼半哄,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舍得我嗎?啊?母親只好順著女兒的意思吃幾口。大妹還在skype前演她如何喚起母親的求生意志,小妹挺著五月肚端著三妹煮的紅豆湯喂母親。我把小家伙抱到鏡頭前。母親在輪椅上好奇地盯著我懷里掙扎的,嗯,其實是六點五公斤的大家伙。唉,我以貓代孫子娛親,母親已經習慣了。她嘟了一下嘴,意思是什么嘛,拿只貓敷衍我。那是我最后一次跟母親說話。
回到中壢后,我開始幫她準備后事,每晚在自家的床上翻轉,活得像游魂。除了誦經,什么事都進不到我心里。
三個星期后,父親弟妹跟死神拔河的手被我一勸再勸,終于松開。母親走的時候,我還在計程車上,再一小時就到怡保了。我又錯了,這回一樣錯在太有把握。一定是凌晨四時,那晚在小妹家,母親如此暗示我。沒想到是下午四時。母親果然是個有主見的人。
進了家門,第一次見到母親沒喊媽。她鋪著我郵寄回去的金色往生被。我給她誦了八小時的阿彌陀經。眼淚已經被父親和弟妹流光了,我一滴淚都沒有。直到現在。
母親總在時光的縫隙里閃現。入睡前,醒來瞬間或夢里。切菜煮湯,掛衣服拖地板,吸塵吸到一半,數不盡的這些那些瑣碎里,突然便想起,很久沒有打給母親。就那么幾秒,短暫發傻,或者出神。再繼續未完的工作。有一把利刃在心上劃來劃去,反反復復。有東西哽在喉頭,不上不下。母親不在了,原來是這樣。
如果,有一天可以流淚,或者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