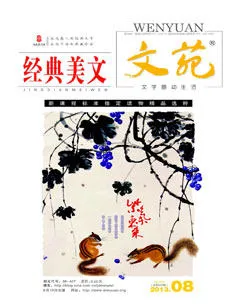向泥土敬禮
半年以前,細細拜讀了耿立先生的這篇《向泥土敬禮》,撲面而來的是一種久違的味道和氣息,像一條溫熱的河流,輕靈明快而又動蕩激越地撞進我的心懷。文章不同于一般的鄉土散文,既不是閑情逸致式的詩意棲居,又不是沉郁頓挫式的深重苦難。不是簡單的情感抒發,而是給我們傳達出一種樸素的哲學和文化理念——勞動創造了美,創造了一切,對于給我們提供衣食的土地和滿身泥土的勞動者,我們要永遠心懷敬意,對于在這土地上共生共長的一切生命,我們都要心存敬畏。文章始終流淌著樸素而崇高的情感,除了敬畏和敬愛之情外,也表達出對和諧美好的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向往。文中的父親樸實、勤勞、善良,極富愛心和悲憫之心——他在松土的時候,不小心斬斷一只蚯蚓,于是他內疚地用裝死一會兒的方式體味蚯蚓的痛;對于莊稼地里的草,父親也不舍得痛下殺手;秋收罷了,父親要把泥土里的瓦塊磚頭剔除出來,怕這些骨頭硌著睡眠的泥土,怕在地里漫游的小動物閃了腰……這樣一個大地之子的形象,在一個個細節的刻畫中顯得光輝生動、親切自然,讀罷,長久地震撼著人的心靈。
與炊煙和蚯蚓是鄰居,木鎮的人就像夫子而言:與德比鄰,道不孤。木鎮人有木鎮人的道,遠親不如近鄰,近鄰不如對門,對門的是樹和泥之河,一打開屋門,房檐下排闥而來的是草繩般的河水,不事喧嘩,冬季里只有一扁擔寬窄,結冰了,牛啊,羊啊,在冰上踏過,有時就跌跤,牛羊就無奈地看著春天還軟的河水,到了冬天就有了脾性和骨頭,都是鄰居,怎么就有了鬼臉,就舍得下起了絆子?
但大地不言語,大地什么時候大聲鏜鞳地咋呼過呢?人們說鄉村是泥土做的,是啊,木鎮的一切都在泥土上,父親說泥土就如一領席子,植物動物泥之河與人都或蹲或踞或躺或臥或立或動在這領席子上。我知道每到秋季,泥之河的蘆葦就白頭了,那些纓子如白蜜蜂亂飛。童年時家里窮,父母常為衣食而憂,到泥之河里割蘆葦,然后編席子編草鞋可到集鎮換錢。每到秋風來到木鎮,母親就睡不著,秋風一掀覆蓋窗欞的草簾子,父親的臉就抽搐一下,等雞開始亂叫的時候,母親聽到父親下床開始在院子里嚓嚓地磨鐮,母親有些于心不忍,就折身靜靜掀起草簾的一角,朝黑糊糊的窗外看。能看到什么呢?哦,下霜了,在草簾的一角,哎呀,滿地銀銀的白霜透過,地上、墻上、房檐上,都是銀銀的,如滿處的蘆葦纓子黏在那里,而黑糊糊的是父親在院子里磨鐮的剪影,母親放下簾子,縮回了身子,溫溫地說,時間還早,再瞇瞪一會兒。
父親編的席子像云彩,有諸多的花樣,人們可鋪床,可做窗帷子,可圍起做盛糧食的囤,但父親說泥土如一領席子,是要人愛惜席子一樣愛惜泥土。
木鎮的人不識字,但不妨礙他們把泥土當作《圣經》,他們知道大地上的一切都是泥土給的,炊煙呼吸,雞叫驢打滾,草的種子,這只是《圣經》不同的文字,如果說草的種子是漢語印制的,父親能讀懂,那村長折騰土地的脾氣就是英文印制的,他讀不懂,有時村長讓大家種水稻,但卻顆粒無收,父親說我們這里的地寒,水稻是金貴喜暖的玩意兒,泥土有脾氣,你不要拗,種子也有脾氣,你把莊稼種到石板上?你把草籽把蔬菜籽撒到瓦楞上?
席子在家里要金貴地用,對土地,對土地上的一切,亦應如是,泥土與人,人與草,草與谷粟,大家都是平等的,要照顧各自的脾胃,不要人有脾氣就欺負泥土,欺負鳥雀,大家都是對門合戶的,抬頭不見低頭見,以免做錯了事說錯了話,臉紅。
我看到父親在田埂上掮著鋤頭走,一遇到牛從對面思索著過來,父親就退后一步,不像西方的人把手捂著胸脯心跳的地方那樣,但絕對的虔敬,如除夕從祖墳把先輩的神靈請回過年一樣,父親相信離牛頭三尺的上方,和人與谷穗離頭三尺的地方有神靈。
我讀過父親的手,雖然如樹皮一樣皺褶蒼老,有點變形,手上的青筋如蚯蚓,但他在泥土里與泥土多年相互扶持,有著泥土的溫暖,我一握的時候,就像莊稼的汁液傳到我的脈管和血管,這是泥土的溫度,父親的手粗糙么?但這樣的手在泥土里絕對靈活,他鋤地時,絕對不傷害莊稼,而對草,也是盡量照顧,只要和莊稼和諧相處,父親是不會對草痛下殺手的。父親的手上長了一雙靈眼,只要靈眼一覷,草留幾棵,莊稼留幾苗,那是一定可巧的,父親說,草來到莊稼的領地是來串門,如果草多了,那是草霸道了,反客為主,那就要教訓了,但一般也是警告,一般不會判處死刑,把草們拿到太陽下暴曬。
但父親年老了,手指有時不太靈便,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在春天的驚蟄后,他在麥田松土的時候,不小心把一只在泥土下路過的蚯蚓斬斷了,父親內疚喃喃:這怎么好,這怎么好。
父親停下手,拿眼睛乜斜地看我一下,從兜里掏出一支用煙葉卷成的煙,咝咝地點著,然后閉上眼睛,他說出了令我吃驚的話:讓我裝死一會兒。
當時我一時沒有明白父親的話,作為農民不能不耕作,在耕作時,父親總是小心翼翼,但他有時無法阻止悲劇的發生,就如他不小心斬斷了一只蚯蚓。他卻屏住吸氣,說,我裝死一會兒,這是在推己及物想象蚯蚓的痛嗎?(多年后,我讀到狄金森的一首詩,我想到父親:如果我能使一顆心免于哀傷/我就不虛此生/如果我能解除一個生命的痛苦/平息一種酸辛/幫助一只昏厥的知更鳥/重新回到巢中/我就不虛此生。父親不是詩人,但他在泥土的圣經里讀出了道悟出了道,作為生命,誰比誰低賤卑微多少呢?)
確實,木鎮的事物在自然的律令面前,懂得尊重,說驚蟄了,羽毛開始上揚,泥之河的冰塊開始放下身段,泥土也解開了懷;說立秋了,知了的聲音就謙遜了,夾襖開始在早晚派上了用場,披在早起晚歸的人的肩頭,而泥土也開始看著牛的反芻盤點一季的收獲。
即使冬令時節,父親也是閑不住,父親會把土墻上的野蜂窩蓋上麥秸,怕小生靈跋涉不過雪季;他也常和叫作家賊的麻雀對話,有時就撒出一些苞谷犒賞一下這些小家伙,作為一年在窗前恪盡職守叫醒農人的獎勵;有時父親要在陽光晴好的時候堆糞翻糞曬糞,這不是輕松活,這是為了對泥土來年的報償,泥土在收獲后,如產后的女人,你想他們陪伴著小麥走了一春,陪伴著苞谷走了夏季秋季,如今到了該歇息的時候,就如女人產后要吃紅皮雞蛋喝紅糖水,父親在把莊稼地騰出來茬以后,就想著為泥土養身子了,到了秋收罷了,父親還會到田地里去,他像逡巡的士兵,把泥土里的瓦塊磚頭剔除,怕這些骨頭硌著睡眠的泥土,怕在地里漫游的小動物們閃了腰,怕來年開春撞壞了犁耙。
在木鎮,村長曾想讓我起草個鄉約,在回木鎮的冬季,在煤油燈下,我擬定了幾條,還沒有定稿,有幾條是這樣的,木鎮鄰里鄉約:
無論植物動物人物,無論姓張的人姓李的人,無論姓楊的樹姓李的樹,還是姓白的羊姓烏的豬,在這片泥土上都平等;大的動物、人物如果見到搬家的螞蟻,腳板要后移5厘米;若是下雨,植物要肯把自己的枝條借給螞蟻作舟楫;要珍重生命,把老死的蚯蚓的尸體要掩埋,以免暴露在野;在過節的時候要互相問好拜年,要長幼有序,知道尊老愛幼……
當父親從田野回來,母親上前接過手中的農具和衣服,父親的頭上冒著汗,我看母親接過的農具是鋤,就疑惑:冬季了還去鋤地?母親說這是為了保墑,父親到地里翻土敲打土坷垃。其實這樣的活就像城里興起的按摩,這是為土地,為貢獻了一茬一茬莊稼的土地,父親心里最清楚,土地糊弄不得,土地和人是兄弟,多少輩子都比鄰而居,對別人好也是對自己好。
從地里回來的父親臉上有一塊泥巴,母親想用手摳下來,接著就想卷起衣襟擦,父親招呼了一下說不用了,是守著我,父親羞澀了,但母親的親昵是對勞作的一種尊重,泥土在臉上怎么了,有時米粒和碎饃掉到地上,雖滿是泥,父親吹一下,或者母親用衣襟擦一下,就填到嘴里。土地在父親的臉上,是土地的徽章么,作為對一輩子的老鄰居的獎賞,是否在父親的臉上撒一把草籽,用洗臉水一澆就能發芽?詩人雅姆說:
如果臉上有泥的人從對面走來
要脫帽致敬,先讓他們過去。
是啊,我們什么時候,對有泥的人有過足夠的尊重呢?我們向泥土敬個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