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旭輝:在寂寞城市上演的悲喜劇
許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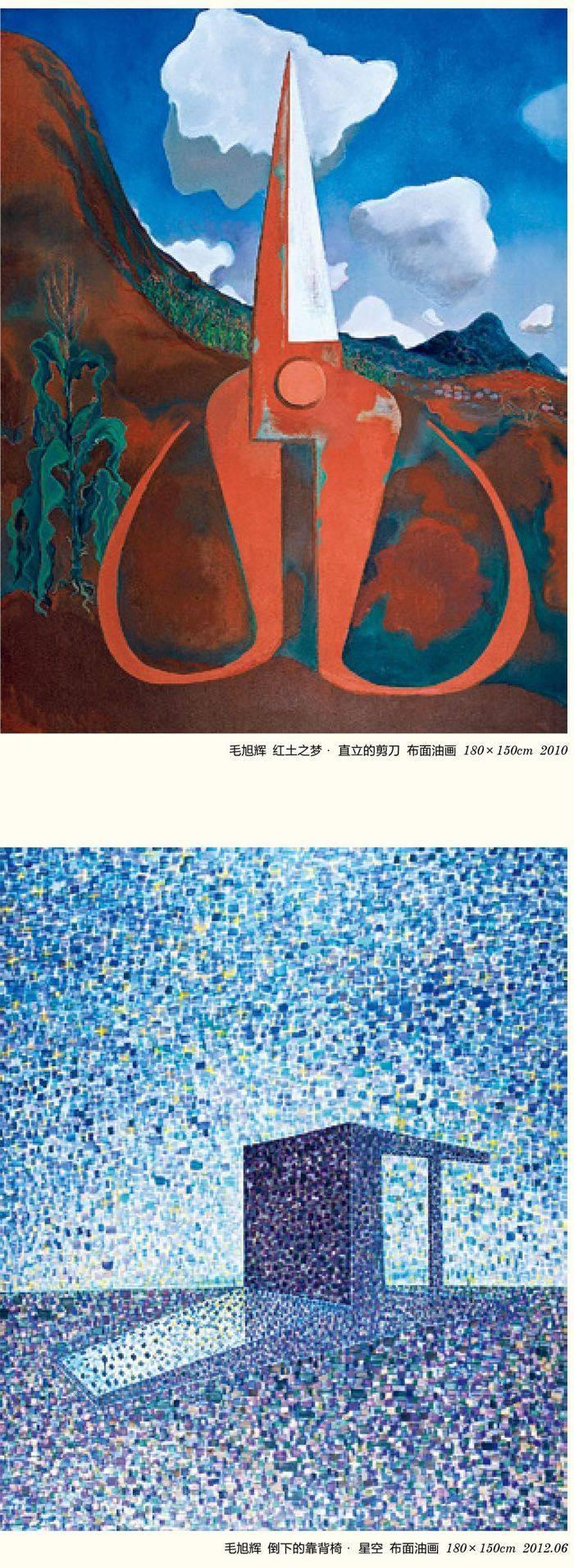
《東方藝術·大家》:您理解的當代藝術的概念是怎樣的?
毛旭輝:我覺得當代藝術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它包含的東西太多,概念很難去界定,現在的藝術圈都在打“當代藝術”這塊牌,我覺得有點爛了。這暴露出中國的關于藝術的價值沒有一個確定的說法,是模棱兩可的,不像歐洲的藝術史發展那么悠久和清晰,許多建設良好的博物館體系放在那里,而中國當代藝術缺乏具體的參照,或者說我們缺乏一種共同的價值觀,那么所謂的當代藝術的概念就是非常混亂的。
《東方藝術·大家》:您認為所謂的一線、二線城市的當代藝術差異在哪里?您覺得北京、上海與您所在的云南當地的當代藝術上有哪些差異呢?
毛旭輝:在我的概念中其實沒有一線、二線城市之分,這通常只是一個經濟概念上的劃分,這對于藝術家來說其實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從藝術的角度來講,更有些許荒謬。關于文化不能用簡單的一線、二線這種量化的概念或是經濟的概念來束縛它,這是需要歷史來證明的。
北上廣等與云南,這就是之前常說的中心和邊緣,差異是永遠存在的。客觀來講,北京、上海等地的文化,無論是商業活動還是歷史文化,這種氣息都要濃一些,大城市有大量的人口聚集,多元的文化碰撞,主要的藝術市場都集中在這些比較一線的城市,這是不可回避的一個客觀存在。這種情況在歐洲并不見得,在歐洲反而小城市形成了比較濃厚的藝術氛圍,比如卡塞爾、威尼斯等地,但在中國大部分還是跟政治、經濟聯系在一起,就形成了具有中國特點的中國文化藝術圈。
每個藝術家都生活在一個具體的環境中,所創作的藝術作品也都是這個環境的真實寫照或是超越這個具體的環境的,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藝術有這種形而上的色彩,它有精神價值,而這精神價值是藝術家對具體的生存環境的超越。這些精神價值必須有一個具體的現實環境作為依托,從具體的環境出發,現實的生活給了藝術家創作的資源。
《東方藝術·大家》:您為什么會選擇云南,當地現實的生存環境對您的創作思考有怎樣的影響?
毛旭輝:選擇源于內心最簡單的初衷。我自小在這生活已有50多年了,年輕時也曾想過去大城市尋找更好的發展,那時候認為遠方會有更多藝術語言的選擇,藝術也能夠獲得更多的尊重。基于這個初衷,我也曾做過北漂或和出國,不過都是很短的時間,后來發現這個地方實際上并不存在,作為一個藝術家,不論在哪里面對的問題都是一樣的,比如當地的氣候、文化氛圍等,你并不能很快地融入進去,大家也不會在短時間內理解你,這讓我覺得不夠自然。基于這樣比較簡單的原因,我選擇留在云南。不是說云南特別好,只是我習慣了它,知道它的好與不好,能更好地融入和把握它。
《東方藝術·大家》:云南當地的豐富性和原生態是否可以為當代問題產生提供土壤?地方上的藝術生態是否已經形成了某些自身鮮明的特色呢?
毛旭輝:對于真正的藝術家來講,很多素材都可以成為他創作的資源,不存在是在紐約還是在昆明,也不存在是在倫敦還是在北京。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從任何地方都可能散發出這種創造性,不是某個特定的環境才能創作好的作品、某個特定的地方才能成就偉大的藝術家。
地理位置的不同,造就了地方藝術生態的差異,進而形成自身鮮明的特色,云南的得天獨厚令它與大自然比較親近,自古就是個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在不同民族間文化的融合和碰撞中,人們尋找到更多元的生存方式來適應復雜的生活環境。我覺得在云南生活的藝術家都比較寬容,樂于接受這種多元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給了藝術家更加豐富的想象力,比如當代藝術領域比較知名的藝術家張曉剛、葉永青、潘德海和曾浩等人,他們的創作或多或少都跟云南的生態環境有著某種聯系。云南的天空、氣候容易滋生夢想,在上世紀80年代,它離所謂的中心城市比較遙遠,在上大學的時候,坐火車去北京看個展覽要2天3夜三千多公里的路途,所以很不方便,而這個不利的因素恰恰激發了一些積極的東西,就是滋生了豐富的想象力。這也是為什么在上世紀80年代會在云南這個地方會產生像“新具像”這樣的藝術群體的原因。
《東方藝術·大家》:與同樣的二線城市,像成都、重慶還有蘇州南京當代的藝術氛圍特別好,整個生態圈建設也特別好,您覺得云南跟它們的區別是什么?些限制云南發展的因素在哪里?
毛旭輝:成都、重慶發展得好,也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扶持。可以說生活在云南的藝術家會更寂寞一點吧,其實我也曾向往過外面的世界,在這里藝術沒有被很好的被理解,藝術家沒有得到相應的尊重,我覺得主要還是地方文化意識的限制,比如說10多年前,在云南就可以花很少的錢買到葉永青、潘德海等大家的作品,但極少人有這樣的意識。
《東方藝術·大家》:云南的畫廊、美術館拍賣系統相對較少一些,對當代藝術的發展交流有什么影響?
毛旭輝:中國的美術館其實離真正意義上的美術館還相距甚遠,美術館在功能上還沒有完全達到引領藝術潮流的精神殿堂的作用,還不具備研究和對當代藝術文化進行的判斷的能力。云南的畫廊和美術館更是鳳毛麟角,幾乎沒有什么交流,生活在云南的藝術家對這些資源不會有任何幻想,對于藝術來說是更為純粹的,藝術單純是藝術家生命和心靈碰撞的精神產物。
《東方藝術·大家》:您覺得這種差異,差異體現是一種什么樣的背景和考量呢?
毛旭輝:經濟還沒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都還沒有意識到藝術精神食糧的重要性,還沒有意識到“梵高”可以為你賺錢吧,這個城市即使有一個“梵高”,也未必有人肯投資給你。
《東方藝術·大家》:當地的一些藝術院校與本地的藝術生態的互動方式有哪些您能簡單的介紹一下嗎?
毛旭輝:在當地這種互動特別少,只有少數畫廊靠出售風景畫來維持運營,藝術院校的展覽互動最多就是作為一個公司的文化活動來舉辦,公司提供場地來展出學生的作品,這也是一種藝術生態,最終沒有什么實質的作用,相對還是閉塞和寂寞的狀態。作為老師我還是鼓勵學生,在“地球村”的環境下,更多地跟外面進行交流,這對于創作和開闊眼界都是有益的。
《東方藝術·大家》:就現在年輕藝術家面臨選擇的時候,您能給一些建議嗎?
毛旭輝:藝術有超越現實的能力,它是與夢想息息相關的。我們還是要扎扎實實地生活,沾著地氣兒,用心去感悟、體會生活,這樣才能超越生活,創作出杰出的作品。不能每天夢想著去到藝術的大都市,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還是要選擇一個適合自己心靈的環境,安心創作。所以問題的焦點不在地理位置,其實每個人都是很普通的人,但是你應該利用個人的生存經驗,可能就是你未來去發展的一種特別的資源—別人所沒有的、所不具有的,應該去尊重自己的生活。藝術家就是去尋求、實現自己夢想的人,就看你想要的這個夢是悲劇還是喜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