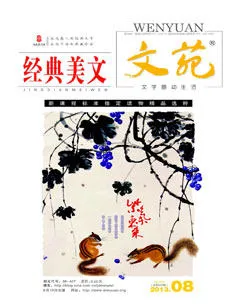母親的年
本期客座主編:
尉克冰,1978年生,河北內丘人。2012年8月,榮獲第五屆冰心散文獎。現為河北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河北省散文學會理事,多次榮獲國家級、省級獎項。
名家品讀名家。2013年,我們每期邀請一位名家,對經典的文章和書籍進行推薦和點評。透過這扇窗,借一雙慧眼捕捉別樣風景。歡迎大家支持參與。或許您就是我們要找的名家,只要您有足夠的自信,那就請趕緊和我們聯系,把您的和您喜愛的作品與萬千讀者分享。
母親的年,不是正月初一,而是正月初三。
按我們當地的風俗,每年的正月初三是姑爺給岳父岳母拜年的日子。這一天,街頭里巷人流如織,飯館酒店棚棚爆滿。花花綠綠的點心盒子或者煙酒穿梭在街道里,朝著岳父岳母家的方向飛。
母親有兩位姑爺,每到正月初三,她都會喜上眉梢,忙得不亦樂乎。可是,她一不喜歡讓姑爺到飯店請客,認為在家吃飯有過年的氣氛;二不喜歡讓姑爺行跪拜禮,說這是舊規矩,孝不孝順不在乎這個形式。可我知道,在我們當地,過年時,很多人家直到現在還十分在乎姑爺的跪拜禮,就像在乎一定要張貼對聯一樣。然而越是如此,兩位姑爺就對我的父母越是敬重孝順。
母親總是在初二的晚上,就把她買的最好的糖果瓜子擺出來,把菜和肉清洗干凈,餃子餡兒剁好,將雞鴨魚燉好。她那雙干澀粗硬的手不停地洗涮,因此泡得通紅。
每年的大年初三,一家人都盼望著。一進門,我兒子和小外甥女就會跳到母親懷里,母親臉上的皺紋頓時卷曲成花朵。不多久,一道道美味佳肴躍上了餐桌,那是母親的杰作。在這中間,只要我和妹妹一進廚房幫忙,就會被母親推出來,“你們平時工作忙,都歇著去吧,陪孩子玩兒!”吃飯時,母親就更忙了,給外孫剝蝦,給姑爺夾菜,給女兒添湯。忙來忙去,我們都快吃完了,她自己的飯還沒動。
多少年來,母親就是這樣忙個不停。家里家外,處處有她忙碌的身影,想到這些,我就不忍抬頭看母親,不忍看她日漸松弛的眼袋,不忍看她爬滿皺紋的額頭,不忍看她染上霜雪的兩鬢。這一天,她的臉上始終掛滿笑容,她因為擁有我們而幸福、快樂著。
人老了,是渴望兒女陪伴的,尤其過年的時候。當春聯貼起來、鞭炮響起來的時候,老人從內心盼望著能夠享受兒孫繞膝的天倫之樂。可母親要從年三十盼到正月初三,才能有這樣的享受。這日子是在母親默默巴望中到來的。
因為她沒有兒子,只有兩個女兒。
不知是哪年哪月哪輩留下的風俗,女兒出嫁后,不能在娘家過除夕和初一,連父母的面也不能見,說是不吉利。迷信觀念認定,已逝的老祖宗年底從天上回家享受供奉,如果看到家里有“外人”,就不愿進家;在初一(或初二)晚上,老祖宗重新回到天上,女兒才能回家。這個規矩在舊社會特別是農村是很嚴格的,違反了就是大不敬。新社會里,人們雖然不大信鬼神了,可在我們當地,誰也不愿成為“始作俑者”,落得沖撞祖先的罪名。
因此,我想母親內心最深處,可能依然埋藏著些許沒有兒子的遺憾,尤其是過年的時候。
兩個女兒先后出生了,家里越來越熱鬧;兩個女兒先后出嫁了,家里越來越清冷。
二十九年前,妹妹出生了。當這個小生命呱呱墜地的時候,全家人沒有太多的喜悅,尤其是奶奶和父親。作為長子的父親,一直希望母親能為他生個兒子。在一絲嘆息中,父親低頭離開了產房,回家為母親煮雞蛋。可是,在失意和困意雙重糾纏下的父親居然歪在床上睡著了,等他醒來時,雞蛋早就被煮開了花。產后虛弱的母親,抱著襁褓中的妹妹,流著淚。三天后,同一產房里,一個男嬰誕生了,他是家里的二小子。為了圓兒女雙全的美夢,兩家決定將孩子交換撫養。可到正式要換的時候,母親的目光不肯從妹妹身上挪走一寸,看著孩子忽閃忽閃的大眼睛,母親將她緊緊抱在懷里,不肯松手。
許多年過去了,母親還偶爾提起這件事。看得出,她的態度是慶幸。而令她慶幸的不只此事,還有我們的婚事。我們當地有些沒有兒子的人家,為了傳宗接代,會招女婿上門。在我即將談婚論嫁的時候,姥姥三番五次叮囑母親,一定要留一個女兒在家里。母親只是笑笑,最終也沒有遵從姥姥的意見,放飛了我們。姥姥杵得拐杖篤篤響,擰眉嘆氣說,傻閨女,不聽娘的話,到時候你就后悔嘍,過年時人家家里都熱熱鬧鬧的,就你們跟前沒個人兒陪。
姥姥的話一半對一半錯。母親從來沒有后悔過,因為她的雙眼,可以捕捉到我們的幸福。兩個優秀的女兒也逐漸成為父母的驕傲。每當有人在母親面前夸獎我們的時候,母親總是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尤其是搞業余創作的我,成了別人眼中的“作家”,時有文章發表在各地的報刊上。每次發表了文章,我都會拿到母親面前“炫耀”,那種炫耀成了讓母親感到欣慰的精神食糧。
我們都飛向不同的巢穴,老巢里,只剩下身子骨越來越單薄的父母。而我也越來越在母親那細長佝僂的身影里讀到孤獨與堅韌。
過年那天,女兒不能回家的風俗像一條無形的巨大繩索,將我和妹妹攔在了母親門外。繩索的一頭是孤獨,另一頭是思念。每當年三十和初一,我們一家三口和公婆團聚在一起,談天說地、觥籌交錯的時候,我就會想起我的父母。震耳欲聾的鞭炮聲里彌散著濃濃的年味,在人們的聽覺和嗅覺里此起彼伏,一直連綿到一百公里以外的太行山。這是萬家團圓的日子,火紅的日子。而母親和父親卻守著兩盤餃子,默默無語。餐桌上沒有酒,也沒有菜,除了餃子還是餃子,并不是家里沒有,也不是他們舍不得吃,只是過節的時候缺少了我們,他們就缺少了興味和樂趣,一切都變得同平素一樣簡樸。于是,我就在電話那頭勸他們多做好吃的,勸他們到親戚朋友家里玩牌,勸他們去看電影……我也勸過我自己,沖破那繩索,去陪他們吃上一頓飯,可是卻沒有成功。因為攔住我的,不僅是那無形的繩索,還有人們不理解的目光。這條由來已久的繩索,攔住的也不僅僅是我和妹妹,而是農村里世世代代、千千萬萬個過年時無法回娘家的姐妹。
今年春節,母親的年里沒有紅火和熱鬧,即使是在大年初三。因為父親躺在病床上。每天,母親和我游走于病房和醫生辦公室之間,穿行在住院樓的走廊里,飛馳在醫院和家之間的路上。眼睛看不到街上紅色的春聯、燈籠和花花綠綠的年畫。眼前,全是白色。醫護人員白色的大褂和口罩,病床上白色的床單和被子,還有父親蒼白的臉色。
守候著父親,看著透明的液體一點點從瓶子中滲出來,滴入父親的血液,流進他的身體。監護儀上顯示著父親的心率、血壓和血氧。一根又一根的線,將父親的身體和種種儀器接通。這時候,生命的特征就是一個個不斷跳躍和變化的線條和數據。這些數據又通聯所有家人,心隨著它們的變化而跌宕起伏。
我注視著病榻上瘦削的父親和守在床邊的母親,感覺時間過得太快了,又一年終結了。父母真的老了。我們無法阻擋時間的腳步,它鋒利得如同刀子,我們如同在刀上行走。我甚至聽到,時光沙漏磨蝕父母皮膚的聲響,它摧塌他們曾經飽滿的臉頰,橫掃他們的眼角和額頭。它固執、高高挺立,強大而又隱秘,無法擺脫,更無法抗拒。
這個春節,我們幾乎是在醫院中度過的。一切鞭炮和禮花、過年的盛事,皆與我們無關。對于父母,唯一的幸事,就是大年初一那天,與兩個女兒團聚在一起。是父親的病,暫時擊倒了世俗的觀念。
我的內心不免一陣凄涼。
在中國最盛大的節日里,父母的孤獨成為我揮之不去的疼痛,他們孱弱的身影、單調的生活,不斷浮現在我的頭腦里。可是,他們卻不承認,總將內心深處的落寞隱藏起來,怕我們擔憂。
父親出院后,我開始上班,不能經常守在他們身邊。每當我打去電話的時候,母親總說一切都很好,只要我們過得幸福,他們就很開心。而我能做的就是經常回家看看,多陪陪他們。因為我發現,家里只要有了我們,即使平常的日子也像是過年。
一個母親,從孕育了兒女的那天起,她的命運就緊緊與孩子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母親如同一棵大樹,兒女便是樹上的花朵。無論身下的土地是肥沃的,還是貧瘠的,深扎地下的根須總是把最充沛的營養提供給花朵,花兒才能開得更加豐盈飽滿。母親是不變的圓心,兒女是圓心周圍的弧線。無論半徑有多長,也走不出圓心的視線,只要有我們圍繞在身邊,幸福就會在母親的時光里環繞。
母親的年不是正月初一,也不僅僅是正月初三,而是有我們陪伴的每個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