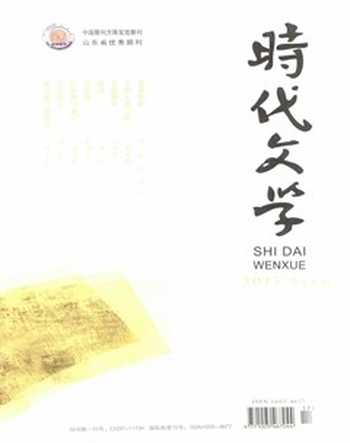半坡春早
向本貴
一
三月的陽光像一只溫暖的手,輕輕地撫摸著身子,讓人渾身發軟,心里還有一種癢酥酥的感覺。水田旁邊的林子已經泛起了新綠。兩只喜鵲蹲在枝椏上它們剛剛壘好的新家里,身首相偎,一邊說著悄悄話,一邊恩恩愛愛地做著只有春天里才做的事兒。李玉年看它們的時候神情有些發呆,后來眼淚就出來了。
山風里纏綿著一縷花的芬芳,沁人心脾。李玉年朝旁邊的山坡看去,一叢刺玫瑰在春陽下開得正艷,一只蝴蝶探頭探腦地在花叢上面飛來飛去。李玉年真想去摘一朵花兒戴在頭上,想一想,她又沒有去摘。半埡村的人們都說她自己就是一朵開得正艷的花兒哩。這么想的時候,她就看了一眼正在耙田的男人田長松。田長松卻沒有看她,他當然不知道女人現在的心理活動,更不知道她在默默地掉眼淚。從他嘴里傳出一聲緊著一聲地吆喝。水田再耙一遍,就可以插秧了。只是借來的一頭公牛卻不怎么聽使喚,甚至還有些消極怠工。它的心思早就跑到下邊田里那頭母牛身上去了。在下邊田里做活的是村里張大全。張大全昨天晚上來到李玉年家對田長松說,再不能在家里待了,得打工去了。怎么說在城里打工比在家做陽春劃算。
平時,半埡村在外面打工的人都是過年的時候風風火火趕回來,跟家里人吃頓團年飯,除夕守守歲,就又風風火火往城里趕,連擠車趕路的時間算一起,前前后后也不過十天八天。中國人一輩一輩傳下來的風俗習慣,注重的就是那餐團年飯。不管吃的是什么,雞鴨魚肉也好,粗茶淡飯也好,全家人坐在一塊吃就行。
田長松和張大全一起在廣州一家廠子打工十多年了,每年的臘月二十八九往半埡趕,正月初一初二又得趕回廣州去,不過在家住三兩天。但他們愿意擠車,愿意趕路,愿意吃苦受累。他們有動力。他們才三十來歲,身強體壯,精力旺盛,想老婆想得發瘋。往廣州趕雖是依依不舍,也還是有動力的,他們想錢,錢是個好東西,誰都喜歡它。能改變家里貧窮的面貌,能讓人腰桿挺直,說話硬氣。但田長松和張大全掙錢卻是另有打算,他們要送兒子讀書,一直讓兒子讀到大學去,不能像他們那樣,一輩子做農民工,做城市的過客,像是浮萍一樣,無論漂到什么地方,最終還是要回到農村來。兒子讀完大學就在城里工作,買房子,找老婆,成為真正的城里人。
去年過年的時候,田長松和張大全都沒有回來。不是因為火車票難買,火車票再難買他們也能想到辦法,想老婆的動力能讓他們排除一切困難的。廠里的領導說春節期間工人都不能回去的,留下來加班。廠里接到一個外商的訂單,要在春節的時候把貨趕出來。廠領導答應漲工資。年關將至,空氣里飄散的都是過年的味兒。這些遠離家鄉的農民工們歸家心切,漲不漲工資已經沒有了吸引力,廠領導就動用他的殺手锏,誰在這個時候回去,明年再不要來廠子上班了。工人們就不敢動了。上得好好的班,工資也不錯,活兒也不是很累,被開除了,心有不甘。
加班加點,貨是趕出來了,正月也將過去,廠里許多人還是陸陸續續往家里趕。父母盼著,老婆孩子盼著。這時,田長松和張大全卻改變了主意,這個時候回去,還不如等兩個月回去,也好幫著女人做做陽春;再說,過年不回去了,把過年的時間用來加班,就又可以掙一筆錢了。兩個男人,肩頭挑著一副擔子,一家人的幸福,兒子日后的希望,都靠著他們的。即便是夜里想女人想得睡不著覺,想得發瘋,都要讓位于頭等大事。
田長松說:“這次回來算是時間最長的一次了,住了十來天。把秧苗插下去,是該走了。耽誤十天半月就幾百塊錢啊。”
就是說,今天把田做好,明天插秧,后天男人就要去廣州了。少說也要到過年的時候才能回來。九個多月,在李玉年看來,那是很長很長的日子,那是無邊無際的等待,那是如饑似渴的憋忍,那是如火如荼的煎熬。要是按男人說的,明年過年的時候再回來,那就不是忍耐和煎熬了,那等于是要命。前年,田長松就隔了兩年才回來的。自己把嘴唇都咬出血來,夜里才沒有打開那扇讓自己能陷入罪惡深淵的房門。
眼淚從李玉年好看的臉上一滴一滴流下來的時候,被三月的太陽一照,就有幾個太陽落在她的臉上了。
這天晚上,李玉年殺了一只雞。往常李玉年辦了好菜總要給隔壁郭婆婆送點去的,今天她同樣送了些雞肉去給老人吃。郭婆婆七十多歲了,還上山做活兒養活自己,可憐啊。只是,李玉年沒舍得把雞腿給郭婆婆,她把兩個雞腿全讓男人吃了。田長松想把雞腿給她吃,怎么說雞腿都應該女人吃的啊。她卻不要,只是含情脈脈地看了男人一眼。田長松就不再推辭,把兩條雞腿全都吃了下去。一邊吃,他似乎還一邊在心里憋著勁兒。他知道,夜里的活兒不比白天耕田耙地輕松。
李玉年洗過,又給男人舀好水,就先上床了,她沒有忘記隨手拉滅吊在房梁上那只二十五瓦的燈泡。這是催促田長松上床的信號。他們的兒子已經八歲了,但李玉年仍然像個大姑娘似的,做那個事的時候是不讓田長松開著燈的,她說那樣真地羞死人了。
田長松匆匆洗了,爬上床,就被李玉年擁上了身子。田長松把吃下的兩條雞腿全都變成了勁兒。李玉年在田長松的身子下面卻不像平時那樣哼哼唧唧地發出甜蜜的叫喚,也一動不動。田長松知道她是在做打持久戰的準備,他就覺得自己的壓力更加大了。
其實,他跟她一樣,在外面打工的時候,想她心里都想開坼了,想發瘋了,可是不能因為想她就不打工了,就往家里跑吧。他和她的遠大目標才剛剛踏上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啊。八歲的兒子讀的鎮里一所封閉式學校,封閉式學校當然比普通學校要好。按他們的說法,兒子不能輸在起跑線上。讀封閉式學校當然比一般學校的錢要多得多。他們說,用錢鋪墊兒子的錦繡前程,值。錢從哪里來,當然靠自己這雙手掙來。這是一個連環套。掙錢,就得舍棄身子下面這個漂亮得如美人魚一樣的身子,就得忍著、憋著,就得煎熬著。
田長松還常常想一個很傻的問題,這個事情為什么就不能透支呢,要是能透支的話,回來的這些日子里把今后幾個月或是今后一年多時間的活都給做了,那樣今后的日子就不用煎熬了啊。這個想法原本不應該從他這個高中輟學的有知識有文化的人腦殼里面冒出來。這是動物的生理本能,今天再做得精疲力盡,彈盡糧絕,過十天半個月,年輕的身子就又會膨脹起來。
不過,即便不能透支,他還是要連著做幾次的。像平常那樣,明天夜里還得躺在這個如錦緞一般柔軟的身子上面不能下來的。再汗爬水流,再氣喘吁吁,再彈盡糧絕,都得堅持著。眼下,她就已經做好了持久戰的準備,不然她怎么連吭一聲都不,她是要把甜蜜的叫喚和撕扯都放在后面,她知道怎么給身子上面這個男人鼓勁、加油。當然,那也是給她自己加油鼓勁啊。
田長松正在為自己沒有力氣堅持下去而懊惱的時候,李玉年卻在下面開口說話了:“我想好了,今年你不能去打工的。”
這是田長松沒有想到的。這么多年來,他在去打工的先天夜里,李玉年總是摟著他說:“你放心打工去吧,我會照顧好我們寶兒的。”過后,就依在他的胸口跟他算起賬來。她算的是兩筆賬,一筆是他在城里打工掙錢的賬;一筆是她在家插田種地喂豬養雞賣錢的賬。算來算去,等到兒子跨進大學門的時候,兒子讀書的錢他們已經準備足夠了。不過,他們仍然不能有半點松懈,掙的錢還是要存著的。怎么說兒子大學畢業之后,還向爸爸媽媽伸手請求一點支援的話,他們還能拿出十萬八萬資助兒子的啊。
小兩口的話題圍繞著兒子打轉,但小兩口的行動卻總是想把他們骨子里想的那個事給對方多透支一些。
今天有點反常,李玉年怎么不讓自己打工去了。田長松說:“在家種田養雞喂豬掙不到那么多錢的。”
李玉年不再說話,淚水卻是像泉水一樣從眼里溢出來,把田長松的胸口都洇濕了。田長松從李玉年的身子上面滾下來,把她緊緊地摟在懷里,哄她說:“我們再堅持幾年,把兒子讀大學的錢掙夠,我就不出去打工了,陪著你在家種田,養豬喂雞。”
李玉年不說話,只是哭。田長松不知所措,不知道說什么才能勸慰她了。這時,李玉年卻又把他擁上了身子。
女人這么一哭,田長松心里特別的不好受。不過,現在他就知道女人說的不過是一時撒嬌的話,并不是真正不讓他出去打工了。他得趕緊調整情緒,讓女人高興才是。
這天早晨,李玉年起來得很早,她說:“今天星期六,我去把寶兒接回來。你明天出去打工,今天就別做活去了,在家陪陪兒子吧,不然,這一年我們寶兒不知道要叨念多少次爸爸的。”
田長松說:“昨天把田做好了,今天剛好一天的活兒。把秧苗插下去,我出去打工才放心啊。”
“我過兩天插不就行了嘛。這么多年你不在家,插秧割谷還不都是我一個人。”李玉年是心疼男人,昨天晚上他沒得睡覺,白天做活哪有精神。
吃過早飯,田長松還是沒有休息,插秧去了,他也心疼女人啊。李玉年也就不去學校接兒子了,說:“那我還是跟你一塊去插秧吧。打個電話給學校,說我下午去接寶兒。”
田長松說:“封閉式學校就是好,星期六星期天不回來也不用擔心,有老師管著。”
兩個人插秧的時候,居然都是呵欠連連。李玉年看看田長松,嗔他說:“今天晚上可不能那樣了,明天上午要坐半天汽車,中午坐火車,后天早晨才能到廣州。”
田長松這時卻想著昨天晚上她不讓自己去打工的話,說:“要不,我打幾個月工,就回來一趟。”
李玉年說:“那還不如不去打工,辛辛苦苦掙來的錢,都送給車站了。”
田長松就不做聲了,心想再要提起這個話題,只怕明天就走不成了。看了一眼下面水田里正在插秧的張大全,問道:“大全,明天去廣州,沒有變化吧?”
張大全沒說話,他女人劉如卉卻是搶著說:“我就懷疑你們在外面有什么名堂,說起打工,那個高興,恨不得馬上就走。”
田長松說:“如卉你這個話說得太沒良心,你以為我們想出去打工呀,我和大全除了白天做活兒沒機會說話,夜里說的就是你們。”
劉如卉問:“說我們什么了?”
田長松說:“還用問嗎,從頭說到腳,從上說到下,從里說到外,越說越睡不著覺。”
劉如卉說:“我不信。”
張大全說:“信不信由你。我們的確是這樣的。”張大全問李玉年,“你怎么沒接你家寶兒去。”
李玉年抬起頭來的時候,田長松發現她的臉上全是淚水,心里不由一驚,對張大全說:“她說下午去接寶兒。”
張大全說:“你要是對我娘說一聲,我娘就把寶兒一塊帶回來。”
劉如卉問李玉年:“明天他們要走了,你給長松哥辦的什么好吃的啊?”
李玉年沒抬頭,反問劉如卉道:“你辦的什么好吃的?”
劉如卉說:“殺雞,兩條雞腿全給他吃了,晚上還是要死不活的樣子,消極怠工,你說氣人不氣人。”
劉如卉這話說得太露骨,李玉年的臉早就紅到耳根去了。李玉年是個很靦腆的女人,她哪敢像劉如卉這樣張張揚揚把兩個人夜里做的事情說出來。
這時,劉如卉又說話了,她說:“你還沒有告訴我昨天辦的什么好吃的呢。”
李玉年說:“還不就是那些菜。好菜要留給我們家寶兒吃的啊。”李玉年心里卻在想,今天還是要殺只雞的,不過,今天的兩只雞腿他只能吃一只,兒子也要吃一只的。
二
李玉年和田長松是一對好夫妻,這是半埡村人公認的。李玉年長得漂亮,還勤勞,賢惠,在半埡村有口皆碑;田長松勞力好,會攢錢,心疼老婆,這也是半埡村人公認的。
李玉年和田長松從小一塊長大,按書上的話說,叫做青梅竹馬。兩人一塊讀小學的時候,還坐一條凳子,共一張桌子呢。雖然兩人有時也在桌子上劃“三八線”,卻是友誼多于矛盾。有時兩人從家里帶了好吃的,還悄悄送給對方吃。做游戲扮演小夫妻,是一定少不了他們倆的。后來慢慢長大了,知道害羞了,他們才不敢像兒時那樣過于親密。那時,倆人讀書的成績也特別的好,從小學到高中,一名二名都非他們倆莫屬,于是他們的眼前鋪起了一條斑斕的五彩之路,讀大學,到城里去工作,現在不是談情說愛的時候。老師也說,要讓他們倆為學校爭口氣,考重點大學。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兩人美好的愿望結果都成了掛在天邊的彩虹。開始是李玉年因為父親去世輟學,后來田長松也因為母親生病輟學了。農村的孩子輟學之后,是說不上再有走進學校去的機會的,兩人離大學的門也就一步的距離。十八九歲,兩人就都成了家庭的頂梁柱,挑起了生活的重擔。那時,他們都在廣州打工,他們都沒有忘記對方,有時休息,兩人會通通電話,或是到對方的廠子看望對方。后來,田長松干脆就到李玉年的廠子打工去了。他們在廠子旁邊租了一間小房子,就那樣同居了。他們劃算著怎么才能少用錢,除了給家里寄錢,還能余下一點錢來。幾年之后,他們結婚了。所謂結婚,就是有了一張貼著兩人半身照片的結婚證,沒有辦酒席,甚至連一張結婚彩照都沒有拍。那時,李玉年的母親也已去世,李玉年打工的錢主要是給一個比她小三歲的弟弟讀書。直到弟弟大學畢業,在城里找到了工作,李玉年才算真正卸去了肩上的負擔。
按說,他們的日子應該會好起來了,孩子由田長松的母親帶著,倆人一心一意打工掙錢就是,日后寶兒讀書上大學都不愁的。不料,這個時候田長松的母親卻出了事,給豬喂食的時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居然把腰脊骨摔斷了,再也起不來了,這不應了農村人說的那句話嘛,人背時,喝水也能咽死人啊。提著豬潲桶過門坎,摔倒在地就成癱子了。田長松的父親去世早,田長松是母親含辛茹苦養大的。母親躺在床上起不來,兒子那個心疼啊。李玉年說:“我回去侍候母親,帶孩子,把田種上,把地種上,再喂養一頭豬,比在外面打工差不到哪里去。”
那幾年,李玉年忙得兩腳不沾地,要給兒子和婆婆做飯洗衣服,要給婆婆洗澡換褲子,水田和旱地也都種上了,還喂養了一頭豬和一群雞。因為這,李玉年在半埡村爭得了好名聲,田長松的母親死的時候握著她的手斷斷續續說:“玉年,你就是我的女兒啊。”
婆婆去世,李玉年的活兒就少了許多,心里的那種負擔也沒有了。這時,兒子也進了鎮上一所封閉式學校。按半埡村人的說法,先苦后甜。李玉年也覺得這話一點都沒錯,好看的臉上那笑都變得燦爛了。
只是,李玉年臉上的笑容雖然常在,心里的那種幸福感卻慢慢就變了味兒,中間夾雜著苦澀,雜夾著無奈,這種苦澀和無奈還不能在臉上流露出來。李玉年不是白天做活兒苦,她是因為夜里躺在床上睡不著苦惱。睡不著,就胡思亂想,內心深處的那種饑渴和沖動怎么都無法排解。她只能把和男人在一起的一次次的美妙和甜蜜用來回味和咀嚼了,只能給田長松打電話了,她知道田長松也想她,每次在電話里她真地想告訴他,她想他心肝都想開坼了,可是,這個話她不敢說出口,從電話里傳過來的嘆息聲,她就知道他比她想得還要厲害。她是知道一些年輕的農民工在城里所做的一些出格的事情的。天黑下來之后,城里那些黑暗的小街小巷里就會鉆出來一些年輕女人,這些年輕女人專門靠做那個事情討吃,她們的對象就是那些遠離家鄉,遠離老婆的年輕農民工。李玉年就又不敢多打電話了。
李玉年甚至想,或許那時婆婆就躺在隔壁的房里,現在隔壁房里沒有躺著婆婆了,心里的那個沖動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在心里茁壯成長了。
這個時候,李玉年就會想起一些白天聽到的閑言碎語。劉如卉跟趙前生睡覺了,劉如卉跟伍明清有一腿。劉如卉跟趙前生睡覺她不相信,跟伍明清有一腿卻是有可能的。
半埡村的人們都說,半埡村李玉年長得第一漂亮,劉如卉長得第二漂亮,長得第二漂亮的女人卻跟一個和自己父親差不多年紀的男人睡覺,實在是不可想象。但伍明清有他的優勢,他是村主任,在半埡村算得是最有權力的人,況且伍明清在半埡村的口碑還不錯,群眾的好處能爭的他一定會去鄉政府爭來,村里的事情該他管的他一定會管。劉如卉也許就是想到了這一點,跟伍明清睡覺,解決了饑渴,還能得到好處。
說劉如卉跟趙前生睡覺,只有鬼才相信。趙前生人老實,還肯幫助人,年紀也不過三十多歲,這是他的優勢,但他是個殘疾人,左腳比右腳短了三寸,走路那樣子實在太難看,身子一歪一歪,頭像雞啄米一樣。趙前生找不到老婆,打單身,就因為他是個跛子。沒有去城里打工,也因為他是個跛子,哪有廠子會要他。跟他睡覺,還真的不知道那只短了一截的腳是怎么安排的。
這天夜里,李玉年一直要田長松趴在自己的身子上面,緊緊地摟著他,像是擔心他跑掉似的。天剛亮的時候,張大全在外面叫田長松。張大全的話說得太露骨:“長松,一個晚上還沒喂飽呀,六點的中巴車,趕不上,就得再耽誤一天。”
田長松想起來,李玉年卻是不肯松手:“我不讓你去打工。”這個話李玉年昨天夜里又開始說了。現在,李玉年是帶著哭腔說這個話的。
田長松卻是沒有半點猶豫,說:“不去打工,我們的計劃就不能實現了。”田長松覺得這次回來,女人有些異樣,一時不讓他去打工,一時又叫他去打工,他真地有點摸不透她為什么要這樣了。
張大全在外面叫第二次的時候,田長松就不管不顧地把李玉年的手掰開,去那邊房里看了看還在熟睡的兒子,就匆匆地走了。
李玉年沒有起來,就在田長松走出門的時候,她卻是聲嘶力竭地叫了一聲:“長松,我不讓你走的啊。”
田長松不由一怔,腳步也就停了下來,只是才停了片刻,他就匆匆地出門去了。
李玉年起床的時候,太陽已經升起老高了。李玉年有些發呆,飯也不想做,豬呀雞呀也不想喂,她就那樣呆呆地坐在門前,眼睛一動不動地盯著遠方。遠方是連綿起伏的群山,李玉年知道一條公路在群山中左纏右繞地翻過去,就到了縣城,再走幾個小時,就到市里了,一條鐵路線從那里過,田長松和張大全是從那里坐火車去廣州的。
這時,劉如卉從禾場外面走進來,老遠就笑著說:“玉年姐,長松走的時候把你的魂也帶走了呀。”
劉如卉其實比李玉年還大一歲,張大全跟田長松同年,比田長松小月份,她是依著男人才叫李玉年姐的。她一臉的笑樣,精神也特別得好,看不出昨天晚上加班加點勞累的痕跡,也看不出男人走后的依戀之色。
劉如卉卻是發現了情況,說:“玉年姐,你拿個鏡子照照自己吧,昨天夜里沒讓長松哥下身子呀,眼睛周圍一個大大的黑圈,臉也像是打了蠟一樣。”
李玉年苦笑道:“老鴉別笑豬嘴黑。昨天夜里你就沒有做幾次。”
“做幾次就成你這樣了?”
李玉年不再跟她說這些,她問劉如卉:“大全說什么時候回來?”
“今天才走,就想到什么時候回來了。我才不問他呢。過年的時候買不到車票,就明年三月的時候回來,那時候回來還能幫著做些重活兒。”劉如卉過后說,“秧苗插下去了,當緊的活兒也讓他們給做了,多好。走,我們去鄉場玩玩去,死鬼回來的這些日子,連鄉場都沒去了。”
李玉年說:“我家寶兒還在睡覺呢。”
劉如卉說:“把他的飯做好,他起床之后自己吃了就去我家跟我兒子一塊玩,一會兒學校的車要來接他們的。”
李玉年說:“你回去,我一會兒去你家吧。”
這樣說過,李玉年就匆匆把兒子的飯辦好,把兒子叫了起來。寶兒睜開眼睛的第一句話就是問爸爸到哪里去了。李玉年說:“你爸爸打工去了,給你掙錢日后好讀大學,你要認真讀書啊。”
寶兒聽說爸爸已經走了,原本想哭的,后來又不哭了,說:“這個話你和我爸不知道說過多少遍了,我肯定要努力讀書的啊。我們老師也說,不努力讀書,日后就出去打工,做苦活、累活,臟累,錢還掙得少。”八歲的寶兒說話居然也像大人的口氣了。
李玉年說:“我兒子懂事了就好。”看著兒子吃飽飯,把兒子的衣服收拾好,用一個包裝著,帶著兒子去了劉如卉家里。
劉如卉眼睜睜地站在自家門口等著她的。李玉年說:“你經常去鄉場上逛是什么意思啊?”
“把鄉政府那些干部給眼饞死,讓他們跟在屁股后面打轉轉。”
李玉年也是聽到過鄉干部一些閑言閑語的,說哪個鄉干部跟鄉場上哪個漂亮女人關系不一般。還說誰誰穿的漂亮衣服就是鄉干部給買的。說:“你就那么有信心啊?”
劉如卉一臉無奈地說:“說的玩笑話,他們哪看得上我們這樣的女人,三十歲,在他們眼里已經是老女人了,鄉場上多少擺攤做生意的年輕漂亮的女人,還不像我們做農活曬得像個黑雷公,還一身的汗臭,人家整天不曬太陽不淋雨,身上灑的香水熏得人頭暈。”
兩人說話的時候,劉如卉的婆婆從那邊屋里走出來。劉如卉的婆婆跟劉如卉的關系不好,快七十歲了,卻不愿意跟劉如卉一塊過,自己在一邊辦飯吃。卻是把孫子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孫子回來,也不讓他跟媽睡,要孫子跟自己睡,平時去學校接送孫子,也不讓劉如卉去,她自己去。劉如卉懶得跟老人爭,你這樣,我才省心呢。
李玉年嘴邊的話就又咽了回去,對老人說:“校車一會兒就到的吧,我也送我家寶兒去學校。”
老人說:“你要有事你就去,我把他們一并送到學校去就是了。”
劉如卉拉著李玉年的手說:“我們走,他們才不要我們送呢。”
李玉年說:“我們坐便車去鄉場,不是更快嗎。”
李玉年和劉如卉來到鄉場的時候,已經快中午了。今天不是趕場的日子,又是農忙的季節,來鄉場買東西的人并不多,一個接著一個的店面和那些地攤都十分的冷清。
劉如卉和李玉年東瞧瞧,西看看,卻不想買什么,那些攤主們開始還叫著喊著,后來也就懶得答理她們了。
“你們怎么來了?”
一個十分熟悉的聲音從那邊店子傳過來。抬起頭,是伍明清站在那邊店子里對著她們笑。劉如卉拉著李玉年的手就走了過去。
伍明清問:“長松和大全打工去了?”
李玉年沒有回答他的話,劉如卉卻是問他道:“你來鄉場做什么?”
伍明清說:“在鄉政府開了半天會,準備買點農藥化肥帶回去。”
劉如卉說:“秧插完了,他們打工去了,我們也要歇歇氣啊。伍主任,我們不經常來鄉場的,來了也不一定能碰上你,你得請我們的客。”
伍明清似乎很樂意請客,說:“好啊,你們說要吃什么,你們只管吃,我掏錢就是了。”
劉如卉說:“你就知道鄉場上沒有山珍海味我們吃,最多也就吃碗豬腳粉。”
伍明清笑道:“這可怪不得我。”
劉如卉說:“我們不吃豬腳粉,我們去山妹子酒家點菜,不吃一百兩百不出來。”說著就要往山妹子酒家去。
李玉年說:“我沒餓,什么都不吃。”
伍明清卻是不管不顧地扯著李玉年的胳膊往山妹子酒家拖,說:“別客氣,我們一塊去吃。”
李玉年生氣地說:“大街上,拉拉扯扯做什么。”
伍明清只得把手松開,有些尷尬地說:“我有話要對你們說,你就不愿意聽了?”
劉如卉問道:“剛才鄉政府領導說什么了,是不是又有什么補貼下來了啊。”
這些年,國家對農民的補貼實在多,一級一級放下來,放到村主任的手里,就算是放到了頭,村主任再往下發,就是直接受益的農民了。別看村主任不是個官,手里握著這些東西,就能得到很多的好處,占到很多的便宜。伍明清有幾分得意地說:“肯定啊,李玉年你就不想聽了。”
李玉年就不做聲了,跟著全明清來到山妹子酒家。伍明清說:“要吃什么,你們自己點,我結賬。”
劉如卉說:“真要狠狠地放你一次血,我還是有些不忍心。”問李玉年,“你說,吃點什么?”
李玉年說:“我說了,我不餓,什么都吃不下。”
劉如卉就不再問她了,自作主張地點了幾個菜,要了兩瓶啤酒,過后對伍明清道:“這個樣子,沒有放你的血吧。有什么好事快對我們說,還賣什么關子。”
伍明清說:“國家又撥錢下來了,造林,按棵算,造下去有錢,年年培育有錢,林子長大了,賣木材的錢還歸自已。”
劉如卉對這個好消息并不感興趣:“我還以為什么好事呢。造林,我們造在什么地方啊。”
伍明清一臉壞笑地說:“你們不都有一片山彎嗎,土地肥沃,林子造下去長得就快……”
沒等伍明清把后面的話說出來,李玉年站起身就走了。她真的有些臉紅,伍明清跟她們的父親差不多大的年紀,這樣的玩笑,他也開得出來。
也許,李玉年這一走,正合他們的意呢,劉如卉沒有追出來,伍明清也沒有叫她回去,兩個人坐那里頭對著頭說起悄悄話來了。
李玉年覺得來鄉場一點意思都沒有,還白白地耽誤了半天。三月里,草鞭落地都要生根發芽,得趕緊回家做點事情去。
三
這天晚上,李玉年睡了一個好覺,天黑就上床了,第二天天亮才醒來。她自己都覺得好笑,做那個事,其實也是很累人的啊。
吃過早飯,李玉年去后山坡看稻田里的水。李玉年覺得男人三月回來還真有三月回來的好處,以前到了犁田插秧的時候,她就著急,沒有牛,要借;沒有人犁田,要請。借牛請人都麻煩,春耕大忙的季節,都忙,再說男人們大都到城里打工去了,留在村里的男人就那么幾個,除了伍明清,就是老人和趙前生這樣的殘疾人了。
秧苗插下去了,接下來的活兒就輕松了,管管水,殺殺蟲,施施肥,這些活兒女人都能做。
“怎么,昨天插下去的禾苗,今天就來看水了呀。”是伍明清,他扛著一把鋤,站在山溝那邊的水田旁邊。那不是他家的水田,但他是村主任,到處看看,檢查檢查,是他的工作。說不定什么時候鄉政府就會打電話來,問他半埡村的春耕生產進度如何,又拋荒了多少田地啊,他都要能答得上來。這些都是伍明清自己開群眾大會時說的,他說他這個村主任拿的錢不多,管的事卻不少,操的心也不少。
李玉年不想跟他說話,接上腔他就沒完沒了了。伍明清卻不管這些,一邊往這邊走,一邊說:“我剛才在你的水田邊看過了,你那水田得放點水進去,就把水溝旁邊的一股山泉水往你禾田里放了。水淺了,剛插下去的禾苗難得起身。”
李玉年果然看見水溝旁邊新挖了一道小水溝,一股泉水正往自己禾田里流。她有些感動。心想,他百樣都好,村里的工作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就是有點打年輕女人的主意,趁著人家男人在外面打工一年半載不回來,就占別人的便宜,不然他是會受到大家的敬重的,自己對他也會高看幾分的。
李玉年往回走的時候,伍明清卻趕了上來,笑著說:“長松這一走,又要幾個月才能回來啊。”
李玉年知道他說話的意思是什么,心不由怦怦跳起來,腳步也就加快了許多。伍明清說:“過幾天來你家,你可不能又不肯開門啊。”
李玉年回頭瞪了他一眼,說:“你要臉不。”
伍明清卻是笑著說:“要看什么時候,什么地方。”
李玉年說:“也不想想你有多大年紀了。”
“怎么,你嫌我老了。”
李玉年再沒有跟他說話,逃也似地走了。
回到家,劉如卉卻來了。劉如卉今天穿了一件新衣裳,老遠就問李玉年:“看看我這件衣裳漂亮不漂亮?”
李玉年看了一眼,還真的很漂亮,問道:“大全給你買的?”
“他知道給我買衣服?他只知道要我的身子。”
李玉年說:“他不會給你買衣服,給你錢你自己買不一樣的嗎。說起來還是大全給你買的啊。”
劉如卉笑說:“昨天你要是不走,你也有這樣一件漂亮衣服的。”
李玉年就知道她穿的衣服是誰買的了,說:“我不喜歡穿這樣的衣服。”
“自己可以挑啊,喜歡哪件挑哪件,他付錢不就是了。”
李玉年道:“鄉場才多大,才多少店子,誰不認得誰,你就不怕別人說你?”
“這樣的事情算什么事情啊。你沒聽說吧,鄉里領導給一些姑娘買的衣服那才叫衣服,幾百塊錢一件。我們沒她們那樣的本錢,得不到那樣的好衣服穿,只有穿這樣幾十塊錢一件的衣服了。”
李玉年不想跟她說這些,問道:“還沒吃中午飯吧。我去辦飯,就在我家里吃。”李玉年知道劉如卉的婆婆不會給劉如卉做飯,她自己卻有點懶,兒子不回來,她一天就做一次飯。
劉如卉跟著她往灶屋走,說:“對你說個話,你可不能說出去。”
李玉年看見她一副神神秘秘的樣子,不知道她要說什么話,看著她。劉如卉說:“幾天前的晚上,孫小環去敲鄒如娜的門,碰上了伍明清,伍明清狠狠地扇了孫小環幾個耳光,伍明清還去鄉派出所報了案,把孫小環弄去關了三天。我一直就想不通,孫小環誰都不怕,就怕伍明清,在伍明清面前就像老鼠見著貓。真是一物降一物。也不知道伍明清是怎么把孫小環給降住的。”
李玉年渾身不由打了個寒顫,她說:“孫小環怎么會去敲鄒如娜的房門?”
“他怎么不會去敲她的房門?他還敲過我的房門呢。不過,跟他睡覺可沒有想頭,那只爛眼坑里流出的眼淚又臭又腥,熏得人死。賠了身子還要貼飯菜。他說他睡累了,要給他弄好的吃補身子,世上哪有這樣無賴的男人。他就沒有敲過你的門?”
李玉年連連搖頭說:“沒有。”心里卻想,一個剛剛勞改回來的勞改釋放犯,夜里也敢敲別的女人的門呀。
劉如卉道:“這就怪了,他怎么不來打你的主意?等著吧,他肯定會來的。”
李玉年說:“你可別嚇我。”
劉如卉說:“嚇你做什么,一桿槍,還是勞改釋放犯,破罐子破摔,誰的門他不敢敲。”
這天夜里,李玉年躺在床上許久沒有睡著,后來她覺得自已的胸口好像被什么東西壓著,動彈不得,她哭啊,叫啊,掙扎啊,醒來,是一個夢,渾身的汗水像是從水里撈起來一樣。李玉年就更加地睡不著了,腦殼里面老是晃動著那個被叫做一桿槍的男人。他是孫小環。孫小環三十來歲,半埡村人,有一只眼睛瞎了,瞎的這只眼睛凹陷下去很深,像一個銅球坑,特別的嚇人。這只瞎眼還有一個毛病,只要他一激動,就流出一種黃黃的稠稠的水,又腥又臭。
孫小環的這只瞎眼是他自己給弄瞎的。孫小環的父母去世早,他是跟著爺爺長大的,從小沒有管教好,好吃懶做,偷雞摸狗。爺爺死后,生活沒有了著落,又不認真做農活,也不去城里打工,整天在鄉場上跟幾個年輕人鬼混。一次,跟幾個年輕人干仗,卻輸了,不服氣,回來關著門在家做火槍。他想把火槍做成之后就去報仇。那樣,鄉場上就再也不會有人敢跟他說不了。還別說,他的火槍還真地做成功了,一根指頭粗的無縫鋼管套在一個木頭做成的槍盒子里面,無縫鋼管下面套著一個用鐵絲做成的扳機,扳機上纏的是橡皮筋,點火用的是鄉場上能賣到的那種紙炮子,一打一個響。只是,孫小環在槍管里灌了些火藥之后,扣動扳機的時候,紙炮子響了,槍管里的火藥卻沒有點著。孫小環就把槍管對著自己的左眼,他想看看什么原因槍管里面的火藥沒點著呢。就在這時,轟的一聲響,一股火焰從槍管里噴出來,他的那只左眼球就不見了,眼坑里卻是一坑的血漿。孫小環用手握著那只沒有眼珠的眼坑,卻是慶幸槍管里只放了些火藥,沒有放鐵彈兒,不然,就不僅僅是眼珠變成了血漿,整個腦殼都變成一攤血漿了。
當時正是中午,村里人做活回來在家吃中午飯,孫小環的鄰居聽到隔壁屋里的聲響,過來一看,嚇得可不輕,連忙去叫伍明清。伍明清和幾個人把孫小環送到鄉醫院住了半個月,那眼就成一桿槍了。伍明清覺得這家伙不給治一治還真不行,日后還不知道會干出什么壞事來,去鄉派出所對姚所長說了孫小環造槍的事。姚所長一聽也嚇得不行,私自制造槍支,還了得,犯國法啊,連忙向上面匯報,就把孫小環送到西湖農場去了。
前不久,孫小環刑滿被放了出來,居然沒有半點改變,還是好吃懶做,還是偷雞摸狗,居然夜里還敲女人的門。要說有什么不同,就是半埡村的人們更加地怕他了。那只瞎眼像一口深井,又像一個彈洞,還像一個藏著罪惡的深坑,讓人見了心里發毛。孫小環沒有出去打工,也不做陽春,吃的什么,人們不知道,白天夜里他都干了些什么,人們也不知道。用伍明清的話說,孫小環那樣的人,最好的去處,應該還是勞改農場。也許,就因為擔心再去勞改農場,孫小環就怕伍明清一個人。伍明清跟孫小環約法三章:你孫小環干什么勾當我伍明清都不會管,但你孫小環不能在半埡村干什么,我是半埡村的村主任,我要保半埡村一方的平安和諧。你要敢在半埡村干什么,我就對你不客氣。伍明清碰著孫小環夜里敲女人的房門,那還了得,當然是會出手重重地抽他的耳光的。
李玉年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想起孫小環來。孫小環回來這么多日子,李玉年也沒有看到孫小環幾次,有一次看見了,李玉年就遠遠地避開了,實在說,她至今還不知道孫小環到底是個什么樣子。
這天天剛亮,李玉年就起床了,她不知道自己為什么這個時候就起床,呆呆地坐在那里,直到天亮明白,她才生火做飯。
吃過飯,李玉年就上山做活兒去了,家里還有一片地沒有種上,她想種點黃豆,過年才有豆腐吃。田長松最喜歡吃豆腐了,他曾對她說過,要是把豆腐和豬肉擺在面前,問他喜歡吃什么,他會說他喜歡吃豆腐。
山地就在屋子的后面,李玉年挖了一個上午的地,整好,太陽偏西的時候開始下種,天黑的時候才種完,回到家的時候,累得腰酸背疼,但李玉年高興。心想今天晚上會睡個好覺了。
吃晚飯的時候,鄰居郭婆婆來家里要她給她穿針。郭婆婆手里拿著一件破爛的衣服,另一只手里拿著一根針和一根線。實在說,平時李玉年只覺得郭婆婆可憐,卻不怎么注意這位老人,有時辦了好菜,給老人送點去,卻不愿意聽老人說的那千恩萬謝的話,更不愿意看到老人眼坑里冒出來的渾濁的淚水。
抬頭看了老人一眼,李玉年的心里不由生出許多的同情來。飯也不吃了,接過老人手里的針線,穿上,又把老人的那件破衣服拿過來,慢慢地縫補。郭婆婆蹲在一旁,昏花的眼坑里又有渾濁的淚水流出來。李玉年想勸老人幾句,卻不知道說什么好,把衣服補好,從箱子里找了幾件舊衣服給老人,說:“也不知道這些衣服你穿得穿不得。”
郭婆婆的眼淚更多了,說:“怎么穿不得,冬天不冷著就行。”
李玉年說:“要是能穿,我有空就再找點你穿。”
郭婆婆千恩萬謝地走了。李玉年飯也不吃了,把門關上,一個人坐那里看電視。她不想睡覺,擔心躺在床上胡亂地想這想那。
直到電視熒屏上出現了晚安兩個字,李玉年才站起身準備進房去。就在這時,她突然聽到有敲門的聲音,不由嚇了一跳,接著,她就鎮靜下來,她沒有去開門,她知道這個時候是千萬不能開門的,問道:“誰呀?”
外面的回答有些不耐煩:“你說我是誰。”
是伍明清的聲音。李玉年說:“伍主任,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你開門,我對你說。”
李玉年說:“半夜了,有事明天說吧。”
“明天一早我要去鄉政府匯報。”
“你去匯報村里的工作,與我有什么相干?”
“當然與你相干。要填一份表呢。”
“什么表,要我填啊?”
“插禾補助表。每畝插下的禾有三十塊錢補助。”
李玉年知道填表不過是他想進來的由頭,白天多長啊,怎么不來。她說:“我家那一畝水田插上禾了,你還給管過水呢。你要愿意,你就給我填上;你要不愿意,那三十錢我不要了。”
伍明清說:“國家關心農民,你不領情呀。”
李玉年說:“我當然感謝國家啊。”
伍明清說了一句什么,李玉年沒有聽清楚,她也不想聽清楚他說什么,這個時候,他能說什么呢。伍明清在門外站了一會兒,就走了。
李玉年躺在床上,她又失眠了,她不知道這樣一次又一次地把伍明清堵在門外,是好還是不好,但要自己像劉如卉那樣,她還真的不得干,不說對不起男人,也對不起自己啊。二十多歲,長得漂漂亮亮的,怎么就和一個跟自已父親一樣大年紀的男人上床呢。
四
李玉年是掰著手指頭算著日子的,開始的時候,那日子似乎還過得比較快,加上她又有意地找活兒做,整天在勞累中度過,夜里睡得還算踏實。過了四月,又過了五月,李玉年就覺得這日子是越來越慢了,白天太陽落下得慢,夜里就更長了,眼睛盯著那扇窗,那扇窗總是一片迷蒙,怎么都不見那一縷曙光從窗口透進來。
以前使用的辦法也失靈了,白天再累,夜里還是睡不著,躺在床上像是翻燒餅。就是睡著了,做的夢還是那個事,跟田長松要死要活的,醒來的時候,渾身大汗淋漓。李玉年特別的煩惱,她懷疑自己是不是患了什么病了。于是,她有意無意地問村里幾個跟她一樣年紀,留在家里帶孩子侍候老人的女人。不問則罷,一問可把她嚇了一跳,這幾個女人中間,雖然也有跟她一樣,把身子看得重,守得緊的;其余的幾個,早就沒有把身子當回事了,她們說,那樣還不如這樣,重活累活,還有人幫著做,大小事情,還有個照應呢。李玉年心想,這是什么事啊,怎么會是這樣呢。我是決不會這樣的。忍吧,憋吧,熬吧,長松總會回來的啊。
六月,太陽像個火球掛在天上。插下去的稻禾青蔥蔥的一片。后來,就開始打苞了。這個時候,水田里是不能沒水的。按農民的說法,叫做養苞。李玉年去自己那片水田也就勤快了許多。那天,李玉年來到自己水田邊的時候,她看見伍明清正在給劉如卉水田里灌水,手里拿著一把鋤,一副十分認真的樣子。
禾苗插下去之后,劉如卉就再沒來自己田邊看過禾苗。施肥呀,殺蟲呀,中耕呀,這些苦活累活是趙前生幫著做的,管水這樣輕松活兒則是伍明清幫著做的。李玉年常常想,這個劉如卉,一塊骨頭,哄著幾只狗搖頭擺尾啊。
伍明清說:“玉年,我原本是想給你田里也放一些水的,只是,上面水壩的石堤漲端午水的時候被沖垮了,水壩里沒水,山溝里的一絲泉水還不夠灌如卉的禾田。”
水壩被山洪沖垮,李玉年早就知道,她是抱著一種僥幸心理的,要是今年風調雨順,水壩就不用修了。可是,現在該怎么辦啊。李玉年站在干涸了的水溝旁,看著從山腳石頭縫里淌下的一絲山泉水,汩汩地流進了劉如卉的水田里。只是,這一絲山泉水在六月的烈日下也無濟于事,劉如卉的水田其實也干了的。李玉年還是相信伍明清的話的,要是水溝里有水,他也會給自己水田里放水的,禾苗剛插下那陣,他不是給自己水田里放過水的嘛。
“這條水壩,除了你們兩家,還有郭婆婆的水田也用水壩的水,你們三家得趕緊想辦法把水壩修一修,這天氣,還不知道什么時候下雨呀。”
李玉年心想,郭婆婆七十多歲了,怎么好叫她來修水壩,就是把她叫來,她也做不起這樣的重活兒。
伍明清已經來到了她的面前,說:“這幾天我要去鄉政府開會,不然我就來幫著砌一下水壩,怎么說我這個做村主任的不能看著大家的水田減產。”
李玉年說:“我去對如卉說,石頭我們自己抬,你只抽時間幫著砌一下石堤,好嗎?”這是這么多年來,李玉年對伍明清說的一句求他的話。
伍明清說:“我說了,我要去鄉政府開會,三天會開完,就來不及了。”
李玉年不知道他說的是真還是假,再沒有說話,匆匆找劉如卉去了。
劉如卉坐在禾場前的梨樹下乘涼,一副十分悠閑的樣子,也不知道她心里有什么高興事,嘴里還哼著歌子。她婆婆則在那邊屋里剁豬菜,咚咚的聲響似乎是在跟這邊的兒媳婦唱對臺戲一般。
李玉年說:“如卉你真悠閑啊,我們兩家的稻禾快旱死了。”
劉如卉說:“禾苗插下去之后,我就沒去田邊了,你剛才到那里看了?”
“漲端午水的時候,水壩被沖垮了你也不知道?”
“聽說了。”劉如卉看著李玉年,問道,“長松哥打電話來了嗎?”
“沒有。大全打電話來了?”
“那個死鬼,出去三個多月,才打過兩個電話回來,我就懷疑他在外面找那些不干不凈的女人,不然他怎么不把我當回事。”
李玉年就不做聲了,心里想,這么多年來,也都是自己給長松打電話,她要不給他打電話,他是不會打電話回來的,他說可惜錢。她說:“別說他們了,我們說當緊的事,水田干了,你說怎么辦?”
“砌水壩啊,還能有什么別的辦法。”
“我們不會砌堤啊。”
“叫他們砌吧。”
“你說誰?伍主任說他這幾天要去鄉里開會,幾天才能回來。”
“那就叫趙前生砌。每天給他開八十塊錢,他還不高興死了。”
李玉年當然是心疼八十塊錢一天這樣高工錢的。可是,沒有辦法,工錢再高,也得請他來才行。她說:“石頭還是我們自己抬吧,總能節約幾個錢。”
劉如卉說:“抬石頭的活兒多累,六月天,太陽又大,還不把皮給烤脫呀。再說,郭婆婆抬得起石頭。”
李玉年笑她道:“看你,被誰嬌慣成這樣了啊。以前六月天就不做活了。”頓了頓,李玉年又說道,“郭婆婆就不要攤上一份了吧,可憐啊。她就半畝水田,壩修好了,讓她放點水不就是了。”
劉如卉懶洋洋地說:“那好吧。什么時候開始啊。”
“水田干開坼了,不能等的。我們今天去抬些石頭擺那里,明天叫趙前生去砌堤。”
劉如卉說:“還不如現在就叫趙前生一塊去。他砌堤,我們抬石頭。”
李玉年說:“這樣當然更好。”
兩人來到水田上面溪溝里的時候,趙前生已經在那里等著她們的。他是劉如卉打電話叫來的。趙前生三十來歲,高高瘦瘦的個子,五官端端正正,說話也是一副斯斯文文的樣子,要不是因為左腿短了三寸,還真是個挑不出什么毛病的小伙子。看著趙前生,李玉年就想起一件事情來。聽說去年八月的一天晚上,村里兩個女人不知道跟趙前生是怎么約定的,居然同時出現在村口那間米碾坊里,那天天氣不好,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全被厚厚的云層遮住了,兩個女人聽到腳步聲,就迫不及待地把對方緊緊地摟住了,直到發現對方的胸口有些不對,趙前生的胸口是平的,可對方的胸口卻是鼓著豐厚的兩坨。咬著對方耳朵的時候,才知道對方并不是趙前生,而是跟自己一樣的長頭發女人。兩個女人連忙松開雙手,就那樣默不作聲地離開了。吃苦的當然是趙前生,第二天兩個女人把趙前生狠狠地抽了兩巴掌。趙前生捂著火辣辣的臉,才知道她們是誤會了自己,其實他并沒有答應她們,是她們從他的眼神里看出了別的什么,自己多情起來了,造成了誤會。
看著趙前生,李玉年心里不由生出一種苦澀,跛子也成香饃饃了。說:“前生,要辛苦你幾天的啊。”
趙前生不看李玉年,盯著劉如卉說:“你們把石頭準備好,也就兩天的活兒。”
劉如卉笑道:“你是想給我們節約錢吧。不過,我們每天只出得起八十塊錢的。”
趙前生說:“給別人做活,每天收的一百,你們說八十就八十吧。”
李玉年不由一驚,村里沒有男人,跛子做一天活居然要一百塊錢一天呀。
劉如卉道:“這樣說,你給我們多大的情了。玉年姐,我看這樣吧,兩天,我們各人給他六十塊錢,再供他一餐飯。對郭婆婆說,她出四十塊錢就是了。”
李玉年說:“她那四十塊錢我出,我共計出一百,再供前生一餐飯。郭婆婆那個樣子,怎么好開口向她要錢,壩修好了,她田里灌點水要什么緊。”
劉如卉笑說:“那陣村里選婦女主任的時候,怎么沒讓玉年姐做村婦女主任啊。秀玲選上婦女主任,沒管村里的事,到城里打工一年都不回來幾天的。”
李玉年說:“村里幾個村干部,除了伍明清,誰還在家里,不都打工去了嗎。”
劉如卉笑道:“不過,伍明清就希望他們都出去打工,他又做村主任又做村婦女主任。”
李玉年不想跟她說這些,母狗不擺尾,公狗不爬背。你不開門,他伍明清爬窗子進你的房去不成。
趙前生一只腳有毛病,手上的活兒,卻是沒有影響的,把李玉年和劉如卉抬來的石頭一塊一塊地壘起來,再填上土,溪溝里的水慢慢地就往上漲了。
下午的時候,劉如卉對李玉年說:“今天你給趙前生做飯,明天我給他做飯。”
李玉年說:“那我現在就回去做飯去了。”
劉如卉說:“人家幫我們砌堤,你要辦好菜給他吃啊。還要多放點米,等會兒我懶得回去做飯了,一塊來你家吃吧。你炒的菜好吃,卻從來不叫我去吃飯的。”
李玉年說:“好,收工的時候你和前生一塊去我家就是了。”
李玉年這天晚上認真辦了一桌子飯菜,有臘肉,還殺了一只雞,還炒了許多可口的菜,人家趙前生是給自己做活兒,再說劉如卉提出要來家里吃飯,不辦好菜不好,人家會說自己小氣。飯菜辦好,趙前生和劉如卉還沒回來,李玉年就用碗盛一些好菜送給隔壁郭婆婆,郭婆婆眼睛不怎么好,耳朵也有些背,看見李玉年端了好菜過來,眼淚就出來了,嘴里說:“玉年啊,你是好人,菩薩保佑你的啊。”
李玉年原本想對老人說說修水溝的事,想一想她又沒有說,錢呀飯呀說了老人會怎么想,她哪來的錢給趙前生,她哪辦得好飯菜讓趙前生吃。
郭婆婆命苦,二十多歲男人就死了,帶著一個幾歲的兒子過日子,把淚水和著飯菜一塊咽進肚子里。好不容易把兒子養大成人,老人也該享福了吧,沒想到兒子在外面打工時偷東西,案子還犯得大,勞改去了。老人的眼淚流盡,還得煎熬著把日子往下過啊。
現如今政策好,農民年滿六十歲了每個月就有五十塊錢。對于有錢人來說,五十塊錢也就兩包煙。困難人有那五十塊錢卻能活命。郭婆婆自己說,她今年七十五歲了,可她的那五十塊錢卻沒有拿到,她還得種那半畝水田過日子。郭婆婆沒有拿到那五十塊錢的原因是她的年齡上出了問題,她的戶口本和身份證至今還不到六十歲。郭婆婆不識字,當時領戶口本和身份證的時候也沒有請別人看看年齡上是不是有錯,當然更不會想到今后國家會給農民“發工資”。發工資這話是農民自己說的,他們高興啊,他們感謝國家啊,國家居然也給滿了六十歲的農民發工資啊。
郭婆婆的年齡往后寫了二十年,至今也沒有弄清楚少寫二十年的錯在鄉里還是在村里,伍明清去鄉里找姚所長,又找民政委員,要他們改一改,他們說改年齡那是很難的,后來郭婆婆自己去鄉里,他們看到這樣一個勾腰駝背的女人才五十歲,年齡只怕是真地弄錯了,答應改,卻是一直沒有改下來。因為這伍明清去鄉里吵過幾次架了,鄉里工作人員說,吵也沒有用,等吧。伍明清和郭婆婆心里都明白,這個等是遙遙無期的,田坪鄉誰不知道郭婆婆的兒子是個大盜竊犯,那年抓她兒子的時候,姚所長還帶著縣公案局的人去她家里搜查過的呢。誰愿意把一個大盜竊犯母親的事情放到心里去。
李玉年有時辦了好菜,就會給老人送點去,她常常想,郭婆婆過得苦啊。有時,李玉年還想,郭婆婆二十多歲就沒有了男人,她是怎么過來的啊。
天快黑的時候,趙前生和劉如卉才相邀著來到李玉年家。李玉年說:“如卉你這個監工也太厲害了吧,天不黑不收工。”
劉如卉不跟她說這些,眼睛盯著桌子上的飯菜就不松開:“啊呀,玉年姐辦了這么多好菜呀。”
李玉年說:“你說了,要辦好的吃啊。”
“我沒說要你殺雞,也沒說要喝酒。你看,雞呀,臘肉呀,酒呀,過年也就這個樣子。玉年姐,你真地很心疼前生的啊。”
這話讓李玉年的臉不由就紅了,說:“請人家做活,不辦餐好吃的,怎么好意思。”她有一句話沒有說出來,你自己才更應該給他辦好吃的啊。給趙前生倒了一杯酒,說,“前生哥,辛苦你了,喝杯酒,解解疲勞。”
劉如卉又嚷了起來:“怎么不給我倒酒?”
“你也要喝酒呀?”
“我怎么不能喝酒。前生哥,有好菜,我們倆把這瓶酒給干了。”
趙前生不說話,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又夾了一塊臘肉往嘴里塞。看來他真地是餓了。
劉如卉也就不說話了,一仰脖子,把一杯酒全倒進喉嚨去了。
李玉年說:“如卉,這樣喝酒不行,要醉的。”
“我就想醉一回。”劉如卉拿起瓶子自己把酒倒滿,對趙前生說,“快喝,我好倒酒。”
趙前生只得把杯子里的酒喝干。李玉年見狀,也就不說他們了,只是把好菜往他們碗里夾。
一餐飯吃到天黑一陣才放碗,一瓶酒還真地被劉如卉和趙前生給喝光了,劉如卉看樣子是喝醉了,說話有些放肆,說:“前生哥,玉年姐辦這么好吃的飯菜,你還要收她一百塊錢呀。”
趙前生的臉有些發青,卻不說話。
李玉年說:“不要你讓我錢,講好一百塊錢,我這就給你。”這樣說的時候,李玉年就從房里拿了幾張票子給趙前生。
劉如卉搶過錢,從中抽出一張二十元的票子退給李玉年:“飯不能白吃,二十塊一餐飯,前生你值。”過后就罵起張大全來了,“我家那個死鬼,出去打工他就像是過年,也不問問女人在家過的什么日子,錢不叫寄他就不寄回來,以為我在家就不要用錢了。前生,我的工錢要記賬的啊,我沒錢。”劉如卉這樣說的時候居然就哭了起來,淚水成溝兒地流淌。
李玉年把那二十元錢拿在手里,趁著劉如卉不注意,又給了趙前生。沒有料到,卻讓劉如卉看見了,她用手在臉上一抹,說:“玉年姐,我對你說,你別做起那個樣子。把身子裹得緊緊地,誰都別想沾,留著讓長松哥回來,我說你是何苦啊。”這樣說過,就對趙前生說,“送我回去,我醉了。”
李玉年說:“他喝酒了,我送你。”
劉如卉說:“不要你送,你送我沒有想頭。”
李玉年的臉一下紅到了耳根,心想張大全的老娘就住在一個屋子里,你就不怕她對兒子說嗎。
劉如卉這時已經把趙前生的手摟住了,對李玉年說:“你以為他是個跛子就不行了,除了走路不好看,干別的只怕你家長松哥都不如的。”
李玉年再沒有說話,看著兩人搖搖晃晃地走了,心里想,這個劉如卉,怎么就變成這個樣子了啊。
第二天,李玉年早早就去了溪溝的水壩上。劉如卉沒有來,趙前生卻來了。趙前生看見李玉年,有些不怎么自然,李玉年說:“前生哥,你怎么不討個嫂嫂,三十多歲了,年紀不饒人啊。”
趙前生嘆了一口氣,說:“誰愿意跟我?”
這些年,農村的女孩都往城里跑,進了城就不愿意回來了,長得漂亮一點的,找個城里的男人,年紀大也好,結過婚也好,都無所謂;找不到城里男人的,就找家里條件比較好一點的農村小伙。田坪鄉這樣偏遠落后的山區,女孩只有往外面跑的,沒有女孩嫁進來的。許多的小伙就成單身漢了。半埡村這樣的地方算得是田坪鄉最窮的村,小伙子找女人就更難。有人算過,半埡村三十多歲的單身漢就有幾十個,像趙前生這樣的殘疾人,找女人更是難上加難了。
李玉年就不再說話,一個人默默地扛石頭。趙前生說:“你不用扛石頭,累,等會兒我扛點石頭把石堤往上再砌一點,水就進禾田里去了。”
李玉年有些感動,心想還是一個會心疼人的男人。
劉如卉來水壩的時候,已經半晌午了,她好像還沒有睡醒,老遠就說:“你們來得真早啊。”
趙前生說:“你就別做活了,在旁邊休息,今天的活兒不多。”
劉如卉說:“也好。過一會兒就回去辦飯,玉年姐,你今天去我家吃晚飯。”
李玉年說:“不去了,昨天晚上還剩了許多的菜,再不吃,就餿了。”
劉如卉就不再邀她了,坐了一會兒,果然就回去了。
趙前生對李玉年說:“你也回去算了,你們的要求不過就是田里有水嗎,我把水趕到田里去就是。”
李玉年說:“我還是幫著做一會兒活,不能說給了你工錢,就讓你累到天黑還收不了工吧。”
天氣太熱,李玉年做了一會兒活,已是滿頭大汗,趙前生再不讓她做了,她就坐在旁邊看著趙前生做活兒。趙前生做活兒踏實,勞力還真的不差。李玉年不由又舊話重提,說:“前生哥,你真地就這么過一輩子啊?”
李玉年的話里有話,但她沒有說出來。趙前生何等聰明的人,說:“她又不是我一個人。”
李玉年說:“就是啊。”
趙前生再沒有說話,勾著頭認真地砌堤去了。李玉年就不好再說什么了,心想劉如卉的工錢是肯定不會給他的。這樣的男人也可憐呢。
五
日子在半埡村那些獨守空房的年輕女人的企盼和煎熬中,一天一天往下過著。那天,李玉年鋤黃豆草回來,辦了飯吃,天就黑了。半邊月兒斜斜地掛在天上,把四周的山影變得黑魆魆的。不知道什么時候開始,李玉年總覺得半埡村沒有過去熱鬧了,到了夜里,村子就是一副寂寂封音的樣子,幾點昏暗的燈光從窗口透出來。就連狗也懶得叫了。李玉年就覺得這日子過得特別的寂寞和壓抑。
李玉年想去劉如卉家對她說說,明天一塊到學校接兒子去。兒子要放暑假了。
剛走到劉如卉家門口,看見劉如卉提著一個保溫盒往外走,李玉年就站住了,說:“到哪里去啊。”
劉如卉說:“給前生哥送點吃的去。”
李玉年說:“送什么好吃的?你還真地投入感情了呀,大全回來看你怎么辦啊。”
劉如卉說:“什么感情不感情,前生哥起不來了。”
“病了?”
“被打了。”
“被誰打了?”
“伍明清打的。”
“什么時候,我一點都不知道?”
“那個時候打的,你怎么知道。”
李玉年就不做聲了,不用說,肯定是夜里兩個男人撞一塊了。
劉如卉匆匆就走了,李玉年問她:“明天接兒子去不?”
劉如卉說:“要辦飯要做家務,還要給他送飯,哪有時間。”
“兒子放暑假了,也不去接一接。也好問問老師這一個學期的表現啊。”
劉如卉說:“我忘了對你說,我兒子放暑假不回來的。學校辦了個預習班,學下學期的課程。別人的孩子學,我們的孩子也得學啊,不然,怎么趕得上班。”
李玉年問:“一個暑假要多少錢?”
劉如卉說:“再多的錢也要學。”
李玉年想問一下到底要多少錢啊,劉如卉已經走遠了。李玉年就只有往回走了,心里想,明天多帶點錢去,報個名,也讓兒子讀那個預習班吧。
回到家,坐了一陣,李玉年就睡了。天氣熱,電扇吹出的風也透著一股熱氣,李玉年把關著的窗子開了半扇,想讓屋后面的山風吹進房來。
開始的時候,李玉年還穿著衣服躺在床上的,后來實在熱得不行,她就把衣服脫了,只是穿著一條短褲。二十五瓦的燈泡掛在房梁上,燈光不是很亮,卻是透著一種曖昧,李玉年就不由自主地往自己的身子上瞅。
以前,李玉年從來沒有這樣看過自己的身子,她害羞。田長松平時總是說她的身子長得如何好,她就紅著臉問他好在什么地方。田長松還真能說出很多的好來,皮膚白得像煮熟的雞蛋膜兒,腳桿又長又直,奶子像棉花團,肚皮像是門前怡溪六月的水面……
李玉年當然是最喜歡聽他說這些話的,但她沒有去認真地想他說的這些話的真偽,她已經被一種幸福的浪潮覆蓋。今天,她想起男人說的這些話,男人卻不在身邊,也就涌不起那種幸福的浪潮把自己淹沒。借著迷蒙的燈光,她要好好看看自己的身子。
李玉年的臉不由得紅了。她果然看到了一具美如玉雕的身子。她真地想不明白,一個從小吃苦受累的山野女子,一個過去沒有好的吃,沒有好穿的山野女子,一個直到現在也沒有用過什么護膚膏之類東西的山野女子,怎么就有這樣一副冰清玉潔的身子啊。這時,她心里不由怦怦地跳了起來,她想起田長松每次跟她做那個事的時候的情景了。她跟田長松結婚快十年了,但他們做那個事的時候從來都是把燈關著的。好多次田長松要開著燈,她不讓,她說那還不羞死人呀。田長松說看著你的身子,我就會激情萬丈。李玉年嗔他說,沒激情你就不要做那個事,開著燈,休想。不管他在身子上面怎么的拳打腳踢,她在下面怎么地享受著那種要死要活的甜蜜,都是在黑暗之中,讓黑暗把他們的幸福和甜蜜悄悄地消失。現在,李玉年突發奇想,要是兩個人在電燈下做那個事,該是一種什么樣子。
突然,李玉年就想起劉如卉來,劉如卉不會像自己這樣想男人的,張大全去也好回也好,她一點都不在意。張大全回來了,她接納他,張大全去打工了,伍明清和趙前生會時不時地去她家里,現在孫小環回來了,去她家里的男人就又多了一個,她沒有饑渴感,她被這些野男人寵著,愛著。有男人做活兒,有男人買衣服。可是,自己不會,也不能那樣的。那樣,還是一個女人嘛。
李玉年什么時候睡著的,她不知道,她只知道睡著之前她哭了。她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哭,她只知道眼淚像斷線的珠兒,沒完沒了地流。
不知道過了多久,李玉年覺得田長松回來了。田長松跟過去一樣,不管什么時候回來,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她的身子。如果是晚上,那是沒得說的,她也特別想做那個事,順理成章,兩個人躺在床上盡情地做就是了。要是在白天,就有點麻煩,雖說她也火急火燎的。可是,不行,兒子在家里。兒子不在家也不能做啊,要是來個人怎么辦,不能說陽天白日的關著門在家里睡覺吧。
田長松卻是不答應,軟磨硬纏的。田長松那樣子可憐啊,他想啊,他憋著的啊。作為女人,她得想辦法讓他滿足才是。想什么辦法?她依了他,但她提出一個要求,要快。像吃飯一樣,狼吞虎咽,快餐。也就解解饑渴吧。晚上再慢慢享受。田長松當然會依著她,只要能沾她的身子就行。
今天也跟平時一樣,田長松二話沒說就把她壓在身子下面了。李玉年當然也享受到了那種甜蜜,那種歡悅。她說:“你真好,知道我想你了。”
只是,田長松卻不像平時那樣,會說:“這一年來,我的心肝都開坼了。”他只是用嘴緊緊地把她的嘴堵住,像是不讓她說話似的。
就在這時,李玉年突然聞到了一種刺鼻的腥臭味,哇地一聲就嘔吐起來。
李玉年醒了,是個夢。只是身子上面壓著一個男人卻是實實在在的。而且身子上面的這個男人還在使勁地扭動著,那樣子像是要把她吃下去一樣。李玉年不由大驚,使出全身的力氣,想把身子上面的男人推開,可是她怎么都推不開,身子上面的男人力氣真大,壓得她氣都喘不過來了。李玉年就哭著叫喊起來,那個男人就像剛才那樣,用自己的嘴想把她的嘴給堵住。李玉年就又聞到了那種惡心的腥臭味了。
李玉年似乎已經知道身子上面這個男人是誰,她被嚇壞了,連哭都不敢了。
一陣,身子上面的男人似乎是滿足了,從她的身子上面滾下來,一邊穿衣服,一邊惡狠狠地說:“跟誰都不能說我們的事,不然,我要你兒子的命。”
是那個一桿槍孫小環啊,他怎么進得房來了啊。
孫小環從從容容地開門出去了。這時,李玉年才看見那半扇開著的窗子,她真的后悔呀,夜里貪涼,卻引進來一個惡棍啊。李玉年把窗戶關好,躺在床上悲悲凄凄地哭了半夜,想起孫小環留下的那句話,她的身子就不由哆嗦起來,她真地不知道該怎么辦了。
第二天起床之后,李玉年還是決定去鄉派出所報案,姚所長不把他抓起來,他還會來的。李玉年早飯都沒有吃,她不想讓村里的人看見她這么早就去鄉政府,她沒有走那條簡易公路,她想從一條小路出村去。
沒有料到,她還沒有走上小路呢,孫小環卻從什么地方冒了出來,他像是在這里等著她的,惡狠狠地說:“我知道你要去干什么,你走進派出所的時候,你兒子也許就已經沒有命了。我是進過籠子的人,又是個瞎了一只眼睛的家伙,我怕誰呀,你要是不相信,敢跟我打賭嗎。”
李玉年抬頭看了他一眼,她發現那只深陷下去的眼坑陷得更加的深了,那只好眼卻是射出一縷兇光。她渾身不由打了個寒顫,站那里就不敢動了,她擔心他真地會去殺自己的兒子的。
孫小環說:“你去啊。你不去我可是要去了。我不會讓你兒子死,先讓他斷一條腿吧。”
李玉年嗵地一聲就跪倒在地上了,說:“你不能……我求你了。”
“行。我們就說定了啊。”這樣說過,孫小環揚長而去。
李玉年回到家里的時候,伍明清卻來了,伍明清老遠就對李玉年道:“這次你要請我的客才是。”
走進屋,伍明清不由就呆住了,問道:“玉年你哭什么?”
李玉年沒抬頭,說:“我沒有哭啊。”
“臉上有淚水,眼圈也是黑的。昨天夜里想長松了?”
伍明清來李玉年家里,也許就打的那個算盤,三句話,就離不得那些事了。李玉年還真想把昨天夜里孫小環爬窗子進房強奸她的事情對他說一說,他畢竟是村主任,再說,孫小環又那樣怕他。
只是,話到嘴邊她又咽了回去,對他說這個事,只怕他不但不會管,還會幸災樂禍的,我敲門你不開,卻讓一桿槍給干了。活該。李玉年還想,他要是管這個事,怎么管呢。他不可能天天跟著孫小環的啊,那家伙可是個惡棍,他自己也說了,他是頭上長皰,腳底流膿,什么都不在乎了。稍不留神,他真地對兒子動手怎么辦啊。
李玉年不敢說,她就想著一定要把這個事嚴嚴實實地保密才是,怎么說都是一件見不得人的事,一件不光彩的事,村里人要是捕風捉影地說開了,自已的臉往哪里擱,在半埡村怎么待得下去。李玉年抬起頭來,問道:“有什么好事要我請客?”
“插下去的禾苗,每畝三十塊錢到位了。”
“半埡村人人有,為什么要我請客。”
伍明清笑著說:“我不這么說,怎么好來你家啊。田長松不在家,擔心別人說閑話。”
李玉年說:“你不往那上面想,別人怎么說,人正不怕影子斜。”
伍明清說:“我人不正,影子就更加的斜了。”
李玉年說:“伍主任,你就沒有一句正經話嗎。”
伍明清說:“沒有。今天夜里要給我開門啊。田長松打工去四個多月了,你還不想,我給你來解解渴吧。”
李玉年說:“你敢來,我讓人打斷你的腿。”
伍明清驚道:“你有人了,誰有膽量敢打斷我的腿?”
李玉年也覺得這話說得不好,她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會說出這句話來。
伍明清卻是盯著她:“告訴我,你跟誰有一腿了。是那個跛子嗎。他除了年紀比我小,別的能跟我比?”
李玉年差點就把孫小環的名子說了出來,她不是要用孫小環來嚇唬他,她是想告訴他,她遭他強奸了。可是話到嘴邊,她還是沒敢說,眼淚簌簌地流淌著,說:“你快走吧,我今天身體不舒服,我想去鄉醫院弄點藥。”
伍明清一臉狐疑地看著她,他想問問她哪里不舒服,張了張嘴,又沒有問出口,只得走了。
李玉年看著伍明清遠去的背影,心里若有所失,就哭得更加的厲害了。
這天晚上,李玉年睡覺之前把窗戶認真地檢查了一遍,把門閂好之后,還用幾條凳子堵著,覺得萬無一失了,她才躺下來。只是躺在床上,她怎么都睡不著,眼睛一動不動地盯著窗口。窗口是灰蒙蒙的,她知道那是星星灑下來的光亮。一只螢火蟲落在窗臺上,像一盞閃著一點光亮的燈,又像是一顆星星從遙遠的天空掉了下來,擱在了窗臺上,像是要窺探躺在床上這個年輕女人的什么秘密。
李玉年突然想起田長松來了。劉玉卉說,她就是懷疑她家張大全在外面找小姐,不然他不會在外面打工一年不回來。劉如卉還對她說張大全跟她做那個事的一些細節,她說張大全在家的時候,每天晚上都要做那個事的,即便她身子不干凈,他也強要做,她說這樣的男人能做得到一年不沾女人的身子嗎。那他還不瘋呀。李玉年心想你說的這些我家田長松也一樣的,男人么誰不那樣啊。離開了自己的女人,他們就真地管不自己了嗎。
李玉年是經常給田長松打電話的,她覺得田長松并沒有像劉如卉說的那樣,不在廠子里,或是說話吞吞吐吐,或是旁邊有女人說話的聲音。問他,他不是說在床上躺著,就是在加班。田長松說他經常加班,加班有錢,時間也過得快。李玉年知道他話里的話,躺在床上,他想自己啊。
今天,李玉年又想給田長松打電話。田長松有手機。李玉年坐起身,把電話撥了過去。田長松接電話了,田長松說,今天沒有加班,他也躺在床上睡覺呢。李玉年聽到男人的聲音,她就想哭。她有一肚子的屈辱要對他說。可是,她不敢。田長松問她:“你有事嗎,電話通了你怎么不說話?”
李玉年把想說的話強咽了回去,說:“沒事,我們寶兒也聽話。你放心吧。”
這時,李玉年卻聽到田長松在那邊輕輕地說:“我想你。”
淚水就嘩嘩地從李玉年的眼眶里溢了出來,她說:“多掙點錢,我們寶兒長大了好讀大學。”
田長松說:“我知道,你要保重身體。”
李玉年說:“你也要保重身體,離過年還有四個月,那時你就可以回來了。”李玉年準備問問張大全的,可是,她沒有問,劉如卉守不住,就編些話來說自己的男人。
李玉年在床上才躺了一會兒,她就聽到窗子外面有輕輕的腳步聲,李玉年渾身不由發起抖來,心也不由得提到嗓子眼了。
“開門,我來了。”
現在,李玉年就不僅僅是心提到嗓子眼,渾身發抖,眼淚像是決堤的壩水,嘩嘩地流淌,她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了啊。
孫小環在外面說:“不開門,我就敲門了,讓全村的人都聽到是我在敲你的門。”這樣說的時候,孫小環敲門的聲音果然就大了許多。
李玉年哭著說:“昨天才來,今天又來呀。”
這話一出口,李玉年就后悔得不行,自己怎么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果然,孫小環就在外面說話了:“你說,隔幾天再來。”
李玉年說:“你不能再來這里了。”
孫小環說:“那就今天開門吧,我等不及了。”說著又咚咚地敲起門來。
這個時候,村里許多人家都還沒有睡覺。不知道是誰家的狗首先吠了起來。李玉年哭著說:“小環,我求你了,你不要這樣。”
孫小環說:“就這一次,我就不會再來了。你要不開門,我就只有把我們睡覺的事情說給大家聽了。”
李玉年萬般無奈,只得開了門。孫小環進了房,就把李玉年抱到床上去了。這時,李玉年又聞到了那股腥臭味,不由哇哇地嘔吐起來。她說:“這樣一股腥臭味是從哪里來的?”
孫小環說:“我的眼睛流出的淚水有一股味兒。要是你不喜歡,往后我戴個眼罩就是了。”
李玉年說:“你剛才說就這一次……”
李玉年的話沒有說完,她已經被壓在他的身子下面喘不過氣來了。
一陣,孫小環才心滿意足地從李玉年的身子上面滾下來,還有些意欲未盡地說:“我睡的女人,就你最好。”
李玉年說:“你睡過多少女人了?”
“只要我喜歡,想睡誰就睡誰,有的女人我不想睡,人家夜里還開著門等我呢,不像你,讓我動了許多的腦子。”
李玉年說:“你為什么不找個女人正正經經過日子?”
“村里多少男人找不著女人,打單身。我這么個樣子,還是勞改釋放犯,誰愿意跟我。”
李玉年說:“你怪誰呀。我說,你不能破罐子破摔,好好做人,還是有女人愿意跟你過日子的。”李玉年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了,自己為什么跟他說這些呢,這不是像兩個通奸的狗男女,做完那個事,再說些家務話嗎。
孫小環這時卻說:“跟別的女人睡覺,人家會向我要錢,你怎么不開口要錢?”
“我不是那種女人,我沒同意跟你睡覺,昨天你是爬窗子進來強奸了我,今天是我自己開的門,我是擔心別人知道了,沒臉面見人,還擔心你對我兒子下手。往后,你不要再來這里了。這話是你自己說的。”
孫小環不說話,心里想,身邊這個女人,把兒子看得重,把面子也看得重。他說:“我還要一次。”
李玉年說:“你答應我,往后不再來這里了。”
孫小環說:“好。”
李玉年只得又讓他睡了一次。孫小環心滿意足地離開之后,李玉年就又哭了起來,她哭得特別的傷心。直到五更都沒有睡著。
第二天起來,李玉年突然想起隔壁的郭婆婆來,孫小環又是敲門又是叫喊的,也不知道郭婆婆聽到沒有,雖說老人的耳朵不好,有點背,日子久了,只怕紙是包不住火的。
辦好早飯,李玉年盛了一碗飯,還夾了許多好菜送了過去。以前給郭婆婆送飯送菜,是因為同情老人,現在給郭婆婆送飯送菜,是不是摻雜了別的什么,李玉年心里都說不清楚了。
郭婆婆還沒有起床,門閂著的。李玉年知道郭婆婆平時起來早,今天怎么還不起床,是不是病了啊,她大聲地叫了幾聲,沒有人答應,李玉年就走到房子的后面,想問問郭婆婆,要是病了,她就給她弄點藥來,無兒無女,可憐啊。
問了幾聲,郭婆婆還是沒有答應。李玉年就趴在窗子上往里面看,這一看可把她嚇得半死,連滾帶爬就往伍明清家里跑去。還在伍明清的大門口李玉年就哭叫起來:“郭婆婆吊頸死了啊。”
伍明清正在吃早飯,放下碗就往郭婆婆家里跑。把郭婆婆頸根上的繩子解下來的時候,郭婆婆的身子早就硬了,也不知道老人是什么時候吊死的,也不知道老人是病了動不得吊死的呢,還是因為老了生活艱難吊死了。兒子在勞改農場,不會回來的。伍明清把趙前生叫了來,還叫了幾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在屋后面的半山坡上挖了個坑,釘了一副棺材,把郭婆婆草草埋了。
伍明清對李玉年說:“還真地要感謝你,要是你不給郭婆婆送吃的,她臭了都沒人知道的。郭婆婆對我說過多次了,你經常給她送吃的。還真看不出,你心還這么好,下一屆換屆選舉,村婦女主任我讓你來當。”
伍明清說的話李玉年一句都沒有聽進去,眼淚卻是成溝兒地流淌,她是想起郭婆婆來了,郭婆婆二十多歲就守寡,一輩子吃了多大的苦,到頭來卻上吊死了。
六
李玉年像是變了個人似的,常常一個人坐在家里發呆,還默默地哭泣。她常常想起郭婆婆來,她為什么要上吊死,大家都不說,其實李玉年知道,老人心里有事情想不開啊,老人日子過得苦啊,老人飯都弄不上口了啊,在這個世界艱難地熬日子,還不如死了好。
當然,讓李玉年哭泣的還有孫小環。李玉年無法忍受孫小環經常來糾纏她。她要不開門,他就威脅她。一次又一次地忍受他的威脅,他的凌辱。她連死的想法都有了,像郭婆婆那樣,一根繩子掛在脖子上,一切就都了結了,可是,她舍不得兒子,她舍不得男人,她還舍不得這日子,雖說有苦有累,有說不出口的苦澀,但怎么說這日子還是好過的啊,日后還要看著寶兒讀大學,在城里工作呢。
“玉年姐,多久沒有聽到你叨念長松哥了,你不想他了?”
劉如卉一副高興的樣子從禾場外面走來,李玉年抬起頭,把臉上的愁苦收起來,問劉如卉:“又有什么高興事,看你那嘴都合不攏了。”
“能有什么高興事。前生哥前幾天幫著把油菜種下去了。你那田怎么不種油菜。九油十麥。去年這個時候,你家田里的油菜苗已經長好高了啊。”
“沒心思種了。”李玉年有些懶洋洋地說。
劉如卉說:“我說,還是別憋著,熬著,找個男人解決一下,還可以幫著你做點重體力活兒。”
李玉年不做聲,她像是想別的什么事情去了。劉如卉說:“我是來告訴你一個事情的,伍明清這次是長臉了,鄉里領導準備獎勵他。”
劉如卉把話說了一半,就不說了,像是要吊李玉年的胃口。李玉年不由得問:“什么事,讓他長了臉?”
“孫小環昨天夜里偷鄭美秀家里的豬,被伍明清發現了,抓孫小環的時候,讓孫小環咬了一口,胳膊被咬傷了,伍明清那個氣,狠狠地抽了孫小環幾耳光,硬是把孫小環送到鄉派出所去了。鄉領導說,伍明清五十多歲了,還敢抓一個三十來歲的小偷。保一方平安,有功。”
李玉年心里不由一陣怯喜,說:“那個孫小環,這次又得勞改三年的吧。”
劉如卉說:“我真地希望他勞改去就別回來。前些日子的夜里敲開我的門,睡過之后就要我給他煮飯吃,還要吃魚吃肉。我真地想對伍明清說的,讓他好好收拾收拾他,想一想又沒有說。伍明清會說我自己也想他來敲門呢,還不把我也弄得一身不干凈呀。我希望那個孫小環遭雷劈死就好。”
這個話李玉年其實早就聽她說過了,卻是脫口道:“你也遭他的手了?”
劉如卉眼睛盯著李玉年,說:“你剛才的話說得不干凈,那個一桿槍是不是把你也給睡了啊。”
李玉年連連搖頭說:“沒有。”
劉如卉說:“我不信。孫小環說,半埡村他想睡誰就睡誰,你這樣的女人他不想?”頓了頓,劉如卉又說,“孫小環這人做那個事還真行,就是那只瞎眼里流出來的臭水讓人受不了。”
李玉年問:“如卉呀,你那樣,你家婆婆就不知道?”
“她知道要什么緊,有意見,把她兒子叫回來啊。”
劉如卉說了張大全母親的許多處不是。過后,就說她聽來的許多有關田坪鄉男人和女人的事情。李玉年對她說的這些都不感興趣,劉如卉說了一陣,只得沒趣地走了。
劉玉年站起身,從柜子里拿了幾個雞蛋,用手巾包著,就出去了。
李玉年是去看望伍明清的。人家是村主任,怎么說對自己還是很關照的,聽得說了,不去看看情理上過不去。
來到伍明清家里,把雞蛋放在桌子上。伍明清的女人忙著給她倒茶,伍明清則坐在那里眼睛盯著李玉年不離開。
李玉年說:“剛才如卉說伍主任被孫小環咬傷了,也不知道傷得重不重。”
伍明清搖晃著胳膊說:“小事,要你看什么,還拿了雞蛋來。”
其實,李玉年來伍明清家有三個目的,一是來看看伍明清;二是想打聽孫小環會不會去勞改;她還想打聽一下孫小環被抓到派出所去之后姚所長會怎么審問他。一般情況,鄉派出所抓到壞人,先要審問的,孫小環要是把他跟自己睡覺的事情說出來,自已這輩子怎么做人,別的不說,伍明清還不知道會怎么報復自己啊。
伍明清什么都不說,卻是罵開了:“孫小環那個狗東西,把我們半埡村的名聲都弄壞了,走出去人家說我們半埡村有個勞改釋放犯,聽起來讓人矮三分。他居然還不改,還要做那些偷雞摸狗的事。”
“你怎么就把他給抓住了啊?”李玉年心里還真有一個疑團沒有解開,鄭美秀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女人,伍明清不可能夜里去打她的主意的嘛。
伍明清說:“你以為我這個當村主任的就只是拿著國家補貼的錢不做事的嗎。孫小環回來之后,夜里我總要起來幾次,到村子里走一圈的。村里青壯年男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村治保主任也打工去了,留下來的都是些老弱病殘,再就是一些在家帶孩子侍候老人的年輕女人,村里有了這么一個頭頂生皰,腳底流膿的壞蛋,我放心嗎。孫小環幾次要爬人家的窗戶,都被我趕走了,這次他動手的時候,我打了響聲的,他不聽,我只得把他抓起來,送到派出所去。”
李玉年問:“這次只怕又有幾年吧?”
“鄉派出所姚所長說,他肯定要把他送到縣里去的,怎么發落就是縣里的事了。”
李玉年坐了一會兒,伍明清的女人要給她辦中午飯吃。李玉年就不好再坐了,幾個雞蛋,怎么好意思吃人家的飯。
李玉年沒有回家去,她去了鄉場,心里的一塊石頭似乎還是沒有落地。
半埡村到鄉場其實并不遠,也就翻過幾個小山坡就到了。還有一條簡易公路,是伍明清前年向縣里要來的錢修通的。比過去走那坑坑洼洼的山間小路要好多了。
來到鄉場,李玉年又不知道自己來鄉場做什么了,去對派出所姚所長說,一定要把孫小環送到縣里去,判他幾年。自己怎么好說那個話,對他說孫小環不僅僅是偷盜,他還強奸女人,這個話她也不敢說,證據呢,自己沒有留下證據的。再說了,現如今有幾個人會相信這個話。劉如卉跟半埡村好幾個男人都睡過覺,跟孫小環也睡過,能說是男人強奸她嗎。
李玉年在鄉場上漫無目的地徘徊了一陣,她去了一趟學校,看了看兒子,在老師那里問了一下兒子的情況,才回來。
這天夜里,李玉年睡得特別的踏實,她不再擔心孫小環會來敲她的門了。
第二天,李玉年居然到禾田里整地種油菜去了。遲點就遲點,不把油菜種上,明年就沒油吃了。
季節具有一種無與倫比的魔力,已經把滿目綠色的山野變成了一片枯黃,沒有了春天的生氣,也沒有了夏天的活力。秋風瑟瑟,萬物蕭條。但李玉年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她覺得秋天也十分的美妙,瑟瑟秋風那是彈奏出的動聽的音樂,幾朵野菊那是點綴秋天的美麗。太陽高高地掛在藍天,幾片白云飄呀飄的,格外的清閑自在。
李玉年渾身像有使不完的力氣,把干得開坼的水田鋤過來,整好,把油菜籽播上,又施了肥,再有十來天,油菜苗就會從地里長出來,綠油油一片。
只是,李玉年還在憧憬著明年收油菜時的豐收景象,李玉年才放心落意地睡了半個月的安穩覺,孫小環又來敲她的門了。開始的時候,李玉年還以為是伍明清,說:“你不要有那個想法,我不會開門的。”
沒有料到,外面的敲門聲變成了撞門聲了,還傳來惡狠狠的話語:“再不開門,我就放火把這屋子給燒了。”
李玉年的渾身就發起抖來,問道:“你沒去勞改農場?”
“你想我去勞改農場?”
李玉年知道自己這個話沒有說好,說:“我求你了,不要來找我好不好。”
“你開門,我有話要對你說。”
李玉年知道不開門的后果。只得把門打開。孫小環帶著一股惡腥臭的氣味沖進屋來,惡狠狠地說:“在縣公安局拘留半個月,吃了多大的苦,你還希望我去勞改呀。”
李玉年說:“不學好,偷人家的豬,拘留半個月真地便宜你了。”李玉年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說這樣的話。她覺得這話說出口就變了味兒,就像他是自己的什么人似的。
孫小環不跟她說這些,把她拖進房,三下兩下把她的衣服扒光,就壓在自己身子下面去了:“你知道嗎,在拘留所我還想著你的。”
心滿意足之后,孫小環沒有像平時那樣匆匆就走了,對李玉年說:“你知道我為什么要偷鄭美秀家里的豬嗎?告訴你,這次偷豬是因為你。”
李玉年吼他道:“我讓你偷人家的豬了?”
“我想給你買衣服,卻沒有錢。”
李玉年的眼睛就瞪大了,過后就哭了起來:“你強奸我,我沒報案就便宜你了,今后你再要來找我,我一定要報案的。”
孫小環卻說:“你要是想報案還不早就報案了,你其實是喜歡我的。我想好了,要跟你結婚。你不是說要我討個女人成個家,好好過日子么,我就討你。”
這是李玉年萬萬沒有想到的,她說:“不可能。我有長松,我有兒子,怎么可能跟你結婚。”
“你跟長松離了,我們再結婚。”
“你是癡心妄想。跟你結婚,還不如去死。”
孫小環卻不跟她再說下去了,穿好衣服,揚長而去。
李玉年越想越氣,越想越覺得可怕。哭了半夜,第二天起來,早飯也沒有吃,就出門去了,她想好了,這次是一定要去報案的,不然還不知道孫小環會弄出什么后果來。
鄉派出所姚所長李玉年認得,不過三十來歲,長得十分帥氣,態度也十分的和藹。三年前,姚所長來半埡村抓孫小環的時候,還來她家里調查過孫小環的情況的。那時田長松的母親還沒有去世,躺在床上起不來,李玉年接屎接尿侍候老人。因為這,她還被鄉政府評為全鄉孝敬老人的好兒媳呢。姚所長那天來家里的時候,還對她說起這個話來,姚所長說,他就喜歡那些孝敬老人的女人。姚所長說他也是農村人,他女人也在家里做農活,帶孩子,侍候他的母親。那個時候,李玉年心里就像是灌了蜜一樣,腰上別著一支短槍,穿著一身制服,多么威武帥氣啊,他的女人居然跟自己一樣也是農民,身上也有汗臭味兒,她仿佛覺得自己跟他的距離一下拉近了許多。她還想他女人的命真好,嫁的男人是國家干部。
可是今天自己卻要去對他說遭孫小環強奸的事,要是孫小環一口咬定說不是強奸,是自己開門讓他睡的呢,要是姚所長詳細地問起這件事情,自己該怎么說。自己能說孫小環已經睡了自己多少次么,自己為什么不早報案呢,是不是像孫小環說的是通奸。那樣,姚所長不但不會把孫小環怎么樣,還會把自已看扁了啊。
李玉年沒有勇氣去找姚所長了。她去了伍明清家里。
伍明清沒有起床,他女人坐在門前哭泣,這讓李玉年有些吃驚,伍明清的女人算得是半埡村最賢惠的女人了,支持男人的工作,還不聽人們的閑言閑語,別人就是把一些話說到她的耳朵里去,她也就一句話:“你們說這些沒用,我男人我自己知道。”
今天怎么了啊。李玉年問:“嬸嬸,伍主任在家嗎?”
女人抬頭看了李玉年一眼,說:“我就知道你們一個二個都不是好東西,沒有安好心,男人不在家,你們守不住了,夜里誰敲門都會接納。我家明清也被你們哄得團團轉,到頭來,還要受你們的害。”
李玉年的臉紅一塊,白一塊,說:“我沒有啊。嬸嬸,你怎么說出這樣的話來。”
“我還不說這話,我家伍明清昨天夜里差點被別人打死了。”
李玉年不由吃了一驚,問道:“誰打伍主任了?”
“大全昨天夜里回來了,他能不打他?”
李玉年想好的話也不敢說了,心想張大全這個時候怎么突然就回來了呢,他是聽到別人說什么了,還是他老娘給他打電話了。她想去張大全家問問長松還好嗎,他會不會回來。走到張大松家門口,她還是沒敢進屋去。人家家里出這樣的事情,自己怎么好摻和啊,說不定還會弄得一肚子氣慪的。
七
李玉年不敢去鄉政府找姚所長,也不敢去對伍明清說,孫小環卻是天天夜里來她家,對她說跟她結婚的事。孫小環像是跟女人商量家務事,教李玉年怎么跟田長松離婚,教李玉年怎么才會要得一些家產,還要李玉年把寶兒分給田長松,他要和她再生一個他們自已的孩子。李玉年怎么哭,怎么求,怎么拒絕,甚至同意在田長松沒回來之前讓他來家里睡覺。孫小環卻是一句話:“我就喜歡你。我要跟你結婚。你要不同意,我們就走著瞧。”
那天,田長松打電話回來,問兒子讀書的成績好不好,聽老師的話不。當然,田長松打電話回來,還有悄悄話要對李玉年說,他想她。田長松卻是沒有想到,他在千里之外打電話的時候,李玉年的眼淚已經成溝兒地從眼坑里滾了出來,田長松的話還沒說完,李玉年卻是帶著哭腔說:“長松,你快回來。”
田長松聽到李玉年的聲音有些不對,著急地問道:“玉年,你怎么了?”
李玉年還是一句同樣的話:“長松,你快回來。”
“村里出什么事了。張大全沒對我吭一聲,就回來了,你現在又叫我快回來。”
李玉年仍然是那一句話:“你快回來。”不過,聲音已經帶著哭喊了。
放下電話,李玉年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她想等著長松回來之后,她就不讓他出去打工了。他在家,孫小環是不會來家里了吧。
這天晚上,孫小環又來了。李玉年沒有拒絕他,她知道拒絕也沒有用。心想這么多日子都熬過來了,再受委屈,再受凌辱,也就這兩天了。
孫小環來到家里之后,還是跟過去一樣,首先是要和李玉環做那個事,之后就跟她說離婚和結婚的事情。
李玉年說:“我家長松過幾天就回來了,不再出去打工了。”
孫小環開始還怔了怔,后來就說:“這是怎么了,張大全也說不出去打工了,要在家守著女人。不過長松回來更好,我就開誠布公地對他說說我們的事。”
李玉年著急地說:“你可不能說啊,那樣我真地只有死了。”
孫小環臉上流露出一種讓人捉摸不透的笑,穿好衣服就走了。李玉年的心就懸了起來,她不知道田長松回來他會做出什么來。
田長松是第二天天黑的時候趕到家的。田長松說,他接到李玉年的電話之后,連夜買了一張火車票,轉了一次火車,又轉了兩次汽車,才趕到家:“玉年,聽你在電話里說要我回來,我那個急呀,玉年,你怎么了啊?”
李玉年撲進田長松的懷里,哭著說:“往后,你不要去打工了,在家跟我一塊種田。”
田長松著急地問道:“快告訴我,誰欺負你了?”田長松看到女人比過去瘦多了,臉也沒有了過去的紅潤,眼里還隱隱含著一種恐懼和憂慮,眼淚卻是簌簌地淌落,心疼地摟著她,“快說,我這就去收拾他。”
李玉年不肯說,她只有一句同樣的話:“我們在家種田、養雞、喂豬,也一樣能掙到錢的。我們家寶兒到時候還是能讀得起書的。”
哭了一陣,李玉年準備去給田長松辦飯。田長松說他還是早晨在火車上買了盒方便面吃了的,早就餓得肚皮貼后背了。李玉年那個心疼呀,她一定要給他弄些好吃的才是。
就在這時,李玉年聽到禾場外面傳來叫喊她的聲音。孫小環又來了。李玉年只是怔了片刻,她就走了出去,她不能讓孫小環走進門來。
十月下旬,一絲涼意襲上身來,李玉年走出門,不由得打了一個寒顫。
這天夜里沒有月亮,天上的星星也被云彩遮住了。李玉年覺得眼前一片漆黑,走路都有些跌跌撞撞了。
“聽說長松回來了,我想跟他說一說我們的事情。”也許,孫小環還是有些怕田長松的,不然,他怎么不直接走進屋去,而是站在禾場外面叫喊李玉年。
李玉年說:“你不要做夢了,快走吧。”
“我不走,我要讓田長松知道我們的事情。”這樣說著,孫小環就想往屋里去。
李玉年攔住了他,帶著哭腔說:“我求你了,不要再說那個話了。”
孫小環說:“你答應我了?我不說,你自己去說吧,我在這里等著的。”
李玉年仿佛是下了很大的決心,說:“我們去那邊說吧。”
“到哪里去說?”
“不能讓長松聽到的地方。”
孫小環說:“為什么不能讓他聽到呢,就是要讓他聽到,事情才辦得好啊。”
李玉年不再說話,往禾場外面走去了。
孫小環只得跟在她的身后往禾場外面走,口里說:“也行,我們先商量好,怎么開口說那個話。”
禾場外面是一片水田,水田里的油菜種得早,長得青枝綠葉的樣子,可是今天卻是什么都看不見。孫小環似乎有些不耐煩了,問:“還要往哪里走,就在這里說。”
孫小環的話還沒有說完呢,他就覺得腦殼上像是被什么重重地敲了一下,他才啊那么一聲,就身不由己地倒了下去。
當時,田長松還在想呢,黑天黑地,誰在外面叫玉年,玉年怎么不讓他進來,卻是帶著他往禾場外面走。田長松跟了出來。才走了幾步,他就又踅回身子,外面太黑,他想找玉年用的手電筒,卻是沒有找到,只得從口袋掏出打火機,借著打火機的光亮走出禾場。
田長松是真真切切地聽到了那一聲響了,像是菜刀切西瓜的聲響,過后,他又聽到了啊的一聲,他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一邊往前走,一邊問:“玉年,誰叫你啊。”
田長松聽到一串腳步聲正匆匆地往前面的那條簡易公路去了,卻是看不見是誰。
田長松心里不由生出一團狐疑,女人怎么了,家里發生什么事了啊。就在這時,田長松的腳突然踩著了一團軟綿綿的東西,可把他嚇了一跳,勾下頭,他被嚇得半死,借著打火機的那一星點光亮,他看見孫小環躺在地上的,張著嘴,一口一口地喘著氣,那只沒有瞎的眼睛瞪得老大,血從他的頭上噴出來,把一片油菜都染紅了。
田長松似乎已經覺出了什么,大叫:“玉年,快跟我把孫小環送到醫院去,不然會出人命的。”
那一串匆匆的腳步聲就停了下來,過后腳步聲就又響了過來。借著打火機的光亮,田長松看見自已的女人手里拿著一把柴刀,柴刀上還沾著許多的血。“玉年啊,你怎么能這樣,有什么事不能解決的啊。我們趕快把他送到醫院去吧。”
李玉年勾下身子,伸手在孫小環的鼻子下面試了試,過后就揚起柴刀,狠狠地向孫小環砍去。孫小環就不再喘氣了,他的腦殼,已經被李玉年劈開了。
田長松想去搶李玉年手里的柴刀,李玉年卻走了,一陣零亂的腳步聲向遠處去了。
田長松聲嘶力竭地叫道:“玉年,你為什么要這樣啊?”
李玉年這時回他的話了:“長松,帶好我們的寶兒……”
李玉年的聲音在空曠的黑夜里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沉默的夜,是那樣的深沉,那樣的迷惘……
責任編輯 王宗坤
郵箱:wangzongkun200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