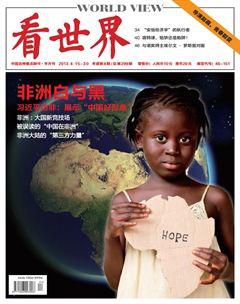艾滋病可能被終結?
津田


32年前,人類第一次發現了艾滋病,之后這種病一直被視為不治之癥;不過17年前,治療艾滋病的藥物首次問世,讓這一絕癥變得可以治療。然而這其中存在一個障礙:患者需承擔平均每年高達1萬美元的藥費,這讓很多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覺得這種病依然是一個不治之癥。不過,最近有個好消息傳來:一名出生即攜帶艾滋病毒的小女孩在兩歲半時被功能性治愈。這樣一個消息無疑振奮人心。
被功能性治愈的女嬰
2010年7月,一名早產兒在美國密西西比州出生,然而她的降生并非伴隨著希望和喜悅:她的母親在分娩時才被查出攜帶艾滋病毒。由于嬰兒出生在農村,無法得到較為良好的治療和護理,很快她便被送往密西西比大學醫學中心,由兒科中心專家漢娜·蓋伊診治。
由于接手時小孩兒已經感染艾滋病毒,蓋伊便給她開出了猛藥,在孩子出生30小時內,就用3種混合藥物對孩子進行阻斷病毒的治療,這在當時看來是一個風險極大的舉措。對于大部分在子宮內或是分娩時接觸艾滋病毒的嬰兒,醫生會在確診之前用1-2種藥物對他們進行治療,以降低他們的感染幾率,一上來就用猛藥治療,藥物的毒性很可能對孩子的身體造成傷害。
但蓋伊卻另有想法。由于嬰兒的母親在懷孕期間沒有接受任何病毒阻斷治療,女嬰極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因此蓋伊認為用藥上要更快更狠。事實證明,蓋伊的這次冒險是值得的。出生29天后,嬰兒的血液中已經檢測不到艾滋病毒。隨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兒科專家黛博拉·佩爾紹德根據這一結果發表聲明:“我們認為,及早進行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能阻止病毒庫的形成。”
這里提到一個關鍵詞: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它的原理在于抑制艾滋病毒的復制,通過連續藥物的輸入,為艾滋病毒的擴散和扶植豎起一道“銅墻鐵壁”,使病毒數量保持在較低水平。醫學界一致認為,艾滋病毒十分擅長“捉迷藏”,愛變身,或是耐著性子玩潛伏。一旦停止抗逆轉錄病毒藥物,銅墻鐵壁一消失,病毒很有可能會卷土重來。因此,醫生通常會建議患者終生服用此類藥物。然而,2012年1月,也就是這名艾滋女嬰18個月大的時候,不知出于何種原因,嬰兒的父母決定不再為孩子服用抗逆轉錄病毒藥物。那么,艾滋病毒還會重新來過嗎?
5個月后,女嬰再次回到醫院進行血液檢查,結果令醫生們大吃一驚。主治醫生蓋伊說:“我非常驚訝,停止用藥5個月后,我們竟然檢測不到孩子體內的艾滋病毒載量。”又過了5個月,女嬰再次來到醫院進行檢測,血液中依然檢測不到病毒,蓋伊此時驚喜萬分:“也許是無心插柳,但我們確實治愈了這名女嬰。”
治愈,這是一個對于艾滋病研究學界來說幾乎難以說出的詞語。不過,即便醫生宣布目前治愈了這名嬰兒,然而這并不能確保擅長“躲貓貓”的艾滋病毒永不現身。因此,佩爾紹德將這一結果定性為“功能性治愈”。
功能性治愈是指艾滋病毒檢測為陰性,即使不再吃藥,機體免疫功能也處于正常狀態,但體內仍有病毒存在。那么,現在又有一個新的疑問:從功能性治愈到完全治愈是否存在這一可能?
布朗的“美妙基因”
現年48歲的美國人蒂莫西·布朗給了這一問題肯定性答案。1995年,布朗在德國被確認感染艾滋病毒;1年后,他開始服用抗病毒藥物,之后被功能性治愈。但在2006年,布朗又被確診患有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為了治療白血病,2007年2月開始,布朗在德國先后兩次接受了骨髓移植。幸運的布朗在進行了骨髓移植后白血病痊愈;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經過醫學檢測,布朗體內的艾滋病毒竟也完全消失。他也因此成為世界首例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也被稱為“世界上最幸運的人”。
在接受骨髓移植前,布朗和醫生都沒預料到,向他捐獻骨髓的人體內存在一種罕見的變異基因:CCR5。這一基因被稱為“美妙的基因”,擁有它的人對艾滋病毒具有免疫力。CCR5是一種細胞膜蛋白,艾滋病毒如果要攻擊細胞,就必須先與這種細胞膜蛋白結合。而變異后的CCR5基因的特點就是可以抵御所有病毒性基因的傳染。布朗在接受骨髓移植的同時,體內也就擁有了這一“美妙基因”,艾滋病毒因此就無法再侵入細胞進行復制,病毒載量自然下降,布朗的艾滋病得以完全治愈。
但是布朗的幸運很難被復制。在更多醫學專家看來,被功能性治愈的女嬰或許能對艾滋病治療研究帶來更大的借鑒意義。密西西比的這一案例提出了一種誘人的可能:感染艾滋病毒的不同人群可以通過不同的方法治愈。“柏林病人”布朗的痊愈源于一系列復雜、昂貴、高風險的醫學步驟,而這一新案例卻是花銷相對較小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的結果。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密西西比女嬰的案例也凸顯出早期治療的重要性。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艾滋病毒母嬰傳播的概率為15%—45%,但及時的產前檢查和實施藥物阻斷治療,能使母嬰間傳播幾率下降到2%以下。然而如今在全球范圍內,每年仍有30萬到40萬艾滋嬰兒出生,其中90%來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
雖然這一系列的進展和突破讓人們看到了希望,不過我們仍然得在“終結艾滋病”的后面畫上個問號。在世界上所有艾滋病患者當中,前NBA著名球星、“魔術師”約翰遜無疑是最有影響力的一位。這位前洛杉磯湖人隊控球后衛在1991年因感染艾滋病毒而宣告退役,經過科學的治療,他已經平安地度過了20多年,而且有了孫女。然而,治療艾滋病的昂貴費用可能只有約翰遜這樣的有錢人能承擔下來,對于更多的平民甚至是亞非拉美地區的窮人來說,這無疑是個不可能完成的治療任務。因此,在柏林病人布朗和密西西比女嬰案例帶來喜悅的同時,這一條抗艾之路仍然任重而道遠。
當然,從上世紀80年代到今天,人類社會確實還沒有找到能夠根治艾滋病的方法。不過如前文所說,從被完全治愈的柏林病人,到被功能治愈的密西西比女嬰,我們還是欣喜地看到這些昔日的艾滋病患者可以正常地學習、工作、生活。在和疾病的戰斗當中,我們絕不放棄,就會埋下希望的種子。最后,借用波斯詩人薩迪的一句話:你雖在困苦中,也不要惴惴不安,往往總是從暗處流出生命之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