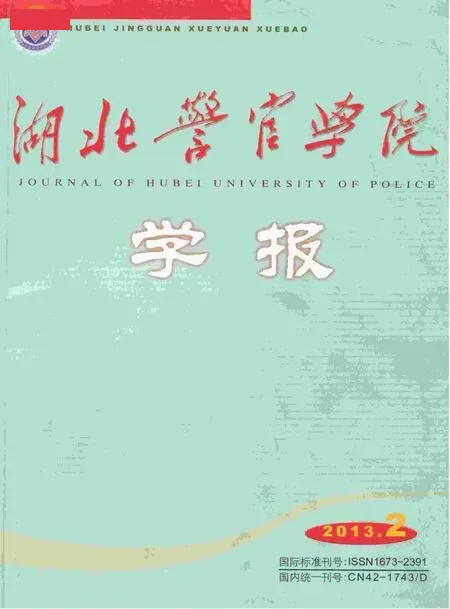非法經營罪兜底條款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探討
文定君
(黃石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湖北 黃石435000)
一、非法經營罪兜底條款的由來
1979年刑法中的第117條規定“違反金融、外匯、金銀、工商管理法規,投機倒把,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處、單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由此可見,經濟領域的犯罪行為均可納入投機倒把罪的懲治范圍,這就導致投機倒把罪成為1979年刑法的“口袋罪”之一,一直受到學界的強烈批評。1997年刑法修訂后,取消了投機倒把罪這一罪名,并將一些與經營活動有關的違法活動規定為獨立的犯罪,如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等,同時為了更好地適應現今經濟犯罪活動的新型性和多樣性,將需要刑法予以懲治的非法經營行為納入到非法經營罪的管制范圍。
1997年刑法第225條對于非法經營罪做了明確的規定,1999年頒布的刑法修正案和2009年頒布的《刑法修正案(七)》也對該條文進行了修改,條文內容由原來的三項增加到四項,其第四項“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即為非法經營罪的兜底條款的規定。
(一)法律本身的局限性是該兜底條款存在的根源
卡多佐曾感嘆:“法律必須穩定,但又不能靜止不變,我們總是面臨這一巨大的悖論,無論是靜止不變,還是變動不居,如果不加以調劑或不加以制約,都同樣具有破壞力。”“刑法是一個封閉自足的完美體系”,這是法典國家立法者的最終理想,它能最大程度地維護刑法的穩定性和權威性,但“法有限、事無窮”是立法者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成文法雖能保持法的穩定性,成文刑法典使罪刑法定化,將罪刑如數規定在法典內,讓刑法成為相對封閉的規則體系,但刑法典并不能將犯罪的行為方式統統囊括。無論立法技術如何發達,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立法均具有局限性,不可能將未來社會發展的一切可能變化在現今或以前就制定出來。因此,設立具有高度涵蓋性的兜底條款成了必然選擇。兜底條款以其語言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使得刑法可以在維持其規范系統相對穩定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滿足社會生活的發展需要。同時,犯罪現象的多變性,也決定了兜底條款的存在。
(二)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狀況是該兜底條款存在的客觀背景
任何法律條文的形成都有其特有的客觀的社會背景,非法經營罪的兜底條款也不例外。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是采取由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的,大量的規則并非由市場內部產生,所以它們難以在短期內獲得市場主體的認同。隨著激烈的社會變革,不斷涌現出各種新型的市場失范行為,市場規則的建立就出現了嚴重的滯后性。通過設立高度概括、抽象的“一勞永逸”的罪刑條款,使刑法能從容應對繁雜的市場失范行為,為國家能夠在必要時介入經濟領域行使刑罰權提供合法的依據。
二、關于非法經營罪兜底條款的司法適用
非法經營罪的兜底條款,從設立以來一直廣受非議,理論界認為這與罪刑法定的要求相沖突,給人們確切地把握刑法規定的具體內容造成障礙,可能助長司法恣意。但從現實看,兜底條款的存在具有不可避免性:它是立法技術存在難以克服障礙的產物,也是國家為避免刑罰處罰空隙而有意采用的保留手段。兜底條款對于嚴密刑事法網、強化刑法的社會保護功能具有積極意義,但現代刑法在保護社會的同時,必須重視人權保障。兜底條款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如果被司法者過分依賴或運用不當則會成為司法機關濫用刑罰權的合法工具,而且,兜底條款對特定犯罪行為的包容性大大降低了裁判活動的司法風險,使司法者在實際辦案過程中盲目擴大兜底條款的適用范圍,從而導致兜底條款適用標準一再降低。要實現非法經營罪兜底條款契合罪刑法定原則,對兜底條款的適用應采用嚴格限制解釋的立場。筆者將就適用體系解釋的原則,對非法經營罪的兜底條款的司法適用進行探討。
體系解釋就是在對其含義進行闡釋時,不僅僅局限于相關刑法條文,而是從整部刑法的角度出發,就該條文在整個刑法中的地位及其與其他相關法條的關系來闡明其涵義的解釋方法。由于其著眼于運用其他相關法條來輔助解釋,這種解釋方法往往更加具體、準確、全面。運用體系解釋原則解釋非法經營罪的兜底條款可以保證法律條文的“同質性”,將兜底條款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并契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避免超出罪刑法定的界限。
(一)“違反國家規定”是前提
“違反國家規定”是構成非法經營罪的必要條件,要限制對兜底條款適用范圍的無限擴大,明晰“國家規定”的確切范圍是首要條件。《刑法》第九十六條規定:“本法所稱違反國家規定,是指違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和規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根據體系解釋的原則,構成非法經營罪的行為所違反的“國家規定”,應只包括最高立法機關及其常設機關、最高行政機關制定和發布的規范性法律文件。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國家機關,包括國務院各部委、各專門委員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和發布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均不屬于“國家規定”的范疇。
針對這一點,2011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準確理解和適用刑法中“國家規定”的有關問題的通知》(法[2011]155號)中又專門進行了明確,并且要求“各級人民法院審理非法經營案件,要依法嚴格把握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的‘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有關司法解釋未作明確規定的,應當作為法律適用問題,逐級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由此可見,適用非法經營罪兜底條款,明晰“違反國家規定”是基礎。
(二)“嚴重擾亂市場秩序”是核心
“嚴重擾亂市場秩序”是構成非法經營罪的核心,體現了非法經營罪所保護的法益,明確其指向是劃定這一兜底條款規制范圍的核心。“兜底條款要想避免被隨意擴大,應取決于法條本身能夠暗示其內涵和外延。”《刑法》第225條列舉的非法經營罪的前三種行為方式分別為:(1)未經許可經營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的行為;(2)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準文件的;(3)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非法經營證券、期貨、保險業務的,或者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的。依照體系解釋的原則,“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指向應與非法經營罪上述三條款的指向相同。以上三條的共同之處在于,都是違反國家的經營許可制度的經營行為。重點在于:其一,經營主體都無合法資格,他們在沒有經營資格許可的情況下,就擅自從事國家特許經營的相關行業,違反了國家的經營許可制度;其二,經營客體是國家禁止經營的產品。由此可見,兜底條款中的“嚴重擾亂市場秩序”行為是指,除了非法經營罪中第一、二、三項規定的行為以外的,侵害國家經營許可制度,限制市場主體自由進入的經營行為。
(三)“情節嚴重”程度是重點
刑法的謙抑精神要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犯罪。非法經營罪已經明確的非法經營行為都具有行政違法性,但并非所有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都應劃入非法經營罪調整的范圍,有些行為如果沒有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法律規定可由其他法律進行調整,如果對所有擾亂市場秩序行為都入罪,可能會將非法經營罪兜底條款的調整范圍無限地擴大。
我國刑法關于犯罪的規定主要是采取立法既定性又定量的模式,所以行為的危害程度對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具有決定意義。由此,“情節嚴重”是重要的定罪要件,其程度必須予以明確。我國刑法分則在很多具體罪名的罪狀上均有“情節嚴重”的規定,依據體系解釋的原則,聯系刑法其他條款,認定非法經營罪兜底條款中的“情節嚴重”應從以下五個方面著手:(1)非法經營的數額。非法經營罪是以獲利為目的的典型經濟犯罪,犯罪數額是認定行為危害程度的首要標準,數額較大即可認定為“情節嚴重”。(2)違法所得的數額。違法所得數額是行為人非法經營行為的獲利數額,與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往往成正比,違法所得越多,社會危害程度越大,違法所得數額較大即可認定為“情節嚴重”。(3)多次進行非法經營,屢次經行政處罰而不悔改。行為人在一定時期內多次反復從事非法經營,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以一定時期內從事非法經營行為的次數作為衡量“情節嚴重”的標準具有合理性。(4)嚴重擾亂市場秩序,造成重大損失。非法經營行為擾亂了市場的正常交易秩序,勢必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損失。以造成的具體損失為標準判斷情節是否嚴重具有可取性。(5)非法經營行為引起較大范圍內市場混亂的。非法經營的行為如果造成社會影響的范圍特別大也應認定為“情節嚴重”。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將非法經營罪兜底條款所述之罪狀限定為:違反國家規定,破壞國家經營許可制度,嚴重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非法經營行為。這樣一來,非法經營罪的兜底條款在司法適用中,既能涵蓋紛繁復雜的經濟犯罪形式,又能契合罪刑法定原則。
三、非法經營罪兜底條款在案件中的適用
下面就一起近期偵辦的違法發放高利貸涉嫌非法經營罪的案件,對該條款的司法適用發表一些學理見解。
(一)基本案情
2010年2月,審計署《審計要情》反映:武漢2家民營企業通過多家關聯企業,非法開展金融業務,非法發放高利貸數額達54億元人民幣,從中獲利2億多元。為此,中央有關領導同志相繼作出重要批示,要求銀監會和公安機關依法查處,中國銀監會核查認為這兩家單位涉嫌犯罪,遂將案件移送公安部。公安部通知湖北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經相關領導同意后,省公安廳指定我局立案偵查該案。
我局經一年多偵查查明:這兩家公司在2006年6月至2010年8月期間,單獨或結伙,借用其下設典當公司為道具,以類銀行金融機構的名義,參照銀行發放貸款的業務模式和流程,采取扣押封存借貸方的工商營業執照、房屋產權證、土地使用權證、財務印鑒等相關證照印章(其俗稱“封包”)等控制方式,以28.8%-78%的年利率(約為同期銀行基準利率的5-14倍)發放高利貸。其中一公司非法向55家單位發放高利貸總計19.8億余元,非法獲利總計8233萬余元。另一公司非法向184家單位發放高利貸總計49.4億余元,非法獲利總計2.3億余元。在非法發放的高利貸資金中,大量資金提供給貸款企業從事虛報注冊資本、串通圍標等其他違法犯罪活動。
(二)運用體系解釋原則,適用非法經營罪兜底條款對該案定罪
運用體系解釋原則解釋,該案是非法經營罪兜底條款規定的“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
1.兩公司的行為是“違反國家規定”的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的商業銀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設立的吸收公眾存款、發放貸款、辦理結算等業務的企業法人。”第十一條規定:“設立商業銀行,應當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審查批準。未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從事吸收公眾存款等商業銀行業務,任何單位不得在名稱中使用‘銀行’字樣。”
《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第二條規定:“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負責對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及其業務活動監督管理的工作。...”第十九條規定:“未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準,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設立銀行業金融機構或者從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第四十四條規定:“擅自設立銀行業金融機構或者非法從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的,由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予以取締;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第三條規定:“本辦法所稱非法金融機構,是指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擅自設立從事或者主要從事...發放貸款...等金融業務活動的機構。”第四條規定:“本辦法所稱非法金融業務活動,是指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擅自從事的下列活動:……(三)非法發放貸款……”第五條規定:“未經中國人民銀行依法批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設立金融機構或者擅自從事金融業務活動。”第二十二條規定:“設立非法金融機構或者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是國務院發布的命令,均屬于《刑法》第96條規定的“國家規定”。故兩公司的行為是違反“國家規定”的行為。
2.兩公司的行為是“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經營行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的規定,只有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設立的商業銀行才能開展貸款業務,我國《貸款通則》中也有“貸款人必須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經營貸款業務,持有中國人民銀行頒發的《金融機構法人許可證》或《金融機構營業許可證》,并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準登記;企業之間不得違反國家規定辦理借貸或者變相借貸融資業務”等規定。
兩公司借用其下設典當公司為道具,以類銀行金融機構的名義,參照銀行發放貸款的業務模式和流程,向社會不特定的對象發放高利貸的行為,其實質是一種經營行為,有別于普通的民間借貸。并且中國銀監會《銀監函[2011]1號》也認定“兩公司高利放貸行為屬于非法金融業務活動,涉嫌犯罪。”
因此,兩公司的經營行為是除了《刑法》第225條第一、二、三項規定的行為以外的,侵害國家經營許可制度,限制市場主體自由進入的經營行為。
3.兩公司的行為是法定的“情節嚴重”行為
兩家公司中一公司非法經營的數額達19.8億余元,違法所得數額達8233萬余元;另一公司非法經營的數額達49.4億余元,違法所得數額達2.3億余元,涉嫌犯罪數額巨大。而且在兩家公司非法發放的高利貸中,大量資金被提供給貸款企業從事虛報注冊資本、串通圍標等其它違法犯罪活動,甚至在調查中還發現,某些銀行為了完成存款任務,也向上述公司借高利貸。其非法經營行為已經嚴重擾亂正常的市場秩序,并引起了國家審計署和中國銀監會的關注,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可想而知。由此認定上述兩家公司非法經營行為的情節已經到了特別嚴重的程度,屬于法定的“情節嚴重”的行為。
綜上所述,該案中的兩公司的行為已適用非法經營罪的兜底條款,構成非法經營罪。目前該案已經我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法院已作有罪認定,正在按最高法相關規定呈報最高法請示認定。
[1]馬克昌.經濟犯罪學新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
[2]陳澤憲.非法經營罪的若干問題研究[J].人民檢察,2000(2).
[3]陳興良.刑法的價值構造[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4]儲槐植,梁根林.論刑法典分則修訂的價值取向[J].中國法學,1997(2).
[5]儲槐植.刑事一體化與關系刑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 97.
[6]林山田.經濟犯罪與經濟刑法[M].臺北:臺北三民書局,1981.
[7][美]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長法法律科學的悖論[M].董炯,彭冰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
[8]周光權.刑法總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