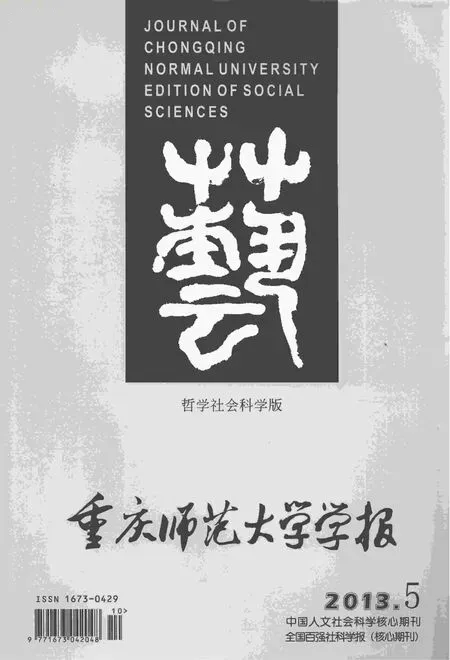《鏡花緣》中李汝珍尚才主智的價值觀
陳 呈
(四川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成都 610064)
一、女子的才學展示欲
李汝珍筆下的才女可以被看做一個整體來討論,學者夏志清曾在文章中調侃:“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漢性格懸殊、出身迥異、智勇不同。但那百個女子,全屬綺年玉貌、蕙質蘭心,要分辨她們,更戛乎其難。為了幫助讀者記憶,所有孟家女子,作者都在其名字上著一‘芝’字。而所有嫁給章家的,則著一‘春’字,有些名字則提示我們,某某女子擅長繪畫、音樂或書法,或某些又長于什么。否則,就沒有什么容易的辦法去辨認那百個女子中較不重要的了”[1](31)。雖然這是小說文本技巧上的缺陷,但也正因為才女們的太過相似,由此構成了群像,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價值觀。
作為《鏡花緣》的主角,那一百個名字被刻于泣紅亭玉碑上的女子,其第一重身份就是才女,李汝珍也因此塑造了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數量最龐大的才女群像。她們各懷才學,既有經史諸子、醫卜星相、音韻算法、經商習武等社會實用性的才能,也精通傳統女學里琴棋書畫及文人宴樂中燈謎酒令、雙陸馬吊、射鵠蹴毬、斗草投壺百戲之類,可謂文武雙全,剛柔并濟。然而,與李汝珍同時代的親友序跋中并沒有表現出對《鏡花緣》中女性才能的強烈關注和興趣。究其原因,當與同時代的女性創作之繁榮、才學活動之頻繁有關。
從整個古代社會的女性作品中來看,清代女性的創作無論從數量上和文體上都達到了高峰。胡文楷的《歷代婦女著作考》是目前關于女性著述最全的匯總。此書中用十五卷的篇幅專列清代婦人的作品,而之前的明代不過兩卷。就人數而言,據初步統計,漢代至元代有116家,明代244家,清代一朝就有3518家。胡文楷在該書的自序中概括云:“清代婦人之集,超軼前代,數逾三千”[2](5),可見當時女子創作的盛況,在這些女子中,尤以李汝珍長期居住的江蘇一帶為盛,學者史梅在其《清代江蘇婦女文獻的價值和意義》的論文中,除了《歷代婦女著作考》中著錄女作家1425人,著作1707種外,還從江蘇各地250部地方志中輯得其未收的118名女作家,著作144種。
《鏡花緣》從第六十九回《百花大聚宗伯府,眾美初臨晚芳園》到第九十三回《百花仙即景露禪機,眾才女盡歡結酒令》,百位才女在宴會中切磋詩藝,聚于雅室小亭或小園香徑,賞魚逐蝶、弈棋撫琴、潑墨揮毫,儼然是當時女子結社的寫照。清代女子對才學展示和實踐的欲望增加了,她們與當時的才子名士一樣,以地域為范圍結社結派,著書立說,往來唱和。《歷代婦女著作考》中錄入的《清代閨閣詩鈔》清暉樓主序曰,“至有清一代,閨閣之中,名媛杰出,如蕉園七子、吳中十子、隨園女弟子,至今猶膾炙人口”[2](927)。這些閨秀互相結社、酬唱應答、品評詩文。據學者王英志《隨園女弟子考評》統計,最有規模的隨園女弟子,其人數至少在50人以上,大大超過有記載的男弟子數量20余人。這些女弟子經常自發地聚在一起進行文藝創作,如《隨園詩話補遺》卷一:“庚戌(乾隆五十五年)春,掃墓杭州,女弟子孫碧梧邀女士十三人,大會于湖樓,各以詩畫為贄”[3](693)。女子詩社之類的文化社團的興起和流行,無疑極大地豐富了清代才女們的生活。
隨著習得的才學種類增多,書中才女們對施展才華的領域也有了更多的想法,除了傳統的閨閣范圍,更將理想伸向了長久以來被男子獨占的社會朝堂。本來,有關才女對科考抱有積極態度的敘述在更早的文學作品中也可以看見,但如此群體性地對科舉產生向往卻是罕見的。由百花仙子化身的唐小山是一百才女中的領袖人物,她出生在普通的文人家庭中,在年少時期就開始對科考向往。小山四五歲就喜讀書,能過目不忘,而且文武雙全,時常舞搶耍棒。長大些就詢問叔叔唐敏女科考試的時間,以便早早用功,早作準備。書中的才女們在經過和男子一樣的經史詩文發蒙教育以后,自然想要有一番作為。即便是商人林之洋的女兒婉如和多九公的侄女在女試盛典頒布后也趕去一試身手。世家大族中的才女群體對科考的向往就更不必說。卞、孟、蔣、董等官家的閨秀因父親是考官不能應考,各個悶氣,其父母將其聚在一塊散心,散心不成,她們還要卜卦看有沒有機會補考,算得上簽才各個舒心高興,可謂應考心切。書中最特別的一位應考才女還要數黑齒國才女盧紫萱之母緇氏,她自幼飽讀詩書,只是一直沒有考試機遇,雖然已經嫁作人婦,卻仍想證明自己的才華,在亭亭(盧紫萱)要隨唐小山去天朝赴考時,她以女兒為要挾,要求小山帶自己同去天朝一試。到了天朝,緇氏的科考也是一波三折,但她越挫越勇,終于因考官的體諒拿到了才女匾額,這才心滿意足地打道回府。這個百折不撓,不顧老臉的喜劇角色身上也帶著些許辛酸,她是為了證明自己的真才實學,努力尋求舞臺的平凡讀書人。
二、他者的才學保護欲
女性有了才學展示的自覺和要求,但畢竟處在弱勢地位,要想實現她們的需求必須借助外力的支持。李汝珍首先從社會認同方面為才女們的才學提供保護。《鏡花緣》中的“他者”就是才女們展示才學的社會思想輿論上的堅強后盾,“他者”普遍對才女的才學持贊美、肯定和支持。書中第六回,上官婉兒被命與群臣一同做詩,一連兩日都沒有一人在上官婉兒之先交卷。滿朝大臣對于輸給一個女子并沒有表現出氣惱,反倒是大大方方地認輸并稱贊:“天生奇才,自古無二”[4](17)。就眾才女的家庭看,由于對才女的教育投入了大量心血,所以對她們參加科考也是多加鼓勵的。主考官卞濱等人的女兒出身官宦之家,自小受教育自不用說。即便在落魄文人家庭出身的唐小山也是自幼讀史通經、舞槍弄棒,不但無人約束,還得到了叔叔的指導。商人林之洋對女兒婉如酷愛學習的行為也是欣喜與鼓勵的。
不僅如此,李汝珍還直接將社會認同的力量擴大至朝廷統治者,以最高權威來為女子才學正名。作者將故事發生的時代定在武則天統治時期,這有兩層意思,一是女皇統治下,才女們自然有一展抱負的機會;二是唐初正是科舉制度的確立時期,如果能在此期形成傳統,那么今后才女們的命運便會大大不同。于是李汝珍借武則天的身份為才女們創造了一個曠世盛典。第四十一回中,唐敏說出了武則天設立女科考試的原因:“太后自見此圖(《蘇氏蕙若蘭織錦回文璇璣圖》),十分喜受。因思如今天下之大,人物之廣,其深閨繡閣能文之女,固不能如蘇蕙超今邁古之妙,但多才多藝如史幽探、哀萃芳之類,自復不少。設俱湮沒無聞,豈不可惜?因存這個愛才念頭,日與延臣酌議,……即于前次所頒覃恩十二條之外,續添考才女恩昭一條”[4](193)。歸根結底,興此制度還是因為愛才。此后頒布恩詔,其中外籍可參加考試的規定頗有大國的胸襟氣魄,同時也保證了諸如黑齒國紅紅和亭亭、女兒國陰若花等漂泊海外的才女能有同樣有參加考試的機會。并且“因生病或路遠可補考”一條規定也化解了影響才女參加考試的不利因素。其后更是寬容地表示,恩詔頒布突然,恐諸女學業未精,所以專門延遲到圣歷三年三月部試,這就保證了此次考試的有效性。考試期間,武則天的愛才與惜才的表現也層出不窮。擔任部試主考官的官員子女本應避嫌缺考,武后卻特發諭旨,欽賜各才女至期一體殿試。在部試中“俱因污卷貼出”的花再芳、畢全貞、閔蘭蓀三名女子,再三乞求殿試,武后也能體諒其少年要強之心和千里迢迢趕考的辛苦,姑念污卷乃無心之失,準其一并殿試,以彰顯求才若渴之至意。這次特殊的女子科考從惜才的角度出發,既有嚴格的條例規范作為制度保障,又處處體現著對人才的珍視與寬容,以官方的權威作為女子展現才能的最堅強的支撐。
其實女子以自身才能為社會所用早已見諸各種文學作品,比如南北朝時期描寫女子替父從軍、衛國立功的《木蘭辭》、徐渭所撰雜劇《女狀元辭鳳得凰》等。但這些作品中,花木蘭從軍、黃春桃參加科考,無一不是變裝過后的巾幗英雄,都是以個體身份單槍匹馬地在男權社會里小心翼翼,或者可以說是偷偷摸摸地爭取自己才能的展示機會。她們以男性模樣在社會上風光無限,然而一旦女性身份被識破,只能被打回原形,重新回到閨房,回到男權的壓制中。而《鏡花緣》中的才女能夠以女性的身份公開地參加科舉考試,光明正大地走出家門,走向社會,這是李汝珍愛才的集中體現。
三、尚才主智的價值觀
李汝珍對才的重視和褒揚不只是對于女性而言,這種審美觀是普世性的。這一百才女是作者樹立的有才之人的典型。他在全書中表現了自己鮮明的立場:以才學作為衡量人高下的基本標準,無關性別。有真才實學的人值得真心實意地贊美,而那些不學無術或不懂裝懂的假儒士就該被毫不留情地嘲笑。從書中對海外黑齒、白民、淑士三國的描述可以看到李汝珍明確的態度。
李汝珍在文本中塑造了一個女子教育極其發達的黑齒國。黑齒國是作者對女子才學認同的體現,更是作者想要塑造的理想審美觀中“以才為美”的集中體現。這個國家以才作為衡量女子的最高標準,男人對女性之美的評判不再是品頭論足。林之洋見此處女子長得黑,以為是沒有脂粉用,懷著奇貨可居的心態想要帶脂粉去售賣,卻發現這里的女子反覺脂粉丑陋,倒是買書的很多。唐敖見識了兩位女子的才學之后,走在黑齒國的街上,只覺得每個帶有書卷氣的黑女都美貌無比。這里的風俗是“無論貧富,都以才學高的為貴,不讀書的為賤。就是女人,也是這樣。到了年紀略大,有了才名,方有人求親。若無才學,就是生在大戶人家,也無人同她婚配。因此他們國中,不論男女,自幼都要讀書……這里向來分別貴賤,就在幾本書上”[4](77)。腹有詩書氣自華,作者借黑齒國的習俗明確地矯正著世人的審美觀念。
白民國是作為黑齒國的反襯而出現的。白民國的人個個面白如玉,美貌異常。唐敖、多九公在黑齒國吃了虧,見白民國人生的清俊,以為他們是天資聰穎又博覽群書,于是在學塾前畢恭畢敬地聽候老夫子訓誡,正當準備離去時,卻聽見夫子在里面“切吾切,以及人之切”,[4](96)本以為又是什么深奧學問,突然反應過來,不過是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幼”字讀錯了,兩人好不羞惱,原來這夫子不過是一個不學無術,又喜歡自吹自擂的騙子。
淑士國則是作者用來諷刺名不副實的酸腐之士。這里的人個個儒者打扮,人人斯文,處處書聲。可惜這些儒生皆為腐儒。不通文墨的林之洋胡編的《少子》竟令一群“好學”的生童歡喜不已。酒樓中酒保戴著眼鏡,還拿著折扇,一開口便是“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菜要一碟乎,兩碟乎?”[4](102)上的下酒菜盡是青梅、齏菜。林之洋喝了一口酒,連忙吐出,原來那酒太酸,誤以為是醋。這一吐引起旁邊一個本來晃著身子“之乎者也”吟個不停的老者的注意,接下來一段長篇大論,一口氣五十一句,句句帶“之”:“先生聽者:今以酒醋論之,酒價賤之,醋價貴之。因何賤之?為甚貴之?真所分之,在其味之……倘鬧急之,我惟跑之;跑之,跑之,看你怎么了之。”[4](103)林之洋以俗人的角度一針見血地評道:“你這幾個‘之’字,盡是一派酸文,句句犯俺名字,把俺名字也弄酸了。”[4](103)與唐敖談分科考試的“大儒”臨走前千叮嚀萬囑咐酒保一定要留好喝剩的兩杯酒和吃剩的醬豆腐、糟豆腐,已經走了兩步,見旁邊桌上放著一根人家吃完飯剩下的禿牙簽,“取過,聞了一聞,用手揩了一揩,放入袖中。”[4](104)這些人外表倒是像儒者了,但透過點滴小事表現出的卻毫無儒者氣度。這些人的作為與作者尚才主智的價值觀背道而弛,自然受到作者的無情嘲諷。
四、尚才主智價值觀的形成
1.漢學學風
李汝珍對博學多識、真才實學的贊賞和對空疏無識與迂腐僵化學風的譏諷所體現出的褒貶鮮明的態度,與當時主宰整個時代的漢學學風分不開。作者所處的時代,恰好是考據學的鼎盛時期。乾嘉漢學的門戶確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與日漸充斥文化界的空疏不學、虛談性理的風氣劃清界限。清代的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談到經學之所以自兩漢后衰落而在清朝復盛的原因時就曾說過:“一則明用時文取士,至末年而流弊已甚。顧炎武謂八股之害,甚于焚書。閻若璩謂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時文者而極。一時才俊之士,痛矯時文之陋,薄今愛古,棄虛崇實,挽回風氣,幡然一變。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皆負絕人之姿,為舉世不為之學。于是毛奇齡、閻若璩等接踵繼起,考訂校勘,愈推愈密。”[5](299)
胡適曾以李汝珍身處一個博學時代的無奈來解釋《鏡花緣》掉書袋的嫌疑。從漢學的啟蒙時期到興盛時期,漢學一脈的學者無一不是窮經通史,博學強記之人。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說的吳派代表惠棟的治學范圍是“以經學為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佚等等”[6](5)。皖派代表戴震則是17歲師事經學大師江永,學習聲律、音韻、天文、歷數、典禮。李汝珍的老師凌廷堪是乾嘉時期的禮學大師,其友阮元對其學問多次稱贊,“次仲于學無所不窺,九經三史過目成誦,尤精三禮,辨析古今得失,識解超妙。”[7](88)阮元《凌母王孺人壽詩序》戴震弟子樸學大師盧文弨為凌廷堪《校禮堂初稿》作序時,將其列于顧炎武、戴震、程瑤田實學一脈,而“顧、戴不能為詩與華藻之文,而君兼工之。詩不落宋元以后,問責在魏晉之間,可以挽近時滑易之弊。”[7](169)盧文弨《校禮堂初稿序》凌廷堪自幼擅長詩文,乾隆四十七年,翁方綱看過凌氏所作辭后驚嘆為“不朽之業也”[7](78)張其錦《凌次仲先生年譜》,并收其為弟子。凌廷堪也通金石,曾勉牛坤留心于此,“誠以其有益于考訂。”[7](109)凌廷堪《答牛次原孝廉書》至于音韻,李汝珍《李氏音鑒》里曾說“母中麻韻,即夫子所贈也。”[7](163)李汝珍《李氏音鑒》第三十三問此外,阮元在編篡自然科學家列傳《疇人傳》時,也得到了凌廷堪的幫助。李汝珍的妻舅兼好友許喬林是揚州派的重要人物,除了貫通經史,在小學方面也頗有研究。比如算術方面曾向凌廷堪請教戴震《勾股割圓記》中的疑難問題。許喬林之父與作《疇人傳續編》的羅士琳之父為至交,許喬林與精通算術天文的羅士琳也時有唱和互訪的交流。被李汝珍引為莫逆之交的許祥齡,“性喜吟詠,業醫”[7](336),想必《鏡花緣》中的幾張藥方正是與此人相關。李汝珍本人被許祥齡稱為“博物君子”,對音韻、圍棋十分精通,著有《李氏音鑒》、《受子譜》兩本專著。李汝珍與友人往來時不僅有尋常文人聚會的詩文唱和,更有技藝切磋,譬如乾隆六十年李汝珍在板浦舉行公弈,與顏希源、沈謙、李汝璜、吳焯等對弈。嘉慶七年,與許喬林、許桂林、徐鑒、徐栓、吳振勃、洪棣元等切磋時,為《音鑒》新添11個韻母。可以說,李汝珍在《鏡花緣》中關于種種學問的獺祭展示,既是他對博學實證學風崇尚的一個表現,也是他受漢學學風浸淫的證明。
2.師學脈承
考據學在經歷了清初啟蒙階段之后,于乾嘉時期大興。清代學術自興起之初便有求實求真,精審博證的優良傳統,至李汝珍師友凌廷堪、許喬林一代,漢學雖以地域分派,但扎實樸素的學風是各派均尊奉的基本治學方法。此外,自戴震起,這一脈學者開始真正試圖從思想上充實漢學,雖然如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所說,大概主要部分只是新瓶裝舊酒,是對朱子思想的回歸,但仍是對當時思想界的一個矯正。戴震義理學說中很重要的一點,即德性至當,必先務于知。“德性始乎蒙昧,終乎圣智”,“不能盡其才,言不擴充其心知而常惡遂非”,“古賢圣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學問,貴擴充”[8](225)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凌廷堪在《荀卿頌》中以上智下愚分劃善惡兩性,他的學友焦循論性善時也說:“性何以能善?能知故善……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能善;人知之,則人之行善矣……人之性可引而善,亦可引而惡。惟其可引,故行善也。”[8](107)焦循《性善解三》“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8](38)凌廷堪《復禮中》無論文才武德,還是小學經義,都是格致工夫。除了德行教化的強調,其實還包含了諸如天文、歷算、金石、堪輿等。
李汝珍每每將才、德放在一起,以才學之高成全德行之美,又以德行之美驗證才學之高。最明顯的表現是作者的“才女薄命論”邏輯。才女們因為有較之平庸女子更為自覺的道德意識,于是以才學踐行道德價值觀,并以此來保全自己的名節。“紅顏薄命”在第一回出現后,第四十八回又在泣紅亭的對聯“紅顏莫道人間少,薄命誰言坐上無”中再現。第七十一回中,將泣紅亭匾額念給眾才女聽之后,師蘭言勸諸女“但行好事,莫問前程”[4](327)。錦云問及顏子并未妄為,卻何愆而夭,蘭言道,“他如果獲愆,那是應分該夭的,夫子又哭他怎么,就同嘆那‘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一個意思,因其不應夭而夭,所以才‘哭之慟’了。”[4](47)這里作者已經開始引經據典地說明薄命觀的真正內涵。第九十回,宴會上無意得知了自己命運的眾才女,在經過道姑的點化后,大多對這樣悲劇命運的態度發生轉變,如玉芝所說,“及至聽到名垂千古、流芳百世幾句話,登時令人精神抖擻,生死全置度外,卻又惟恐日后輪不到自己身上。只要流芳百世,就是二十四分慘死,又有何妨!不知區區日后可有這股福氣。”[4](429)小說中花再芳等三個才女是一百才女中的倒數三名,才疏學淺又不懂謙遜,以致在科考前后以及才藝宴會上頻頻出丑。此三人對玉芝所謂死得其所的觀點全不認同:“妹子情愿無福,寧可多活幾時,那怕遺臭萬年都使得,若教我自己朝死路走,就是流芳百世,我也不愿,現成的真快活倒不圖,倒去顧那死后虛名,非癡而何。”[4](429)這種反應與小說前幾章中,這三人不顧道義,賣主求榮,為保命而應武后開花之詔,導致一百花仙下凡,其言行可謂一致。很顯然,在作者的觀念中,才疏學淺的人更容易為名利性命而不顧名節,是應該遭到否定的。
3.理想自寓
《鏡花緣》中,作者給才女們安排了最寬容的社會環境來保護她們的才學。科舉是官方對一個文人才學的最高認可,李汝珍就如同書中身懷各種才學的才女,也在尋求著自己才學被認可的機會。關于李汝珍身世的文獻所存不多,胡適在《<鏡花緣>的引論》中說,“《順天府志》的《選舉表》里,舉人進士隊里都沒有他,可見他大概是一個秀才,科舉上不曾得志”[9](369)。孫訊佳在《<鏡花緣>公案辨疑》中以張其錦《凌次仲先生年譜》所列受業于凌氏的弟子中喬紹僑、紹傅兩兄弟為證,其一為舉人,一為廩生,而無李汝珍,那么很有可能“恐怕連個秀才都不是”[10](5)。嘉慶六年,李汝珍曾得豫東治水縣丞之職,有許喬林送別詩《送李松石縣丞汝珍之官河南》可證,其官職性質類似于投效河工。但河南方志同樣沒有李汝珍做官的記錄,《<鏡花緣>叢談》中的推論是:一種可能是這是候補縣丞,后來也并未實授;另一種可能是嘉慶四年七月在黃河碭山附近的邵家壩決口,朝廷允許捐資投效河工,李汝珍的官是捐來的,因為清朝捐納制度規定,捐納官不能實授正印官。據孫佳訊的考證,石文煃在《音鑒序》中所言“今松石行將官中州矣”一句,李汝珍確實有再度“之官河南”,但極有可能是嘉慶十五年《音鑒》付刊時,李汝珍深感這次河南行并沒有如石文煃所言“黼黻皇猷,敦諭風俗”,于是把這段刪掉,導致了頁心同樣有“寶善堂”字樣的兩個版本的石序中,一個有“將官中州”一段,一個卻沒有。無論如何,作為一個傳統文人,從仕宦生涯的貧乏可見其不得志的程度。李汝珍在一生僅有的兩次官宦經歷中所擔任的都不是重要職位,他空有一身才學,卻無人賞識。
《鏡花緣》的科舉有兩個鮮明特點,都帶有李汝珍的個人理想色彩。一是武則天開設女科。人分男女,陰陽平衡,缺一不可。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讀書仕宦向來是男子的人生道路,女性被科舉這個朝廷最主要的人才選拔方式所拋棄,她們的才華被局限在家庭里,最終也只能做自我消遣之用。作者在書中提出女試,既是在為才女爭取才學展示的機會,也是在借此安慰同樣懷才不遇的自己。所以女科的開設,并不簡單只是因為當時的李汝珍有了男女平等的先進思想,而是女科考試彌補了社會上另一半人才被閑置的缺憾。作者以跨越性別界限的女科考試制度,表達了自己渴求社會上終有一天能“野無遺賢”的愿望。二是分科考試。淑士國不但實行全民教育,也實行全民考試,士、農、工、商各個行業莫不從考試出。因為考試之例各有不同,“或以通經,或以明史,或以辭賦,或以詩文,或以策論,或以書啟,或以樂律,或以音韻,或以刑法,或以歷算,或以書畫,或以醫卜。只要精通其一,皆可取得一頂頭巾,一領青衫。”[4](104)以分科考試選拔各種人才,從事任何行業都要有才學,確實達到了其國王勉人讀書上進的目的。而且這些才能的列舉讓人不禁想到李汝珍本人,余集在《李氏音鑒》中評價他,“少而穎異,讀書不屑章句帖括之學,以其暇旁及雜流,如壬遁、星卜、象緯、篆隸之類,靡不日涉以博其趣。”[11](605)余集《李氏音鑒序》在普遍重道輕器的社會傳統中,經學被奉為至高無上、甚至是惟一的正經學問,那么李汝珍這樣的全才可能在當時文人的眼中根本只是“賣弄稗販拉拉不休”[11](605)王之春《椒生隨筆》的失敗者。李汝珍當然會為自己的滿腹才學抱屈,考試一直是正統的但并非最好的挑選人才的方式,李汝珍設想以分科的形式最大化地保證考試可以發掘與鼓勵不同領域的人才,使任何只要具備一種專長的人都有機會通過考試得到社會的認可。而這兩個“創意”無疑正體現了李汝珍想要為自己才學正名的欲望,亦即對理想科舉寄寓的改革期望。
李汝珍以才女為主要載體,呈現了自己尚才主智的儒者理想。他寫才女們的各類才學,寫她們渴望展現才華的愿望,為她們提供最寬容的環境和最高的舞臺。李汝珍對真才實學毫不吝嗇地贊揚,對不學無術、裝腔作勢或只知死讀書的假儒生則是毫不留情地嘲諷。這種價值取向的形成,既與當時名士大儒對女性才學的包容,以及漢學興盛帶來的崇尚博學的社會風氣相關,更有李汝珍對漢學中戴震、程瑤田、凌廷堪一脈經世思想的服膺相關。同時也不能忽略李汝珍本身懷才不遇的遭際。博學真知是知禮崇德的基礎,越是才高越是德備。李汝珍在《鏡花緣》中展現的價值觀,是一位儒者對社會殷切關注的產物,是對世人,特別是讀書人的深切關懷。
[1]夏志清.人的文學[M].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2]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張宏生.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M].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4]李汝珍.鏡花緣[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皮錫瑞.經學歷史[M].中華書局,1959.
[6]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東方出版社,1996.
[7]李明友.李汝珍師友年譜[M].鳳凰出版社,2011.
[8]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9]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0]孫佳訊.《鏡花緣》公案辨疑[M].齊魯書社,1984.
[11]朱一玄.明清小說資料選編[Z].齊魯書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