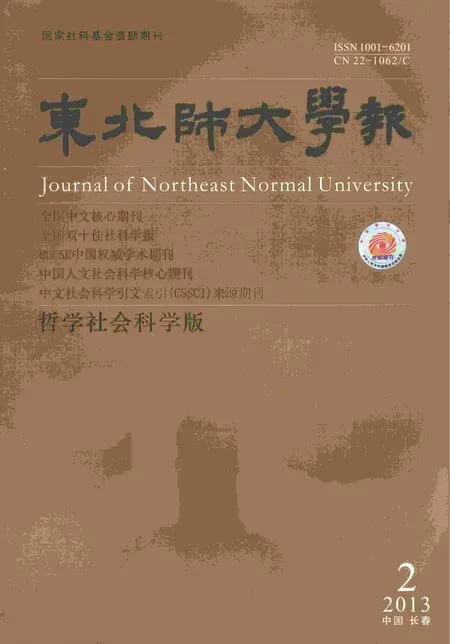郁達(dá)夫創(chuàng)作與翻譯的美學(xué)一致性
張萬(wàn)敏,馬建華
(長(zhǎng)春師范學(xué)院 外語(yǔ)學(xué)院,吉林 長(zhǎng)春130032)
郁達(dá)夫是“五四”文壇上與魯迅并稱“雙峰”的優(yōu)秀、多產(chǎn)的作家,他涉足文壇30余年,發(fā)表了近50部小說(shuō)。他有留洋經(jīng)歷,精通英、德、法、日等多門(mén)外語(yǔ),是個(gè)名副其實(shí)的語(yǔ)言天才,然而他在翻譯方面卻并不多產(chǎn)。他單獨(dú)發(fā)表的譯作僅有28篇,其中包括3首詩(shī)歌、10篇小說(shuō)、15篇雜文。在文學(xué)工作者地位卑微、多數(shù)作家難以靠創(chuàng)作活命、不得不靠兼做翻譯聊以為生的舊中國(guó),這是非常罕見(jiàn)的,也是非常難以付諸實(shí)際的。這充分說(shuō)明了郁達(dá)夫翻譯選材之嚴(yán)格以及他對(duì)翻譯所持的審慎態(tài)度。郁達(dá)夫的創(chuàng)作與翻譯相互影響、相得益彰,二者有著極大的美學(xué)一致性。本文所探討的郁達(dá)夫創(chuàng)作與翻譯,主要是指他的小說(shuō)類作品。
一、從作品看郁達(dá)夫創(chuàng)作與翻譯的美學(xué)一致性
(一)作品中的“零余者”人物形象
郁達(dá)夫“最喜愛(ài)、最熟悉”[1]552的作家便是屠格涅夫。“我的開(kāi)始讀小說(shuō),開(kāi)始想寫(xiě)小說(shuō),受的完全是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點(diǎn)憂郁,繞腮胡子長(zhǎng)得滿滿的北國(guó)巨人的影響”[1]552。郁達(dá)夫讀了很多屠格涅夫的作品,寫(xiě)了《屠格涅夫的〈羅亭〉問(wèn)世以前》等文章,還翻譯了屠格涅夫的《哈孟雷特和堂吉訶德》。屠氏筆下的“多余人”形象,給了他諸多啟示。郁達(dá)夫小說(shuō)中的“零余者”多是受過(guò)良好教育的知識(shí)分子,然而他們卻“十之八九堪白眼,百無(wú)一用是書(shū)生”,“袋里無(wú)錢(qián),心頭多恨”(《零余者》);他們雖有改變個(gè)人命運(yùn)和報(bào)效祖國(guó)的強(qiáng)烈欲望,卻苦于沒(méi)有機(jī)遇、毅力或勇氣去踐行自己的理想;他們“吃盡了千辛萬(wàn)苦,自家以為已有些事物被我把握住了,但是放開(kāi)緊緊捏住的拳頭來(lái)一看,我手里只有一溜青煙”(《青煙》)。理想的幻滅導(dǎo)致更大的精神空虛,他們變得更加孤僻、憂郁、敏感、脆弱,或是仰天悲嘆“自己的一生,實(shí)在是一出毫無(wú)意義的悲劇”(《蜃樓》),或是沉湎于酒色以宣泄郁悶,如此又引發(fā)了更加深刻的“沉淪”,徹底淪落為“生則于世無(wú)補(bǔ),死亦于人無(wú)損”(《蔦蘿行》)的“零余者”。這正是“零余者”的三部曲:從滿懷理想、追求積極的人生到現(xiàn)實(shí)的殘酷、理想的幻滅再到沉淪或自戕。譬如《楊梅燒酒》,主人公留學(xué)海外學(xué)習(xí)應(yīng)用化學(xué),滿懷希望想學(xué)成回國(guó)后建一座工廠以報(bào)效祖國(guó)。然而在那個(gè)暗無(wú)天日的時(shí)代,他的滿腹經(jīng)綸、滿腔熱血卻是沒(méi)有用武之地,理想最終破滅,這叫他怎能不沉淪?
郁達(dá)夫譯作中的主人公也多是“零余者”。他們經(jīng)濟(jì)拮據(jù)、生活貧困,常常找不到自己在社會(huì)中的位置,被邊緣化了;他們多愁善感、空虛壓抑,情感也無(wú)所寄托,終日落落寡歡。《一個(gè)敗殘的廢人》中的那個(gè)“出身高貴”卻因“自己不習(xí)上”而導(dǎo)致中道敗落的藝術(shù)家,他酷愛(ài)藝術(shù),對(duì)藝術(shù)有著絕妙的構(gòu)想,乃至于高呼“藝術(shù)萬(wàn)歲”;他嗜酒如命而又酒后無(wú)德,不斷與人爭(zhēng)吵以至于無(wú)人同他往來(lái),“所受的教養(yǎng)痕跡一點(diǎn)兒也沒(méi)有了”,形同“無(wú)聊的放蕩敗落的下流文乞”,最終被家人寄放在鄉(xiāng)下。酒醉后,他頹廢地高叫:“我是一只難破的船……一個(gè)敗殘的廢人”[2]149-165。《浮浪者》則刻畫(huà)了一個(gè)快樂(lè)、勇敢的浮浪者與八個(gè)受過(guò)良好教育卻懦弱、疲憊的貧民形象,他們經(jīng)濟(jì)上無(wú)錢(qián)、政治上無(wú)權(quán)、精神上空虛(除了浮浪者本人之外)、情感上空白,又是一群“零余者”。
(二)作品的格調(diào)多呈現(xiàn)灰暗、感傷、頹廢的色彩
“感傷主義”(也被郁達(dá)夫稱作“殉情主義”)深受郁達(dá)夫的推崇:“把古今的藝術(shù)總體積加起來(lái),從中間刪棄了感傷主義,那么所余的還有一點(diǎn)什么?莎士比亞的劇本,英國(guó)18世紀(jì)的小說(shuō),浪漫運(yùn)動(dòng)中的各詩(shī)人的作品,有哪一篇完全脫離感傷之域?”[3]243“感傷主義”的主要特征是“缺少猛進(jìn)的豪氣與實(shí)行的毅力,只是陶醉于過(guò)去的回憶之中。而這一種感情上的沉溺,又并非是情深一往,如萬(wàn)馬的奔馳,狂飆的突起,只是靜止的、悠揚(yáng)的、舒徐的。所以殉情主義的作品,總帶有沉郁的悲哀,詠嘆的聲調(diào),舊事的留戀,與宿命的嗟怨。”[1]128-129他認(rèn)為這種文學(xué)思潮產(chǎn)生的語(yǔ)境是“國(guó)破家亡,陷于絕境的時(shí)候”,或是“生活不定的時(shí)候”[1]129。郁達(dá)夫的文學(xué)實(shí)踐也頗受“感傷主義”的影響。無(wú)論是在創(chuàng)作中還是在翻譯中,他都極其注重主觀抒情,著意描寫(xiě)人生的悲苦和不幸,重點(diǎn)刻畫(huà)人的精神痛苦和情感危機(jī)。“閱讀郁達(dá)夫的小說(shuō),濃郁的感傷氣息可謂撲面而來(lái):感傷的個(gè)性與心理,感傷的情節(jié)與環(huán)境,感傷的情緒和氛圍,感傷的抒情與敘事……這一切因素的融合,構(gòu)成了郁達(dá)夫小說(shuō)的感傷美學(xué)風(fēng)格。”[4]49《南遷》中的伊人學(xué)識(shí)淵博、才華橫溢,外語(yǔ)水平很高,還深受社會(huì)主義思潮影響,同情大眾。他胸懷三大抱負(fù):金錢(qián)、愛(ài)情、名譽(yù),有志為祖國(guó)奉獻(xiàn)青春和智慧,卻又為社會(huì)所不容,報(bào)國(guó)無(wú)門(mén)。最終他的理想破滅,縱情酗酒,自甘墮落,憂傷、凄涼無(wú)處不在。難怪人們常說(shuō),郁達(dá)夫的《沉淪》是悲鳴之作,《蔦蘿行》是悲哀的結(jié)晶,《寒灰集》是訴苦愁的哀曲,甚至連《春潮》中對(duì)兒童生活的描述也含著淡淡的哀傷和童心早熟的苦淚。
讀郁達(dá)夫的譯作,我們也幾乎感受不到快樂(lè)和陽(yáng)光,只有灰暗的色彩疊加著頹廢、感傷、陰郁、悲苦等情緒,逐漸將讀者的視線引向悲苦的人生,將讀者的情緒引向憂郁、低沉。《幸福的擺》為我們彈奏了一支凄美的愛(ài)情悲曲:高中教員華倫愛(ài)上了百萬(wàn)富豪的女兒愛(ài)倫琪兒瑪,卻因?yàn)殚T(mén)第差異無(wú)緣牽手,只能眼睜睜看著心愛(ài)的姑娘嫁入豪門(mén);從此華倫開(kāi)始浪跡天涯,直至彌留之際,他才聽(tīng)到他鐘愛(ài)一生、等待一生的女人說(shuō):“我是愛(ài)你的,老早就愛(ài)你的,還沒(méi)有把你忘記過(guò)。”[2]73這個(gè)故事還揭示了這樣一個(gè)生活哲理:期待越高,失望越大;而當(dāng)你無(wú)欲無(wú)求時(shí),便再也沒(méi)有失望和痛苦了。還有《馬爾戴和她的鐘》、《一女侍》等幾部譯作也都是關(guān)于普通人的悲劇,其中的主人公或因失去了他們的最愛(ài)而過(guò)著凄慘、孤獨(dú)的生活,或因過(guò)度勞累、憂郁而失去健康乃至生命。故事的色彩都是灰色的,情調(diào)都是感傷、沉郁的。
(三)強(qiáng)調(diào)作品的主觀性、抒情性,而不注重故事情節(jié)的設(shè)計(jì)和人物形象的刻畫(huà)
郁達(dá)夫的小說(shuō)常被稱作散文化現(xiàn)代抒情小說(shuō)或“自敘傳小說(shuō)”,這是由他首創(chuàng)的一種新的小說(shuō)體裁。這種小說(shuō)一般沒(méi)有復(fù)雜曲折的故事情節(jié),也不注重精心刻畫(huà)人物形象及性格,但是它注重主人公通過(guò)直抒胸臆的反復(fù)詠嘆表達(dá)自己的主觀感受,展示自己的心理活動(dòng)和內(nèi)心獨(dú)白,作品的語(yǔ)言多為娓娓道來(lái)的抒情散文式的,簡(jiǎn)單質(zhì)樸、清新綺麗、韻味十足、流動(dòng)性鮮明,彰顯著散文詩(shī)的風(fēng)格,作品中鮮有人物對(duì)話,并自由地插入詩(shī)歌等。這與傳統(tǒng)的情節(jié)小說(shuō)截然不同。譬如他的早期代表作《沉淪》就沒(méi)有生動(dòng)曲折的情節(jié),對(duì)主人公的形象、性格等著墨也不多,但是對(duì)主人公主觀情緒的宣泄、內(nèi)心苦悶的傳遞卻是濃墨重彩。他的后期代表作《遲桂花》同樣沒(méi)有離奇的情節(jié),沒(méi)有復(fù)雜的人物關(guān)系,也沒(méi)有鮮明的典型人物形象。作者以“遲桂花”這種自然景物為自己情感與理想的隱喻,是一個(gè)象征性的抒情形象,其他主要人物形象也多是象征性的抒情形象。
郁達(dá)夫的譯作也多注重主人公的心理及情感的表達(dá),而不注重曲折情節(jié)的構(gòu)思和鮮活人物形象的刻畫(huà)。《馬爾戴和她的鐘》中的孤女馬爾戴自雙親去世后便失去了歡樂(lè),離群索居,十年里與一個(gè)“她最能談話的伴侶”[2]10和她“在一道的經(jīng)過(guò)了許多甘苦”[2]14的舊鐘相依為命的哀婉故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只有“我”和馬爾戴,所謂的情節(jié)也不過(guò)是以時(shí)間為線索,白描了馬爾戴從天真的少女直至人近中年時(shí)暮氣沉沉的生活,其中穿插了些許對(duì)往事的簡(jiǎn)單回憶。然而小說(shuō)對(duì)馬爾戴凄清、封閉、孤寂、苦悶等心理及情感的傳遞,卻是非常成功。《一女侍》則以悲哀的語(yǔ)調(diào)講述了一個(gè)愛(ài)爾蘭姑娘的凄慘遭遇。她漂泊到巴黎,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個(gè)咖啡館里做女招待,她得了肺炎卻無(wú)錢(qián)看病也不能休息。該作品同樣沒(méi)有用很多的筆墨刻畫(huà)女招待的形象,也沒(méi)有生動(dòng)、曲折的情節(jié)描繪女招待的悲慘經(jīng)歷,只是通過(guò)“我”的旁觀視角,夾雜著女招待輕描淡寫(xiě)的自我述說(shuō),以及咖啡館里其他客人所透露的一些信息,最終繪成了一幅被命運(yùn)“撥弄到極邊的咖啡館”[2]24的女招待悲慘一生的素描。郁達(dá)夫的譯作中也鮮見(jiàn)濃墨重彩地描繪人物形象、刻畫(huà)人物性格,而是多通過(guò)對(duì)人物心理、情感的描述,通過(guò)周?chē)说囊暯呛驼Z(yǔ)言,反映主人公的性格、境況及命運(yùn)等。
(四)對(duì)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偏愛(ài)
郁達(dá)夫在日本留學(xué)期間就閱讀了1 000多部外國(guó)文學(xué)作品,深受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影響。郁達(dá)夫認(rèn)為浪漫主義“把理智和意志完全拿來(lái)做感情的奴隸。情之所發(fā),不怕山的高,海的深,就是拔山倒海,也有所不辭”[1]131;它是“情熱的、空想的、傳奇的、破壞的”[1]131。郁達(dá)夫非常崇拜盧梭(被其稱為“盧騷”),認(rèn)為“他的精神,到現(xiàn)在還沒(méi)有死,他的影響,籠罩下了浪漫運(yùn)動(dòng)的全部”[1]375;世人對(duì)盧梭的不公正批評(píng)令郁達(dá)夫極為憤慨:“喜馬拉雅山的高,用不著矮子來(lái)稱贊,大樹(shù)的老干,當(dāng)然不怕蚍蜉來(lái)沖擊,……小人國(guó)的矮批評(píng)家,你們即使把批評(píng)眼裝置在頭頂?shù)陌l(fā)尖上面,也望不到盧騷的腳底,還是去息息力,多讀幾年盧騷的書(shū)再來(lái)批評(píng)他吧。”[1]359郁達(dá)夫還撰寫(xiě)了《盧騷傳》和《盧騷的思想和他的創(chuàng)作》等文章,翻譯了盧梭的著作《一個(gè)孤獨(dú)漫步者的沉思》,極力向中國(guó)讀者推薦盧梭。在盧梭的影響下,郁達(dá)夫格外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的主觀性,認(rèn)為自我表現(xiàn)是文學(xué)的主要功能,文學(xué)中的情感表達(dá)遠(yuǎn)重于理性思考,文藝的重點(diǎn)應(yīng)放在個(gè)人經(jīng)驗(yàn)、個(gè)人想像及個(gè)人情感的傳遞上,文學(xué)家應(yīng)更多依賴自我感覺(jué)。郁達(dá)夫的小說(shuō),如《沉淪》、《春風(fēng)沉醉的晚上》、《茫茫夜》等多帶有濃郁的浪漫主義氣息,他所翻譯的小說(shuō),如《一位紐英格蘭的尼姑》、《愛(ài)的開(kāi)脫》、《理發(fā)匠》等也都帶有鮮明的浪漫主義色彩。
郁達(dá)夫先天的感傷氣質(zhì)以及后天造就的憂郁氣質(zhì)使得他對(duì)充滿凄涼、哀婉、痛苦、憂傷等格調(diào)的文學(xué)作品格外偏愛(ài),所以他對(duì)唯美主義情有獨(dú)鐘。他曾撰寫(xiě)了《集中于〈黃面志〉的人物》介紹王爾德等唯美主義作家,還寫(xiě)了《讀了珰生的譯詩(shī)而論及于翻譯》,評(píng)價(jià)珰生詩(shī)歌的翻譯問(wèn)題并據(jù)此提出了“學(xué)思得”翻譯觀。他的小說(shuō)《銀灰色的死》就是取材于珰生的一段羅曼史。“寫(xiě)《沉淪》的時(shí)候,在感情上是一點(diǎn)兒也沒(méi)有勉強(qiáng)的影子映著的;我只覺(jué)得不得不寫(xiě),又總覺(jué)得只能照那么地寫(xiě),什么技巧不技巧,詞句不詞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時(shí)候,不得不叫一聲一樣,又哪能顧得這叫出來(lái)的一聲,是低音還是高音?”[1]466這正是他感傷、苦悶、厭世、頹廢等唯美情緒的一種近乎真實(shí)、自然的宣泄。他的譯作《一個(gè)殘敗的廢人》、《馬爾戴和她的鐘》、《幸福的擺》等也都具有鮮明的感傷、頹廢、苦悶等唯美傾向。
二、郁達(dá)夫創(chuàng)作與翻譯的美學(xué)一致性的其他佐證
對(duì)于翻譯,郁達(dá)夫認(rèn)為,“譯文在可能的范圍內(nèi),當(dāng)使像是我自己寫(xiě)的文章,原作者的意思,當(dāng)然是要顧到的,可是譯文文字必使像是我自己做的一樣”[1]615。可見(jiàn),他在尊重原作者的思想及原作意義的同時(shí),強(qiáng)調(diào)要以創(chuàng)作的精神對(duì)待譯文,并盡量使譯文在文字、風(fēng)格等方面與自己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保持一致。他同時(shí)代的作家、評(píng)論家也認(rèn)為他的翻譯與創(chuàng)作有著諸多的相似性。鄒嘯認(rèn)為郁達(dá)夫“所譯的《小家之伍》幾乎是他的創(chuàng)作,因?yàn)槟切┩鈬?guó)人所要說(shuō)的話正也是作者自己所要說(shuō)的話。”[5]序1還有,《幸福的擺》發(fā)表后,很多人誤以為它是他本人的創(chuàng)作,沈從文就是其中一例,他以為這是郁達(dá)夫自己所做的小說(shuō),只不過(guò)是“加了一個(gè)外國(guó)人的假名而已”[1]628,因?yàn)樗诒憩F(xiàn)手法和寫(xiě)作風(fēng)格上與郁達(dá)夫所創(chuàng)作的小說(shuō)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后世的研究者也認(rèn)為郁達(dá)夫的翻譯與創(chuàng)作有著明顯的一致性。謝天振、查明建說(shuō):“創(chuàng)造社的另一位重要作家郁達(dá)夫……的翻譯活動(dòng)與他的創(chuàng)作有著特別密切的關(guān)系,翻譯的選擇和其創(chuàng)作中的借鑒有著明顯的一致性。他所譯介的俄國(guó)作家屠格涅夫和德國(guó)作家林道,恰好都是對(duì)其創(chuàng)作影響極大的外國(guó)作家。”[6]76劉久明也持相似的觀點(diǎn):“郁達(dá)夫的小說(shuō)不僅在表現(xiàn)內(nèi)容和人物塑造上與施篤姆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在藝術(shù)風(fēng)格上,也明顯地借鑒了施篤姆。”[7]162這些都進(jìn)一步證明了郁達(dá)夫的創(chuàng)作與翻譯確實(shí)存在著明顯的美學(xué)一致性。
三、郁達(dá)夫創(chuàng)作與翻譯的美學(xué)一致性的影響及意義
郁達(dá)夫創(chuàng)作與翻譯在美學(xué)上存在著鮮明的一致性這一特色,反映了創(chuàng)作與翻譯之間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jìn)、和諧共生、共同發(fā)展。首先創(chuàng)作影響翻譯。承擔(dān)翻譯任務(wù)的譯者,不可能不受到目標(biāo)語(yǔ)語(yǔ)言、文學(xué)及文化的影響;譯作的意義,也誕生于目標(biāo)語(yǔ)的語(yǔ)言及文化語(yǔ)境之中,它必然要受到目標(biāo)語(yǔ)語(yǔ)言、文學(xué)、美學(xué)及文化等觀念的制約。有些情況下,譯者在翻譯選材時(shí)就刻意尋找與目標(biāo)語(yǔ)中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作品的特色、風(fēng)格相類似的原語(yǔ)作家之作品來(lái)翻譯,或者在翻譯過(guò)程中有意采用相似性的翻譯策略,刻意采用與目標(biāo)語(yǔ)文學(xué)作品的語(yǔ)言文字、篇章結(jié)構(gòu)、寫(xiě)作風(fēng)格等方面相類似的手法來(lái)翻譯,使讀者感覺(jué)似曾相識(shí),在心理上產(chǎn)生親近感,這有助于譯作在目標(biāo)中的接受和傳播。反過(guò)來(lái),翻譯也影響創(chuàng)作。有些創(chuàng)作就是在翻譯的影響和刺激下而誕生的,有些創(chuàng)作本身就是著意模仿翻譯作品而為的,其中的語(yǔ)言、結(jié)構(gòu)、主題及寫(xiě)作手法、美學(xué)特色等均與翻譯作品有著很大的相似性。好的翻譯可以使一些原本一般的原語(yǔ)文本得到較好的闡釋與傳播;也能使一些原本較差的原語(yǔ)作品獲得新生,以嶄新的面貌走入讀者視野;還能使一些原本優(yōu)秀的原語(yǔ)文本更加生機(jī)勃發(fā),光彩照人。出身于文學(xué)家的郁達(dá)夫,他的翻譯自然會(huì)受到他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及技巧的影響,同時(shí)他也會(huì)主動(dòng)選擇一些與自己的美學(xué)品味、寫(xiě)作風(fēng)格比較相近的作家作品來(lái)翻譯;身為翻譯家的郁達(dá)夫,他的創(chuàng)作也自然會(huì)受到他的翻譯經(jīng)驗(yàn)的影響,把在翻譯過(guò)程中學(xué)到的寫(xiě)作技巧、敘事手法等自覺(jué)或不自覺(jué)地運(yùn)用到創(chuàng)作中去。他于翻譯中學(xué)習(xí)創(chuàng)作,于創(chuàng)作中領(lǐng)悟翻譯,二者相互影響、相得益彰,最終錘煉出了一代文學(xué)宗師和翻譯大師。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個(gè)性鮮明的文學(xué)家和翻譯家,郁達(dá)夫非常偏愛(ài)散文化抒情小說(shuō)。他所注重的不是如何對(duì)人生和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加以客觀的反映或揭示,而是如何對(duì)作品中人物的主觀感受和心理情感進(jìn)行率真而深刻的表達(dá)。這種獨(dú)具特色的寫(xiě)作手法,強(qiáng)烈地沖擊了“樂(lè)而不淫,哀而不傷”、“文以載道”、“抒情言志”等傳統(tǒng)文學(xué)觀及美學(xué)觀,為“五四”文學(xué)開(kāi)創(chuàng)了新的文體形式,豐富了文學(xué)的表現(xiàn)手法,豐富了文藝美學(xué)的內(nèi)涵。
郁達(dá)夫文學(xué)實(shí)踐中的這一特色還說(shuō)明,對(duì)于一國(guó)之文學(xué),翻譯與創(chuàng)作同等重要。盲目地崇洋媚外,只把眼光放在譯介外國(guó)文學(xué)作品而忽視本國(guó)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必然導(dǎo)致本民族文學(xué)的滯后、衰落,必然導(dǎo)致它在世界文壇的失語(yǔ)和邊緣化;然而注重創(chuàng)作而忽視翻譯、過(guò)分褒揚(yáng)創(chuàng)作而貶低翻譯或者把翻譯視為創(chuàng)作的附庸,同樣也是偏頗的,文學(xué)的近親繁殖必然導(dǎo)致創(chuàng)作才思的枯竭、寫(xiě)作技術(shù)的陳腐,最終還是要招致本民族文學(xué)的枯萎和衰竭。一國(guó)欲圖文學(xué)之發(fā)展,必須翻譯與創(chuàng)作二者兼重,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都將誤入歧途。這對(duì)于當(dāng)下及今后的文學(xué)建設(shè)都具有警示性意義。
[1]郁達(dá)夫.郁達(dá)夫文論集[C].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
[2]郁達(dá)夫.郁達(dá)夫譯文集[C].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
[3]陳子善,王自立.郁達(dá)夫研究資料(上)[C].廣州:花城出版社,1985.
[4]劉久明.郁達(dá)夫與英國(guó)感傷主義文學(xué)[J].中國(guó)文學(xué)研究,2001(2).
[5]鄒嘯.郁達(dá)夫論[C].上海:北新書(shū)局,1933.
[6]謝天振,查明建.中國(guó)現(xiàn)代翻譯文學(xué)史[M].上海:上海外語(yǔ)教育出版社,2004.
[7]劉久明.郁達(dá)夫與外國(guó)文學(xué)[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xué)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