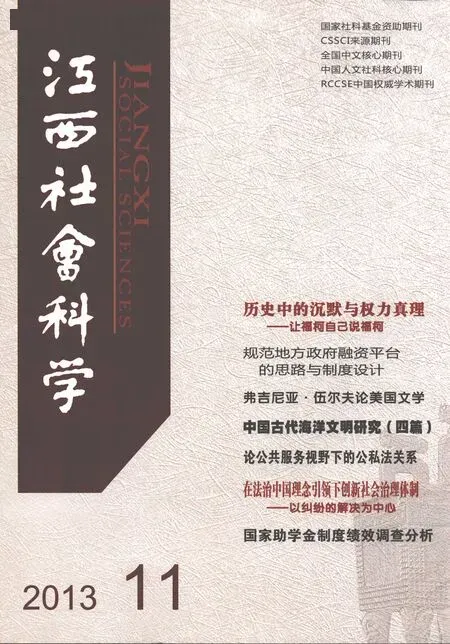從汪楫奉使琉球看清初中琉關系
■李圣華
明清兩代遣使琉球的次數,據不完全統計,明朝有16次,清朝有8次。[1](P190)明清易代,清政府接收明朝對藩屬國的統理權,先后遣使安南、琉球等國。在諸藩屬國中,琉球奉職尤為虔謹。但由于偏處海隅,交通不便,東南兵事頻繁,清初50余年間,遣使琉球活動僅有兩次:康熙二年(1663)張學禮奉使琉球;康熙二十二年汪楫奉使琉球。汪楫之行在清代中琉關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清人查嗣瑮云:“須知使節同圖畫,總是中朝第一人。”[2](卷八《題汪悔齋遺照》)這次中琉交流既有復雜的歷史原因與內容,又對清代琉球政治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借助汪楫所著《使琉球雜錄》、《中山沿革志》加以探討,冀稍有助于清代中琉交流史以及相關歷史問題研究。
一、汪楫奉使琉球的原因與經過
探討汪楫奉使緣起,我們有必要追溯琉球歸屬清政府以及張學禮出使之事。明成化間(1465—1487),定琉球“二年一貢”之制。后因倭患嚴重,萬歷后期改為“十年一貢之例”。天啟三年(1623),琉球世子尚豐遣蔡堅等人入貢請封,明禮部議“暫擬五年一貢,俟新王冊封更議”
[3](卷三百二十三《外國四·琉球》,P8635-8639)。崇禎改元,杜三策敕封琉球。崇禎十七年(1644),尚豐第三子尚賢遣使金應元入貢請封。適逢清兵入關,金應元請襲封未果,阻道不得歸,留滯閩中。及南明唐王“立于福建”,琉球“猶遣使奉貢”[3](卷三百二十三《外國四·琉球》,P8370)。順治三年(1646),清兵入福建。金應元與通事謝必振等至江寧投經略洪承疇,轉赴北京。但清朝禮部持議“前朝敕印未繳,未便授封”。順治十年 (1653),琉球遣王舅馬宗毅、正議大夫蔡祚隆入貢,上繳明朝所頒敕印請封。翌年,清順治帝遣張學禮、王垓往封。張學禮的準備工作耗時費日,繼因鄭成功、張煌言水師在福建沿海活動頻繁,直到順治十五年(1658)還在北京待命。康熙改元,海路漸通。康熙二年(1663),張學禮終于成行,但詔書還是順治十一年 (1654)所頒,敕則是康熙元年 (1662)所制。[4](卷下,P27-28)至次年,張學禮還朝復命。此次出使,前后花費了11年之久。
康熙七年(1668),琉球國主尚質卒。康熙十九年(1680),琉球世子尚貞遣使入貢。康熙帝以尚貞恪守藩職,當耿精忠叛亂之際,仍屢獻方物,恭順可嘉,賜敕褒諭。翌年,尚貞又遣耳目官毛見龍、正議大夫梁邦翰入貢,請遣使敕封。但這一請求卻遭到清朝禮部的反對。汪楫使錄載:“禮臣議航海道遠,應如暹羅例,不遣官恤封,儀物敕貢使赍回便。見龍等搏顙固請,禮臣持不可。”[5](卷一《使事》,P1-2)禮部奏折《恭請天朝恩賜封爵以昭盛典,以守藩服事》提出反對遣使的三大理由:“航海道遠”,“隨去官兵甚多”,“所需錢糧甚廣”。[6](P10-11)其實,禮部回絕遣使要求與張學禮出使之失有著密切的關系。在禮官看來,張學禮琉球之行有三大失:其一,耗時長久。盡管存在交通、兵事等復雜的不利因素,但一次使節耗時10余年,畢竟有所未妥。康熙元年(1662)《封王尚質敕》:“乃海道未通,滯閩多年,致爾使人物故甚多。及學禮等奉掣回京,又不將前情奏明,該地方督撫諸臣亦不行奏請,迨朕屢旨詰問,方悉此情。朕念爾國傾心修貢,宜加優恤,乃使臣及地方各官逗留遲誤,豈朕柔遠之意?今已將正副使、督撫等官分別處治,特頒恩赍,仍遣正使張學禮、副使王垓,令其自贖前罪,暫還原職,速送使人歸國。”①汪楫使錄也提及張學禮“逗留遲誤”之過:“先是臣懲前使逗留之失,疏請亟行。”[5](卷一《使事》,P2)其二,耗費繁劇。張學禮一行因航海道遠,逗留太久,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耗損。關于這一點,汪楫使錄有明確的記載:“前使臣駐閩,一切皆取辦于藩司,即留滯不行,每歲亦支用公費銀五千余兩。藩司奏銷,不盡得請,則派之八府,取驛站綱銀津貼焉。今各項皆無所出,而海疆軍需方亟,豈可復以此費公帑。爰取舊案,盡汰之”,“合計所費,較曩時僅百一焉”。汪楫歸來不入會城,兼程復命,城中百姓鼓樂彩幟趨送,泣告說:“欽差駐閩,動輒數年。造船則有采木購柁之擾,深山窮谷,無得免者。今一到即行,不少留滯,逮于驛騷,一也。有欽差,必有公費。公費一則,私派必倍。今事畢而民不知,二也。往者百物,皆取辦于行戶,官一而役三之,今一物不取,即公署鋪設之一氈一燈,必歸原主,使來者盡然,閩其世世如新受賜乎!”[5](卷一《使事》,P3-4)據福建巡撫金鋐《冊封事關大典等事》奏疏,汪楫出使“較前省約甚多”,“核實用銀九百二十三兩,米三十三石,價銀三十二兩,通共用銀九百五十五兩五錢零”。[6](P47)這一數字經戶部核查無誤。汪楫出使費用不足白銀千兩,由此計算張學禮所費,則多達近10萬兩。所謂“即留滯不行,每歲亦支用公費銀五千余兩”,當是實錄。當然,耗費太繁,擾民甚重,明代使臣已然。但張學禮出使對清政府與福建地方而言,確實帶來不小的負擔。其三,作用未著。禮官認為張學禮之行,勞民傷財,得不償失。張學禮著《使琉球記》,時人批評其“夸謾”②,張學禮憤然毀所鏤板。在禮官看來,夸大出使意義也是張學禮之過。此外,禮部的態度亦與當時東南海防兵事局勢有關。三藩雖已平定,但“海疆軍需方亟”,禮官以為沒有必要再為一次平常的使節而耗費甚繁。這也可從《中山沿革志》中覘知:“二十二年,臣楫等至閩,時總督臣姚啟圣等方治兵攻臺灣,遂不候造船,徑取戰艦渡海。”[4](卷下,P32)康熙帝特允遣使同樣別有原因。自康熙十二年(1673)吳三桂起兵,康熙帝的主要精力便放在戡亂上。但隨著平叛局勢日益明朗,他將目光放在長治久安與加強藩屬國及海疆管理上。既然禮部鑒于張學禮之失,以為當今之務在于海防兵事,遣使琉球意義不大,故汪楫琉球之行遇到不少阻力,在人力物力方面都受到了限制。
康熙二十一年(1682)四月,汪楫與林麟焻在接受出使任務后,即咨訪舊例,“得未盡者七事條上之,旨下禮臣,議格不行”[5](卷一《使事》,P1)。所謂“七事”,具見汪楫《冊封事關大典,奉使理宜詳慎,謹陳管見,仰冀睿裁事》一疏,其中包括:請頒御筆;諭祭海神;渡海之期不必按部議專候貢使同往,各事備齊,有琉球向導,便可按期出洋;帶修船官匠一同渡海;請給關防,以便章奏文移;酌增護送渡海官兵;預支二年俸銀。此前張學禮出使,也曾疏請“十事”,包括“部議賜一品麟蟒服,于欽天監選取天文生一人,南方自擇醫生二人,賜儀仗給驛護送,外給從人口糧,至福建修造渡海船,選將弁二,兵二百人隨行”[4](卷下,P28-29)等。相比之下,汪楫的請求可謂簡易,但禮部猶“盡格不行”:
一、請頒御筆一款。查得會典,御筆無賜給使臣帶往頒賜外國之例。……一、請諭祭海神。查得會典,凡往封外國,無諭祭海神之例。……一、請渡海之期。……查得水路與旱路不同,今汪(楫)等如遇進貢來使在閩,一同前往,來使沿已起身,仍炤前議,俟進貢來使一同前往。一、請給關防。查得會典,冊封官員無頒給關防之例。……一、請帶修船官匠一同渡海。查得監修船只官匠應否一同遣發之處,事隸工部,應交與工部議奏。一、請酌定護送渡海官兵。查得所請增添官兵,事隸兵部,其應否增添之處,應交與兵部議奏。一請炤現賜品服預支二年俸銀。查得職掌內無炤所賜品服頒給俸銀之例。[6](P23-24)
康熙帝命禮部會同戶部、兵部、工部再議,“允行三事,而許帶修船匠役,則特旨”[5](卷一《使事》,P1)。所謂“三事”,是指御書“中山世土”四字;制祭文二道,祈報海神;給俸二年以往。[4](卷下,P33)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汪楫一行至福建,亦未得到地方官的有力支持。時總督姚啟圣視師廈門,巡撫董國興移疾返京,布政使馬斯良入覲,知府張懷德病廢不視事,閩縣令缺官,省會之地,上無督撫藩司,下無府縣官,冊封大典“事如亂絲,無有理其緒者”[5](卷一《使事》,P1-2)。盡管如此,汪楫還是克服阻力,從儉治裝登舟。六月二十日,諭祭海神天妃于怡山院。月末,至琉球那霸港天使館。八月,諭祭尚質,冊封尚貞。十一月二十四日,冒風濤返國,明年入朝復命。
二、汪楫一行在琉球的活動及與琉球國的交流
自明初以來,出使琉球者多作為使錄筆記。陳侃、謝杰、蕭崇業、夏子陽使錄之作俱名《使琉球錄》,張學禮有《使琉球記》、《中山紀略》。汪楫延續了明代以來的傳統,撰《使琉球雜錄》五卷、《中山沿革志》二卷。但其意尚不止于記載行役、異聞,而更在于以下兩點:一是糾正前人載記之誤,補史乘之闕。明人使錄多有誤說、夸飾、紕漏、失載等問題,汪楫“據事質書,期不失實”[5](汪楫《使琉球雜錄序》,P1-2),以匡正謬說;又“搜羅放軼,補舊乘之闕”[4](汪楫《中山沿革志序》,P2),以備國史采摭。二是于康熙帝遣使之意甚明,條錄禮俗、政事、教治、刑禁,周知天下之故,以為實用。《使琉球雜錄》、《中山沿革志》進呈御覽后,得到康熙的褒獎。
根據汪楫的使錄,其一行在琉球的活動及與琉球國的交流,可分為兵防、禮制、習尚、文學等四大方面。
(一)兵防
汪楫不僅關心清廷海防,而且關心藩屬國安全問題,向琉球國王提出了加強兵防的建議。六臂女神曾被琉球國奉為守護神,以婦人不二夫者為尸,尸名女君,傳聞“鄰寇來侵,神能易水為鹽,化米為沙,尋即解去”,琉球國王、臣民“事神甚謹”。對于琉球國不重兵防而信巫神,明使已憂之,但琉球國王曰:“可恃以無恐也。”[5](卷三《俗尚》,P8-9)萬歷三十七年 (1609),薩摩島津氏出兵入侵琉球,占領首里城,擄走尚寧王等百余人,久之始釋。琉球國王自此不復尊奉六臂女神,寺院也不復貢祀。汪楫到時,供奉六臂女神早已成舊聞,但琉球“國無城郭,少兵甲”的狀況未有改變,汪楫不免為之擔憂。琉球去日本不遠,他詢問與日本的交流,琉球人甚諱之,“若絕不知有是國者,惟云與七島人相往來”。七島為琉球國屬地,汪楫疑七島人“其狀獰劣,絕不類中山人”。迨其來謁,“諭以朝廷威德”,“衍說開導之”。各以土物為獻,不受,而人給以布扇,犒及從者。后來汪楫歸舟將發,七島之口島人駕小舟近百只牽船出港,“依依不遽去”[5](卷二《疆域》,P5-6)。
琉球那霸港當大海之沖,港口炮臺緣石而筑,臺上環以埤堄,中無一人一物。土人說:“國無險可守,惟港口數里,皆鐵板沙,非生長斯土者,不能引舟入港。大海中既不得泊,近山又慮觸嶕,且遙望雉堞翼如也,有望洋返耳,以故恒不設備。”汪楫以為不然:“然萬歷間薩州島倭猝至,王被執去,則所謂鐵板沙者,亦不足恃已。”炮臺附近有演武場,“專為天使所率官兵演武而設”[5](卷二《疆域》,P7-8)。琉球馬不適合征戰,當地善騎射者極少。即使首里,亦不見有兵。冊封日,“自王廟至首里,約十數步,即對立二人,執長竿如槍,其末加短鞘,迫視之,中無寸鐵也,亦無弓箭、火器。近王城,有槍刀十數對,即王之儀衛云”[5](卷三《俗尚》,P11)。這些皆為汪楫所憂。他才識敏決,在琉球“有言必以誠告,有事必以實應”[5](汪琬《使琉球雜錄序》,P2)。當他將兵防問題“誠告”時,琉球國王也接受了一些建議。乾隆間,潘相教授琉球入監官生,詳考琉球歷史地理、風土俗尚、政治文化,著《琉球入學見聞錄》四卷,卷二述及琉球兵刑:
南北沿海筑長堤,兩炮臺并峙,聚兵守之。……國少鐵,盔甲與刀猶堅利。……火藥炮位,多用銅鑄,備舟艦水戰之用。辻山旁有演武場,武職有儀衛使、武備司,余皆文官兼之。兵制仿古制,五家為伍,五伍又各相統。親云上、筑登之以下,皆習弓箭,家有刀甲,有事則各領其民,如百夫長、千夫長之屬。[7](P418-420)
從中可窺知,在汪楫出使后,琉球兵防已有所變化。
(二)禮制
汪楫此行的主要任務是諭祭、冊封。按出使舊例,應有禮部所頒儀注。汪楫詢問儀注,禮部官員回答說:“此儀制司職掌也。”儀制司官員又推諉主客司,得到的結果是“案卷雖存,儀注無有也”。汪楫入閩后,博訪儀注,“十得六七,而中多未安”,不得已“酌古準今,定為諭祭、冊封儀注二篇”。部頒儀注不備的問題,也反映出清初朝廷疏于藩屬國管理。汪楫既酌定儀注,還應琉球王之請,于其未曉者“繪圖示之”。國王與臣民奉行甚謹,“登降進反,揖讓拜跪,威儀肅然。國之老成以為從前未睹云”。[5](卷一《使事》,P7)
關于諭祭、冊封儀注,《使琉球雜錄》載記甚詳。對觀陳侃《使琉球錄》、張學禮《使琉球記》所載儀注,即可知汪楫更定的情況。陳侃儀注,乃明使諭祭、冊封琉球通行禮制,琉球王臣“數代相承,不敢違制以行”[8](P33-34)。張學禮冊封儀注大抵沿襲明使舊制。汪楫重新更定,著者有四:其一,諭祭先期命琉球長史灑掃王廟中堂,詳細布置開讀臺、開讀位等;冊封預設闕庭、世子受賜位等。闕庭之設等皆前使儀注所未有。汪楫還以為王殿中楹之右樓梯妨于行禮,世子特造板閣。由于王殿西向,故儀注中止分左右,不分東西。其二,諭祭,按舊習,世子迎龍亭“向第立候于廟門外”,汪楫以為“非禮”,更定為世子率眾官迎伏于真玉橋頭道左[5](卷一《使事》,P11-13);冊封,按陳侃《使琉球錄》儀注,世子在國門五里外中山牌坊候龍亭[8](P34-38),按張學禮《使琉球記》儀注,世子出城三里至守禮坊下候迎[8](P651-652),汪楫則更定為世子率眾官迎伏于守禮坊外。其三,諭祭宣讀禮、謝恩禮、相見禮,陳侃儀注甚簡,汪楫更定繁詳,如焚帛畢,世子回露臺同眾官再行禮謝恩,“捧先王神主由廟東邊門進廟內,安于東偏神座”[5](卷一《使事》,P9)。冊封拜詔禮、宣讀禮、謝封禮、謝賜禮、問安禮、謝恩禮、相見禮、拜謝禮,汪楫更定內容也頗異于陳侃、張學禮儀注。如授國王詔、敕,按舊習,“使臣故欲收回,待跽請至再,而后索閱舊軸,趨走往復”,汪楫以為“幾同兒戲”,令“其預捧呈驗,庶不失禮”[5](卷一《使事》,P13)。其四,按陳侃冊封儀注,世子候龍亭“行五拜三叩頭禮”,諭祭蓋亦如此,張學禮冊封為“行九叩禮”,汪楫改諭祭、冊封皆“行三跪九叩頭禮”。
汪楫一行入琉球,嚴于禮制。入天使館次日,例當行香,通事以天妃宮、至圣廟告。前導問:“宮與廟孰先?”答曰:“先廟。”入廟,升堂搴帷,審視后始下階肅拜。時有竊笑其迂者,汪楫曰:“外國淫祀最多,名稱不一。若入境誤拜倭鬼,辱莫大焉。如俟徐訪而后恭謁,則是奉神慢圣,豈可以訓遠人?”[5](卷一《使事》,P14)對陪臣進謁中使禮,汪楫也有約定:法司官、王舅、紫金大夫、紫巾官為一班,跪三叩頭禮,天使立受,揖答之;耳目官、正議大夫、中議大夫為一班,跪三叩頭,天使立受,拱手答之;那霸官、長史、遏闥理官、都通事為一班,跪三叩頭,天使坐受,抗手答之。稟事必長跪,命坐賜茶,法司官等則設氈堂內,耳目官等坐廊下,那霸官等坐露臺下。[5](卷一《使事》,P16)
(三)習尚
琉球國歷史悠久,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地域俗尚。國王居常裹五色帕,見明使則服明朝衣冠。明清易代后,見清使,“仍明時衣冠”③。琉球官員與百姓,“服無貴賤,男女皆大袖寬博,無衣帶”。國王衣冠“苦束縛”,張學禮使琉球,“有各從其便之諭,遂沿明制以見”。汪楫嘆曰:“今不可復更。”琉球國王受封后,亦欲著皮弁,以朝祭之服參謁,“意實恭謹,而通事以為倨,令易前服,故皮弁未得見”。[5](卷三《俗尚》,P1-2)
汪楫對琉球舊例與習尚也進行了改革。如因使臣供應、隨行兵役廩給甚腆,裁減之以“柔遠恤下,期于兩盡也”。國王五日一遣官赍牛酒問安,辭之不可,遂理諭之:“牛以力耕,不得擅殺。使臣非為國惜物,命律不可也。”[5](卷一《使事》,P14)國王不肯受命,然不久汪楫聞琉球國中禁宰牛,改問安之期為十日一至。又如琉球待客習俗皆席地布幾,國王宴使臣,汪楫堅持不可席地,及赴宴,“陳設畢具,賓主皆高坐,揖讓如禮”,蓋“聊以覘天使易與否耳”。[5](卷一《使事》,P15)
(四)文學
文學交流往往是古代遣使活動的重要構成。明清使臣出使安南、朝鮮等國,都留下大量唱和之作。汪楫一行與琉球能詩之士往來酬唱,并將贈答詩匯編成集,從中亦可見清初中琉文化交流的情況。
自明初琉球奉中國正朔以來,迄于清初,始終未建學宮。“國人就學,多以僧為師,僧舍即其鄉塾云。”[5](卷二《疆域》,P15)琉球僧人分為兩宗,居首里者曰臨濟宗,居那霸者曰真言教。首里有三大寺,即天界寺、圓覺寺、天王寺。圓覺寺額為靈濟法嗣徑山和尚所書。三寺僧人皆嗣法靈濟,然汪楫“叩以禪宗,茫如也”[5](卷二《疆域》,P20)。首里僧人能詩者,瘦梅、宗實、不羈最著。瘦梅為天王寺詩僧,奉元釋英《白云集》為宗,與萬松院僧不羈并好苦吟,互相唱和。汪楫使錄載:
天王寺僧瘦梅則工詩,詩奉《白云集》為宗。《白云集》者,元僧英所作。英俗姓厲,字實存。集有牟巘、趙孟頫、胡汲序。國人鏤板譯字以行,然中國人購之,殊不易。讀之,則多屬明初張羽詩,而牟序又與《陵陽集》所載不同,殊不可解。[5](卷二《疆域》,P20)
明初張羽與高啟、楊基、徐賁并稱“吳中四杰”,著《靜居集》四卷。傳世有《靜居集》六卷本,與釋英《白云集》之詩多有重復。后世遂以為張羽之詩誤入《白云集》,實則釋英之詩誤入《靜居集》。④汪楫所謂釋英之詩“多屬明初張羽詩”的說法,顯然有誤。他之所以拈出這點,意在含蓄指出琉球詩人水平不高,“殊不可解”也透露出這一消息。
當然,汪楫的主要唱和對象還是陪臣。其所編《中山詩文》一卷,僅收文兩篇:卷首一篇《奉送翰林汪先生還朝,兼祝誥封檢討公八十大壽序》署名國王尚貞,作于康熙二十二年 (1683)秋;卷末一篇為琉球國使臣毛國珍、王明佐、昌威、曾益等祭汪楫父之文,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夏。余皆《題畫奉祝誥封翰林檢討汪太公壽》唱和詩,作者包括琉球王室尚弘毅、尚純,法司官毛國珍、毛泰永、翁自儀,王舅毛自義,紫巾官夏德宣、毛允麗,紫金大夫王明佐,耳目官吳世俊、章受祜,正議大夫鄭宗善、梁邦翰、鄭永安,中議大夫鄭宗德、陳初源、孫自昌,遏闥理官楊自、文克繼、毛知傳,長史蔡應瑞、鄭弘良,那霸官柏茂、吳彬,共24人,人各一題[9],俱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當然,汪楫與琉球人唱和之詩遠不止于此,但《中山詩文》刪選較嚴,每人僅存一題。
三、汪楫奉使琉球對中琉關系的影響
清廷禮部認為遣使琉球意義不大,乃是一種短淺之見。汪楫出使的意義,可概括為四方面:加強了清政府對琉球的管理;加深了對琉球歷史、國情、現狀的了解;促進了中琉政治文化的交流;在中國文化傳播方面也起到積極的作用。
《中山沿革志》、《使琉球雜錄》為中琉交往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在汪楫出使前,有關琉球國的沿革,無論是明廷,還是清廷,都不甚了解。琉球國于其世系沿革,厲禁外泄。汪楫借諭祭的機會,“密錄”其世系概況,復購得《琉球世纘圖》,撰為《中山沿革志》。盡管所載尚不完備,但已屬前所未有,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序》謂其“典實遠非前比”。《使琉球雜錄》搜輯甚備,據依亦詳,汪琬《使琉球雜錄序》云:“上之可作軒之指南,次之可備史家之筆削。”康熙帝通過汪楫出使情況及其著述,了解到琉球國的歷史和國情,遂不以琉球管理為憂,將精力集中放在收復臺灣上,晚年始遣翰林院檢討海寶、編修徐葆光使琉球。
汪楫酌定儀注,為后來琉球使臣效法。康熙五十八年(1719),海寶、徐葆光諭祭琉球國王尚貞、尚益,冊封尚敬,儀注俱依汪楫所更定。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卷二“儀注”大抵錄自汪楫使錄,自注云:“俱從前使臣汪楫更定。”[10](P116)中國禮儀制度也引起琉球人濃厚的興趣。如程順則,字寵文,父泰祚官都通事,曾隨張學禮謝恩入朝,返國后參與創立琉球至圣廟。康熙二十二年(1683),順則授通事,隨王明佐入朝謝恩,后任接貢存留通事赴閩,注重考察中國典章制度、禮儀習俗,回國后奉命修訂“中山王府官制”,“還參照中國禮儀,修改琉球冬至、元旦百官朝賀國王之禮儀,提出‘殿下中道設香案’、‘百官分左右翼,各照品級排立’、‘于墀下左右設五方之旗,設彩蓋于殿下左右’、‘陳設儀仗、鳴金鼓、奏漢樂’、‘王上先拜北天后,升殿受朝賀’等,‘維茲之舉,悉遵天朝之制,以為考定’”[11](P248)。潘相《琉球入學見聞錄》卷一詳述諭祭、冊封儀注,大抵同于汪楫使錄,然非照抄舊籍,實是有據而來。
相比清朝,琉球的教育無疑是十分落后的。其至圣廟在那霸港二里外久米村,創始于康熙十二年(1673),翌年建成,構制簡陋,不過屋二重,其外臨水為屏墻,翼以短柵。汪楫既喜至圣廟創立,“立國以來所未有也”,又為琉球教育落后擔憂,希望國王重視人才教育,因廟而擴之為學,擇師以教,甚而請助于朝。《琉球國新建至圣廟記》云:
夫秀才者,將以儲異日長史、大夫之用,則教之不可無專師,試之不可無成法。誠因廟而擴為學,擇國中敦行誼、工文章者為之長,俾以時訓,督其子弟,修舉釋菜、釋奠之禮。國之中或難其選,則直疏其事而請于朝,乞如往昔教育故事。圣天子聲教誕敷,方教登四海于文明之治,吾知其必得當也。如此則琉球之經學日明,因所及而益廣其未備,于以表率友邦,凡有志于圣人之學者,無不奉琉球為指歸。嗚呼!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琉球國無學宮,童子習字多以僧為師。“大約讀書時少,作字時多,字皆草書,無楷法也。”[5](卷二《疆域》,P12)建學宮非易事,汪楫建議國王奏請“愿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4](卷下,P35)。康熙二十三年(1684)他返朝后,即轉奏之。《恭述遠人向化之誠,請賜就學以廣文教事》云:
國中舊無孔子廟,自康熙三年受封后,貢使時通,聲教漸被,十二年始建至圣廟于那霸之久米村。雖制多荒略,而意實可取,但苦地無明師,以故譽髦終鮮。臣等事竣將旋,中山王尚貞親詣館舍,酌酒祖道,令陪臣、通事向臣等致詞曰:……執經無地,向學有心。稽之明代洪武、永樂年間,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皇上圣學高深,超邁萬古,愿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敢祈天使轉奏,不勝悚企。[6](P31-32)
琉球人最早入國子監,始于明洪武后期。洪武二十五年(1392),中山王察度遣從子日孜每、闊八馬,寨官子仁悅慈入監讀書,“國人就學自茲始”[4](卷上,P6-7)。終明之世,國學琉球生甚眾。汪楫一行考察琉球歷史沿革,意識到教育是維系藩屬國與中國政治文化“母體”關系的一個紐帶,因此向康熙帝建言沿襲明制,準許琉球生入監就學。康熙二十五年(1686),尚貞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秉均、阮維新、蔡文溥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鄭秉均甫離琉球,即遭海難。康熙二十七年(1688)九月,梁成楫等人入監,康熙帝特為設教習一人,此為清代琉球人就學國子監之始。康熙三十一年(1692),尚貞懇請令梁成楫等三人返國。[12](P3)三人回國后,充任經師和訓詁師,勤于教習。后來,梁成楫官都通事,蔡文溥任接貢存留通事赴閩,累官紫金大夫,阮維新累官紫金大夫,康熙末充貢使。蔡文溥工于詩,潘相《琉球入學見聞錄》卷三說他“以其所學教久米村及國人,人多化之”[7](P564-565)。海寶、徐葆光出使琉球,交往的官員就包括阮維新、蔡文溥。徐葆光撰著《中山傳信錄》,更是多得二人之助。汪士鋐《中山傳信錄序》載:“其國官之尊者,曰紫金大夫。時為之者,即舟次先生前使時所請陪臣子弟入學讀書者也。其文辭可觀,與之言,娓娓有致。今之所述,皆得之其口與其諸臣所言,證之史牒,信而有征。”康熙五十八年(1719),汪楫建琉球學宮的想法終成為實現。是年,琉球建明綸堂于至圣廟南,稱之府學,是為琉球有學校之始。“國王敬刊圣諭十六條,演其文義,于月吉讀之。官師則由紫金大夫一員司之,三六九日詣講堂,理中國往來貢典,察諸生勤惰,籍其能者用備保舉。”次年,海寶、徐葆光自琉球歸,循汪楫舊例,代請官生入學。至嘉慶三年(1798),琉球又建國學于王府北,“命王子及三品以上陪臣之子弟,以及首里人子弟入學試讀。又建鄉學三所。外村小吏,百姓之子弟,則以寺為塾,以僧為師”。[13](P82)
還要指出的是,汪楫使琉球撰著頗異于明人使錄之作,也與張學禮《使琉球記》、《中山紀略》有所不同,真正開啟了清人為琉球撰史的先河。后來徐葆光撰《中山傳信錄》六卷,周煌撰《琉球國志略》十六卷,齊鯤、費錫章撰《續琉球國志略》五卷,趙新撰《續琉球國志略》二卷,都繼承了汪楫所創的傳統。《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外國四·琉球》成書,亦多參咨汪楫之作。這也可視為汪楫對中琉交流的一個貢獻。
注釋:
①見周煌輯《琉球國志略》首卷,《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匯編》中,第612頁。《清史稿》以及程魯丁《琉球問題》錄此,文字時異。
②汪楫《使琉球雜錄序》稱學禮所著“質實無支語。已鏤板行,后為所知誚讓,謂海外歸來,稍夸謾以新耳目,誰相證者,而寂寥如是。學禮乃毀所鏤板,而他客輒以意為之,今刻遂與原本大異”。所謂“質實無支語”的說法,大抵可信。
③見汪楫《使琉球雜錄》卷三《俗尚》,第1頁。按: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卷六稱琉球人自國王以下皆遵從時制衒發,“留外發一圍,綰小髻于頂之正中”(《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匯編》第479頁),恐有未確。當以張學禮《中山紀略》“男至二十,成立娶妻之后,將頂發削去,惟留四余,挽一髻于前額右,傍簪小如意。如意亦分貴賤品級”為確(同上,第662頁)。汪楫《中山竹枝》詩下自注:“國俗,男子二十始衒頂發,為小髻,服與婦人無別。”(《觀海集》,《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4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80頁)亦可證之。
④參見楊鐮《元佚詩研究》(《文學遺產》1997年3期),李舜臣、胡園《元代詩僧釋英考論》(《文藝評論》2011年第2期)。
[1]李金明.明清琉球冊封使與中國文化傳播[A].福建師范大學中琉關系研究所.第九屆中琉歷史關系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C].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2](清)查嗣蠾.查浦詩鈔[M].清刻本.
[3](清)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4](清)汪楫.中山沿革志[Z].京都本.
[5](清)汪楫.使琉球雜錄[Z].京都本.
[6](清)汪楫.冊封疏鈔[Z].京都本.
[7]黃潤華,薛英.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匯編(下)[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8]黃潤華,薛英.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匯編(上)[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9](清)汪楫.中山詩文[Z].京都本.
[10]黃潤華,薛英.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匯編(中)[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11]賴正維.康熙時期的中琉關系[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4.
[12](清)王士衳.紀琉球入太學始末[M].昭代叢書(乙集卷十二).世楷堂藏板.
[13]傅角今,鄭勵儉.琉球地理志略[M].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